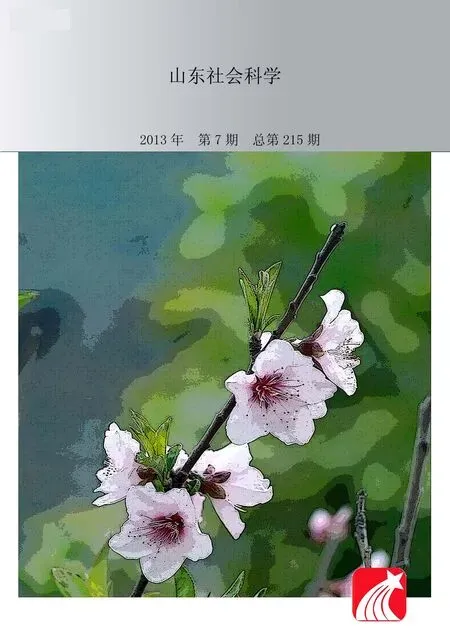论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特色
董龙昌
(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作为享有国际盛誉的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在其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极力倡导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只有这样人类学才算得上是一门真正科学的学科。他在其艺术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同样秉持这一立场,将结构主义方法广泛运用于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结构主义实际上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色。本文拟对此予以详细考评。
一、“结构”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列维-斯特劳斯1977年访问日本时曾做过一次公开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结构”进行了明确界定。在他看来,结构指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注转引自[日]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日本学者渡边公三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一定义作了深入解读。在他看来,这一定义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列维-斯特劳斯将要素本身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平面上加以审视,也就意味着在结构的视域中内容与形式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对将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这一做法的纠偏;第二,列维-斯特劳斯对“不变”概念的强调透露了其结构主义的真正研究对象;第三,列维-斯特劳斯对“变形”概念的强调则指出了结构运行的动力机制。注转引自[日]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虽然渡边公三的解读存在过度阐释之嫌,但对我们深入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概念还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通过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对社会结构特征的论述来加深对其结构概念的理解。他在《民族学中的结构概念》一文中认为,社会结构同现实经验无关,它只同建立在现实经验基础上的模型发生联系。一个模型只有具备四个条件才能被称之为结构:
首先,一个结构表现出系统的特征。对于它的某一组成成分做出任何变动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动。
其次,任何一个模型都隶属于一组变化,其中每一种变化都对应于同类模型内的一个模型,以致所有这些变化加起来便构成一组模型。
再次,上述特质使我们能够预见,当模型的某一成分被更改的时候,该模型会如何反应。
最后,构拟一个模型应当使其运行能够解释全部被观察到的事实。[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由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看,他实际上强调了结构的三个典型特征,即系统性、转换性和恒定不变性,这同皮亚杰所强调的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三方面特质大致相同。[注]详见[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所不同者在于,皮亚杰主要是站在发生心理学科学认识论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结构主义的,因而强调认识主体在结构构造中的作用及结构与功能的密不可分性,这些却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并不认同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除了具有上述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关系性和共时性的特点,这主要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结果。索绪尔语言学对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共时性与历时性、语言与言语、所指与能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的区分不仅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进行结构分析的重要依凭之一。在索绪尔、雅各布森及特鲁别茨柯依等语言学家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犹如语言:“谁要是说‘人’,就是在说‘语言’;谁要是说‘语言’,也就是说‘社会’。”[注]转引自程代熙:《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结构主义》,《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因而,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系统中加以研究。以亲属关系为例,列维-斯特劳斯讲:“一个亲属关系的系统,哪怕是最基本的,也是同时存在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的。”[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然而,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只看到了历时性的一面,过于强调亲属关系的起源问题,其失误就在于只看到了兄弟/姐妹、父亲/儿子这四个词项,却没有看到这些词项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因而,我们应当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通过揭示亲属关系系统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来达到匡正传统社会学研究弊病的目的。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建立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一基础之上。以此为出发点,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艺术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构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如男/女、干/湿、生/熟、天空/大地、冷/热、上/下、生/死等,以此来考察原始造型艺术、神话、诗歌和音乐。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二元对立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结构分析中的一切关系事实上都可以还原为二元对立关系,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中的每个要素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找到相应的社会价值,这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分析的最突出特色。
综上所述可见,系统性、转换性、恒定不变性、二元对立性和共时性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概念的主要特点。就“结构”的来源来看,还应加上无意识性。[注]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予以重点介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把握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结构主义特色。
二、结构的来源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毋宁说它为人类本身所固有,主要源于人类心灵的无意识运作,这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范式的显著特征。他认为,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是无意识在发挥作用的。对此他解释道:“如果精神的无意识活动意味着把一些形式强加给某一内容,而且这些形式对于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教化了的所有精神从根本上说都是相同的——就像对表现在语言行为当中的象征性功能的研究已经明白显示的那样——那么,为了获得同样适用于其他制度和习俗的诠释原则,就必须把握隐含在每一种制度与习俗后面的无意识结构。”[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埃德蒙·利奇从人脑对世界的认识过程的角度出发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结构的无意识特性。在他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可以作如下理解: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实际上依据的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正是意识的运作方式及大脑对外界刺激物的整理方式赋予了我们所认识到的外界事物的某些具体特征。人脑在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整理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倾向于将我们周围的时空连续体切割成片段以后加以认识,“这样我们就能事先把环境看作是由大量被分门别类的个别事物组成的,把时间段看作是由个别事件的系列组成的”[注][英] 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吴琼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当我们对人类世界的文化产品进行认识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模仿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序。以色谱和交通信号灯为例,色谱本来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由于人脑具有能将连续统一体切割为片段的能力,我们得到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同时倾向于将红色和绿色看作一组对立的颜色,并认为黄色处在它们的中间,是一种过渡颜色。在交通信号灯中我们之所以选择红、黄、绿三色分别作为停止、告诫(准备停或准备走)及通行的标志恰是因为信号系统同颜色系统具有相同的结构,信号系统是由颜色系统转化而来的。利奇用这个例子清晰地表明了人脑是如何根据对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类的文化的,同理,通过研究人是如何认识自然及人类文化的,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人脑的思维运行机制,在利奇看来,这便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的具体思路。[注][英] 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吴琼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6页。由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实际来看,利奇的这一观点大致是令人信服的。以神话为例,列维-斯特劳斯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入手对遍布美洲大陆的数以百计的印第安神话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努力揭示人类心灵的运作方式。在他看来,透过对神话的结构分析所折射出来的正是人类心灵的结构性特征,这也就意味着结构是内在于人的身体的,它并不是单纯概念的游戏。[注]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4页。列维-斯特劳斯在另一处明确讲道:“人们有时抱怨结构主义者不关注事实,只玩抽象游戏。我曾经试图说明,结构分析远不是业余爱好者和唯美主义者的消遣,它在头脑中进行,是由于它的模型已经存在于身体之内。”[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邢克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虽然在无意识问题上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本人对此供认不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没停留在单纯照抄照搬的层面上,而是对其进行了合理扬弃。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将无意识视为人的杂乱无章的非理性冲动,在他看来,无意识是先验存在的,它是人所固有的理智能力,对人的理性思维起着制约作用。这是列维-斯特劳斯与弗洛伊德在无意识问题上最大的区别。
三、列维-斯特劳斯为结构主义的辩护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从其产生之初就备受争议和质疑,有人批评他具有唯心主义、反历史主义倾向;有人批评他不重视经验事实;还有人批评他的形式主义倾向等。针对这些批评他在其著作中进行了一一回应。
(一)结构与经验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要是通过抽象演绎的方法得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类学的经验事实漠不关心;相反,他极为重视人类学的经验事实,并将其视为结构研究的基础。在《遥远的目光》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明确指出:“人类学首先是一种经验科学。……经验研究是进入结构的条件。”[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邢克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他对经验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结构分析的河床之下隐秘地潜藏着对经验事实的尊崇。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分析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弥合经验与理性之间的界限进而从一个更为高远的层次上来看待人类社会的种种文化创造活动。他反复强调:“结构主义立志在可感觉的东西与可理解的东西之间架起桥梁,讨厌一切牺牲一个方面去支持另一个方面的解释。”[注]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3页。他的结构主义分析可以看作是以结构的名义统一感性与理性、经验与智力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的一种尝试。
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在谈到对他走向人类学研究之路至关重要的三个学科(即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及地质学)时曾指出,这三个学科共同面临同一个问题,即感觉和理性的关系问题,它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想达到一种超级理性主义,把感觉与理性整合起来,同时又不使两者失去其各自原有的一切性质特征。”[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受此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也以追求这种“超级理性主义”为鹄的,这在他对野性思维的论述及神话学研究过程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日本学者谷川渥在《作为美学的结构主义——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论》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注]详见[日]谷川渥著,刘绩生译:《作为美学的结构主义——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论》,《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2期。
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只进行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田野调查,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同行的诟病,但这却并不代表他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轻视,恰恰相反,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极为重视田野调查及实践的重要性。以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结构分析为例,在他看来,神话分析不能脱离事实,必须深入了解某一神话所产生的历史背景、生态环境和社会习俗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神话展开具体的结构分析,否则只会得到空洞无物的形式,“一旦我们不掌握相关社会的民族志资料或独立于神话之外的民族志信息,我们必须放弃对这个社会的神话进行结构分析”[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猞猁的故事》,庄晨燕、刘存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二)结构与历史
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研究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问题上,通行观点认为他过于重视共时性研究,而对历时性研究表现得极为漠视,列维-斯特劳斯显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结构主义研究虽然主要重视共时性研究,但却没有因此忽视历时性。以亲属关系为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亲属关系系统,哪怕是最基本的系统,也是同时存在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的。列维-斯特劳斯对历时性的关注也就意味着他在研究过程中对历史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一书中明确指出:“结构分析并不否认历史。恰恰相反,结构分析赋予历史以第一线的地位:把权利还给不可还原的偶然性,而没有偶然性,甚至无法设想必然性。”[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页。在对北美洲太平洋沿岸民族的面具艺术研究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再次指出:“结构分析绝不是置历史于不顾,而是为历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对此他以对和面具相关的神话起源问题的研究为例作了具体说明,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主义分析在逻辑上抽绎出来的各神话系统之间的流变关系必须同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所展现的神话传承关系相一致,唯其如此,结构分析才会更有说服力。
与结构和历史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传统观点往往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两门学科却有着沟通的可能性。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解,马克思的“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知自己正在创造历史”这一名言的前半句是对历史学的辩护,后半句则是对民族学的辩护。“它同时也表明,这两种方法是不可分割的”。[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历史学与民族学在对无意识结构的获取上走到了一起,历史学对社会的解释固然以对具体事件、具体现象的考察为基础,但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发现他们应当求助于整个无意识加工活动的武库,这就进入了民族学的研究领地,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对历史事件有一个恰切的解释,因此,任何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必然受到民族学成果的浸润。同理,民族学的结构分析本身就要求不断向历史学求助,因为“历史学把变化当中的各种制度展示出来,只有它才能够把隐含在多种提法当中并贯穿于一系列事件中的深层结构提取出来”[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三)结构与形式
一般的批评者多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视为一种形式主义,对此他在其著作中极力反对并为结构主义作了有力辩护。在他看来,就结构分析而言,内容与形式是密不可分的。在《神话学:生食和熟食》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明确讲道:“在结构分析中,内容与形式不是分离的实体,而是对于深刻理解同一个研究对象来说必不可少的两种互补观点。”[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与形式的区分及对结构主义的辩护集中体现在他对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的批判中。在他看来,普罗普将他对民间故事的分析简化为一系列功能的做法使得民间故事显得枯燥而干涸,这种将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的做法严重脱离了具体事物,实际上毁灭了他所研究的对象,这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而结构主义却不是这样,“如果说少量的结构主义脱离了具体事物,那么大量的结构主义又回到了具体事物上来”[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2页。。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形式主义之“形式”是依据外在于它的质料获得的,它与具体事物是相对立的,而结构主义却并不将具体事物与抽象事物对立起来,也不承认抽象事物的优先地位,这也就意味着“结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因为,它就是内容本身,而这种内容是借助被设想为真实之属性的逻辑活动得到把握的”[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页。。
在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上,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否认形式主义在结构主义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启发作用,然而这二者又存在着截然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处理上。在形式主义看来,形式与内容应该严格区分,只有形式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内容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一种残留物;结构主义则认为并不存在形式与内容的绝对对立,事实上,这二者在性质上不仅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它们可以通过同一个分析得到说明,“内容从其结构获得实在性,所谓形式就是内容所在的局部结构的‘结构化’”[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0页。。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如何看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最大的不同。
四、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方法的反思
总体来看,列维-斯特劳斯将源于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不仅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中,而且还有意识地将其进一步扩展到艺术研究中,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通览他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他首先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的是亲属关系,然后又在神话、诗歌、音乐及原始造型艺术等领域中加以进一步验证、深化和拓展。如他在对俄狄浦斯神话的解读过程中就表明了这一研究意图,在他看来,他对俄狄浦斯神话的解读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个被专家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不如说是为了说明一种技术,是为了验证结构方法在神话研究中的效力;[注]参见[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森联手对波德莱尔诗歌进行解读的初衷也是为了验证结构方法在文学中的合法性及有效性问题;他在对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原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的研究过程中同样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当用文化传播论的观点研究不同地区艺术所共同存在的“裂分表现”法行不通时,“那么就让我们转而求助于心理学或者对形式的结构分析吧”[注][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通过结构方法的广泛运用,列维-斯特劳斯获得了变混乱为明晰的本领,正因如此,他在对美洲神话的研究过程中才能够将数以千计的神话及其异文理出一个头绪并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结论来。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让人信服,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技术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注]参见李幼蒸:《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社会科学启示之我见》,《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埃德蒙·利奇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不是对对立的双方及它们相互间多样的排列组合的形式主义的探讨,而毋宁是他在分析过程中运用的真正具有诗意的联想方式:在列维-斯特劳斯手中,再复杂的事物也会马上由混乱变得清晰明了。”[注][英]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吴琼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在我们看来,列维-斯特劳斯所具有的“诗意的联想方式”是同其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密不可分的。他的这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不仅可以为美学、艺术学研究提供理论武器,有利于当代思维模式的建构,[注]此处所论受到周均平先生《中国古代“比情”自然审美观论纲》(《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一文的启发,特此致谢。而且提供了文本解读上的具体范例,这对于增强美学、艺术学批评的具体可操作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与此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在其文本中围绕结构与经验、结构与历史、结构与形式的关系为结构主义作了有力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结构方法的运用有时过于主观随意,其对具体研究对象“结构”的剖析充满了先验性,具有极强的演绎色彩。通过结构方法的运用,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艺术研究过程中收获了明晰性,任何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到了他的手里一经结构分析立即变得简单起来,这是他的非凡之处。然而,其结构方法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究竟是否科学却是值得反思的。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结构方法(以二元对立为主要标志)充满了主观随意性,以神话研究为例,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的结构不过是人类心智之无意识结构的体现,它是先天存在的,所以他对神话结构的分析更多地是立足于他本人的“结构”通过演绎得来的,而不是真正从客观存在的神话的“结构”出发概括出来的。程代熙先生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把‘二元对立’当作一个框架,把他所需要的东西往框架里一放,并根据自己的心愿来加以解释。因此,他的‘二元对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武断色彩。”[注]程代熙:《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结构主义》,《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他的这一判断大抵是正确的。
——《对面的撒旦》的文艺心理学分析
——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角度解析《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