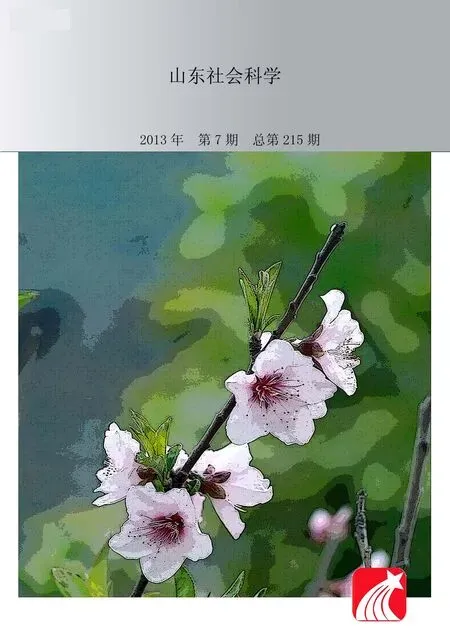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郭恋东 杨蓉蓉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200030;复旦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433)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先锋的“意识流”在其产生之初即引起中国文坛的注意。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意识流”的译介多表现在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接受,这一译介倾向可被视为是对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之追求。为了实现对传统的急于否定和采用线性时间观以预告一种跨国意识或全球意识的出现,五四知识分子在译介中对“意识流”采用了有意的误读策略。而这一基于实用主义工具性的误读策略使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此时期都成为服务于科学进步理性主义范式的工具。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对“意识流”的译介倾向既有误读的加深,同时又有文化层面上的深入理解与批判性接受。而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在民族战争的夹缝中得到发展,呈现出向文学本身回归的倾向。本文力图追寻“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倾向之流变,借由代表性的译介实例追寻中国现代文坛对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实验的接受轨迹。中国现代文学30年间对“意识流”的译介也谱写了一曲“求新”与“寻异”的交响曲,而二者的消长正体现了现代文坛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一、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
1.作为科学主义的“意识流”——对“意识流”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
“意识流”进入中国现代文坛的最初途径是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不论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柏格森的片面借用,还是对弗洛伊德的实用主义解释都符合五四知识分子追求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一目标。这种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表现为对传统的急于否定和一种采用线性时间观预告其跨国意识或全球意识的出现。正如学者所言,“五四一代学者无可避免地陷入巨大的现代性焦虑之中。在诸多复杂性问题上都作了过于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简单地在‘新’‘旧’、‘中’‘西’之间划等号”注温奉桥:《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对柏格森的有意误读很显然是为科学进步的理性主义范式服务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符合这种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悄悄掩盖了柏格森哲学本身与中国用法之间的矛盾。最好的例子是方珣1919年发表于《少年中国》的《柏格森之哲学》一文。在此文中,对柏格森的引进,在于证明其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通过知识的普遍性和进步观来确定柏格森的最初合法性;同时强调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需要柏格森:通过帮助训练中国人的理智和直觉以促进社会的进化。[注]参见[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4页。正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中的论证,方珣是根据进化论的线性轨迹来解释柏格森的时间观念。另外柏格森哲学对自由与个性的强调也符合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欲反传统、打破旧有道德规范的目的,而非对真正意义上的柏格森哲学的解读。另一个例子是1919年冯友兰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注]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2页。一文中对柏格森的解释。在此文中冯友兰竭力维护直觉理论的科学性特质,反复强调直觉是科学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二例都是五四进步观的意识形态对柏格森的误读。也就是说为了实用目的,中国哲学家并非需要柏格森的真实思想而是采用了符合中国时代语境的对柏格森的“借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被称为“误读”。柏格森的生命和心理哲学被视作唤醒国人蛰伏的创造力以促进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工具;而直觉与知识和概念一道,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科学及其他事业的有效工具。[注]参见[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2页。
同时中国思想界对“意识流”心理学基础的弗洛伊德理论的借用也可被认为是经过了改造的有意“误读”。对于明显与五四不能相容的弗洛伊德学说,五四时期是将其作为使个体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方式用于服务社会之进步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了中国现代作家批判封建禁欲主义的锐利武器,郁达夫、郭沫若、叶灵风、许杰、施蛰存等对中国的传统性道德进行反叛,在作品中大胆地描写性欲,冲破封建禁欲主义的囹圄。”[注]吕周聚:《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渊源》,《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弗洛伊德学说主要被用来作为声讨封建性道德的理论基础,五四知识分子借此来赞成一种色情性欲,将弗洛伊德学说视为此时期反传统的工具之一。在朱光潜的解释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成为实用主义的象征,被提升为一种鼓励“自然”和对自我欲望的认知更少压抑的崭新教育方法之理论基础。[注]参见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利用精神分析学说五四语境中与性有关的讨论获得了暂时的合法性。精神分析学说在此时期是作为西方最现代与新进的思想,同时也作为社会现代性的文化对等物,五四知识分子通过对其的借用承诺了一个通向西方现代性的捷径。
2.体现“新”与现代性的“意识流”——对“意识流”代表作家、作品的译介
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对“意识流”代表作家、作品及评论之译介也有迹可循。如徐志摩对《尤利西斯》的赞美[注]参见徐志摩:《康桥西野暮色》,《时事新报副刊》1922年7月6日。,沈雁冰对乔伊斯及《尤》作的推介[注]参见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专栏,《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赵景深翻译《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注]参见John Carruthers著、赵景深译:《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文学周报》1929年合订本第8卷。一文及发表于《小说月报》的论文《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注]参见赵景深:《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小说月报》20卷8号,1929年8月10日。都可被认为是将“意识流”及其代表作家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最初尝试。同时在一些世界文学史专著中亦可找到“意识流”的存在:如郑振铎撰写的《文学大纲》[注]参见郑振铎:《文学大纲》,上海书店1927年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译著《现代文坛的怪杰》[注]参见土居光知:《现代文坛的怪杰》,冯次行译,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社1929年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注]参见千叶龟雄等:《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张我军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等书籍都对“意识流”的文学地位、相关作家作品的特色进行了介绍。综观此部分译介材料可见:一方面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坛在五四时期对“意识流”的认知较为隔膜,有自己观点的评论文章较少;另一方面也可见其开放性。当时文坛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学术见解并不陌生。与对“意识流”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观点相一致,这部分译介材料多注重“意识流”及其代表作家所具有的“新”质和现代性,对“意识流”的译介旨在接触世界现代思想。如其间对乔伊斯的译介在于看重乔伊斯作为新近西方现代小说之代表,其代表的新质与反传统性符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直线向前的时间认知作为前提对现代和西方的理解。这亦是五四作家追求西方现代性的有力表现。
二、20世纪30年代:理解与误读的双向深化
如果说五四时期作为第一个阶段对“意识流”的译介体现出站在前现代立场上、处于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叙述开端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普遍现代性的追赶行为和一种带有滞后性质的模仿行为,“意识流”多以一种科学主义的形象为五四文坛所接受;那么现代文坛第二个阶段对“意识流”的译介则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倾向:综观30年代中国文坛对“意识流”的译介,既有对“意识流”误读的加深,也存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旨在理解与批判的接受。此时期的特点可被归纳为理解与误读的双向加深。
1.理解之深化
20世纪20年代末期直至抗战爆发,赵景深、叶公超、费鉴照、范存忠、赵家璧、卞之琳、朱光潜等当时一批一流的作家与学者的研究与译介对“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意识流”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文论在现代文坛悉数登场。同时中国研究者通过译介对“意识流”的评价也有所深化:如称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夫以及爱尔兰的乔伊斯属同一阵营,将他们作为“心理小说”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来理解[注]参见赵景深:《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小说月报》20卷8号,1929年8月10日。;抓住“意识流”小说异于传统小说的本质特征,认为对于时间的不同观念而导致这类作品对时间的不同处理[注]参见赵景深:《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学》,神州国光出版社1930年版,第80页。;强调乔伊斯、伍尔夫在打破文学陈规方面的特殊贡献[注]参见千叶龟雄等:《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张我军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78、79页。;对“意识流”小说的题材特点和形式结构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注]参见叶公超:《墙上一点痕迹译者识》,《新月》1932年4卷1期。。尽管综合此时期中国文坛对“意识流”代表作家的译介史料可见对“意识流”的评价多以肯定其代表作家之创作技巧为主,同时很多评价多间接引自或译自欧美评论,但如果纵观“意识流”及其代表作家在20世纪上半期欧美文坛的接受情况所经历的长期深化过程,30年代中国文坛对“意识流”及其代表作家的译介不可谓不活跃。
2.误读之加深
理解深化的同时,受实用译介观的影响此时期中国文坛对“意识流”的译介还呈现出批判其创作思想为主导的误读倾向。典型的例子如对福克纳的引介。1934年《现代》杂志5卷6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对福克纳的译介就基于福克纳作为新近美国作家这一身份。事实上整个专号的问世都强烈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注重实际的现代译介观:译作不是为了满足读者个人的情感需要,而在于调动读者使其参与到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去。当时中国文坛选译美国文学的原因在于看重新兴的美国文学对致力于摆脱传统影响、发挥独创精神的中国文学的鼓舞作用。正是因为当时文坛“为我所用”的实用译介观促使新文学家们在一段时期内大力介绍新兴的美国文学。而这种先行的译介目的也使当时文坛对福克纳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误读色彩。“中国文坛对英美两国文学和作家有不同评说,而这又与译介倾向有关联。细察起来,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潜藏着一种现实意识,即选取两国文学中对中国语境有所助益的那部分品质。”[注]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在这样一种现实意识的指导下,整个中国文坛对“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对其具有的创新性技巧表现出有节制的肯定,而对于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多表示批判”[注]参见郭恋东:《论中国现代文坛对“意识流”的接受》,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的倾向。此时期对“意识流”及其代表作家的译介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坛“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译介观。
同时30年代对乔伊斯的译介研究也同样带有误读倾向。1935年5月6日,《申报·自由谈》刊载了周立波的评论文章《詹姆斯·乔易斯》。认为乔伊斯完全是一个无益于文学发展的颓废派作家。同年9月25日,周立波在上海的《读书生活》2卷10期上发表另一篇有关乔伊斯的文章《选择》,与上文遥相呼应。并直接提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即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才可以看清现实的本质和社会的矛盾;而乔伊斯式的文学则是市民文学之代表,其作品描写的内容及心理恰是没落阶层的阶级心理的必然反映。透过周立波的这两篇文章其实不难看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中国新文学同中国革命一样也走了一条“以俄为师”的道路。早在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托尔斯泰等许多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是当时作家、评论家介绍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到了30年代,苏联文学得到巨大发展,以高尔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进步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向往和学习的楷模,《选择》这篇文章可以说就是一个例证。30年代苏俄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发展,可被认为是降低了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西方现代主义,当然包括其中的“意识流”文学,在当时与现实主义这个强大的对手相比,只能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形态存在于中国文坛。
三、20世纪40年代:向文学自身回归
20世纪40年代,马列文论与苏联文学在中国文坛得到系统译介,这也是40年代中国文坛的整体译介倾向。但与时代氛围大相径庭的“意识流”文学的译介却在此时期出现了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吴兴华对于乔伊斯的评价几乎都在小说艺术的范畴之内”[注]段美乔:《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与中国文坛对意识流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萧乾更是在1940年代后期的“意识流”小说译介中非常引人注目,“他对意识流小说具有整体的把握,同时也具有更为开放的视野”[注]段美乔:《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与中国文坛对意识流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吴兴华、谢庆垚的集中译介
“意识流”在40年代的译介与《西洋文学》杂志的创刊具有密切关系。1940年10月《西洋文学》第2期刊发了两篇由吴兴华著译的文章:一篇是翻译介绍H.S.Gorman原著、1939年出版的《乔易士研究》一书,另一篇是对《菲尼根的醒来》的书评。在对《菲》的书评中吴兴华对乔伊斯及其作品的艺术性基于客观分析而大加赞美:指出乔氏文字优美而富于音乐性;并以《菲》为例论证现代主义小说所具有的两大特质——语言和对时间的把握,从而对这部天书进行了较为准确客观的评价。这一基于对乔写作技巧及创作方法的准确把握而进行的详细研究,不仅揭示了乔作的深层叙事模式,也对其语言进行详细探究,论证《菲》作的文体和文字特点,从而为乔伊斯正名。作为在诗歌创作、学术研究及翻译三个领域均取得不凡成就的吴兴华来说,在40年代对乔伊斯的译介所体现出来的对艺术及文学作品创作技巧之自觉追求与吴兴华本人在诗歌创作中对技巧、形式之探索可谓一脉相承。与此同时《西洋文学》还在1941年3月第7期上为纪念乔伊斯去世刊载了乔伊斯特辑,成为乔伊斯作品在中国的又一次试探性登陆。在这期“乔易士特辑”中共有《乔易士像及小传》、《乔易士诗选》(宋悌芬译)、《一件惨事》(郭蕊译)、《友律色斯插话三节》(吴兴华译)、《乔易士论》(张芝联译)等文章,非常完整地介绍了有关乔伊斯的一生及其创作情况。
同时对另一位“意识流”代表作家伍尔夫的译介在40年代也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如《时与潮文艺》2卷1期刊登的谢庆垚的《英国女小说家伍尔夫夫人》、吴景荣的《伍尔夫夫人的〈岁月〉》等评论文章,冯亦代的两篇译作——伍尔夫的文论《论英国现代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雷蒙·莫蒂美的《伍尔夫论》[注]分别发表于《中原》1卷2期,1943年9月;《中原》1卷3期,1944年3月。。这些译介材料都旨在突出伍尔夫小说中“意识流”艺术的作用:替小说技术疆界开辟了新大陆,证明了“内在真实”的合理性。除了期刊上的推介,单行本的译介对伍尔夫及“意识流”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也功不可没。1945年11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伍尔夫长篇小说《到灯塔去》的中文节译本,在译者“序”中谢庆垚对伍尔夫的评价可谓意义深远:强调了伍尔夫小说的艺术价值及对文学之贡献;称其所实验的是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具有与众不同的风格特点;且伍尔夫文论中对传统小说精密布局之反对其实更有利于小说的发展;同时向中国读者介绍伍尔夫的文学理论,说明小说家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真实性之揭示;而伍尔夫小说所具有的抒情诗特点正开拓了小说领域的新园地。这样一篇建立在对作家作品深入研究上的评论文章,体现了40年代中国文坛对伍尔夫的写作风格与创作思想的认识深度。
2.萧乾的整体性评价
除了吴兴华、谢庆垚等学者对乔伊斯、伍尔夫之经典译介与深入理解,萧乾在40年代发表的多篇研究文章体现了现代文坛对“意识流”理解的新高度。萧乾对“意识流”的反思被认为是“将艺术历史化的研究态度”,显示出“一种横向的思想的开放性和纵向的历史的客观性的结合,可以说远远超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诸多译介者”[注]段美乔:《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与中国文坛对意识流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特别是在发表于1947年1月19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5期的《小说艺术的止境》一文中,萧乾对“意识流”的文学试验性予以肯定,认为这种带有试验性质的创作通过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探索体现了小说艺术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为一度致力于系统研究西方心理小说的萧乾来说,中国作家对“纯心理小说”的研究与借鉴具有必然性与积极意义,“中国不妨有人试写纯心理小说,应该有人(性格和文学观点相近的)碰碰这硬钉子,为同行探索一下新领域,正如中国应该有人研究原子,探索喜马拉雅极峰和试验起死回生术一样。有气度,真正关心中国小说前途的批评家,可以严格地检查试验者的成绩,却不必去挫折他们的勇气,阻挠他们的尝试”[注]萧乾:《詹姆士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文学杂志》2卷1期,1947年6月1日。。尽管萧乾认为当时中国的现实土壤并不利于“意识流”这类纯心理小说的生长:“中国现阶段的处境,中国人热爱生活的先天气质,从小说本身的血肉性来看,《大使》、《金碗》是死路。但那并不是说,它们为达成‘深度’而走过的路是不足借镜的。”[注]萧乾:《詹姆士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文学杂志》2卷1期,1947年6月1日。仔细体味萧乾的这段话,“深度”一词可谓意义深远:饱含着对探索现代小说发展过程的呼吁,也由此可见40年代中国研究者的文学自觉意识;同时探索的目的也并非追赶西方最新与最现代的潮流(因为这毕竟是一条死路),而在于借鉴,以创造中国小说的“深度”。
四、“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由“新”而“深”
借由以上的代表性译介实例不难看出“意识流”在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译介流向:由五四时期所树立的体现“新知”与科学主义的形象,经由30年代在两个方向上的发展而转变为“具有异质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先锋”形象出现于中国文坛。“意识流”形象在译介中的流变也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理解的深化。这种流变亦可归纳为由五四时期的“求新”而至40年代的“求深”。这一发生在40年代民族战争夹缝中、基于探寻中国文学之文学性发展的转变可谓意义深远:既体现了现代作家的艺术自觉,也是对五四以来译介作为改造社会现实、唤起民众参与社会现实以达到足救时弊的实用主义工具性的反拨。正如评论家所说,4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方面出现了一个全面复苏阶段,究其原因是因中国抗战现实发展到一定阶段、处于此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困境使然。[注]参见段美乔:《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其实这更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次成果展示。此时期包括“意识流”在内的现代主义小说及其理论译介的繁荣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异质性文学自五四以来的进一步深入认识:他们真正开始“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状况为潜在背景自觉地去思考和理解这些创作”[注]段美乔:《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从这个角度来看,萧乾所呼吁的“求深”实际上表达了此时期中国学人对异质性文学/文化的一种态度:接受西方的影响不是为了趋同而是为了存异。“借由在把西方的价值转化成为其内在化的经验之后,它也创造性地拓展自身的异质性。”[注]陈晓明:《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此一转折可以说真正开始将中国文学引领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道路。早在五四时期就发出的探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途径——“将中国现代文学纳入整个世界文学,达成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注]《世界文学发刊词》,《世界文学》,1934年10月1日1卷1期。,发展至此可谓有所收获。这同样解释了为何40年代被当代评论家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在风格上表现出多样化特征的时期”[注]严家炎、范智红:《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在文学上孕育着辉煌收获的年代却在紧接着到来的“排除异己,追求一元化”的中国现实要求下被迫中断。伴随着民族战争的结束,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提出的“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之要求,文学为政治所控制的局面已不可避免。对于40年代出现的“超越时代规范的艺术家们的选择:他们有的沉默(如沈从文),有的则从承认“工农兵文艺的小说征服了读者的‘现实’出发”[注]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四卷 1937—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皈依(如萧乾),从而使得这个本应无比辉煌的中国文学繁荣时期过早结束,直到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才得以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