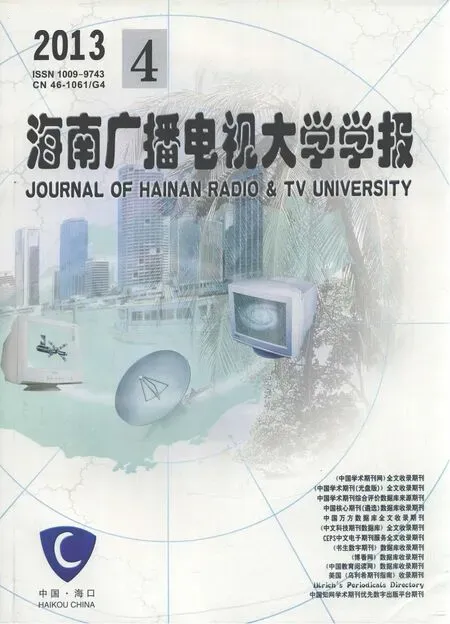为一座城、一代人写心
梁 伟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每一座城市居民,都会有对于自己所处那座城市的想象。这种想象,反映着这座城市居民的深层心理。历史上,海南岛一直孤悬海外,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岛即成一个王国。海口作为这座岛屿的行政中心与最为繁华城市,本城居民性格可谓自傲与淳朴并存。他们视海口为世界上最惬意生活场所;同时,这种自足自然生活也使他们少了一点生存压力和进取精神。
事实上,不同状态中城市会给人不同观感。你观看一座老城,它给你带来的是历史沧桑;你观看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所得到的是一种灯红酒绿的不确定感和幻灭感。这在现代叙事中,常被叙述为一座罪恶之城。毋庸讳言,作为前者,海口并不具备足够厚重,如南京、北京等;作为后者,也不拥有足够繁华,如上海。若要准确名之,或可称为一座处于变动中正欲向后者的繁华发展城市。一座正处于变动中的城市,给人的观感与前两者不同。总之,其居民在心态上倾向于前一种城市;而其所处环境,却又已具备后一种城市特质。
现代小说,在本质上不是一种英雄传奇,它是在各种官方非官方宏大叙事包围中,力图突围去刻画与还原每一个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命运,并对其作出导致这种命运的严肃思考。虽然这种思考,常未必能给出确定答案或明晰揭示。《我们的三六巷》照此原则,在自己艺术构造中,为一座城以及这一座城中的一代人写心。
海口如崽崽所言是块“福地”,它造就了其居民带着封闭性的自傲与淳朴并存性格。但当这座城市遭遇变动时,这种性格特征,却亦可能会造成他们被抛却的命运。在大办特区与十万人才涌海南中,海口本城居民正是被推上了这一种命运关口。尽管在作为小说叙事的发生场域海口三六巷中,也有着狗六这样“见过世面”的弄潮儿,但最终却也免不了人生悲剧下半场。三六巷居民在与外来“人才”卓金、琼生接触中,产生了自身与他者形象碰撞。在对他者窥视中,“没见过这样白净雅致的人儿”,他们反观的实质是自身形象。在见到卓金和琼生前,他们并非没有见过“人才”,“街上的人才见多了”。但卓金和琼生是作为三六巷“闯入者”身份出现的,“这样的人怎么会到三六巷来呢”!这才是小说叙事的核心秘密。即便是海口这样的城市,对于三六巷居民来说,仍是太大,外来者只有闯入他们生活时,才能与他们发生联系。这确是一种“闯入”,以最具切近性形式让他们见证这座城市的变动。
坦白说,小说正面叙述三六巷居民生活变动的笔墨并不多,或至少并不足以给人留下足够深刻印象。在小说叙事结构中,三六巷居民更像一群旁观者,看着卓金、琼生、星星等“闯入者”发迹变化与人生悲欢离合。他们初到时,三六巷居民惊讶他们的神色;他们陷于事业瓶颈时,三六巷居民以小市民式的精明发觉他们不过尔尔;但当他们取得辉煌成就时,三六巷居民则艳羡乃至嫉妒,然后又出于性格上惰性,自我安慰说他们毕竟是“人才”。这种叙事结构的设定,符合三六巷居民性格特征。总之,三六巷居民不是反应积极的时代弄潮儿,而是城市变动的延缓反应者。
“这样的人怎么会到三六巷来呢!”这句话所以能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秘密,乃是因为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揭开以及理解这一场城市变动根本性质。显然,这一场变动的意蕴并非单纯指涉建省或办经济特区,而是在此种意蕴基础上,更是一场朝向现代城市、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历史性变动。在此前,中国并非没有经济特区,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即是。但这些都离三六巷居民太远,唯有海南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才能让他们身临其境。这些经济特区的设办,无论其设计者初衷如何,若非遽然关闭,一旦维持下去,则必然导致向一种现代城市、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敞开。我们今天所处的情景,即是此种敞开既具有普世性亦具有“特殊国情”性结果。一百多年前,面对古老王朝在世界列国格局中的处境,李鸿章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感叹,实在,以今观之,李鸿章可能感叹得过早了,今日中国,才可能正是处于此一“大变局”关口。
现代城市叙事,即便是对于只有短短百年历史的白话新文学来说,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1930年代即由“海派”文人开启了充满现代城市感觉的书写。但1949年后,经过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人们的文学理解对此一种城市叙事可谓是久违了。《我们的三六巷》并不是一部城市叙事开风气之作,却是一部海口城市叙事力作;我们若要对小说中人物如卓金、吉仔、那伟宏、琼生、李梦莲、王连财、狗六等人的坚守或沉沦进行准确理解,则必须要回返去探析此一座城的变动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新特征。此种全新特征,正是诞生于历史向着一种现代城市、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敞开。且在小说故事中,这是一种开启,而非纵深发展,更非完成;到现在亦未完成。但虽只是一种开启,却亦足够让人猝不及防;正因只是一种开启,才更让人猝不及防。
要准确理解这样一种开启对故事中人的影响,我们可寻找一个中介,那就是金钱。在小说中,金钱牵引着“人才”闯海;金钱,勾结人与人间关系。在小说中,金钱的中介可说无处不在。金钱是一个新世界根本属性的表征,就像“经济特区”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向度。
“货币古已有之,现代经济生活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从前,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觉》)
现代新世界利用各种手段向人们许诺平等,而在这些手段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无疑就是金钱。因为在现代世界,金钱成为一种通行语言,是任何人都可以追求的,没有说谁没有追求金钱权利;不同于古代世界,一个等级社会,是不许诺用金钱可以打破的。而平等,“实际上就是‘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把个别的、高贵的品质(这恰恰是自由的个性要寻求的)拉到最低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觉》)
在这样一种开启中,在这样一座城的变动中,卓金、吉仔、那伟宏、琼生、李梦莲、王连财、狗六等人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以金钱为表征与通行语言的现代新世界。在小说中,琼生、李梦莲、王连财、狗六等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了这个现代新世界;而卓金、吉仔、那伟宏则选择了一种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坚守,即是他们拒绝金钱这样的“一种夷平过程”。在这样一个五色迷目世界,人应当如何自处与生活,卓金对琼生所说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作者崽崽的理想与心声:
“人生最高的智慧是简单,最美的感情是真诚。如果你认为社会复杂你就耍计谋,社会险恶你就耍手段,你去挣扎吧,琼生!我对你说,为了幸福你得简单和真诚,为了简单和真诚,你得战胜自己、征服自己、完善自己,人就得有人的样子……”
——评《中国经济特区四十年工业化道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