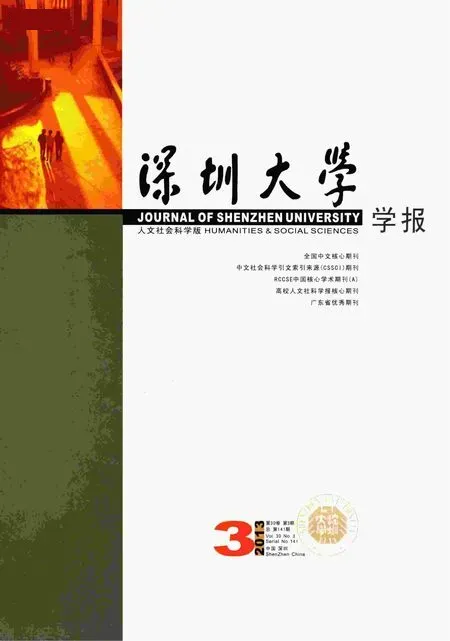脱逸与构建:论平田笃胤的《灵能真柱》
贾 璇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脱逸与构建:论平田笃胤的《灵能真柱》
贾 璇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以《灵能真柱》的问世为标志,平田笃胤实现了对前人国学思想的脱逸和自身国学思想的构建。《灵能真柱》由国学宇宙论和显幽论两部分构成。平田笃胤摆脱了此前记纪二典对国学者的束缚,试图重构“正确的古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独自的宇宙论。关于灵魂的归宿,平田笃胤否定了本居宣长提出的人死后灵魂皆去往黄泉的观点,认为灵魂归于幽冥,永久存在于这个国土之上。构建了一个“天·地·泉”的宇宙世界与“显·幽”二元世界相互交错的空间。隐藏在国学宇宙论和显幽论背后的是平田笃胤的国体观,即“日本优越论”和“天皇中心论”。
近世国学;平田笃胤;《灵能真柱》;国学宇宙论;幽冥论;国体观
日本近世国学形成于17世纪中叶,以契冲为始祖,运用古学派考据方法,提倡去“汉意”而发“和心”,专注于日本古典古语本义的研究。内野吾郎将由此启航的日本近世国学分为两大学派,一派为“古道论系国学”,另一派为“文艺论系国学”。其中“古道论系国学”传承的代表人物先后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1],日本学界史称为“国学四大人”。作为本居宣长“殁后门人”的平田笃胤在继承本居国学思想的同时,逐步创立了独自的国学思想,即平田国学思想,将近世国学推向了新的高峰,《灵能真柱》便可谓这一过程中标志性的作品。
平田笃胤一生著作颇丰,多达百余部。这些著作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祖述本居宣长的国学思想→平田国学思想的诞生和展开→平田对他国学问的研究。成书于1812年的《灵能真柱》正是第一、二阶段的“分水岭”,该著作的问世宣告平田国学的诞生。“平田私塾”将《灵能真柱》列为“平田七部书”之首,并将该著作定位为“学习古道之人必读之书,古学安心之书”[2]。平田笃胤也因该书而得名“神灵能真柱大人”。《灵能真柱》分为上下两卷,由国学宇宙论和显幽论构成。平田笃胤在两部分的著述中都实现了对前人国学思想的脱逸和自身国学思想的构建。
一、《灵能真柱》中平田笃胤的国学宇宙论
这里所谓的“宇宙论”是指“与哲学、神学性质的宇宙形态或世界形态密切关联的,包括宇宙形态论的宇宙生成论”[3](P190)。
在本居宣长的著述中并未提出完整的宇宙观,仅仅停留在对《古事记》中神话展开过程和神的种种作用的注释,或者说本居似乎并无明确的意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本居研究《古事记》,其目的在于批判汉意,确立日本之古道。而本居之所以选择贬“纪(《日本书纪》)”扬“记(《古事记》)”,以《古事记》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其一,本居认为《古事记》保存了古语,即是保存了古意,“此记字之文无修饰,皆以古语为主,不失古代之实,原样而作”。相反,《日本书纪》则汉文修饰过多,沉溺于汉意。其二,本居认为《古事记》是言传之物,并非汉籍中的开天辟地等依靠凡人之心的推测之物,并且既然能在 《日本书纪》成书后依然流传下来,必是正确的史书[4]。不难看出,本居深陷在了文献绝对主义的沼泽中。基于上述原因,本居视《古事记》所记皆为上代的实事,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也正是由于本居将自己束缚在了这种古典注释学的研究框架中,因此势必无法提出完整的宇宙观。
构成国学宇宙论发端的是本居宣长的门人服部中庸,服部受本居《古事记传》的影响,以记纪神话为基础(主要以《古事记》为蓝本),结合西方天文学知识,著有《三大考》一书。服部在该书中推断了天·地·泉(月)的生成过程以及相对应的诸神的生成过程,并配以十幅绘图直观诠释。子安宣邦评价“《三大考》的意义在于构成了国学宇宙论的发端。系统各异的神话传承相互混杂的记纪神话,其本身并未阐释出宇宙的生成。而以这样的神话传承为基础的 《三大考》却尝试了将宇宙以及众神的生成过程秩序化。显然,这已超出了古典注释学的框框,而致力于宇宙论的形成”[3](P190)。 《三大考》中所描述的宇宙生成过程为:最初虚空中有天之御中主神和产灵二神共三神。虚空中生出一飘忽不定之物,天·地·泉(月)由该物垂直纵向分离而成,先萌生出天,余下的部分凝固为地,泉垂至地底。天,即太阳,也就是高天原,由天照大神统治。地,由皇孙统治。(黄)泉,即月亮,由月读命(与须佐之男命为同一神)统治。服部提出的是一种垂直构造的宇宙生成论。
从本居经服部而成立的国学宇宙论在平田笃胤的《灵能真柱》中得以新的展开,或者说国学宇宙体系的构建是由平田笃胤最终完成的。《灵能真柱》在继承本居宣长部分思想的同时,主要参考了服部中庸的《三大考》。然而,在研究方法上,较之本居、服部二人,平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即摆脱了一直以来记纪二典对国学者的束缚,积极拓宽了史料素材,结合其他古书或古代记录,试图重新构成“正确的古史”。平田在高度评价《三大考》的同时,明确提出由于该著作并未意识到古代传说中的众多混乱之处,因此许多地方著述欠妥,唯有重新选定正确的古史才能纠正其中的错误。正如子安宣邦所评价的,平田在《灵能真柱》一书中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就是从依据已有的《记》、《纪》原典而构筑天地生成过程的阶段,向依据诸古典积极地重新构成‘正确的古史’即‘正确的天地生成过程’阶段的飞跃”,或者说“是从在构成宇宙形成论的方向上解释作为素材的神话传承的阶段,迈向了依照构成宇宙形成论的目的、进而依照构成神道神学目的,重新对神话传承本身进行整合的方向”[5](P118)。
除了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平田在《灵能真柱》中也提出了独自的宇宙论。首先,《灵能真柱》并未完全照搬《三大考》中用于阐释天地生成的十幅绘图。除前三图基本一致外,其余七图均有相异之处。例如,第四图中与天之底立神相对应,添注了国之底立神,认为在伊邪那美神掌管黄泉国之前由天之底立神居于其位[6](P191)。不同与《三大考》第四图至第八图中“天·地·泉”始终彼此相连,第九图开始三者才相互分离,《灵能真柱》从第五图开始便将 “天”率先与“地·泉”分离成两部分,并在图下注明“《三大考》中认为此时天与地仍然相连的观点是错误的”[6](P171),“依据沼河比卖神的歌”可以判断“在皇孙降临之前,天与地已然早早分离,已有昼夜之分”[6](P184)。 至第十图时“地”与“泉”相分离,最终完成“天”“地”“泉”三部分的彼此独立。
其次,《灵能真柱》中明确了天地未生成之前,天之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三神已先于天地的形成存在于“大虚空”中,三神的产灵创造了万物。虽然这种造化三神的“先在说”并非始于平田,在本居的《古事记传》、服部的《三大考》,甚至平田的《古道大意》中均有所暗示或相应意思的表述,但是《灵能真柱》中平田笃胤是将其作为“正确的古史”而明确提出的。
再次,平田在《灵能真柱》中指出“天”其“质”如“水晶”般“清明”,而非《三大考》中所认为的“火之精”。所谓的“泉”,实应记之为“夜见国”,因其位于最底部,被大地阻隔,接收不到阳光,“泉者,除‘夜见’之外,无字可记。但因‘泉’字既已俗成,唯有借用。却万不可拘泥于‘泉’字。”并称《三大考》中所述“月泉由水构成,是比寻常水更为细密之物”,是极大的错误,实为“重浊之物”[6](P168-171)。
此外,关于祸津日神,平田也提出了独自的观点。本居在《直毘灵》中称“世间诸事,皆乃神之所为,神有善恶之分,其所为亦随之而为”,“祸津日神暴乱之时,天照大神亦无法制止,人力更无可奈何。世上善人遇祸,恶人得福那诸多的悖理之事,皆源于祸津日神”[7]。认定祸津日神是恶神,是世间的恶事之源。将善人未必得善报之类的非合理性归结于祸津日神的所为,以此来批驳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儒教的阴德阳报思想。然而,平田在《灵能真柱》中却指出“(祸津日神)是源于伊邪那岐憎恨污秽之心而生成的神,因此有污秽之事时即会发怒,甚至会做出不合理的乖张之事,但是若没有污秽之事,就不会发怒,甚至会带来恩泽。故将该神一味地认作邪恶之神,是极大的错误”。“作为人,皆会憎恶污秽之事,且会动怒,这是由于得到祸津日神之御灵”[6](P193-194)。认为人被赋予了“祸津日神之御灵”,因此人心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也在伦理上具有自律的能力。将儒教式的道德说教融入到了神灵观里。
在《灵能真柱》中,平田重构“正确的古史”,从固有的古典注释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素材中脱逸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自的宇宙论。
二、《灵能真柱》中平田笃胤的显幽论
平田笃胤在《灵能真柱》中提出的显幽论是平田国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显事”与“幽事”这对概念最早出自 《日本书纪》中大己贵神出让国土的段落,其中的“显事”(显露事)指现世的统治,与其相对的“幽事”即“神事”,指祭祀。此后,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扩大了两概念的涵义,将“显事”定义为“朝廷的万般事务,世人显露在外的所从事之事”,将“幽事”定义为“世间看不到的,不是某人之所为,而是神之所为。此世间所有的事情,皆是依据神之御心所为,与世人之所为相对,亦称之为神事”[3](P202)。 我国学者牛建科认为,“如果说,在《日本书纪》中,‘显露事’与‘幽事’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指神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在本居宣长这里,则是指神与人之间的关系”[5](P82)。 《灵能真柱》中,对于“幽事”,平田笃胤基本继承了本居的观点。而对于“显事”,平田称“仔细考虑显明事与幽冥事的区别,凡人在现世中如此生存,即是显明事,作为天皇的臣民”[6](P214),表现出了平田的民族主义政治世界观。
虽然平田并未在《灵能真柱》中对“幽事”进行重新定义,但是却提出了“人死后,其灵魂成为神”,“归于幽冥界”[6](P214)的独自的观点。关于灵魂的归宿,平田认为其师本居所提出的“无论神或人,善或恶,死后皆去往黄泉”的观点是错误的,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本居没有意识到 “外国之说混淆了真实的古传”,将中国古籍(如《春秋左氏传》、《伤寒杂病论·序》)中的“黄泉”等同了“夜见国的古传”。而“世上的古学之人,凡事皆依赖老师本居宣长的观点,自身并不努力探究,甚是遗憾”,“不仅是宣长的门人,其他的古学者,也不可能去批判‘灵魂归于黄泉’之说,只是一味地承继宣长的观点”。与这些古学者不同,平田则表现出了彻底的探索精神和大胆的批判意识,明确提出“死后的灵魂去往黄泉之说,是不成立的”。这一点“不仅依据神代的事实可以得知,而且考察人出生的经过和死后的状态也可以领悟到。首先,人的出生是父母所赐,但究其根源,则是奇妙的神之产灵将风、火、水、土四物合一,创造了人,并赋予其灵魂,使其出生”,“人死后,水和土成为尸骸清楚地留在世上,灵魂则与风和火一同离尸骸而去”。“这是由于风和火属于天,而土和水属于地”。并且“灵魂原本就是产灵之神所赐之物,有理由归于天”。平田认为“人死后,灵魂与尸骸分离成两部分,尸骸成为最污秽之物,归属‘夜见国’,接触到尸骸的火产生出污秽”,“而灵魂与尸骸分离后,成为清洁之物,异常憎恨火的污秽”,“如此憎恶不净的灵魂,怎么会去产生污秽或留存污秽的夜见国呢?”[6](P233-241)由此来否定本居的“灵魂归于黄泉”之说。
灵魂的归宿到底在何处呢?平田提出“人死后,其灵魂即成为神”,“归于幽冥”,“因此归服于掌管冥府的大神——大国主神,遵从其规定”[6](P214)。结合此前的“凡人在现世中如此生存,即是显明事,作为天皇的臣民”,平田构建了“凡人在现世”臣服于天皇,“灵魂在幽冥”听命于大国主神的二元秩序体系。既然作为灵魂归宿的幽冥并非黄泉国,那么幽冥(即冥府)又在何处?平田认为“冥府并非在国土以外的某处,而就在这个国土上的任何一处,只是幽冥与现世相隔,无法看见”,“从冥府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世人的所为”,而“从现世却无法看见幽冥”。因此,“要说这个国土的人死后,其灵魂去往何处,那就是永久地留在这个国土上。这一点从古传和现今所见所闻的事实中可以知晓”。“如同大国主神虽然隐藏起来却在近侧守护着现世一样,(灵魂)从幽冥守护着君主、父母和妻儿。被祭奉在神社、祠堂的众神自然是镇坐在那里,而其他的(灵魂),则是镇坐在坟墓旁。这种情况下,(灵魂)和天地一同永久镇坐在那里,如同众神永久地镇坐在神社、祠堂里”。此外,平田还提出“灵魂虽然存在于这个国土上,但是却可以往来于天上”的观点[6](P242-244)。平田的上述论说可总结为三点:其一,人死后,灵魂归于幽冥,而冥府就在这个国土上的任何一处,具体说来,大多数灵魂镇坐在坟墓旁,同时灵魂又可以往来于天上;其二,人死后,即成为神,如同现世和幽冥都存在于这个国土上一样,人和神实际上是共存的,只是神采取的是一种隐蔽的存在方式;其三,人的灵魂是永生的,在幽冥界注视着现世,守护着君主、父母和妻儿。
深入分析平田笃胤的显幽论,可以看出与本居宣长的思想有着极大的不同。本居主张“人死后,抛弃妻儿亲友钱财万事,永远告别人世,无法再返回此世,不得不去往污秽的黄泉国,因此,世间再无比死更可悲的事情”,并且“无论善或恶,死后皆去往黄泉”[8]。本居认为人的这种归宿虽是令人悲伤的,但却是真实的,不同于佛教宣扬的死后极乐世界和救赎观念的虚伪,否定了儒家和佛教关于来世的种种说法,提出对这种绝对悲伤的认识恰恰是“真实的神道的安心”。本居的这种“无安心的安心”论,没有宗教的救济,也不给人丝毫希望,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与本居的重视“现世”、否定“来世”相反,平田则对灵魂的归宿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平田提出人死后,灵魂成为神,即使是现世中的受难者也能在幽冥界得以永生,并且幽冥就存在于这个国土上,从幽世能够看到现世的一切,也能够庇佑亲人,给予幸福。人存在于现世只是暂时,去幽世后才是永恒。平田的观点解决了现世无法解决的非合理性这一课题,让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死后灵魂的永生,得以宗教性质的安心,这是一种与本居截然相反的积极的乐观主义,也无疑是一种救济论。继村岡典嗣、田原嗣郎、三木正太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子安宣邦明确提出 “平田笃胤的救济论确实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6](P56)。石田一良也指出“本居宣长多神教的、现世教的、具有主情色彩的古学神道,到平田笃胤这里,通过与基督教的调和,变成了一神教的、来世教的、具有伦理色彩的神道”[5](P129)。 《灵能真柱》中围绕灵魂归宿的救济论,给其他国学者以不小的思想冲击,也带来了国学理论的宗教化和神秘化,开启了通往神道性质救济论形成的道路。显幽论的提出使得日本的近世国学跨入了平田笃胤时代。
结合前述的国学宇宙论,平田笃胤在 《灵能真柱》中构建了一个“天·地·泉”的宇宙世界与存在于国土上的“显·幽”二元世界相互交错的空间。
三、隐藏在国学宇宙论与显幽论背后的国体观
从结构上看,平田笃胤的《灵能真柱》是由国学宇宙论和显幽论两部分构成的,然而贯穿全篇的是隐藏在国学宇宙论和显幽论背后的平田的国体观。
《灵能真柱》开篇详尽阐明了著者的研究目的和思路,“古学之徒,最重要的是应坚定大倭心”,“欲坚定牢固的大倭心,首先要知道灵魂归宿的安定”,“欲知道灵魂归宿的安定,首先应详细考察天·地·泉的生成及状态,熟知使天·地·泉之所以成为天·地·泉的神之功德,充分明白日本是万国之本国、万事万物皆优于万国的缘由和威严的天皇是万国之君的真理,如此,方能探明灵魂的归宿”[6](P159)。 显然,平田著书的目的是要“坚定大倭心”,但是平田并没有以“心能真柱(万叶假名中‘能’即为‘的’的意思,‘真柱’即为‘坚固的支柱’)”命名,而定为“灵能真柱”,是因为平田认为欲坚定“大倭心”这一“古学之徒”必要的精神,“知道灵魂归宿的安定”是最重要的,也是应首要解决的课题。虽然本居宣长在古学研究中也强调“大和心”,但其核心在于排除“汉意”,是一种“对于古学的真心”的诉求。与本居不同,平田是将“知道灵魂归宿的安定”作为确立和坚固“大倭心”的前提,将这种安心的实现和进而坚固“大倭心”视为自身的使命。《灵能真柱》开篇的这段著述清晰地阐明了平田的研究思路,即通过考察天·地·泉的生成和神的功德,探明灵魂的归宿,从而坚固“大倭心”。从另一角度看,对于平田笃胤而言,探究宇宙论和显幽论的目的,在于明确日本“卓越”的“缘由”和天皇是“万国之君”的“真理”,隐藏于其中的是“日本优越论”和“天皇中心论”。
平田引用了服部《三大考》中“天与地尚未分离之时,与天上下相连的所谓的‘蒂处’就是日本,因此日本位于大地的最顶端”这一观点,称“‘蒂’的部分是(事物)形成之本”,以此佐证日本是“万国之祖国、本国”。并在引用了《三大考》中“外国虽然与日本同样是由皇产灵神之产灵所生成,但并非是由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生成的国家。日本与外国从起初就存在着尊卑美恶之差别”这一论说后,作为进一步的阐述,借用西方书籍中关于日本地理位置的记载“国土肥沃易于居住的地方在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日本恰好处于这一位置,并且是所有国家中位于最东面的”,“这个国家受到天神特别的恩惠,四周被波涛汹涌的海域所环绕,可抵御外来侵犯”,“物产丰富,自给自足”,“这些皆是创造天地的神赐予日本的特殊恩惠”,由此来强调 “日本的尊贵”[6](P176-178),提出“众外国应向日本进献物产,来与日本交好”[6](P206)的观点。 此外,平田还依据中国古籍《尚书》、《史记》、《物理小识》中在尧的时代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遭受洪水之灾的记载,说明那时的“日本正处于神代之末,完全未遭受洪水之灾”,以此证明“日本位于万国之顶端是公平之论”[6](P227-228)。不难看出,平田在《灵能真柱》中极力将宇宙论、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等用以附会其自身的“日本优越论”,力证日本是“万国之祖国、本国”,“四海之宗国”,“卓越”于其他万国。关于国民,平田主张“唯有日本的国民才是神的子孙”,“外国的国民皆不是神的子孙”[6](P205-206),同样旨在宣扬“日本神国论”,将日本神秘化。
平田在《灵能真柱》中声称“日本的古传是由灵慧的创造天地的高皇产灵神和神皇产灵神亲自传授的,是值得确信的”。“日本是万国之祖国,因此其古传是正确的,而外国均是末国之枝叶国,因此没有正确的古传。这就如同是都市的事情被传到偏僻的乡村后便会与事实不符,变得不正确”。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古传“虽是错误的,但也传得了(日本)古传的一部分”。而西方亚当、夏娃二神生出国土之说,则是对日本古传的误传[6](P161-176)。“唯有日本的古传才传达了真实的道”[6](P220)。平田主张日本古传真实性的目的在于为“皇权神授论”寻找依据。平田通过阐述天照大神之所以赐予琼琼杵尊 “丰苇原之瑞穗国,此乃吾子孙应为王之地”这一神敕的因由,证实天孙降临传说的可信性。认为这一权力的授受过程直到仲哀天皇时代才最终完成,并指出赐予琼琼杵尊的天丛云剑和八尺镜是作为 “继承皇统的皇孙的标识性宝物”,“其中一个是与伊邪那岐相关的日之神的信物,另一个是与伊邪那美相关的月之神的信物,皇统继承了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的正统性”。在这一系列的阐述后,平田指出“如此说来,天皇不仅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并且有着天照大神的神敕,因此,(天皇)是全权统治大地万国的君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现在仍然是外国的首领们治理着自己的国家”,但是如同“万国将会臣服于日本”一样,“最终,会按照应有的状态那样,所有国家的首领无一例外地俯首称臣,敬仰归服于天皇”[6](P210-211)。平田笃胤在“皇权神授论”的基础上,竭力宣扬天皇统治权的正统性,大肆鼓吹 “天皇中心论”。并且,在阐释“显幽论”的过程中,妄然构建了“凡人在现世”臣服于天皇,“灵魂在幽冥”听命于大国主神的二元秩序体系。
正是由于平田笃胤的国体观是隐藏在国学宇宙论和显幽论的背后,被粉饰以重构“正确的古史”的“科学性”和探究灵魂归宿的“宗教性质的安心”,又被附会上天文、地理、历史知识的佐证,因此更具煽动力和迷惑力。于国,平田的皇权神授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天皇中心论在成为幕末倒幕运动中有力的思想武器之后,继而成为了近代天皇制国家神道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民,平田狂热的国粹主义和对“幽世”的主张客观上助推了日本法西斯将日本人民引入战争的深渊。
[1][日]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アジア文化の再発見[M].東京:弘文堂.1984.172.
[2][日]中川和明.平田国学の史的研究[M].東京:名著刊行会.2012.130.
[3][日]子安宣邦.平田篤胤の世界[M].東京:ぺりかん社.2001.
[4]蒋春红.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03-208.
[5]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5.
[6][日]相良亨.日本の名著24[M].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
[7][日]大野晋等.本居宣長全集(9)[M].東京:築摩書房.1968-1993.54-55
[8][日]大野晋等.本居宣長全集(8)[M].東京:築摩書房.1968-1993.315-316.
Escape and Construction:Psionic True Column by Hirata Atsutane
JIA Xu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6)
With the advent ofPsionic True Column,Hirata Atsutanemade his escape from the influence of his predecessors’Native Studies and achieve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own thoughts on Native Studies.Psionic True Columnis constituted with the Cosmology and the Nether Theory of Native Studies.Hirata Atsutane threw off the shackles of the previous Kojiki II on the scholars of Native Studie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correct ancient history”and put forward his own cosmology based on this.For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soul,Hirata Atsutane rejected Motoori Norinaga’s idea that the soul was destined for the Acheron after the death of a person,and insisted that the soulwas attributed to the Netherworld and permanently existed at the top of the Homeland.A space intertwined with the universe status of “Heaven·Homeland·Atsutane” and the binary status of “World·Underworld”was constructed.Japanese Superiority Theory and Mikado Center Theory represented by Hirata Atsutane’s concept of State System were hidden in the Cosmology and the Nether Theory of the Native Studies.
Modern Native Studies; Hirata Atsutane;Psionic True Column; Native Studies Cosmology;Nether Theory;State System Concept
B 313
A
1000-260X(2013)03-0019-06
2013-02-26
贾璇(1978—),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博士,大连海事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