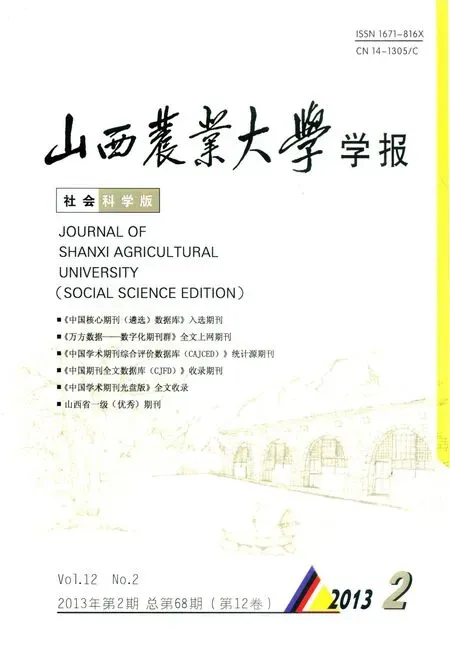欧洲中心主义观照下的19世纪《论语》英译
卢华萍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孔子 (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被后人尊称为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言精炼简洁,含义深邃,集中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睿智又富含哲理,是一部承载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经典。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言 “半部 《论语》治天下”,足见其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时至今日,《论语》仍然是经典中的经典,并不断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力深入海外,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论语》西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抵达澳门之时,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也由此揭开。自此,中国经典古籍开始被翻译并介绍到了西方欧洲。1594 年,利玛窦将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了拉丁文。1687 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里 (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出版 《中国哲学家孔子》,其中就收录了 《论语》、《大学》和 《中庸》的拉丁文译本翻译。1691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并在伦敦出版。因此严格来讲,《论语》最早的英译本是从拉丁文转译过来的。真正意义上的 《论语》英译则始于19世纪初期。1809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在印度塞兰坡翻译了 《论语》上半部译本—— “The Works of Confucius” (第一章至第九章),这也是直接译自原文的最早儒经英译本。不过因为种种原因,马士曼并没有完成其余部分的翻译。自马士曼之后,《论语》的英译经历了一个由西方传教士来进行的一个高潮阶段。1828年,又一名英国传教士高大卫 (Rev.David Collie)翻译出版了“The Four Books”,该译本被认为是苏格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 (James Legge)“翻译四书的直接先驱”。[1]1861 年理雅各来华传教,并且开始翻译中国经典。同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的 《论语》英译本,该译本被认为是 “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版译本”,[2]其所采用的 “Analects”一词也成为西方 《论语》的通用译名。20 世纪开始,《论语》的英译本更是大量出现,译者主要包括英国汉学大师威利 (Arthur Waley),美国汉学家魏鲁南 (James Roland Ware)、诗人庞德(Ezra Pound)以及中国学者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梅仁毅、丁往道等人。
本文主要分析19世纪的 《论语》英译,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解读由其带来的文化中心主义最终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地忽略 《论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从而影响到了读者对于原汁原味的儒家哲学的客观理解。
一、何为“欧洲中心主义”
(一)概念
在Syed Farid Alatas(2002)看来,欧洲中心主义是指 “受欧洲唯一性和优越性思想灌输而形成的价值观、态度、观点及思想导向”。[3]Maulana Karenga(2002)将欧洲中心主义定义为“一种支配和排外的思想和行为;其基础是认为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以欧洲文化和欧洲民族为中心,其他所有文化和所有民族最多只处在边缘地位,甚至是毫不相干的”。[4]
欧洲中心主义的出现受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始于十八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给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由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工业化过程在世界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这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资本主义制度完全确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因此而壮大。此后,随着工业革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扩散,很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欧洲的霸主地位由此诞生,欧洲国家对于东方的最终统治和支配权力也由此开始。因此从19世纪前后开始,欧洲人就认为欧洲地区 “财富最多,军事最强,而且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并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5]这也是学者们所谓的 “欧洲优势”的时代。潜意识里欧洲人开始有了一种优越感,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是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在与外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态度,因此他们在了解和认识欧洲以外的世界时普遍缺乏对这些地区的认同感,从而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历史,也就对欧洲与外界的交流产生了消极影响。欧洲中心主义因此产生。
(二)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
在欧洲人眼里,世界在欧洲的脚下。对于非西方世界,欧洲人似乎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不屑一顾。“白人种族优越论”便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极端表现。 “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6]而中国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在他们眼里更是成了 (与文明人)本质上不同的劣等民族。“欧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 ‘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 ‘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在中东被称为 ‘先生’,在非洲被称为‘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 ‘恩主’”。[6]总之,欧洲人的优越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都可以尽情展现出来,政治经济的强大已经使得欧洲人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优秀。
文化中心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又一重要表现。凭借着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强大优势,欧洲已经想称霸全球。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占有主导支配地位之外,通过文化方面的渗透来取得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也成了他们的一种手段。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欧洲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也占据了强势主导地位,在欧洲国家与他国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他国文化便成了弱势文化,对于强势文化的“洗礼”和渗透,处于弱势一方者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往往是无能为力。那么强势文化一方的代表者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仰仗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态势来应对他国文化,这便有了 “文化中心主义”的说法。
受此影响,来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译者在翻译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其他文化的不屑。因为无论任何翻译活动,译者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倾向、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对于源语文化国的态度都会影响到最后的译文。在诸多传教士把中国经典文化介绍到西方欧洲的过程中,他们选择了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从自身的文化角度出发,习惯性地沿用自己欧洲的思维来解读他国文化,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有意无意地误读甚至是歪曲。
二、19世纪《论语》英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一)翻译背景
19世纪 《论语》的译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基督教在中国曾经有过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其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交流甚至碰撞,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并且具有着独特的意义。而这一切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然过程。因为人类学家看来,任何文化在与他者接触的过程中都想以自我为中心。在文化接触的最初阶段,总有一种文化会认为自己是优于对方的文化的,而在持久的文化冲突中,各自文化所扎根的那片土地则被视为是对立的,直至其中一方逐渐被普遍认可,文化交流才会最终融合,起到真正的交流意义。而在此之前,任何一种文化以及文化的代表者都会自然地将自己的文化以及代表自己文化的经典视作不可替代和逾越的。因此,也就会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使之能够长久生存下去。对于19世纪的传教士来说,他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正好是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时期,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传教士眼中的欧洲文化便成了一种强势文化,欧洲人的霸道和优越感让他们习惯了在接触东方国家包括东方文化时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在此阶段表现得甚为明显。传教士们认为他们一直依赖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文化。在传教士看来,既然基督教能适用于欧洲这一占强势主导地位的地区,那么也就完全可以适用于欧洲之外的其他任何地区,在中国更亦是如此。
此外,这些译者所持有的这种文化强势态度也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19 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千古厄运。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向以天朝自居的大清帝国变得极其脆弱,不堪一击。大清国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遭到了严重冲击,军事、经济等综合国力的差异使得侵略者开始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控制和掠夺中国。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欧洲列强在中国步步紧逼,曾经的泱泱大国则是节节败退。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更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那就是通过传教来宣扬欧洲文明,丑化中国,用扭曲的孔子形象来代替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大师,为列强进一步掠夺控制中国、扩张资本服务。
(二)翻译目的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7]在上述背景之下,传教士翻译 《论语》时就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那种欧洲优于中国的优越感注入到了翻译中,从而对 《论语》进行了基督教式的解读。
虽然作为不同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翻译《论语》的目的略有不同,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竭力从《论语》中找出基督教优于孔教的证据,证明基督教和上帝才是普遍存在的真理,让这个他们眼中落后无知的国度的人们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从而为耶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障碍。
马士曼选择翻译 《论语》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人揭开汉语的神秘面纱,从而为把西方尤其是欧洲强大的科学技术以及作为欧洲文化核心之一的基督教传到中国铺平道路。
高大卫在前言中说道:
" …it might perhaps be of some use to the Chinese who study English in the college,not only by assisting them in acquiring the English language,but especially in leading them to reflect seriously on some of the fatal errors propagated by their most celebrated sages."从中可以看出,高大卫翻译 《论语》是为了帮助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掌握英语,但他却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引导这些中国学生反思孔子这位至圣先师教诲中的致命错误,从而 “唤醒那些沉迷其中的异教徒”。[8]
理雅各也曾经说过:“我认为假若孔子的著作全部被翻译并注释,那么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将来的传教工作。”[9]在他们眼里, 《论语》已经成为一种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障碍,而要去除这种障碍,只有把 《论语》解读为基督教的附庸者,从基督教的角度来阐释 《论语》才有助于他们的传教工作。所以,从最初的马士曼和高大卫开始,他们的译文中就明显地充斥着对中国和孔教的不屑。
(三)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最能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持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既然传教士选择了翻译《论语》来实现自己传教并为列强服务的目的,那么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来服务自己的目的。
首先,他们都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评论性质的注释以及增译,试图用他们自身所持的态度来解读孔子思想,对 《论语》中所包含的儒家思想持加以批判,并对其中的一些核心观念进行否定,用欧洲思想的术语来束缚思维,从而最终影响到读者的接受。
《论语·述而》中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马士曼译文:
Chee says,Virtue ceases to preserve its possessor from evil;he who applies to learning,converses not(thereon);he who hears the instructions of virtue,seems unable to advance in knowledge;and the wicked appear unable to change their course!These things overwhelm me with sorrow.
其实这句话应当看作是孔子的自谦自励,因为他意识到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对世道人生的一种期冀。但是在马士曼看来,孔子的学说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因此他在译文后面的评注中说道:
"The sage had long persevered in his affectionate and laborious attempts to instruct men in the knowledge of their duty;and at length laments the almost complete failure of his endeavors."[10](孔圣人一直热情不倦地教导人们做人的责任,但最终哀叹自己的努力几乎完全失败。)经马士曼的评注,孔子的 “异端”学说在中国已经是到了穷途末路。这样一来,中国人已经可以不需要孔子了,而是需要基督教来播撒福音,光耀四海。
而在高大卫的译本中,指出孔子的儒教存在不足之处并加以批判或嘲讽的注释多达24 条,仅有3条注释对儒家学说表示了认可。[11]从这一数字对比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传教士对于中国经典文化的鄙夷与不屑,那么读者在理解孔子的学说时便会不自主地从译者所传递的信息中捕捉到一些影响原文理解的主观性评价,从而影响到对孔子的客观理解。
《论语·里仁》(4.8):“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高大卫译文:
Confucius says,if in the morning you hear divine truth,in the evening you may die.[8]
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能在早上实现自己一直坚守的政治理想 (孔子一直追求的仁者爱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在晚上死去也是心甘情愿的。这与孔子一直主张的仁政是息息相通的。但是高大卫却无知地认为孔子此处所说的“道”跟基督教的神圣教义是相通的,于是他在评注中说道:
"Nothing can be more foolish or injurious,than for a man to believe principles merely because his forefathers have adopted them……Had Confucius heard the Gospel of Jesus,is it not likely that he would have joyfully embraced it?"[8](仅仅因为古代圣人采纳过某些原理就对他们深信不疑,这真是愚蠢至极……假若孔子听到过《福音书》,他会不会喜笑颜开地信奉他?!)
相比之下,理雅各的注释评论中对孔子儒教的批评则稍显克制和含蓄。但他还是提醒读者要把《论语》跟 《圣经》的某些章节比照阅读,以从对比中发现孔教的弊端,进而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性和耶稣的至高无上。对孔子的一些观点他同时赋予了其宗教内涵和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其沟通耶儒的用心也不言自明。
其次,传教士在翻译 《论语》时所采用的又一翻译策略是对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做基督教式的解读,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数对于 “天”、“神”等关键词的翻译。
《论语·述而》 (7.22):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马士曼译文:
Chee says Heaven hath implanted integrity into me:What is Hoon-khooi to me?(i.e.What can he do to me?)[10]
高大卫译文:
Confucius said,heaven produced virtue in me,what can Kwan Tuy do to me?[8]
理雅各译文:
The Master said," Heaven produced the virtue that is in me Hwan T'ui-what can he do to me?"[9]
孔子所说的 “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神性,但是很显然,此处的 “天”被三位译者不约而同地当成了基督教文化中的“Heaven”,而这一意象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是并不存在的。
所以在 《论语·泰伯》 (8.19),当孔子赞叹:“唯天之大,唯尧则之”时,理雅各就给出了这样的评注:
No doubt,Yaou,as he appears in Chinese annals,is a fit object of admiration,but if Confucius had had a right knowledge of,and reverence for,Heaven,he could not have spoken as he does here.Grant that it is only the visible Heaven overspreading all,to which he compares Yaou,even that is sufficiently absurd.[9]
他认为孔子谈 “天”实在是荒唐可笑,而高大卫也认为孔子的言语实在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blasphemous)。[8]
此外,对于 《论语》中的另一关键词 “神”的翻译,传教士也是给出了基督教式的解读。
《论语·八佾》(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马士曼的译文:
Worship as the deity were(present);worship the deity as though he were present.[10]
很显然,此处马士曼将 “神”翻译成了“deity”。而 “deity”在基督教中正好是指造物主、上帝 (“the Creator”、“the God”),那么马士曼选择如此翻译便是别有用心了。
而高大卫更是直接将 “神”翻译成了“Gods”,因为他从孔子的作品中总结出了一点:“His works afford sufficient proof that he believed in'Gods many and Lords many'”。[8]理雅各稍有不同看法。他把 《论语》中出现的 “帝”或者 “上帝”翻译成了 “God”,因为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对于 “神”他选择了"spirits/spiritual beings"。所以理雅各把此句翻译成了:" He sacrificed to the dead,as if they were present.He sacrificed to the spirits,as if the spirits were present."[9]在理雅各看来,孔子所说的 “神”根本无法与 “上帝”相提并论,顶多也只能算是耶稣门下的一些小 “spirits”而已。理雅各对于孔子的儒教的鄙夷之心以及对基督教的顶礼膜拜由此便可窥见一斑。
除了 “天”、“神”这些关键词之外,《论语》中还有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仁” (109次)。作为“《论语》及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7]“仁”代表了儒家思想最精髓的东西。在 《论语》全书中,除了个别几处孔子用 “仁”来表达一种具体的德行,如 《论语·里仁》之二:“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处孔子将 “仁”和 “知”放在一起作对比。而在大多数章节,“仁”是通指一种完美的德行,是一种道德情感。三位译者将“仁”翻译成了 “benevolent actions”、“benevolence”、“virtue”、“the good”、“virtuous principles”、“the virtuous”等。当然由于中文词义的不确定性,对于 “仁”的翻译不可能有一个统一通用的词汇贯穿全书,译者给出不同的翻译无可厚非。但是此处译者的译文中最为明显的便是采用“benevolent actions/benevolence”这一多见于基督教文化并被赋予基督含义的表达:博爱、仁慈、乐善好施。通过这种策略,他们可以将其改造成为一种宗教情感,进而找出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无异于基督教文化,而是与其相通的证据,从而突出儒家学说与基督教的天然吻合性。
当然,上述例子仅仅只是传教士有意曲解误读孔子哲学思想的一小部分,在他们的译本中,到处都充斥着对孔子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偏见,他们都刻意忽略了 《论语》中所蕴含的哲学含义,仅仅是简单地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加以解读,最终呈现给读者的便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卑微,那么读者对于源语文化中所承载的客观真实的文化内涵便无从理解。
其实,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孔子儒家思想的篡改并非只是个人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一种有意。他们选择居高临下地用自身的文化为依托、以自己的文化价值为标准来解读甚至歪曲别国文化,正是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致。学者侯且岸就注意到了一点:“人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赞美,也看不到像早期耶稣会士那样对中国较为真实的介绍,所看到的只是在外部冲击下每况愈下的、落后的中国。他们鄙视中国的落后,试图以西方为榜样来改造中国。”[12]这也正是19世纪的译者翻译《论语》时普遍持有的一种文化态度。
三、结语
当然,我们指出这些译本的局限性和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非是要否定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相反,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得益于19世纪传教士的翻译,中国经典文化中的精粹才被带出国门,走到西方世界,让西方人对儒家经典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而且,由欧洲中心主义带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对于理雅各的影响已经不像之前的译者那样彻底的负面消极了,他的译文中尽管包含着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子,但是后来他也逐渐意识到了孔子及其 《论语》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孔子思想的深刻价值,并在自己的译文中逐渐摆正了心态,比起之前的译者来说对孔子的解读更为客观一些。因此,整体看来,从20世纪开始,众多译者也开始意识到了文化多元主义态度在文化交流活动中的重要性,在翻译活动中能够尽量撇去文化冲突对译者的影响,力求做到客观公正。虽然由于中外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也正因为此,《论语》的英译才具有了相当大的开放性,并且随着更多英译版本的出现,孔子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也变得更加丰富、深刻、生动,更具有内涵,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魅力也将更加熠熠生辉。
[1]程钢.理雅各与韦利 《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 [J].孔子研究,2002 (2):17-28.
[2]陈旸.《论语》三个英译本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探索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 (2):49-52.
[3]Alatas,S.F.Eurocentrism and the Rol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J].The European Legacy,2002,7 (6):761.
[4]Karenga,M.Introduction to Black Studies(3rd ed.)[M].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Sankore Press.2002:46-47.
[5]E.L.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M].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1981.
[6]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65-566.
[7]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59,153.
[8]Collie 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Malacca: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28:3,20,23,86,103.
[9]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Ⅰ):25,178,233.
[10]Marshman Joshua.The Work of Confucius.[M].Serampore: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1809.xxxiv:67,471,520,562.
[11]儒风.《论语》的文化翻译策略研究 [J].中国翻译,2008 (5):50-54.
[12]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 [C].国际汉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