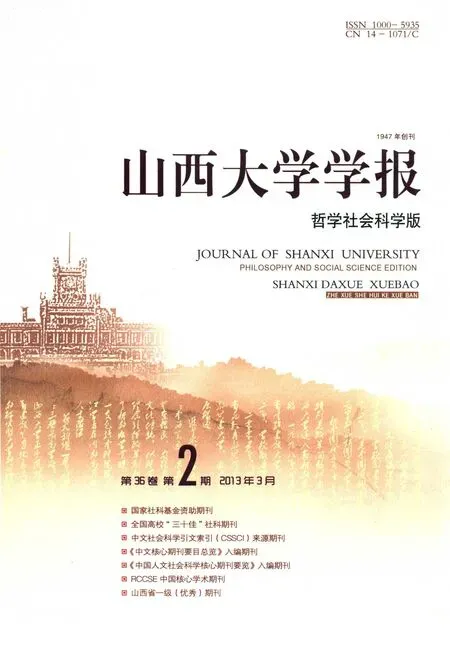战国数术发展初探
邵 鸿,耿雪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数术(术数),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文化事象。它是建立在察象推数基础上的吉凶占卜之术,包括卜筮、占星、占梦、相术、风角、时日、星命、风水、拆字等诸多形式。数术脱胎于上古巫术,但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因而可以视为巫术在中国的一种特殊发展形态。①关于数术的内涵以及巫术和数术的关系,学术界意见不一,对此笔者将另有专文讨论。数术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战国是中国数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本文就这一时期数术发展的表现及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 战国时期数术的勃兴与转型
李零曾将中国传统方术划分为三个系统,即:与天文历算有关的星占、式占系统,与动物和植物之灵崇拜有关的龟卜、筮占系统,和与人体生理、心理现象、疾病、鬼怪有关的占梦、厌劾、祠禳系统。②李零使用的“方术”一词的内涵比数术更为宽泛,大致包括了古人所谓的数术和方技两方面的内容。参见《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81页。宋会群则提出了术数五原生系统,分别是:1.星占、式占;2.卜筮;3.厌胜、相术、梦占;4.形法、风水;5.杂占。[1]19这两种分类是否合理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古代,诸如卜筮、星占、占梦等数术有着悠久的历史。③参见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第二章《开辟鸿蒙——原始社会的术数文化》。商代西周时期,数术应用有所发展,基本形式渐有增加,国家机构中形成了庞大的数术职官——史官集团,数术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长期发展基础上,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二百多年间,中国数术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大发展时期。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其实,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秦汉数术形式,大多直接承自战国。无论从形式还是本质方面来看,战国都是中国传统数术的重要奠基期。战国数术的迅速发展表现在:第一,数术种类激增。战国时期,在古老的卜筮、星气、梦占等数术之外,原先尚不显著的风角律占、相术、式占、时日、形法等数术形式得到较大发展,有关记载大量出现。特别是新起的建除、丛辰、堪舆、刑德、孤虚、遁甲、太乙、纳音等各种时日宜忌选择之术尤为繁盛,④此类数术之盛,从考古发现的多种《日书》中可以得到证明。比如仅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建除术就有四种之多(参见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见《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其时时日选择类的术家之多和分孽之众可知。最早的遁甲、太乙、纳音术出现于战国,据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见同上书。大有超越传统卜筮数术地位的势头。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杂占之法出现,如:人字占、艮山图(均见云梦秦简《日书》)、神龟占、博局占(见尹湾汉墓所出木牍及北京大学藏汉简《六博》)、筳篿(《离骚》)、荆决(北大藏汉简《荆决》)、蠡卜(《春秋后语》)、手相(《韩非子·诡使》)等等,可谓层出不穷。战国是数术勃兴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看不到可与之相比的时期。而且此后,战国新出数术中不少一直是中国传统数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战国数术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随着大量新型数术的出现,时人的数术选择范围大增:无论在占卜、择吉、释惑还是在祭祀、厌劾等方面,都有五花八门的数术足供各取所需;他们也可以选择延请专门术士,或是自行检阅《日书》之类书籍解决问题,即使是使用《日书》,其中也提供了诸多不同的选择。《史记·日者列传》载汉武帝娶媳,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不吉,太一家则说大吉,“辩讼不决”。这正是在数术多样化背景下才可能出现的戏剧性场面,而这种情形,其实在战国时期就应已出现了。
第二,传统数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繇)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此文历来无有达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战国时龟卜、筮占和占梦这三种数术各有若干家并行于世,自成体系,繁复细密。①三兆,郑玄说是“上古以来,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又引杜子春说分别为帝颛顼、帝尧和周人的龟卜之兆。三易,郑亦引杜子春说:“连山,宓戏。归藏,黄帝。”三梦,郑玄则说是夏、商、周三代的占梦之法。但从目前掌握的《归藏》和《周易》的情况看,三易乃是同时存在的不同蓍占之法,而非分属三代之法。《左传》中有不少筮占之辞不见于今本《周易》,学者认为其并非《周易》(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第一章《筮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他的三兆、三梦,以及《仪礼·士丧礼》曾提到的夏商周三祝,应该也是如此。
更典型者为天文占。春秋以前的天文占主要局限于日、月、岁星、大火、彗星等少数天体及云气之象,随着天文历法知识的进步,战国时期其范围要广泛得多。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和《五星占》证明,战国星云之占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而且分类和占断极为繁复,如仅彗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种名称,“气象”(云气)亦有多种,每一图形下均有吉凶占文。更为关键的是,战国模拟人世的星官命名体系的完成,二十八宿的确定以及分野说的进一步发展,为天文占的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学理基础。此外如虚拟太岁的出现并广泛应用于纪年和星占、时日占、式占和形法等,对星辰群聚(如三星聚、四星聚、五星聚)、五星入日月等多天体关联占断等,也都充分反映了战国天文占的创造和发展。
第三,数术著作大量涌现。商代西周之时,受经济、社会条件制约,文献著述很少且均藏于王室和贵族之家,数术文献当亦如此。至战国则已完全不同。《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皇家图书596种13 269卷,其中归属数术的图书多达190种2 528卷,以种数论,数术书占全部书籍的30%。②此据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按刘乐贤以此为“数术略”六类数术著作的数字,另外再加上阴阳家21种,兵阴阳家16种,则总数达到227种,比例高达38%以上。但这一数字是按照《艺文志》自己的说法统计的,今检《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实有书110种,再加上可归入数术的阴阳家21种、兵阴阳家16种、易13种,总计为150种,约占全部书籍的25%。这些书籍较大部分属于西汉著作,但先秦之书也有一定比例。最多的是记载较为翔实的“诸子”之阴阳家,所收21种著作中至少有15种为战国文献,几近四分之三。另据骈宇骞2006年统计,考古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数术类书籍,计天文6种,历谱22种,五行24种,蓍龟3种,杂占11种,③见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lanmu2/mlh.tm仅此即达73种,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数术书籍的三分之一强,且绝大多数不见于该志。这一统计还不包括其他出土文献中含有数术内容的部分,比如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竹简本《孙子》、《孙膑兵法》、《六韬》,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竹简本《盖庐》等书,都包含有多少不等的兵家、阴阳家文字。诸多考古发现的数术文献,应有相当比例属于战国古书。江陵张家山所出汉初《史律》规定:学卜之童,“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三万”,指卜书三万字,足见当时此类书籍之多,这和考古发现完全吻合。可以断言,战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著述高峰期,同时也是第一个数术文献创作的高峰期。
数术文献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社会上知识阶层广泛进行相关研究、创作和传播的产物,因而其不仅是战国时期数术显著发展的突出表现,本身又是推动数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四,数术在民间普及流行和简便化。春秋战国以前,民间已存在数术活动。《诗经·小雅·小宛》:“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榖。”此即西周村落小民为讼事占卜的事例。但我们根据《尚书》、《诗经》等古籍记载和数术的实现条件可以推测,当时民间更流行的可能还是一些简单巫术,而龟卜、筮占、天文云气占等数术占候形式,则主要为王公贵族所掌握和运用。然而到了战国时期,有关民间数术活动的记载大量出现,数术活动在民间已经非常流行和普及。如我们后面将论及的,当时数术活动已成为民间基本职业构成,民众可以方便地获得多样化的数术服务。
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诸多考古所获数术文献,不仅出土地点广泛,而且不少出自小吏或庶人墓葬,如著名的云梦睡虎地《日书》,其墓主喜只是县的令史,九店楚墓《日书》的主人也是一位平民或小吏。[2]23,42值得注意的是,《日书》这一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数术书籍在相关出土文献中为数最多,迄今已达17种以上(出于楚墓1种,秦墓8种,汉墓8种)。①骈宇骞《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数术略)(下)》,见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lanmu2/mlh.tm这些都表明,数术活动显然不是官府、贵族及其祝宗卜史的专利,而在民间普遍流行。[3]当然,当时的社会上层也在使用《日书》,西汉《日书》不少出于王侯贵族墓葬(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墓、长沙马王堆三号軚侯墓均出有《日书》或类似文献②汉代史书中也有此类的例子:如武帝娶妇聚集诸家术士中有“历家”一种,刘乐贤指出可能就是用《日书》类书籍选日的术士(见《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26页);又如文帝时贾谊在长沙,有服鸟入舍,“发书占之”(《汉书》本传);两汉之际刘秀大将吴汉平蜀,公孙述“视占书,‘虏死城下’”(《后汉书》本传)。),但显然,商代西周时期王公贵族在拥有和使用数术方面的绝对优势,战国时已有显著改变。
数术在民间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后果,因而也是突出证明,是战国数术出现了明显的简便化趋势。《日书》的出现和流行,本身就是一个例证。《日书》“勿需借助龟甲蓍草等外在手段,时日吉凶,载之于书,临事查验,一翻即得”,[2]71这是它在战国社会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它仍有不够方便的地方,所以后来逐渐为“具注历”和“黄历”替代)。此外如蓍法对龟卜的逐渐取代,数字卦改变为卦爻,以及“人字”、“艮山图”和“神龟占”之类简单图式占断的出现及流行,亦为其具体表现。民众对数术的功利化态度和对数术服务效率的追求,都必然使数术形式向方便快捷的方向发展,这是数术史的一条规律。③以易占为例,从数字卦到卦爻,从蓍草起占到算筹起占,再到后来的金钱课、木丸筮、数物起卦等等,清楚地体现了简单化的规律。战国时期有些数术喜欢以“须臾”命名(如《日书》有若干不同内容的“禹须臾”),④还有的虽未冠以“须臾”字样,但显然亦属同类,如周家台秦简《日书》中有:“有行而急,不得须良日,东行越木,南行越火,西行越金,北行越水,毋须良日可也。”《后汉书·方术列传》有“须臾”术,可能与先秦的须臾术有关。强调其术简便快捷,正是这一心理和规律的绝好反映。简便化是数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它和市场化趋势一起,赋予民间数术以灵活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数术阴阳五行化。商代西周时期数术已出现了某种数字化发展趋势,最典型的例子是从商代数字卦到《周易》的发展。⑤李零论《周易》说:“它虽然也讲象,但主要是一种数占,即以策数定卦象,卦象定吉凶,象生于卦,卦生于数,主要还是取于‘数’。古代占卜发展到这一步,才比较明显地有了推算的形式和逻辑的形式。”见《中国方术续考》,第88-89页。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并有决定性的变化。在“凡人神以数合之”(《国语·周语下》)意识的支配下,各种巫术和早期数术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数术转变。而其最突出、最关键的变化,则是阴阳五行化。
战国时期阴阳学说逐渐系统化,五行生克和配物也已成型,二者相互结合为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阴阳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概括阴阳家的核心是:“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最完整体现这一模式的,是《月令》类的文献。《月令》本有古老渊源,即《夏令》之类的政书,⑥《夏令》见《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语所引,记叙一年中不同时间国家和民众应做之工作。后来出现的《夏小正》可能与之有关。而从出土的《秦律》看,战国时期各国大致都已形成了制度化的月度政事安排。战国阴阳五行家将其学说和制度化的月事安排相混合,配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4]这种阴阳五行化的国家政事年历,最早见于长沙楚帛书,逐渐成型于《管子》之《幼官》、《四时》、《五行》等篇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十二纪”后来被汉儒编入《礼记》,改称《月令》。《月令》详细规定了君主、官府一年四季十二月中的行为规范,而其依据和原则就是阴阳五行的运行变化规律。对应于这个规律,统治者被要求“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吕氏春秋·仲秋纪》),如春夏多行仁政以利生长,秋冬可行刑用兵以应肃杀之类,否则必然导致灾异频发,社会动荡。《月令》是阴阳五行学说最基本的表现模式,阴阳变化的规律,五行与时空、事物的基本配合由此定型。因此,《月令》的出现是阴阳家和阴阳五行学说已经成熟的标志。由于阴阳五行具有辩证的理论思维和良好的推导性,因而对中国传统数术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其不仅为数术的推演和具体应用开辟了广阔道路,更规定了未来数术发展的基本逻辑法则。
正是在此背景下,阴阳五行学说已经在战国时期的各种数术上显著展开,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框架或打上鲜明印记。比如:龟卜以阴阳五行释其兆象,①《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孔疏引服虔云:“兆南行适火。卜法:横者为土,直者为木,邪向经者为金,背经者为火,因兆而细曲者为水。”《周礼·春官·龟人》:“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筮占卦画从传统的筮数转变为阴阳爻,②这一变化究竟何时发生,现在尚无定论(具体讨论的概述见晏昌贵《巫鬼与淫祠——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7-202页),但战国晚期阴阳爻画已出现是无疑的。《易传》开始用阴阳注解《周易》,释梦“辨阴阳之气”及用五色对应五行解说(《周礼·春官·占梦》),星占将五大行星(太白、岁星、辰星、填星、荧惑)以金、木、水、火、土重新定名并以此为占,云气之占亦以“五云之物辨吉凶”(《周礼·春官·保章氏》),风角律占将五音对应五行辨其属性(《六韬·龙韬·五音》),形法用五色生克论证地利(《孙膑兵法·地葆》),各种择日术多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而加以推演,杂占普遍以阴阳五行来解读各种罕见事物及其后果,祭祀亦讲究按照阴阳及五帝、五方、五色、五数等来安排进行,甚至为此建立与《月令》一致的明堂。于是,不仅刑德、孤虚、六壬、太乙、遁甲等新兴占候数术完全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五行家蔚为大宗,卜筮、占梦、星占等传统数术也都为阴阳五行所支配和改造。同样的变化,也显著发生在方技之学中,如中医学阴阳五行的基本理论模式就从此确立。此外,各种古老的巫术如求嗣、止风、辟邪、驱鬼、禳灾等也有逐渐阴阳五行化的趋势。[5]90-92,199 -200,307-30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秦汉以来数术尽管形式众多,但“要其旨,不出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这是很正确的。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数术史进入了阴阳五行时代,而和此前的阶段判然有别。战国是中国数术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殆无可疑。
二 战国时期数术大发展的原因
《史记·天官书》曾对数术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作出解释:“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工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按照这一说法,战国日益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灾荒疾病的流行,是最重要的导因。此说虽有一定道理,却未能揭示最重要和深层次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以下三个社会因素或条件更值得关注和重视。
一是战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刻变化,为数术的大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春秋晚期以来,原先作为社会基础的古典宗法制度和父系大家族趋于解体,个体小农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贵族世袭政治和天命观念被极大地动摇,新型国家和官僚制度逐渐确立,士人阶层逐渐兴起,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和水平流动性显著增加。在“三姓之后,于今为庶”的同时,大批士人游行各国以布衣骤登庙堂而显贵,洛阳小市民苏秦甚至一人而能佩六国相印,加之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展开,以及商品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逐渐失去宗族保障的战国民众面临着越来越不确定的环境和命运。因此,战国时期的人们对于“凶厄之患,吉隆之喜”的占测趋避的需求更加迫切和广泛,从而对数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需求和拉动力量。
二是战国思想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数术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随着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逐渐兴起和自然科技知识的进步,战国时期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规律和技术手段,就可以获得改变和役使外物的能力,从而改善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最乐观自信者如荀子,甚至意气满满地喊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荀子·天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试图通过数理和逻辑而非鬼神的方式来探求认识和把握命运和天道的奥秘,循数而知天,是很自然的事情。用《鹖冠子·世兵》的话来说是:“道有度数,故神明可交”。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的探索走上了较为符合科学的道路,有的则走向了超自然的神秘主义,数术总体上属于后者,但也包含了一定的科学内涵。显然,没有战国时期的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也就不会有数术的巨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数术并非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它的思维逻辑仍然建立在象征和模拟基础之上而与巫术并无本质区别,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数术较之以崇拜鬼神为特征的中国上古巫术传统是一种进步。
三是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数术的大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这一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盈利性的数术业者——“诸医方食技术之人”(《史记·货殖列传》)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职业群体。其多在市场中执业,小者足以自食其力,大者可以致富厚身。①参拙著《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第四章第五节《“食技术”的知识职业群体的产生》。这些人的收益情况,可以从下面故事中得到证实:墨子曾问弟子,家居和出蓍的“善蓍”者“其糈孰多?”弟子答:“行为人蓍者其糈多”,又说良巫就是在家里,也有余糈。(《墨子·公孟》)《庄子·人间世》描述一残疾人先是“挫针治繲”经营手工业,仅仅“足以糊口”;转而“鼓策播精”,卜蓍占卦,竟“足以食十人”。此尚为其小者,一些大家如相士姑布子卿、唐举之流,出入权门,收入必更可观。《战国策·齐策一》载齐公孙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卜资可观。所以《韩非子·解老》曾把“卜祝之富”与陶朱、猗顿等富商并举。于是,巫数方技日益成为市井基本职业,民众的各种数术需求可以日益方便地通过市场得到满足。“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史记·货殖列传》)在市场生存和竞争压力下,他们必须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和服务水平,这就推动了各种数术方技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在民间逐渐兴起,其规模最大和影响最著者,当属孔子门下累计有三千之众,墨子之徒“服役者百八十人”(《淮南子·泰族训》),可见私学的发达和普遍。私学赖学费而生存,颇具专业分工的特点,诸子百家,皆有传习,师生在其中传播、研究和创造各种知识,乃至于有邓析教诉讼、弈秋教弈棋,支离益教屠龙之技等,②分别见《吕氏春秋·离谓》、《孟子·告子上》、《庄子·列御寇》。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数术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民间数术展现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反之在官府方面,由于其数术活动的礼仪性、行政性和非经济性,注定了其僵化、低效的基本特质,与民间数术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体制机制和传统约束的不同所决定的这种差别,在后世还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③这一现象到秦汉以后表现得更加清楚,秦汉以来,各种新生数术多属私人创获,而国家则屡屡向民间征集方术之士及巫觋入朝服务。宋明时代,国家钦天监等机构的人员素质能力之差,更是广受诟病。参拙作《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宗教——以术数为中心的考察》,《国学论坛》(第一辑)。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晚期以来有很多周王室数术官员流散民间的传说。《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三饭缺适秦,鼓叔方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人士均为乐官,而乐官的职掌与数术有关。④乐事不仅是各种祭祀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所谓“乐以和神”,而且还与风角音占有关。《周礼·春官·大大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国语·周语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韦昭注云:“瞽,乐太师,掌知音乐风气,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所出风角书《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亦可为证。(参见连劭名《银雀山汉简〈五音之居〉与古代的风占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论律云:“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合,然后可同也。”声和数都是人神交接的关键,因而合神必须音乐,音乐可占吉凶。事实上,中国古代以音乐通神占候有着久远的历史。更著名的,则是身为周室典藏史的老子出关而著《道德经》。一些论者如葛兆光先生把这种“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变化作为诸侯和民间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有学者认为方术之学本系“明堂羲和史卜宗祝”所职掌的“王官之学”,这一时期“下潜民间,演变为民间‘小传统’,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信仰和诸子百家共同的知识背景”。[2]3但我们以为,至少在民间数术的发展问题上,对此不能给予太高评价。这是因为,即使这些传说是真实而普遍的,天子数术之官所带来的也并非新的知识。真正重要的动力,还是来自市场化条件下民间数术活动具有的生机活力。①参拙作《战国民间的巫觋术士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还可以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后代例子:宋代以来,江西的赣派风水师,公认其祖师为唐末窃禁中秘术南来的国师杨筠松。此人半神半人,在正史中毫无影踪,朝廷的正统数术官员也绝不可能创造出新型堪舆术来。所以,杨不过是江西风水师为了自神其术而创造或者托附的人物,我们当然不能以此来论证是因为“天子失官”而导致了“学在四夷”。
四是阴阳五行理论的确立,为数术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平台。和巫术知识是零散、习惯的因而虽可传承却难以推拓发展不同,阴阳五行学说深具哲学思维和数理基础,因而有较强的自我推拓发展能力。阴阳理论符合事物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现代哲学原理,对于自然界变化规律——在农业社会中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太阳回归年的规律——不失为一个颇具合理性的描述和解释框架;而五行及其生克规律,则为概括复杂物质现象,逻辑推演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提供了似乎较为严密的分析推导工具和广阔认识空间。从阴阳对立演变和五行生克出发,将其与各种事物相联系,很容易推导出一系列数术认识和结论,并形成包罗万象、逻辑严谨的数术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它和古希腊数学家在很少几个公理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出整个欧几里德几何学公式体系很是相像。它的逻辑性、理论性和严密性已远非巫术所可比拟,阴阳五行一出,不仅古老的巫术,就是各种新出数术都不能不依附其下,原因就在这里。李零先生认为:“古代占卜,本来是各自独立发展,放到一起用,往往会相互撞车。战国秦汉,数术发展的大趋势是,各个占卜门类交叉影响,开始趋同,追求体系的整合。阴阳五行学说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②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整理说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年。这一见解,可谓慧眼独具。
总之,战国时期数术的巨大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其既有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这里简要指出,以供讨论。
[1]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2]晏昌贵.巫鬼与淫祠——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晏昌贵.简帛《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研究[N].光明日报,2006年7月10日.
[4]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M]//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吕亚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