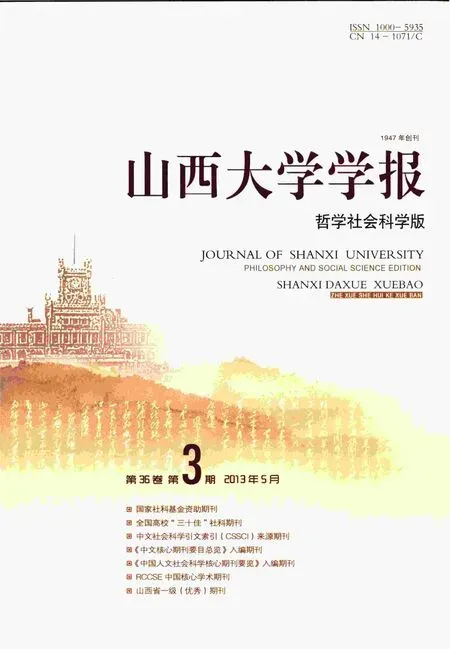女性在城市非场所中的现代性经验——里斯《早安,午夜》研究
尹 星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1966年,简·里斯发表了长篇小说《藻海无边》,确立了她作为经典小说家的地位。1970年以后,后殖民文学研究掀起热潮,这部小说便作为后殖民文本而受到批评界的青睐,评论、阐述和译介纷至沓来,也淹没了里斯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一面。里斯于1928-1939年间创作了四部现代主义小说①依照创作顺序这四部作品分别是:《黑暗航行》(Voyage in the Dark,London 1934),《四重奏》(Quartet,London 1928),《离开麦肯泽先生后》(After Leaving Mr.Mackenzie,London 1930)和《早安,午夜》(Good Morning,Midnight,London 1939)。,对于理解作者的全部创作思想和风格举足轻重,但却始终遭到冷遇,《早安,午夜》(Good Morning,Midnight,1939)就是其中的一部。小说生动展现了一个外来女性在都市夹缝中寻求生存、无法摆脱困境的幻灭之旅,展现了边缘化他者在都市商品社会的消费环境中的尴尬境遇。在叙述女主人公颠沛流离、游走于伦敦、巴黎街头的冒险经历时,小说描写了都市里走不通的死巷,千篇一律的酒店房间,充满敌意的咖啡馆。这些场所见证了女性在城市里孤寂无助的游荡生活,突出了女性在现实和记忆中无法改变的他者和边缘地位,同时又激发了她们对城市生活的精神感知和意愿性记忆。根据城市文化研究理论,城市里居家生活以外的空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生成的场域[1]297,那么,这些非场所就不仅仅是体现城市布局的物理空间,而且是体现城市消费政治、文化建构和性别差异的文化空间,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经验得以形成的场所,因此,非场所的现代性体验与城市里每个个体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一 街道:作为城市迷宫的非场所
西美尔在《大都会和精神生活》中分析了都市性格的心理基础,认为它是由内部刺激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构成的。[2]132这种变化着的刺激和印象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张力,都市人就生活在这种张力之中。《早安,午夜》的主人公萨沙·简森为了忘却伦敦给她留下的痛苦记忆而从伦敦来到巴黎,实施她的“转型计划”,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地点的变化并不等于经验的变化。在现代环境中,不同城市的心理基础是相同的,它给都市人的刺激和印象也是相同的。无论走到哪里,现代城市空间的场所效应并没有改变。对于游走于城市之间、不断变换生活场所的萨沙来说,城市的每一个景象都能勾起她的痛苦回忆:巴黎童年、伦敦岁月、幼儿夭折、丈夫出走等阴影像鬼魂一样缠绕着她;日渐衰老的容貌,现已狼藉的名声,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令她蒙受社会环境的排斥和异化之苦;而穿梭于非场所之间的那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更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她,使她在孤寂和幻灭的双重打击下,在无奈的自嘲意识中,最后认识到了“(我)没有自尊,没有名字,没有脸面,没有国家。我不属于任何地方。”[3]370
按照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提出的新的空间概念,连锁旅店、假日俱乐部、难民营、贫民窟等过渡性地点和临时性居所,飞机、火车和汽车等运输工具,机场、火车站、主题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以及大型零售店、超级市场、咖啡馆、餐厅、自助取款机等消费场所,甚至利用非地面空间进行交流的有线和无线网络,都可以看做空间的非场所。这些场所提供的服务几乎是沉默的,在这些场所中活动的个体都是孤独的,他们在其中的生存也是昙花一现的。[4]18按此理解,街道无疑也是这种非场所之一,而在街道上漫步的一个个个体便成为昙花一现的孤独的存在。奥热认为这种非场所是超现代时期的产物,而实际上,本雅明于20世纪初就在19世纪巴黎的拱廊街上看到了这种非场所,并描述了跻身于街道的漫步者所体现的一系列辩证关系:他既隐身于人群、享受观察的特权,又游离于人群、保持超脱的姿态;既满足于无目的性的漫步,又用洞察一切的目光审视城市看不见的文本,捕获转瞬即逝的形象;既深受商品景观构成的形象世界的吸引,又用冷漠的精神态度和拒绝经济投入的实际行动抵制现代消费的诱惑。与超现代的非场所相比,19世纪巴黎的街道只不过缺少詹姆逊所说的“超空间”,构成“辉煌闪耀的城市”的玻璃摩天楼和高速公路尚未出现,但在其中活动的个体的孤独感和无方向感就已经存在了。
在里斯的作品中,萨沙行走的街道不是19世纪巴黎宽敞的林荫大道,也不是超现代空间里只供汽车行驶的高速公路,而是“鹅卵石铺就的窄街,陡峭地通向山顶上的几级台阶。他们所说的一条死巷”[3]347。萨沙在这些窄街中游荡。她的脚步是迷惑的、恐惧的、小心翼翼的。她投身于匿名的人群,而人群带给她的却是潜藏着杀机的巨大威胁。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但外界刺激时刻让她感到将其置于他者境地的敌意。她希望通过商品装饰的新形象改变环境,但最终无法应对消费市场的残酷规则和瞬息万变的时尚变迁,在瞬间的陶醉之后便堕入了残酷多变的梦魇。
小说一开始就给萨沙生活的外在社会空间罩上了一层氤氲:狭窄的街道、走不通的通道、紧闭的大门、关闭的入口、堵塞的出口,构成了一个没有出路的社会空间网络。“死巷”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典型意象,象征着萨沙在私有空间和社会空间里受到的无法摆脱的双重束缚。外来民族的身份、相对贫困的经济状况和不稳定的两性关系导致萨沙的内心世界也陷入了僵局,因此她想通过改变环境来摆脱困境,摆脱过去,摆脱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但过去总在梦中浮现,巴黎的窄街总会变成伦敦地铁里走不通的通道:“到处都是红色字母印刷的海报:此路通往展馆,此路通往展馆。但我不走通往展馆的路——我找的是出口。有向右的通道,有向左的通道,但没有出口的标记”[3]349。生活就是这样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城市就是这样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就连她曾经工作过的巴黎服装店也是由承载着各种功能的无数房间、上上下下的楼梯和不知通向哪里的走廊构成的一个迷宫,令她眩晕、恐惧,濒临崩溃的边缘。本雅明把城市狭窄的街道和无意识的愿望都说成是迷宫,都是欲望和恐惧的显示;而在超现代空间里,这种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建构迷宫体验的非场所更是无处不在。[5]269
二 梦境:作为城市欲望的非场所
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场域,还是作为超现代的非场所,城市空间都与个体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在西美尔看来,个体的精神状态取决于城市外在现实的刺激,而在本雅明和弗洛伊德那里,城市的秘密话语也就是城市隐藏的欲望和恐惧。现代心理学认为,这种隐蔽的欲望和恐惧只能在梦中才能显示。于是,城市就有了梦的性质,而梦也有了城市的性质。[5]270如伊塔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关于城市的描写:
她既无名称又无地点。[……]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能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者是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外一件。[6]44
里斯笔下的女主人公萨沙也生活在欲望与畏惧交织的梦境里,在白昼与黑夜、醒的时刻与梦的时刻的交界处,只不过她对自己所处的“梦境”似乎始终保持着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她的无名,她的无我,她的无自尊,以及她的无国度。她是被卷入都市生活漩涡的一棵稻草,任人践踏,随处漂流,直至消失。她无时无刻不受欲望的驱使,希望换一个新的地方,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尽享人生的乐趣,事实上,她来巴黎的目的就是要“安排自己微不足道的生活”,忘掉已往的贫穷和不幸。“吃饭。看电影。再吃饭。喝酒。步行回旅馆。上床。安眠药。睡觉。只睡觉——不做梦。”[3]351完美的计划,简单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深陷记忆的黑洞。然而,她无法不做梦。梦的黑洞就在那里,无法避开它,只要迈开脚步,她就会深陷其中。城市现代性让人经历的是异化,而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梦境。如汤姆森在《恐怖的夜之城》中所说:“城属于夜,却不属于睡眠。”[7]25不属于睡眠的夜是梦境,也或许是梦魇。它是孤独与城市密切联系而产生的异化,从严酷现实到梦魇的异化,而且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异化。萨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每更换一次场所,“未曾期盼的、非常不需要的”[3]434事件总会在那里等着她,把她抛回到她想方设法逃离的过去,重新进入那无处不在的恐惧,再度燃起不断重复而又不断破灭的欲望。无论走到哪里,街道都像幽灵一样缠着她。街道是作为里斯小说背景的“非场所”,它影射城市生活的千篇一律,城市面貌的千篇一律,以及街道和人群的千篇一律。在这个千篇一律的“非场所”中游荡的人是“神秘的女性,不可思议的、最彻底的波西米亚人,似乎不属于任何特定社会、没有根基、甚至找不到归路的女人,她所拥有的只是对地点的回忆,只是在都市里的漂泊。”[8]137
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街道已经四通八达,井然有序,但其陌生性仍然给萨沙一种梦的感觉。时尚大道和现代建筑对她毫无意义,非但不能用做路标,反而怀有恶意。如果你有钱有势,那些房子就欢迎你;如果你没钱没势,
……它们会敬而远之。然后扑上来,那些等待着的房子,皱紧眉头,把你压碎。没有好客的门,没有明亮的窗,只有皱紧眉头的黑暗。皱紧眉头、目光斜视、讥笑嘲讽的房子一个接着一个。高耸的黑色锥体,顶端两只明亮的眼睛在嘲笑。它们知道该
嘲笑谁。就和街角上的警察一样……[3]362
街道上的建筑对于行人的态度是有阶级性的:它们能够甄别有钱人和穷人,并对其持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街道上的房屋对待行人就像商店对待顾客一样,是以金钱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的:对潜在的买主,有钱人,它们满脸堆笑;对穷人,橱窗的浏览者,它们横眉冷对。萨沙对夜间街边建筑的这种反应虽然是她主观心理在外界环境中的投射,但也符合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逻辑。对于萨沙这种没有根基的女性漫步者而言,城市的街道危机四伏,她甚至无法用警惕的眼睛回视那些“皱紧眉头”的建筑:甚至“养成了低着头走路的习惯……在梦中、在朦胧中走路”[3]397的习惯。深夜里走在黑暗的街道上,怪物一样的黑压压的房子,没有灯光的窗,充满敌意的门,“皱紧眉头的黑暗”,“高耸的黑色锥体”,萨沙仿佛置身于一种无名的黑暗之中,一个由欲望和恐惧构成的梦魇,一条无论如何也走不通的死巷。它的主题词是“黑暗”。
生活中的“黑暗”就像地毯上的污点一样,或许可以免除,不被它们绊倒,但心灵的黑暗却是无法摆脱的。从伦敦到巴黎,她所改变的只是表面的时空环境,孤寂凄苦的记忆和不知所措的迷茫始终缠绕着她,贫穷压抑的城市生活和边缘化的民族身份挥之不去,她所能做的只是在没有出口的死巷里徘徊。城市经验对于萨沙而言就是危机四伏的外在环境和毫无出路的室内空间。而二者的相互交替强化了房间与街道的关系,同时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所谓室内私有空间独立于工作和社会劳动空间的幻象的本质。对于萨沙而言,二者是没有分别的。街道对于萨沙就是“喝,喝,喝。……清醒了从头再来”[3]369。而房间,“浸透着过去的……被诅咒的房间……。是我所睡过觉的所有房间,是我曾经游荡过的所有街道。现在整个世界都井然有序地、波浪起伏地在我眼前一幕一幕走过。房间,街道,街道,房间……”[3]411这是一个心理觉醒的过程。从伦敦那间可能使她酗酒致死的房间,到巴黎与“死巷”连成一体的房间,对一个来自下层社会孤独的女性漫游者来说,等待着她的似乎只有绝路、僵局、甚至死亡,使人陷入绝境的一种非场所。
三 室内:作为阈限空间的非场所
在这种情形下,城市里的个体生活就成了城市空间锻造的产品:“制定一个计划,严格按这个计划行事”[3]376,这就是城市生活。西美尔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了都市环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锻造。“准时、工于计算、精确是由于都市生活的复杂和紧张而被强加于生活之中的”[2]134。这种精确性和准确性已经构成了最缺乏个体性的生存形式,个体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与之完全妥协,失去自我,进入消极的自我隐退,甚至采取西美尔所说的厌世态度。萨沙试图在无依无靠、遍布荆棘的一条“死巷”里开拓“独立”的道路,但室内外环境却没有给她提供任何“独立”的机会:如果说街道给她提供的是危机四伏、充满敌意、处处走不通的“死巷”,那么,咖啡馆等室内空间所能给予她的也只有焦躁不安、彷徨无措和冷漠排斥。在这样一种时时处处充满恐怖色彩的环境里,她不得不依靠制定详尽的计划来把突发事件导致的紧张和恐惧感降到最低点。除了时间上的准确安排之外,她还必须严格计划活动空间,甚至连去哪家咖啡馆也必须认真考虑。
事实上,咖啡馆作为私人家居环境与公共街道之间的阈限空间,对于巴黎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18世纪起,街道作为商业和社会活动的集散地,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空间。进入19世纪,巴黎上层资产阶级的社会活动逐渐退回到沙龙、客厅、花园等更加私密的场所,将街道留给了下层社会。19世纪60年代的豪斯曼城市改造工程彻底改变了巴黎的面貌,中世纪留下的狭窄蜿蜒的小道被宽阔平整的林荫大道所取代,街道的主要功能也从社交场所转变为交通枢纽和要道。随着下层社会的社交转入咖啡馆,原本封闭受限的空间形式也有了街道自由开放的氛围。而新的高档咖啡馆也吸引了上层资产阶级再次走出自己的庄园客厅,走进延伸到人行道上的露天阳台,他们既可以在那里凝视和体验喧嚣的城市生活,又不必遭遇推搡拥挤的人群的难堪境遇。当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伦敦人还执著于安逸的家居生活和小范围的沙龙文化时,更多的巴黎人已经在半开放、半私密的咖啡馆里探索自我价值、体察社会生活的气息了。因此,咖啡馆、酒馆、饭店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场所,也就自然成了作家再现城市生活、书写个体和社会经验的典型环境。
然而,在《早安,午夜》中,人们去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却“不是来花钱喝东西的,而是来睡觉的。”[3]367随着空间功能的整体转换,来咖啡馆睡觉的人被异化为马戏团里“被耍的猴子”,仿佛一具具没有干枯的尸体,使本来就拥挤闭塞的咖啡馆弥漫着腐尸的恶臭。怪诞恐怖的气氛让萨沙“浑身血液变得冰冷”[3]367。一家“像门钉一样死气沉沉”的酒馆过去曾经卖英国菜,这两年又改卖爪哇菜了;(墙上)英国狩猎场的兴旺场面与酒馆无力扭转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萨沙扭曲的心理状态也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即使在天文台那家顾客很少的咖啡馆里,偶然间听到旁人抱怨自己生活的艰辛,也让萨沙陷入孤寂和凄凉的自我封闭之中。显然,城市生活的“工于计算”已经进入萨沙扭曲的心理,并通过主观臆想而投射出扭曲的城市形象来。
萨沙非常熟悉巴黎左岸的边缘环境,本能地感觉到周围人或接受、或拒绝、或冷漠的态度,并借此对公共空间进行划分,尽量选择相对不排斥自己的地方。“我的生活,看似如此简单、单调,事实上包含一系列复杂的事情,喜欢我的咖啡馆和不喜欢我的,友好的街道和不友好的,我感到幸福的房间和永远不会有幸福感的,我在里面看着好看的镜子和看着丑陋的,给我带来好运的裙子和不会带来好运的,如此等等。”[3]371这种详细的空间规划和对立的细枝末节,主要以友善亲密或敌意排斥为依据,尽量不选择能触发内在记忆的地点。她设计好的行动路线一定要避开“某些咖啡馆、某些街道、某些地点”[3]371,以确保自己不勾起对过去的痛苦回忆。“不要在脑海里开启廉价的留声机而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不要发出‘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的嘶哑声音。总之,不要当众哭泣,只要忍得住就千万不要哭泣。”[3]351
萨沙强制地关闭脑海中回忆的留声机,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将过去的经历归为不值一提的“廉价货”。但她这副看似冷静、超脱、甚至麻木的态度却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惧。她深知重返巴黎后一旦开启记忆的闸门,过去的时光就会重现,这对她本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活将是一种双重打击,令她无法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这体现了城市经验、也即本雅明所说的现代性经验的特征:欲望与恐惧之间的互动,以及意愿性欲望与无意识动机之间的明显矛盾。按照弗洛伊德释梦的观点,被压抑的欲望总会以梦的形式实现;或以伪装的形式潜藏在无意识之中,当受到外界条件刺激时,它们便以普鲁斯特的玛莱德娜点心的效应汇成无法抵挡的记忆洪流,往日的生活片段不断涌现,如此逼真甚至模糊了现实与过去的界限。甚至街道和房间也具有联想的功能,给予漫步者和漫步的地点以意义,驱动了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欲望:在意识的层面,她要忘记过去;在无意识的层面,她要回到过去。如德勒兹所说,记忆的踪迹就隐藏在感觉的褶皱里,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稍稍触动,记忆就会毫无保留地全盘展开。这里,个体活动的室内空间充当了储存和释放记忆的非场所。
四 记忆:作为现实空间的非场所
就在过去与现实、计划与想象的这种交替更迭中,萨沙非常艰难地实施着她的“转型计划”,结果就和她的分娩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痛苦的记忆经过严酷现实的洗礼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原点,她自己生命的灯火也在历史与现实、梦与醒交错的光柱之间徐徐燃尽。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咖啡馆、酒馆,冷酷的过去总是在记忆中向她袭来,镜子都会冷酷地折射出她无法逃脱的现实困境。镜子说:“上次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是吗?你相信吗?那些我照过的脸庞,我清楚地记得的每一个脸庞。我会留下她们的魂灵,下次再照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像回音一样把魂灵抛回去。”[3]448镜子把过去的形象投向现在。从单一的镜像反射,到多元的视角重叠,从静止的凝视瞬间,到流动的视觉回放,镜子不仅记录了主体当下的镜像,还改变了它的整个时空体验。
对萨沙而言,最明显的就是岁月流逝、红颜易老的感伤。因此,当男伴安慰她不必担心衰老的时候,这非但没有打消镜子对萨沙的打击,反而使她更加怀疑他的真诚。“我非常害怕男人,更害怕女人。整个人类都令我恐惧。”[3]450从短暂的情感沟通,到可悲的自怜,从对一个男人的抵触,到对整个人性的攻击,在阴郁情结中,萨沙想象出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所有这一切都毁了。一切都毁了。好吧,别为之哭泣。不,我不会为之哭泣……你们去相互撕咬吧,你们这群可恶的土狼,越快越好……就让这一切都被毁掉吧。就让它继续吧,让冷酷的疯狂结束吧。让这一切都发生吧。”[3]451
末日景象甚至抹杀了萨沙对具体地点的感知,把她带入无名的黑暗中,“就在五分钟前我还在‘双蛆咖啡馆’,穿着那件难看的廉价的黑裙子,谈论昂蒂布,现在我却躺在了漆黑的痛苦之中。独自一人。鸦雀无声,没有触感,没有双手……我还要在这里躺多久?永远吗?不,这次只要几百年而已……”[3]451黑暗淹没了过去的记忆和眼下的现实,可怕的静止会持续几百年。可怕的是,虽然对地点的感知已经失去,而时间却依然流逝,仿佛爱伦·坡笔下被塞进坟墓的活人,他只能在完全的孤寂中无声地等待着末日的降临,这显然比生命的彻底泯灭更阴森恐怖。
如果说普鲁斯特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从记忆和遗忘中编织出栩栩如生的生活,并把那种生活融入自己的日常现实之中,致使生活本身成为艺术,那么,里斯的最大成就也许在于她把生活的现实、对生活的痛苦记忆、痛苦之余勾画的未来梦想,以及梦想破灭给她的毁灭性打击全都融为一体,进而编织出一幅千奇百怪的超现实主义图景。本雅明写道:
对于回忆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忆编织出来,与其说是那种佩内洛普式的追忆的劳作,倒不如说是佩内洛普式的遗忘的劳作。但非意愿记忆,即普鲁斯特所说的mémoire involontaire(不自觉的记忆),不是更接近遗忘而非通常所谓的回忆吗?在这种自发的追思工作中,记忆就像经线,遗忘就像纬线,难道这不是与佩内洛普的工作相等而非相似吗?在此,白日会拆散黑夜编织好的东西。[9]216
里斯将自己从西印度群岛到欧洲大陆复杂多彩的生活经历,编织进萨沙这个落魄潦倒、脆弱无助的边缘女性在街头的漫步和在非场所的驻足之中。她投身于匿名的大众文化,在街道、酒吧、咖啡厅的杂乱人群中打发无家可归的凄凉。她随陌生男子步入巴黎左岸或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的酒店,在虚幻的怀抱中感受转瞬即逝的温存。她流连于衣帽店、电影院和展览馆,在物质和消费的快感中填补精神的空虚。“里斯的小说代表了为满足基本生存所需而必须付出的超越道德底线的努力。城市的边缘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里斯:她对那些污秽的东西深感恶心,但同时又无法抵御它”[10]13。
里斯,就像她笔下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女性漫步者一样,深入街头的人群,采撷生活、记忆的片段,用意识流、戏仿、讽刺等现代主义小说技巧,从不同于上层社会、统治阶级、男性他者的视角,在文本的幻象世界里再现纷繁复杂、气象万千、意义纷呈的城市经验。如果把萨沙从伦敦到巴黎的旅行,特别是她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在两座城市的非场所之间的穿梭游荡,看做身处社会边缘的女性他者的生命之旅,把象征着生命的白昼看作欲望的噩梦,那么漫步者在噩梦醒来时所意识到的就是一种幻灭,一种对寻求独立自主的自我身份的幻灭,对都市消费文化带来命运转机的幻灭,对冷漠无情、利欲熏心的普遍人性的幻灭。边缘女性无法逃脱死巷的尽头,只有无名的黑暗、永久的午夜,那是痛苦的记忆与严酷现实相纠缠的梦魇,也是躁动的欲望和隐蔽的恐惧构成的罪恶渊薮。对边缘女性漫步者而言,真正的觉醒就是告别清晨、回归午夜。她真正的生命归宿是只有在午夜才大放异彩的城市的非场所。因此,与其说里斯在小说中诉诸自我记忆和意识,不如说她的记忆是从自觉向不自觉、从有意识向无意识、从现实向梦境的回归,是从追忆的劳作转向遗忘的劳作的过程,而就在这种遗忘的自然回归中,在悲观的末世主义情绪中,边缘女性的城市现代性经验也随之展现出来。
如果说本雅明的漫步者为后世提供了研究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历史事实,为探讨城市现代性叙事提供了一个内在的隐喻形象,那么,里斯/萨沙交织着记忆与现实、梦幻与想象的游荡的脚步,就为我们提供了解构现代性神话的他者洞察力和想象力。把从殖民地到欧洲大陆的边缘女性看做城市漫步者,就等于站在种族、阶级、女性的十字路口,从模糊、矛盾和辩证的角度,捕捉现代性纷繁复杂的日常经验。作为边缘人物,里斯和她笔下的人物都以“行走”这种基本的城市经验方式对城市进行“空间化操作”,用流动的身体、错综的道路和嘈杂的非场所讲述“既无作者也无读者的多重故事”[11]165。在这个故事中,个体的意识经验与城市的街道景观不断发生碰撞,激发出忘却与记忆、欲望与幻灭、梦幻与现实相交织的动态辩证的戏剧。
[1]达夫妮·斯佩恩.空间与地位[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5-305.
[2]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2-141.
[3]Jean Rhys.Good Morning,Midnight[M]//Jean Rhys:The Complete Novels.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1985.
[4]陈永国.超现代时期的空间非场所[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6-20.
[5]史蒂夫·皮尔.现代城市里的梦游者:梦境中的瓦尔特·本雅明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5-276.
[6]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 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7]Anne Ridler.Poems and Some Letters of James Thomson[M].London:Centaur Press,1963.
[8]Deborah Parsons.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Women,the City and Modern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9]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10]Helen Carr.Jean Rhys[M].Plymouth:Northcote House,1996.
[11]米歇尔·德·德塞都.城中漫步[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