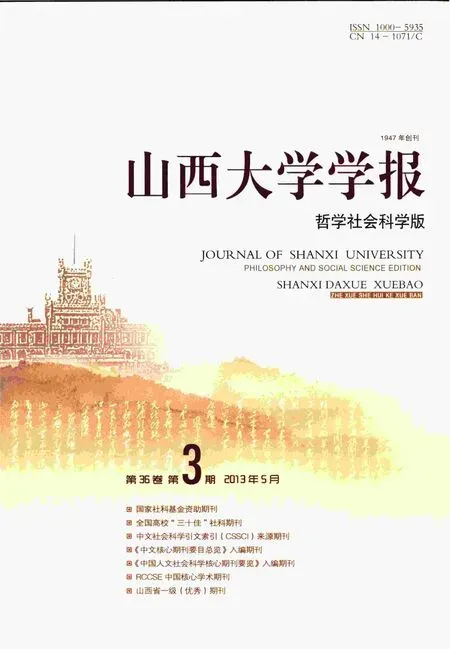1950-1970年代的“现代派”遗产——重读《夜读偶记》
李建立,王继军
(1.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河南 开封475001;2.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0)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派”话语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它与“现实主义”话语的对抗。不管在翻译家的译介中,还是在文学论争中,“现代派”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知识形态都经常是以反现实主义的方式出现的①参见拙文《1980年代“西方现代派”知识形态简论——以袁可嘉的译介为例》(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1期)以及《“风筝通信”与1980年代的“现代小说”观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对其意识形态定位和知识形态进行清理,甚至提出更“正确”的说法,并非本文的目标。本文试图将学界的注意力从“西方/中国”框架中转移开来,转而分析1950-1970年代建构“现代派”话语的方式,从整个当代史的角度认识“现代派”话语本质化过程。有此设想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和“现代派”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和内涵较为固定的概念,其实发生在1950-1970年代。更准确说,是1949年后资本主义的“西方”与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之后,才逐渐明确的②在“延安整风”之前,解放区对“现代派”还比较宽容: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鲁艺建校四周年时,美术部举办了塞。
在1950-1970年代,比“西方现代派”更大的文学概念是“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和“外国文学”。从该时段处理文学遗产的态度看,“西方现代派”的“进步”成分最为稀薄。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在这一时段“西方现代派”几乎处处“在场”但实际上又完全处于“缺席”状态。不仅“西方现代派”长期被污名化,而且在物质形态上也被禁绝。如洪子诚先生所说:“这种拒绝,主要不是通过公开批判的方式进行,而是借助信息的掩盖、封锁来实现。产生的后果是,一般读者,甚至当代的不少作家,都不大清楚有这样的思潮和作品存在。”[1]75“现代派”表述的稀缺——出现也往往是作为一个“有害”的符号被提及——为本文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下面对“现代派”在“当代文学”中存在样态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性重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茅盾的《夜读偶记》——“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2]71——的细读,来分析“当代文学”对“现代派”处置策略及其对1980年代“现代派”问题的深远影响。
尚画展(依当时的条件看,这应该是用印刷品举办的画展),并且在美术工场召开研讨会,对塞尚的绘画艺术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解放日报》还曾就毕加索的作品《踏着圆球的女孩子》的艺术形式和思想性进行过争论。(转引自周爱民:《“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的现代性》,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据茅盾自述,《夜读偶记》是对1956-1957年间出现的有关现实主义讨论的回应,是他的“读后感”和“意见”。这篇文章在《文艺报》1958年第1、2、8、9、10期发表后反响很大,并直接波及文学史写作。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1月出版的四本文学史著作都深受该文论析的观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影响①四本文学史著作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两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学及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的《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明清部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两册。茅盾所撰《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载《文艺研究》1980年第4期,收入《茅盾文艺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该文原为茅盾1959年为《夜读偶记》写的后记,当时因故未发表。。由于作者在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茅盾既是官方认可的经典作家序列“鲁郭茅巴老曹”中的重要一员,也是国家文艺管理体制中的高级官员②对茅盾在1949-1976年的文学活动的研究请参看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使该文成为国家意志对包括“现代派”在内的“文学”的权威性发言。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茅盾本来就是一位著名作家和编译家,在“新文学”的发轫期编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文论资料③除翻译外,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发表了200多篇追踪性的《海外文坛消息》。另外,茅盾还有《文学小词典》《近代戏剧家传》《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大量外国文学类论著。,其中不少和“现代派”相关。从此意义上说,《夜读偶记》也是对之前“现代派”文学观的全面审查和自我改造。
一 术语转换与历史分期
从该文引发的争论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关系并不是重点所在。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参与者大多是以中国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发言,话题也是以相关的文学史写作为中心,几乎没有提及“现代派”问题。但细读全文可以发现,“现代派”一直是茅盾参与现实主义讨论时的一个重要的潜在论辩对象。茅盾曾在写于1959年的《夜读偶记》长篇后记中做过交代:文章的第四节“古典主义与现代派”是最先完稿的,写完后“觉得应当讨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公式”就又“加上现在的第一到第三节”。[2]也就是说,茅盾写此文的初衷正是为了解决“现代派”问题。没有人在争论中提到茅盾对“现代派”的看法可能是和茅盾有共识而无须再议或是觉得当时没有讨论的条件。这里按照茅盾的写作顺序看他如何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定义“现代派”。
茅盾是通过对自己曾多次译介的“新浪漫主义”的深度整理转入“现代派”的。所谓“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20年代后不见有人用它了,但实质上,它的阴魂是不散的。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3]2。查相关的历史资料可知,茅盾所说的“新浪漫主义”,也就是他在1920-1930年代介绍过的New Romanticism或Neo-Romanticism。他在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时曾这样描述“西洋文学”的发展史:“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从梅特林克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4],概而言之,“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c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5]。对于 1920 年的茅盾来说,“新浪漫主义”是同时期世界文学的最新风尚。可当茅盾在《夜读偶记》里把“现代派”约等于“新浪漫主义”时,后者所承载的内容就和“50多年前人们曾一度使用过的‘新浪漫主义’”有了不小的差别。接着,茅盾又将“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在“精神实质”上约等于“超现实主义”。这样一来,曾经处于文学进化最顶端的“新浪漫主义”的内涵也大大贬值——“逃避现实,歪曲现实,亦即是反现实”[3]2。
两次转换首先带来的是“新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微妙变动:“当时(指20年代——引者注)使用‘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人们把初期象征派和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都作为‘新浪漫主义’一律看待。”在这里,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对知识精确程度的调整——只有剪除了初期象征派历史和早期罗曼·罗兰④这和茅盾对象征主义与罗曼·罗兰的评价有关,后文曾提到作为“现代派”始祖的象征主义“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即所谓技巧)方面有些前人未经探索过的成就”,而罗曼·罗兰则是当时被肯定的“进步作家”。(茅盾:《夜读偶记》,第64页)后“现代派”才能与茅盾对其历史分期的描述相适应:“……它们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蓬勃滋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乃至二次大战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对文学史起讫的重新划分:原来的“新浪漫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后半,自然主义文学极盛之后”并仍在“进行”中,而此时“现代派”则是用“战争”(这一不名誉的活动)和“资本主义”(冷战的另一阵营)才得以划定其文学史分期和空间范围。“战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身份戳记正是为了用来支持下面的评价:“反映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狂乱精神状态和不敢面对现实的主观心理,——如果这样说,是科学的,合乎事实的,那么,它是不能否定现实主义的,它是只能造成文艺的衰落、退化而已!”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茅盾消解了原先的文艺思潮发展程序——也就是茅盾在《夜读偶记》一开头提到的“一个公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他认为,这个公式“……表面上好像说明了文艺思潮怎样地后浪推前浪,步步进展,实质上却是用一件美丽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僵尸而已”。由此,“现代派”不再如“新浪漫主义”那样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而是(假)古典主义文学“僵尸”的“还魂”,在精神实质上用“超现实主义”的“逃避现实,歪曲现实,亦即是反现实”就可以“大体上概括”[3]2-3。
经过了这么一番调整,“现代派”成为取代“新浪漫主义”的一个更为妥帖和分明的关键词——既部分地和当时评价含糊的浪漫主义撇清了关系,又在时段上连带上了经历了两次大战(“陷入绝境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当时在描述资本主义阵营的情况时,常常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架构来投射想象,“1950-1970年代”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无产阶级文艺”)作为官方主导的创作方法,那么很自然地,“现代派”就是“‘冷战’阵营另一方的现行文艺形态”①见贺桂梅:《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和80年代中国文学》(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1950-1970年代大量使用类似的想象和修辞模式,如袁可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袁可嘉在文中写道:“托麦斯·史登斯·艾略特(T.S.Eliot,一八八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这么一幅“文艺阵线”的冷战图景借助于两种“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派——的分立被构造了出来。
二 “现代派”诸种范畴的起源
从“新浪漫主义”到“现代派”所做的“更新”不仅限于此,《夜读偶记》阐释“现代派”的方式也有了重要变化。在1920年代,茅盾是把“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两相对照推出后者的:“新传奇主义(即新浪漫主义——引者注)虽亦注重情思,然因已经一次科学精神之洗礼,在本质上已非复旧日之传奇主义(即浪漫主义——引者注)。故虽同一神秘,而旧传奇主义所表现者乃梦幻的空想的神秘思想,而非出自近代怀疑主义之神秘思想也。又如注重主观一点,虽亦为新旧传奇主义所共通,然新传奇主义所谓主观绝非如‘拜伦主义’之狂热奔放,而在以沉静之态度,达观人生,努力要发见(现)人生内在之真实。”[6]到了《夜读偶记》,茅盾换用(假)古典主义与“现代派”的相互对照来解说前者。为此,茅盾不惜花费大量篇幅论述古典主义的历史。不过,茅盾本人也意识到,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放在一起讨论有违文学史常识。用他的话说,这样做“有点像做‘搭题’了”。可是,已经意识到“大概不会做好”的茅盾为何非要以“第三者”的身份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姑且一试”呢?[3]41或者说,促使茅盾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拉到一起论述的动力是什么呢?
茅盾认为,不是二者的“思想基础”——前者是唯理论,后者是“非理性”——而是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同属于资产阶级文学。一个产生于资产阶级初兴期,一个产生于资产阶级没落期。它们的不同在于:古典主义虽然“直接为资产阶级服务”,但“也是符合于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现代派”尽管“自称极端憎恨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文明”,但由于其“完全不适合于新时代的精神”,虽然“他们主观上以为他们的作品起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庸俗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作用,可是实际上,却起到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作用”。也就是说,之所以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这两个“对立”的文学流派编入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学史序列,是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出身”。这么一来,曾经在和浪漫主义对照中得到的正面评价——“以沉静之态度,达观人生,努力要发见人生内在之真实”被一笔勾销。原因很简单,处于资产阶级上升期的古典主义尚“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文学,“现代派”则因资产阶级的没落“是像鸦片一样有毒的”。
不过,这并不影响茅盾因为“出身”问题发现二者的承传关系。他提出,“现代派”是从18世纪(假)古典主义的形式主义蜕变而来的“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3]41-70:“……(现代派诸家)……只是在反对‘形式的貌似’的掩饰下,造作了另一种形式主义”。为了和古典主义的形式主义特征有所区别,茅盾“将‘现代派’诸家概括地称之为‘抽象的形式主义’”[3]3。在茅盾看来,就创作方法而言,“现代派虽然变出许多‘家’,彼此之间,好像距离很大,但实际是一脉相承,出于同一的思想基础(主观唯心主义),对现实抱同一态度(不可知论),用的是同一的创作方法”[3]66,也就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3]57。
众所周知,不只1950-1970年代,即使在“现代派”可以被公开讨论的1980年代,“形式主义”仍然是“现代派”批判者的罪证。不仅如此,译介者和提倡者有时也会用一些变通的方式把“形式主义”当作“现代派”重要的审美范畴。那么,究竟什么是“形式主义”?《夜读偶记》的具体解释是:“这是就它们的坚决不要思想内容而全力追求形式而言;‘只问怎样表现,不管表现什么’,这句话正说明了‘现代派’的这个特点。”[3]56可是,茅盾对“现代派”所能提供的形式方面的探索评价甚低。他甚至认为“现代派”是“没有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
如果说它(指“现代派”——引者注)的始祖(在文学是象征主义,在造型艺术是印象主义)虽然不要思想性,可还注重形式的美(象征主义注重神秘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等等,印象主义在技法上的特点,上文已经提到),因而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即所谓技巧)方面有些新的前人未经探索过的成就,那么,它的末代的子孙就只能以不近人情的怪诞的“表现手法”来吓唬观众,实际上它们是没有形式主义(这里是照向来的涵(含)义,意即仅有形式美而无思想内容的作品)的形式主义。这是现代派的思想方法、创作方法必然要走到的绝境。[3]64
可以看出,茅盾认为“现代派”是连形式美也没有的,即“没有形式主义的”。按照引文括弧内的说明,这里作为形容词的“形式主义”是过分地强调形式美,那作为名词的“形式主义”——或者说作为“现代派”本质特征的“形式主义”——就不会再是此意。看来,围绕“现代派”很难解释到底什么是茅盾意义上的“形式主义”。
稍加留心可以发现,在整篇文章中,茅盾不断地使用“形式主义”这一词语,特别是在叙述文学史时,他把汉赋看做“主要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扬雄“所走的新路却是模仿先秦诸子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魏晋到唐初的文学是“逃避现实的‘玄谈’,和绮丽纤巧的形式主义文学”;明朝的“台阁体”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韩愈到李梦阳都是在反对形式主义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另一形式主义”:象征派的唯美形式主义。连同前面提到的(假)古典主义的和现代派的“形式主义”,如果不是(或不仅是)技巧至上,茅盾在大量使用“形式主义”时究竟想表达什么?
所有被茅盾冠以“形式主义”的文学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另一种是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斗争的文学,由于模仿前人(“复古”)而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以至于“用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综合茅盾对这两类“形式主义”的评价,可以得出茅盾所谓的“形式主义”指的应是“逃避现实”、“歪曲现实”、“脱离人民”、“不能触及当时政治社会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没有把握历史规律”。这正是茅盾所批判的反现实主义文学和处于末路的模仿前人的文学的问题所在。很显然,这是在“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之下推演出来的对文学风格和审美范畴的理解。这一点,从茅盾对《诗经》中两类诗篇(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中可见一斑:
“为谁服务”这一个原则不但决定了这两类诗篇的不同的思想内容,也决定了这两类诗篇的不同的表现方法和文学语言。第一类的诗篇,多用“比”和“兴”,第二类的,多用“赋”;第一类的诗篇,虽然基本上还是四言句,但已有变化,而“章”的结构,则变化更多,重句叠句,反复咏叹。可是第二类的呢,篇章结构和造句,就都很呆板;从前人把这种呆板称为“雍容典雅”,表示了非常的钦佩,这真是嗜痂成癖。至于这两种诗篇所用的文学语言,其不同也很显明。第一类诗篇多用清新活泼、音调和谐、色彩鲜艳、近于口语的文学语言;第二类的可就佶屈聱牙,苍白干枯。[3]6
因此,与其说“形式主义”是“现代派”的审美范畴,不如说是茅盾认为的全部反现实主义文学(和处于末路的模仿前人的文学,下同,不再特别指出)的共有特征,只需根据内容或技巧上的某种突出表现加上诸如“抽象的”、“宫廷享乐的”和“唯美的”等形容词以示区分。“形式主义”指的是反现实主义文学由于看不到“现实”(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劳动人民的力量),而显得“内容空乏”。这种稍显简单的处理方法正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茅盾在频繁使用“形式主义”时所表现出的与其著名作家和编译家经历不相符的修辞贫乏,正是此种紧张关系作用的结果。按这样的逻辑,现行资本主义阵营的“现代派”的“形式主义”自然是“没有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
三 “现代派”话语构造的逻辑
其实,在“形式主义”问题之外,观察一下茅盾叙述文学史时所用的词汇及分类法,会发现他使用的很多审美范畴或思想特征的内涵只能在他使用“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框架评价文学史的过程中予以理解。他的主要做法是:用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对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各自的特征进行预先区分,然后将其做本质化理解,使二者之间的差异根深蒂固。结果,现实主义则总是被赋予“积极”的审美特征:清新活泼、音调和谐、色彩鲜艳、真实、深刻等。相反,反现实主义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标签:佶屈聱牙、苍白干枯、装模作样、官气十足、非理性、形式主义等等。相对于别的“反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派”处于和“当代文学”更直接的敌对位置,而且似乎还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争夺先进性的危险性。因此,它们的对立最为鲜明。实际上,“现代派”正是被当作“当代文学”进行文学规划时的重要“他者”来使用的。而这,也是被附着在“现代派”上的各种标签的起源——其中形式主义和反映现实之间的对立自不必说,还有非理性/历史规律、自我/群众、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悲观/乐观、消极/积极、颓废/明朗、晦涩难懂/喜闻乐见,等等。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正确的世界观作为指导”,对立双方的后者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历史主体地位,在与“现代派”的对照中赢得了无可争辩的正当性。因此,与其说非理性、自我、个人主义、悲观、消极、颓废、晦涩难懂等范畴来自于西方“现代派”,不如说是“当代文学”在建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时对“现代派”的
一种话语分配。
可以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是造成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派”的这些组合及其相关范畴得以归并生成的重要原因。茅盾在《夜读偶记》中对“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历史的揭示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对立并加以稀释放大的结果。他在文章开头对原有文学发展“理论”(即上文提到的文学发展程序的“公式”)产地和非普遍性的警惕——“包含这些‘理论’的书是欧洲学者们以‘欧洲即世界’的观点来写的”——并没有阻止他自己接着用另一个欧洲文学概念“现实主义”去重新解释“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构造作为引擎,赋予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以充分的政治性,将空间上的地缘政治对立转换为不同文学方案在时间中的分裂与“斗争”。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调动各种历史资源制作西方“现代派”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被看做“创作方法”的“现代派”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创作方法”内涵的膨胀——“至少包括这样的三个方面:即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立场,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看法及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没有前两者,也就没有后者”[7]——成为对两种文学观念的整体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借助《夜读偶记》所做的关于1950-1970年代“现代派”的讨论,并不是要看茅盾是否歪曲了“现代派”——依照本文的思路,任何一个被本质化整体化的“现代派”都是可以被讨论的——而是为了勘测“现代派”存在于“当代文学”的方式,以及在“当代文学”中的被定义的过程,包括经典文本和作家的选择、文学史分期、美学范畴和思想特征的定义,等等。这是一个很难被讨论却易于理解的问题。“很难”源自于上文提到的资料匮乏,“易于理解”则和当下所拥有的历史势能有关:早在1980年代,1950-1970年代的对“现代派”的看法已经被质疑——“现代派”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学领域的符号在“斗争”中出现的,当然不能将之看成一个经过严密论证的文学史概念,它的文学史观及相应的文学史分期、分类规则也不再有效——在这里也不用费心解释“当代文学”中的“西方现代派”是被建构的产物。而分析1980年代的“现代派”话语时,就需要提醒人们那个对“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进行清洗之后的1980年代的“西方现代派”,同样不是一种“自然”的西方现代文学。这里通过对《夜读偶记》的细读,不仅能看出1950-1970年代塑造“现代派”的方式与逻辑,还可以将其作为研究1980年代“现代派”话语的参照,看后来对“西方现代派”评价转向的同时,有什么被扭转了,以及还有什么至今仍然左右着我们的知识构成与文学理解。
[1]洪子诚.左翼文学与“现代派”[M]//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75.
[2]茅 盾.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J].文艺研究,1980(4).
[3]茅 盾.夜读偶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
[4]沈雁冰.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N].时事新报·学灯,1920-01-01.
[5]沈雁冰.小说新潮宣言[J].小说月报,1920,11(1).
[6]茅 盾.新传奇主义[M]//茅盾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78-379.
[7]巴 人.重读《夜读偶记》[J].读书,195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