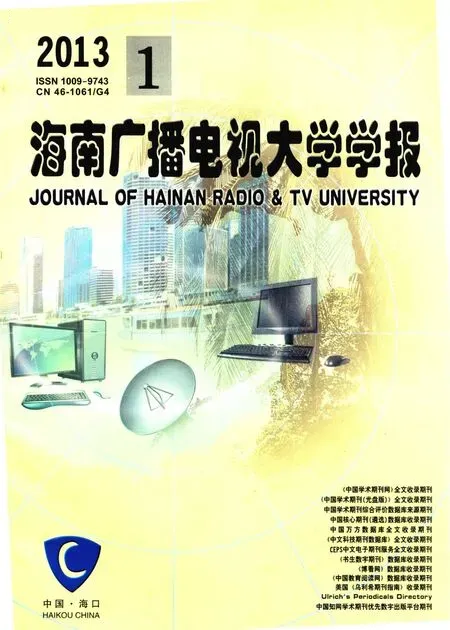试论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从曹丕到陆机
岳 磊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一 曹丕对“丽”的肯定
曹丕在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上主要作用就是对丽的肯定,有首倡之功,其《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周礼·夏官·校人》:“丽马一圉,八丽一师。”郑玄注:“丽,耦也。”也就是说“丽”的本义是偶或者成对的意思。在《书·比命》:“弊化奢丽,万事同流。”孔颖达疏:“敝俗相化,奢侈华丽。”曹丕“诗赋欲丽”的“丽”也是这个意思。陈良运说:“所谓‘丽’,其义即美”,“曹丕所说‘欲丽’就是欲美,突出了诗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美”[1]。
了解一种思想观念,仅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当时的一般知识与思想,即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点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现象与事物的解释,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就是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这些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播通过各种最普遍的途径,比如观看各种娱乐性演出中的潜移默化、一般性教育中的直接指示等等。范围远远超过经典系统,是任何一个精英都会经历的,所以他可以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真正的直接的土壤与背景[2]。曹丕由汉入魏,受汉赋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赋是由诗、骚发展而成的,受楚辞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3]班固《离骚序》亦云:“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4]所以,汉赋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丽”,用“丽”来称赋现在是很普遍的,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汉赋是“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扬雄在《法言·吾子》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4]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4]对于这一点《西京杂记》中的一句话说的很到位:“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刘熙载《艺概·赋概》解释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像班形,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5]于是我们可以说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是对汉赋之“丽”的一个继承。
其次,曹丕的“诗赋欲丽”说,也可以说是对时人的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的总结。有“建安之杰”之称的曹植态度极其鲜明,其《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6]说明自己写作《七启》的缘由是倾慕前贤的“美丽”之作。再如他的《与吴季重书》赞吴质书信的文采:“晔若春荣,浏若清风。”其中“晔”,就是华美的意思。吴质《答东阿王笺》称曹植文采“巨丽”。陈琳《答东阿王笺》赞美曹植文章“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钟嵘《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汉末及以后,动乱纷纷,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古诗十九首》开始忧生之嗟不绝于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难看出曹丕对文章的重视,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是把“声名自传于后”作为他著文的目的。当时的社会风气正如汉末王符《潜夫论·务本》云:“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曹丕也不例外,区别是他更加突出而已。
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对“丽”的肯定。以赋为例,汉赋大多都表现出“丽”的特点,可不少赋作家和批评家都对“丽”有批评。如扬雄在《法言·吾子》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认为赋作的“丽”要有规范,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影响。实际上就是对于赋的“丽”有保留意见。比扬雄更进一步的是王充,他在《论衡·定贤》云:“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认为即使文章美如锦绣,含意深如黄河、汉水。可是于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这是典型的文为世用论。这种观点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赋作“丽”的特点,否定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这些论述涉及到文学观念形态的变革。在汉代,一边是人们在认真地写文辞富丽锦绣的文章,一边是思想界屡屡对文辞艳丽的作品有批评。说明在思想上人们是矛盾的、痛苦的。曹丕主张“诗赋欲丽”,肯定了“丽”,解决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困惑,是对文学独立性价值的肯定,标志着思想界对文学观念认知方面的变化。重审美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鲜明的时代特征。曹丕以后,文学开始一个审美时代,也开启了古代诗歌重形式美的新风尚。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形成了注重审美,关注形式美的热潮。其后的陆机、沈约、钟嵘、刘勰等,踵事增华,将这个热潮推向高潮。不过,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7]首倡之功,居功甚伟。虽有“持论虽高,其说未尽”的遗憾,但在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 陆机对“丽”的深化
陆机是尚丽思想发展的代表者,他推崇尚丽文风并大力推行。陆云认为其兄文“甚有词,绮语颇多”,钟嵘则曰“才高词赡”“文章之渊泉”。作为“太康之英”的陆机,是太康文学繁缛诗风的代表。
理论方面,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说“绮靡,精妙之言,浏亮,清明之称”。李周翰注说“绮靡,华丽也。浏亮爽朗也”。“言诗之缘情而生,言辞华美,声音细腻婉转;赋之描摹物象清新明澈,音节嘹亮。此二句从言诗赋之别,均从意与辞两方面言”。[8]周汝昌在《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一文中的解释更为详细。在文中说“绮”,本义是一种素白色织纹的缯,《汉书》注:“即今之所谓细绫也。”而《方言》说:“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注:‘靡’,细好也。”可见,“绮靡”连文,实是同义复词,本义为细好。认为“绮靡”一词,是用织物来譬喻细而精的意思。“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可见“绮靡”一词,也是当时形容音乐调韵的常用语。缘情的“绮靡”,是和体物的“浏亮”并举对文的。“浏亮”,后来音转为“嘹亮”,可以形容人谈吐的通畅、心胸的豁达。也可以用来形容笛子的声调音色。于是认为“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因此就“浏亮”。“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沈郁蕴蓄的语式声调,也就是“绮靡”了。[9]
从上面论述里不难看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与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如出一辙。陆机对曹丕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曹丕将诗赋合论,强调诗赋之同,没有能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异同,也没有对“丽”的内容作出具体而明晰的规定。“持论虽高,其说未尽”,不免让人遗憾。而陆机把诗赋分开讨论,注意了诗歌与辞赋之间差别,比曹丕论述的详细得多了。首先是丽的表现的差别。认为诗歌的“丽”表现出来是“绮靡”,也就是华丽缠绵之美;辞赋的“丽”表现出来的是“浏亮”,也就是朗丽畅达之美;其次是为什么诗赋需要表现“丽”的特点的原因。陆机认为诗是“缘情”而发,所表达的情志大多比较细致深隐,自然也就“绮靡”了。赋大多“体物”,正如《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侧重直陈铺叙。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就“浏亮”了。最后,在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里,无论“绮靡”还是“浏亮”,都是可以用来描述声调音韵的。说明陆机也注意到了诗赋的声调音韵,在《文赋》后面两句话“暨音声之跌代,若五色之相宣”也说明了这一点。与曹丕相比之下陆机更加注重声色之美。“用现代眼光看,陆机注重诗歌声色之美,且成为创作的一种自觉行为,用前人话说,是‘文艺的自觉’。重视词采和音调,就突出了诗的美质,是诗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陆诗词采华丽精美,音调宛转顿挫,上承曹植、阮籍,下开六朝,泽被唐宋。在汉魏诗风转变上确乎起到枢纽作用。故钟嵘虽批评陆机‘有伤直致之奇’,又赞其‘才高辞瞻,举体华美’,‘张公叹其大才、信矣。’(《诗品》)”[10]
陆机在《羽扇赋》借宋玉之口曰:“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是故烹饪起於热石,玉辂基於椎轮”。言之创始者常质朴,而后世饰之妍丽;烹饪起源于用热石来烤食物,华美之车源于简陋的椎轮,一般看来陆机显然强调的是人类的文明进化,是他的文明史观思想的体现。但是在他这个文明史观里包含着他的审美史观。“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文心雕龙·通变》云“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11]黄帝时代唱的《弹歌》,是很质朴的;唐尧时代的《在昔》就比《弹歌》要丰富一些;虞舜时代的《卿云》又比《在昔》要有文采得多,夏朝唱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代的《卿云》更富有辞采;商周时期的作品,比起夏朝来更加华丽。正如陆机所说“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抱朴子·钧世篇》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12]认为古代作品没有当代的富丽,原因是“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形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12]萧统在《文选序》亦云:“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3]可见在陆机之后葛洪和萧统与陆机的审美史观可以说同出一辙。这与“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修饰便转为字句、篇章的推敲,重视文采因亦成为文人的普通习性。”[14]有很大关系。
创作实践方面,一路极为代表的太康诗风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诗赋的骈偶化倾向。汉赋继承了《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又吸收了战国纵横家铺张的手法,经常使用排比、对偶句法,体现出了“丽”的特点。对于汉赋“丽”的特点上面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魏晋开始赋出现了新的变化,比较显著的就是骈偶化。韩高年在《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骄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中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骄体文之渐萌也。’骄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骄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想。”[15]与韩高年类似,杨东林亦指出“到了魏晋,赋之语体由散体中杂有骈句而迅速骈化,发生了质的变化。陆机、潘岳不用说,曹丕、曹植的很多赋作其主体已成为骈体了。与骈化相伴随的是,辞采也更加繁缛富丽,用典用事也更加频繁,且开始讲求声律之对称回环。赋在汉代“丽”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其‘形’愈‘工’。”[16]如陆机的《文赋》虽是理论著作,但亦是骈赋,又如《白云赋》《漏刻赋》《愍思赋》《怀土赋》《大暮赋》等赋作句型整炼,属对工稳。骈赋到了陆机这里已经完全成熟,是标志骈体文正式形成的典型作家。又如陆机拟古诗对偶表现最为鲜明,在《古诗十九首》中只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等寥寥几句。《拟古诗》多有对偶,如《拟行行重行行》之中“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惊飚褰反信,归云难寄音”。《拟迢迢牵牛星》“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拟明月皎月光》“翻翻归雁集,嘒嘒寒蝉鸣”等。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五云:“建安五言,再流而为太康。然建安体虽渐入敷叙,语虽渐入构结,犹有浑成之气。至陆士衡诸公,则风气始漓,其习渐移,故其体渐俳偶,语渐雕刻,而古体遂淆矣。此五言之再变也。”[17]
结 论
综上所述,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与曹丕和陆机关系密切。“诗赋欲丽”曹丕是对丽的肯定,是曹丕对汉赋之“丽”的一个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时人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的总结。虽有“持论虽高,其说未尽”的遗憾,但在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有首倡之功。陆机推崇尚丽文风并大力推行,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思想,在创作实践上也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所以可以说,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文人在总结前人理论和创作基础上形成的。曹丕和陆机主要起到了一个引领推动作用。当然,这种引领和推动对魏晋“尚丽”文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郭绍虞.历代文论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袁津琥.艺概注稿(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9]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J].文史哲,1963(2).
[10]刘运好.“缘情绮靡”与陆机诗风[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3).
[1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郭绍虞.历代文论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陈伯海.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15]韩高年.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6]杨东林.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7]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