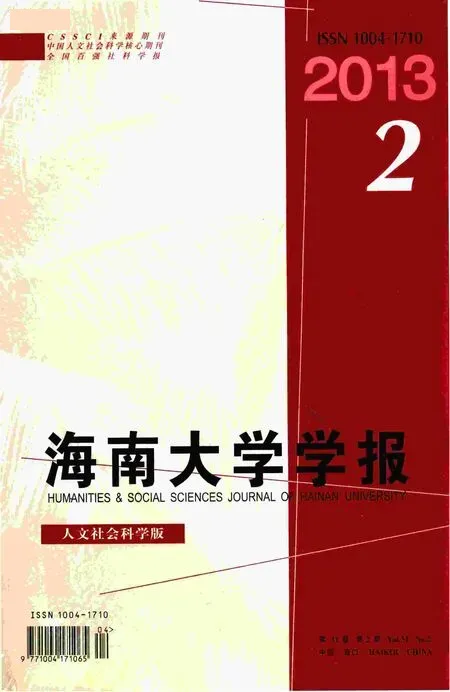常论与悖论——小说《赎罪》中敦刻尔克奇迹的自我消解
胡慧勇
(1.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036;2.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200083)
一
作为当今英国文坛呼风唤雨的语言大师,伊恩·麦克尤恩独步英伦小说界达30多年之久,笔耕不辍,获奖良多。因其娴熟的叙事技巧和深邃独特的伦理洞见,他被看作是“英伦三岛上在世的最伟大小说家”[1]。麦克尤恩于200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赎罪》堪称经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影响颇大。
《赎罪》是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之初的30年里,英国文学界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中的一部经典之作。麦克尤恩像拜厄特、斯威夫特、曼特尔、班布里奇一样,在作品中认真地探讨了如何利用语言忠实地去表达史实真相的严肃话题[2]。虽然《赎罪》未能在布克奖上折桂,但它是“一部特别纠结,具有反讽意味并深深触及人性”的作品[3],同时又是一部“多层次的小说”[4],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小说之一,它的创作巩固了麦克尤恩在英国同时代作家中的领跑地位。
从题材来看,《赎罪》可以看成一部历史小说;从形式看,它继承了麦克尤恩上一部小说《阿姆斯特丹》(1998年)的互文性特征,不过在叙事主题上,它触及了一个全新的伦理纬度,即以叙事求赎罪。虽然小说的结尾是以现代社会作为背景,但是大部分故事发生在二战开始前后的英国前线和后方,也就是麦克尤恩出生之前的时空,这是麦克尤恩所有小说创作中的第一次。小说的主人公是从小就喜欢幻想、热爱写作的布里奥妮,其年幼时一次错误的强奸指证,导致了她家佣人的儿子罗比——一个靠布里奥妮父亲资助还在牛津大学求学,并和布里奥妮姐姐西西丽亚处于热恋的年轻人——身陷牢狱之灾;当战事吃紧时,为了获得自由身的罗比只好参加英国远征军,远赴法国参战,结果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因劳累和伤病凄惨离去;而远在后方当战时护士的西西丽亚,日夜期盼着魂牵梦绕的爱人能平安归来,却也因纳粹空袭伦敦而在地铁掩体中香消玉殒。战后,布里奥妮继续着自己写作的梦想,多年后成为知名作家。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为此而不断地折磨自己,从创作中寻求真相,最后只好以叙事的方式让西西丽亚和罗比幸福地生活在小说里,从而达到赎罪的目的。
小说出版后,麦克尤恩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了幻想在人类道德净化中的作用,他断言个人能够利用想象的力量改变,或者至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5]。对于这部小说,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小说的赎罪主题、互文性、元小说、诗学特征和心理创伤,不过作品中最能感动读者的部分恐怕是敦刻尔克前线血腥恐怖的战争场面。麦克尤恩以其犀利准确的语言,利用史实和虚构,彻底颠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争奇迹”,让读者在恐惧和希望交替中强烈感受到了战争给个人带来的人伦悲剧。
二
二战之初,在德国闪电战的打击下,短短几个月,欧洲十四国迅速成为纳粹法西斯铁蹄下的傀儡,而陷于德国重兵包围的英法军队,却从敦刻尔克死里逃生,几乎全身而退,的确创造了二战的“奇迹”[6],为盟军五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打下了伏笔。
1940年5月26日,在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接到总部实施“发动机”的行动命令,英法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海运船只,开始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在9天之内近三十万有生力量,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演绎了“敦刻尔克精神”,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转移。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军事决策英明、英法合作无间和撤退转移有序的英雄篇章[6,7],然而,这些历史教科书和其他各种叙事文本中的“常论”却在麦克尤恩的笔下逐渐消解,通过小人物的所见所闻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种异类的敦刻尔克大溃败景观——“悖论”。
罗兰·巴特认为“常论”就是指公众的观点、多数人的意愿、小资产阶级的共识、本性的声音或偏见的暴力,也就是老生常谈,普通的观点,重复的意思,似乎什么都不是[8]65。大家知道,作为小说家,他们似乎可以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但是遗憾的是他们通常被语言所限定,他们不可避免的是某种政治的主体或客体,没有别的选择,因此他们无法改变其话语而脱离政治性,他们的话语很多时候只能是重复早已让人疲乏,且众所周知的政治主张或观点。写作者是想象的各种常论的同代人,是神话或者哲学的同代人,而不是其历史的同代人,他们的话语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是历史舞动的反映[8]66。
政治话语的常论当然不可能永远如此强势,一旦有某种层次的话语变动,和这些话语相联系的权势和威严,连同其固定不变的词句一起衰落,常论将为悖论所替代。巴特认为,如若不想重复政治话语,一些苛刻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要么自己创立一套新颖的话语方式;要么通过语言的专门效果,生产出既严格又自由的政治文本,承担起美学特殊性的标志,好像是对已有写作的创造与变化等。在布莱希特看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是直接的,否则会再次生产出过滤的、同语反复的、战斗的话语,而通过美学,反意识形态蕴含于一种虚构之中,虽非现实主义,但是十分合理,美学在社会生活中提供间接而十分有效的话语规则,它改变语言,但是不霸道,因此,美学是颠覆“意识形态”的一种解决方式[8]67。麦克尤恩正是利用他的叙事美学,消蚀了那些压制性的、霸道的有关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常论,那些有关战争的重复性话语。
作为二战后出生的一代,麦克尤恩似乎对战争倾注了许多情感,无论是枪林弹雨的二战(《赎罪》),还是谍影重重的冷战(《黑犬》、《无辜者》),在他的笔下,战争总是故事情节中非常重要的叙事成分。
麦克尤恩每次在创作小说前,对写作的话题均会进行详实的研究和调查[9],《赎罪》的创作也不例外。小说中有关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争场面真实而震撼人心,恐怕要归功于他父亲的影响和他自己辛勤的调研工作。麦克尤恩说,很多退役军人不愿意提及战争的经历,可他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这样的顾忌或恐惧。从少年时开始,一直到倾心聆听的中年时止,麦克尤恩不厌其烦地听父亲述说他的双腿如何被德军坦克上的机枪击中,随后如何和一个双臂受伤的同伴,协同驾驶一辆军用摩托跑到敦刻尔克海边,直到最终被撤离。当然还有他随后在利物浦奥德黑医院治疗六个月的故事,比如倒霉的烧伤病员总是四肢严严实实地被绑在温敷袋里,口渴难忍,痛苦不堪;不论多么坚强的士兵听到护士的喊声时也不禁胆寒,以及护士试图撕掉他大腿上的弹片时,他如何在痛苦中诅咒骂人等[9]。麦克尤恩很享受父亲的故事,因此他能驾轻就熟地把这些真实的情节放在《赎罪》中,可当他尽情地利用作家手中自由之笔时,“在虚构和史实之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责任感”,“那是一种对战争一代所受痛苦的尊重,因为他们是被时代从平和安静的生活卷入了令人恐怖的梦魇之中”[9]。不过,作为历史小说作家,麦克尤恩和其他作家一样不喜欢依赖历史档案、回忆录或亲历者的描述去创作,但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麦克尤恩通过想象在历史事件和虚构叙事之间获得了完美的平衡,并以此重新注解了,同时也是消解了“敦刻尔克奇迹”。
三
首先,敦刻尔克大撤退虽说不是胜利,但是却蕴藏着胜利[10]121,“是一种奇迹”[10]115,这恐怕是一种共识。从1940年5月26日晚,也就是下午6时57分,海军部开始实施“发电机”作战计划后,布洛涅和加来很快落入德军手中,留给英法军队的只有敦刻尔克和连接比利时边境的开阔海滩,英军最高统帅部估计留给英法军队实施撤退的时间顶多两天,最乐观的估计也就是能够救出45 000人[10]104。可事实是,在全国上下一致努力下,共有860多艘舰船参与了救援,救援进行得有条不紊,甚为严密[10]106,而在最后阶段,撤退工作组织得更加熟练和严密了[10]119,及至6月4日下午2点23分,海军部在法国同意下宣布“发电机”作战计划结束时,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共有33万多英军和盟军士兵登上了英国土地,而希特勒空军的损失却是英国皇家空军损失的4倍,这不能说不是一场救援行动的胜利。
不过麦克尤恩通过罗比的视角,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情形是大相径庭的,他看到的“到处都是令人颤栗的惨状”[11]193和海滩上溃不成军的混乱[11]251。因激战而和部队失去联系的罗比,从战壕里死去的军官手里抠得了一张战地地图,在地图的指引下,他和偶遇的两个同伴力图避开大路走偏僻的小径。在林子里,他们见到了挂在树杈上的一条儿童的断腿,“插在离地面二十英尺高的树上第一个树杈间,光秃秃的,齐齐地从膝盖以下斩断。”“这腿摆放的姿势如此精妙,以至让人觉得这纯粹就是个展示,供他们更好地欣赏,让他们看清楚:这是一条人腿。”这场面让人恶心,人物叙事的距离又使人不寒而栗,读者感受更多的恐怕是欲哭无泪了。
出了林子,他们一路面临着轰炸机的威胁,途经一个法国村庄时,听到善良的村民说起他们的恐怖经历:六七个被机关枪扫射成一分为二的英国士兵尸体,满目疮痍的小村子,房屋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罗比在极度疲劳中,躲避猛禽般在空中盘旋的俯冲轰炸机,发现除了北边,哪儿都有耀眼的枪火。“溃败之军如今正匆匆地堵挤在一条走廊上”[11]206,不知何时就被切断了归路。天晴时,避开大路也不见得那么安全,罗比看到50架海因式飞机编队扑向海边,“一个养牛的牧场有十来个炮弹坑,一百码方圆里随处可见被炸飞的血肉、骨头和烧焦的皮肤”[11]218;更为可怕的是斯图卡轰炸机的袭击,“每当飞机俯冲而下,人们便战战兢兢,纷纷躲入角落,听任死神的摆布。”如果幸运躲过一劫,更多的折磨还在后头,恐惧丝毫没有减轻,这时只有中士或者军官过来用脚踢着士兵,命令他们站起来,实际上撤退的部队已经是溃不成军了。而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就成了待宰的羔羊。罗比本想帮帮一对母女,可在紧要关头,母亲被吓傻了,等到罗比他们回头向弹坑走去,母亲和孩子都消失得无隐无踪,甚至连衣服残片或鞋子碎皮都没有[11]242。
坐车就更危险了,罗比亲眼看到20个人坐在三吨车后部被一颗炸弹全炸死了,自己在战壕里才躲过一劫,但是腰部中了块弹片。尽管罗比感到极度的瞌睡,但是必须随时机警地看着天空。在越过一道战壕时,他们发现了五具尸体,三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再走了20分钟,碰上了纵队和军车,却突然遭遇了一架离群敌机的狂轰乱炸,罗比只记得当他越过少校肩膀远眺时,这架离地30英尺的轰炸机横悬在空中,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霎时间火光烈焰四处可见。藏身车下,罗比蜷缩抱头,眼睛紧闭,轰炸间歇,等着下一轮炮火,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昆虫发出晚春的低吟和鸟儿停顿后的歌唱,然而,远处,一个15岁的男孩永远闭上了眼睛,可当时阳光如此灿烂,生与死,如此的靠近。“撤退简直就是一场血腥屠杀……”正如罗比的伙伴在埋葬这个15岁少年时唱起了跑调的赞歌:“四面受敌,全军覆没,放眼望去,吉少凶多。”[11]222-226
终于到了海滩,罗比的伙伴却因衣衫不整被一名中尉大声呵斥,可海滩上什么军容军纪都统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是虚张声势的中士和沉闷无聊的士兵,人们看到的“就是一场混乱无序的撤退(在)走投无路时的场景”[11]252。海上,除了远处一艘被海浪打翻而随波漂流的捕鲸船之外,什么也没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像一粒粒谷子,漫无目标地踟蹰徘徊;六匹马拉着一门大炮,沿着海岸横冲直撞;有些士兵试图把颠覆了的捕鲸船扶正,另一些在准备下海游泳;东边,居然还有一群人在进行足球比赛,隐隐约约传来了齐声唱赞美诗的歌声;还有些在沙滩上为自己挖掘散兵坑,或者掩体,并把头伸出,就像土拨鼠一样;更多的人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左边布雷敦斯胜地的情况更糟,士兵们自行打开咖啡店,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大声喧嚣,还有人在大街上骑着自行车互相追逐,少数醉汉则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一幅混乱颓废的景象,一点儿也不像如临大敌时军纪严明的军事行动。
历史教科书中的战争总是和冰冷的数字联系在一起,士兵、军官、将军和统帅从来都是战争叙事的主角,而平民,在历史和历史学家眼里,只是战争的影子或者干瘪的死伤数字。不过,麦克尤恩通过罗比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和听见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战争中的凄惨遭遇。从挂在树杈上儿童的残肢,到踽踽独行的老人,再到炮弹中粉身碎骨的母亲和孩子,这些描写无不体现作者悲天悯人的胸怀和对人类文明在战争中堕落的焦虑。“他想起了睡在床上的法国小男孩……他们甚至会把一整舱的炸弹砸向铁道旁一个沉睡的小村庄,而懒得去想里面究竟有谁。”[11]205“……进入一座被轰炸过的村庄,抑或是小城镇的郊区—这里一片废墟,难以辨认。但是谁会在意呢?谁会深究这其中的区别,把村庄的名字和这个日子载入史册呢?谁又会持有说服力的证据去兴师问罪呢?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原先的模样。”[11]231
这里不得不提在通往敦刻尔克的乡间小路上,罗比和他的同伴遇上的那个有点疯癫的法国老太太。83岁的年龄,看到士兵就有一股本能的反感,原来他的大儿子在1915年第一次大战时死在凡尔登。一枚炮弹击中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只剩头盔。从那时起,她就痛恨战争。不过她还是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嘟噜了几句之后,她还是让孙女给他们送来了黑面包、奶酪、洋葱和酒。饱受战争之苦的她,在风烛残年还得忍受枪炮的折磨。在敦刻尔克的布雷敦斯,他们还遇到了一位吉卜赛老妇人,当他们向她讨口水喝时,她却要求他们去把她的大母猪从街上撵回来。如此睿智的一位老太太,孤身一人,在乌烟瘴气、充满危险的小镇上仅和一头猪为伴,读者不禁想着她的儿女们身在何方。当猪赶回来后,她让罗比和同伴喝个够,临走还给他们饭盒、水壶装满水,并送他们红酒和包着糖衣的杏仁。麦克尤恩让这些善良而无助的黎民百姓在战争中述说他们不幸的遭遇。
四
“发电机”行动开始之前,丘吉尔告诫政府和他的人民,无论法国的战事发生什么,任何事情都不能使英国放弃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勇往直前的信心,英国会冲破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敌人[10]103。正当敦刻尔克危急时刻,光荣的事迹传到了英国臣民心里,英国士兵特别是皇家空军的战斗经历将彪炳史册[10]109。在谁先撤退问题上,丘吉尔强调了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兄弟手足的关系,救援计划中绝对不会发生把法国士兵丢在后面不管的事件,为此丘吉尔下达命令要尽量使法国军队和英军共同撤离敦刻尔克,而当得知英军由于正常原因撤离人数远远多于法军人数时,丘吉尔建议英军和法军应该按照同等数字撤退——“挽臂同行”[10]115。敦刻尔克撤退体现了英法军队的兄弟友谊和战斗中的英勇气概。
而《赎罪》中的敦刻尔克撤退,在罗比眼里或者说在麦克尤恩眼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面。罗比和许多士兵一样,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有时显得十分自私。一路上罗比不止一次想要摆脱两个同伴的跟随,以便能够快速地到达海滩,而迈斯下士和耐特尔下士总是不停地嘲笑罗比,一旦他沉默不语就说他是不是在想着“那个骚娘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罗比“敌视身边的每个人,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11]220在靠近一片树林的地方,当他们碰上一名上校指挥一队士兵,要把一个德国士兵赶出来时,罗比和两个下士都拒绝服从,而且还伪造哥特爵士的命令,说要尽快撤退,“不得延误,不得迂回”。英法军队似乎也相互抱怨,“没有任何志同道合的迹象。在英军看来,法国人拆了他们的台。他们不愿意为祖国而战。他们高喊着‘马其诺’,借此诅咒和嘲笑他们的盟军。对法军而言,他们肯定听说了有关英军撤退的谣言,而他们正被派往后方镇守。‘懦夫,回到船上去吧,回到裤裆里去吧!’”[11]238
即使是英军内部,他们也是相互责骂。每当敌机来袭,士兵们总是咒骂皇家空军去哪了。在布雷敦斯的一家酒吧里,一名戴着眼镜,矮小结实的空军士兵,受到一群陆军士兵的谩骂和攻击,在酒精和饮料的作用下,人们似乎失去理智,抽他的耳光,质问英军受到攻击时他上哪儿去了,“他像一只处在光天化日下的鼹鼠,惊慌地盯着那群折磨他的人。”[11]256要不是迈斯下士机智地举起他,对着众人撒谎说要把他扔到海里去喂鱼,才救了他的性命,疯狂的人们非得把他撕成碎片不可。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敦刻尔克救援或者战略撤退在二战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是一次蕴藏着胜利的救援行动[10]121;但是,它也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失败,灾难的主要原因,除了愚蠢的战略思想,还有装甲部队和反坦克武器力量的薄弱[12],英国远征军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侥幸的成分不可排除。一是希特勒战略上失策,过分依赖空军和炮火,没有动用陆军;二是沙滩的软沙大大降低了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威力,几乎没造成什么伤亡;第三是希特勒没想到他们的空军损失如此大[10]107。然而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战争就是战争,无论胜利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流血和死亡不可避免,黎民百姓遭受蹂躏和屠杀。富兰克林说过,世界上没有所谓好的战争或者不好的和平,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还有文明和人性的丧失。
五
正如新历史主义思潮所言,“历史的真实不仅仅表现在那些宏大叙事上,而且也体现在那些叉枝旁鹜上。这些历史的‘偶然’现象有可能和大写的历史并不合拍,但是却的的确确发生过,之所以‘被掩盖’是因为有人不喜欢,或者说这些大理石的根部旁逸出的枝杈有损大树的形象。可形象并不等于‘真像’,尽管真像并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13]。《赎罪》中有关敦刻尔克撤退部分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叙事的虚构,罗比·特纳的故事就是“小历史”中的真实个人境遇,是对大写历史的补充,甚至是反叛。
可以说,《赎罪》第二部分有关敦刻尔克大撤退一章的叙述是令人震撼,甚至是让人恐惧的。按照拉康等心理分析理论,《赎罪》中战争场面的血腥“真实”给读者心理造成的情感体验,表明叙事已经成了一种捕捉和传达机械化战争给人们带来日益加速的心灵创伤的有效载体。虽然拉康等理论家并未亲身经历这些震撼人心的场面,但是他们以超出经历者身份的视角理解并消化它们。正如保罗·维利里奥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大国战争时指出,随着战争范围、激烈程度和军事力量部署速度不断增大,战争创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着。尽管《赎罪》中的叙述文本采用了回避和省略等修辞手法,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它能唤起麦克尤恩一代战后读者与他们生活现实相关的创伤性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模式本身不是由文本暗示的,而可能是由文本塑造出的反应和带入阅读过程的心理现象交互作用的结果。另外,叙事“延迟”手法给读者带来的颠覆性情感经历也是令人难忘的,即当读者得知西西丽亚和罗比悲剧性的结局时,他们对悲剧主角之前所倾注的情感体验并非受到消解或降低,而是得到了加强。所以,小说《赎罪》在情节上通过“一段时间的孵化或者潜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暴力、伤疼和死亡到最终被出其不意地抛入隐隐作痛的伤心时刻,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先前的情感体验因此而完全被唤醒[14]。
《赎罪》以所谓的“悖论”彻底颠覆了历史或政治角度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表明小说可以超越历史学科,述说历史所不能触及的维度,从美学角度丰富人们对敦刻尔克,对战争,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麦克尤恩创造的这些经典叙事文本,既是对人皆知之的敦刻尔克神话“常论”的挑战,也是在更广泛层面上对战争进行批评[15]。
[1]SHAH Bruno M.The Sin of Ian McEwan’s Fictive Atonement:Reading his Later Novels[J].New Blackfriars,2009(1025):38.
[2]HIDALGO Pilar.Memory and Story-telling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J].Critique,2005(2):82.
[3]DAVISBarbara Beckerman.All-Fiction Issue:The Bridge Playing Ladies[J].The Antioch Review,2003(1):180.
[4]BLOXHAML J.Book Reviews[J].A Journal of Theology,2008(4):401.
[5]CHILDSPeter.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6.
[6]赵克仁.敦刻尔克大撤退[J].历史教学.1994(7):46-47.
[7]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32.
[8]方生.后结构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9]MCEWAN Ian.“An inspiration,yes.Did Icopy from another author?No”[J].Critical Quarterly,2006(2):46-47.
[10]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11]伊恩·麦克尤恩.赎罪[M].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2]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全:3[M].许步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0-21.
[13]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91.
[14]CROSTHWAITE Paul.Speed,War,and Traumatic Affect:Reading Ian McEwan’s Atonement[J].Cultural Politics,2007(1):51-70.
[15]ALDEN Natasha.Words ofWar,War ofWords:Atonementand the Question of Plagiarism[M].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