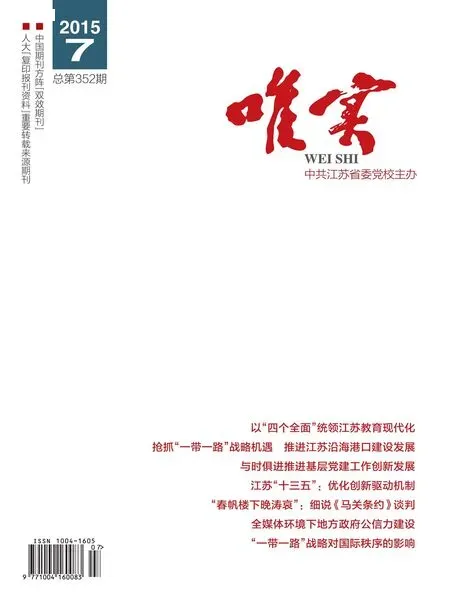我国核安全立法框架探究
张梓太 刘画洁
我国核安全立法框架探究
张梓太 刘画洁
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核能产业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多国核能发展计划被迫搁浅。我国政府在福岛核事故后迅速启动了核安全自查程序,展开对事故隐患的排查与修正,暂停了江西彭泽核电站等审批活动。那么,后福岛时代的中国核电产业究竟何去何从?
一、我国核能产业及安全立法现状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大力发展核电事业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践行减排承诺的首要选择。2012年10月,国务院通过《核电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稳步有序推进核电事业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将达到在运5800万千瓦,已建与筹建核电机组200台左右。未来核电事业将在中国有巨大发展,有望成为我国支柱性能源产业。
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利益冲突进行调整,并将其纳入制度性轨道。我国目前建立了包含三个层次的核安全法律体系:第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宪法》、《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由国务院发布的6个行政法规和47个国家核安全局等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第三,由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70多项核安全导则和180多个技术文件等。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原子能利用方面的基本法,专门法律也只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其立法重点在于污染防治,是从辐射防护的角度防止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因废物排放对环境造成辐射污染,只是核安全立法的向度之一。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从技术和管理角度对核能利用领域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安全导则进行统领、整合的《原子能法》或者《核安全法》,以协调法律冲突,填补法律空白。
二、国际民用核能利用安全立法
核能利用的健康发展与核安全的保障密切相关。因此,国际社会与各核能大国都积极推动核能安全立法。
国际民用核安全条约。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推动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核能安全利用的条约。通过系列公约,明确了纵深防御等核安全基本原则;通过许可证管理制度、检查和评价制度、强制执行制度实现对核设施安全的事前监管;通过国际应急响应体系和国际援助体制实现对核安全的事后监管。形成了以《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为主体的世界核损害民事责任体系,规定了唯一责任和严格责任以降低受害人索赔的难度,限制索赔时效和责任数额以呵护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力。国际条约为各国建立健全本国原子能利用法律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努力方向。
国别民用核安全立法成就。核能安全利用与核能技术开发是核能领域中的两个关键主题,目前核安全立法的体例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制定原子能基本法,其调整领域包括核能技术开发和核能安全利用。世界上有至少36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原子能法》或《辐射防护法》;二是制定核安全法,形成以核安全法为统领的核安全立法体系,至少9个国家颁布了《核安全法》。
美国《原子能法》。美国1954年通过的《原子能法》,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同时规范核能军用与核能民用的原子能基本法。该法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统帅性。表现为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对法律制度的构建注重宏观框架性,不拘泥于细节性规定。第二,协调性。首先,联邦与州的协调性。如2021c条规定,低水平辐射废弃物处理责任原则上由各州承担,但对于能源部研究开发等低放废物的处理由联邦政府承担责任。其次,法律间的协调性。如2019条规定《联邦电力法》的适用,要求州际商业核电活动同时受到《联邦电力法》的约束,避免本法与《联邦电力法》的适用冲突。第三,广泛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表现为:一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涵盖。除了对实体方面的规定,第15分章对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进行了规定,要求可能影响他人利益的许可都应当经过听证程序。二是研究激励与安全保障共进。每项核活动的安全管理中都为研究开发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如2111条第三款规定原子能委员会对副产物用于间接开发的申请人给予优先许可权。三是事前预防与事后补救结合。如2296a条第二款规定,其铀产品出售给美国政府而附带产生副产物的,能源部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并详细规定了补偿数额和通货膨胀系数下的额外补偿。
加拿大《核安全与控制法》。该法授权成立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CNSC)对核能事务实行监管。《核安全与控制法》的主要内容在于明确核安全委员会的设置、构架以及权力范围。依据该法,CNSC实行集体管理,由国会任命不超过7名终身或临时委员,其中一名委员兼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成立执行顾问和委员会秘书处,下设法律服务部、监管业务部门、监管事务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核安全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包括:管理和监督权、司法权、准立法权。
三、我国核安全立法框架构建
鉴于核能安全管理的迫切性与原子能利用之利益格局的复杂性,我国应当在借鉴国际条约和国别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启动核能利用领域的基本法创制工作。由于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根本性冲突,在经济利益诱惑面前,核能技术促进往往享有机构设置、资金支持以及政策支持的优先性,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倾向于保护公共利益,才能实现两种利益的平衡。
核安全监管机构的主导地位确立。核安全监管机构在核安全监管中处于核心与主导地位。作为核安全监管的主要执行者,监管机关唯有保持独立性与可问责性,才能实现有效监管。故立法应当明确以下内容:第一,明确授权,确立核安全局对核安全事务的独立监管权,避免核安全监管机构受到其他部门意志的左右。第二,明确上级机构。我国核安全局内设于环境保护部,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应当将其独立出来,以国家主席或者国务院总理为直接上级,对主席或总理汇报工作,方能保证其独立性。第三,明确权力边界。赋予核安全局领域内准立法权、行政权、准司法权,具体包括制定部门规章、安全导则、指导性文件的权力;颁发核设施、核活动许可证的权力;对核设施运营和核活动的监督检查权;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权;对领域内纠纷的裁决权。第四,明确人事任免权,确保监管者在任期内不会因正常职务行为导致免职,保证监管者监管行为的独立性;第五,明确资金来源。监管者唯有享有完全预算自主权,才有抵制政治干预、经济影响的可能性。目前,各国监管机构的预算主要来源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监管受益者。由监管受益者提供资金,容易造成监管机构对行业的依赖,伤害监管机构的自主权;由政府提供预算,在不利于政府部门利益时,监管机构的决策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由权力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程序授予,才能真正保障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第六,明确核安全局执法人员行政违法、行政不当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
核安全立法的制度框架构建。通过以上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公约、各国原子能领域法律体系的梳理与思考,笔者认为,我国核安全立法应当遵循法律规定的原则性、调整范围的全面性、法律的协调性原则,构建以下法律制度。

核设施许可制度。核设施和核燃料是核安全管理中的核心内容。其中,核设施主要指核燃料循环的设施。其许可制度设计应当包括:第一,许可种类。在综合考虑许可的安全可靠性、许可授予的效率以及国家许可制度的习惯等因素的情况下,保留建造许可、撤销运行许可、设置选址许可更符合核安全保障要求。第二,授权主体。我国目前核安全设施的授权主体是国家核安全局,应当在确认核安全局授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否决权,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核安全决策。第三,许可条件。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条款。第四,许可程序及其文件。鉴于核设施潜在的危险性,许可应当经过申请、安全评估、环境影响评价、听证等程序,从程序上减少错误许可的可能性。
核活动管理制度。在核安全基本法中,应当建立以下核活动管理制度:铀矿开采与加工管理制度、研究堆的运行与退役制度、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活动管理制度、核反应堆的运行与退役制度、核废物的处理活动管理制度、放射性物质运输管理制度、核动力船舶与航空器管理制度、核材料出口活动管理制度、核设施场所的恢复制度。
辐射防护制度。依据辐射防护原则,建立隔离区制度,在核设施及其邻近区域禁止进入和居住;采取屏蔽措施,保护员工和公众安全;完善辐射监测制度和辐射应急制度,运营商和监管组织都有责任进行辐射监测和信息发布,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核损害赔偿责任。核安全法应当对以下几个原则性问题予以明确:一是核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二是责任主体的责任形式;三是赔偿金的支付来源问题。在对《核损害赔偿公约》和其他国家原子能赔偿相关法律借鉴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核安全法应当明确:运营商的唯一责任原则;运营商承担责任的上限以及免责事由,自然灾害不应免除运营商责任;确立三级损害赔偿体系:运营商支付保险金、运营商联盟设立的互助基金、国家的补充保险金。
法律责任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是核安全立法的关键,其责任的承担形式应当具有全面性,即依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应当规定明确的违法行为和责任程度,不能明确规定的应当指定机构另行规定,或者明确可以参照的法律法规。
与核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核能领域立法的滞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将核能安全保障纳入制度性轨道已然成为该领域发展的头等大事,将直接影响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速度与前景。因此,立法机关应当加快立法节奏,尽快出台《核安全法》,以保障我国公民和环境的安全,实现对核安全利用的相关法规规章的统合、引领。
(张梓太:复旦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画洁: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