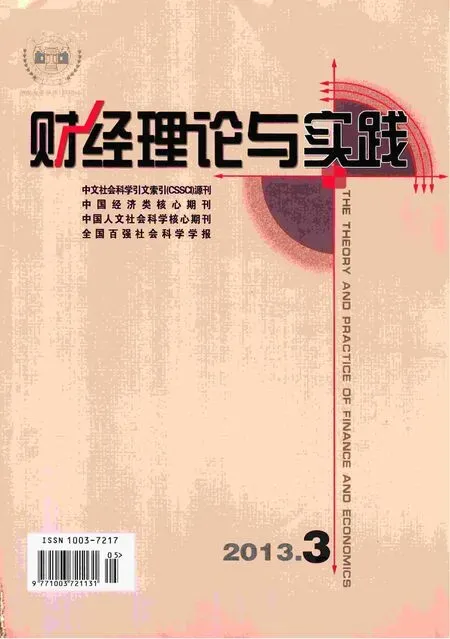中澳反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立法比较
李小明,吴 倩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这部被誉为“经济宪法”的法律,为我国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应当承认,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立法对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关注澳大利亚竞争法律制度。目前,国内对澳大利亚反垄断制度的深入介绍和研究并不多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澳大利亚于1906年颁布了第一部反垄断法《产业保护法》[1],现行反垄断法则是在1974年《贸易行为法》的基础上,历经近40年的完善与修改,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合并后形成的,即《2010竞争与消费者法》。中国和澳大利亚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关系得到全面、稳定的发展[2]。数据表明①,中澳双边贸易和投资有较大的互补性,特别近年来我国有大量投资进入澳大利亚。中澳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上对双方提出了反垄断执法与合作的要求。因此,研究澳大利亚反垄断法是很有必要的。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视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反垄断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用专章进行规定的,涉及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条共有六条,占全部法条的十分之一,可见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之重视。因此研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澳大利亚《2010竞争与消费者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是如何规定的?其制度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原因和背景?与我国的制度相比又有何异同?有何优劣?其立法对我国《反垄断法》完善相应立法有何借鉴意义?中资企业在双边经贸投资活动中如涉及类似问题,应当如何援引与适用该法律制度呢?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对澳大利亚竞争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立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图寻找答案并为今后我国立法之完善提供借鉴。
二、澳大利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立法
澳大利亚《2010竞争与消费者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主要规定在该法第46、46A以及46B节,其中第46节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构成及其认定做了基本规定,而滥用行为种类及具体认定标准体现于判例和相关指导意见中。当然,研究该制度应首先了解其定义。
(一)相关概念及认定标准
1.市场支配力及认定标准。市场支配力是企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先决条件,澳大利亚在法典条文中并没有给市场支配力下定义,但其特别法庭在Queensland Coop.Milling Association案中解释了市场支配力。法院认为:竞争的对立面是过度的市场支配力,当公司拥有市场支配力时,公司可以不受竞争的压力而自行制定价格和买卖商品[3]。根据该定义,公司具有的能够不受竞争者的影响而独立制定价格和实施竞争行为的能力即为市场支配力。
澳大利亚以其法第(3)条和(3A)条规定了认定市场支配力应考虑的主要因素。第(3)条规定:在判断一个公司或数个公司有多大市场支配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公司的行为是否受以下行为的限制进行判断:该公司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行为,数个公司时其中某一公司的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行为;该公司或数个公司的供货商或购货商的行为。第(3A)条规定:在判断公司或数个公司市场支配力时,法院可以根据该公司或数个公司的以下事项进行判断:该公司或数个公司与一方达成或可能达成的合同、约定或谅解;任何对该公司或数个公司有约束力或有效的合约或合约建议②。以上规定主要从主体范围、主体实施的行为以及竞争者的行为来认定公司的市场支配力。在具体实践中,法院认定市场支配力已形成自己的做法:法院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随后将对公司所在市场的进入壁垒进行分析;继而再分析公司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同时,市场范围、需求特征以及买卖双方的规模和数量等因素也是法院综合考虑的因素[4]。
2.滥用市场支配力及认定标准。澳大利亚在其法典中定义了滥用市场支配力且规定了认定标准,其第46(1)条规定:具有实质性市场支配力的公司不得为了下列目的滥用市场支配力:(1)以消除或足以实质性损害市场或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为目的,该竞争者包括公司或法人;(2)以阻止一方进入市场或相关市场为目的;(3)以阻碍或阻止一方在市场上或相关市场参与竞争为目的。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可理解为,滥用市场支配力是有市场支配力的公司实施的以损害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反竞争行为,其行为认定必须以公司具有主观故意为要件。
区分公司行为究竟属于竞争性行为还是非竞争性的滥用行为,法院依据以下因素进行判断。第(4A)条规定:在判断公司是否违反第46(1)条时,法院可以考查:公司是否长期实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及实施上述行为的原因。第(6A)条规定:判断公司是否利用已有的市场支配力实施某种行为,法院可以根据下列某个或所有因素进行认定:该行为是否实质性地源于该公司的实质性市场力量;该公司参与的行为是否依赖于其实质性市场力量;若公司不具有实质市场支配力,该公司是否就不能实施该行为;该行为是否在其他方面与市场支配力相联系,而且法官认定时并不受上述因素限制。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法条规定仅为法院提供某种指引,并非认定的唯一标准。法院考虑的重点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主要依赖于其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不法意图。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表现形式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澳大利亚立法采取了概括立法的模式,其对种类的规定只有该法第(1AAA)条。该条规定:如果公司长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商品或服务,则违反了第(1)条的规定,即使该公司不能或不可能收回因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的损失。本条定义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掠夺性定价行为。依据澳大利亚的大量判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垄断高价、价格歧视、拒绝交易、压榨价格或供货量、捆绑销售等。[5]澳大利亚采取概括性立法可以避免法律滞后性带来的不良效果,法院在具体案例中归纳出的滥用类型,在种类与范围上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滥用行为相似,可见澳大利亚立法的规定与世界主要国家并无不同。
(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责任
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主要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只在少数国家有所规定。澳大利亚反垄断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五篇。澳大利亚法典也仅规定了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未作规定。第76(1A)条规定,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公司,法院最高可处以1000万澳元的罚金;如果认定有违法所得的,则可处以三倍违法所得的罚金;如果无法认定违法所得的,则可处年营业额10%的罚金。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个人,法院最高可处以50万澳元的罚金。第80(1)条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院可以依申请人的申请颁发禁令,以阻止行为的发生。第82节规定:“任何人因垄断行为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救济方式有颁布禁令、处以罚金、没收违法所得、要求民事赔偿等。在处罚幅度方面,罚金的数额相对较高,尤以3倍违法所得最严厉。在民事责任方面,澳大利亚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规定的是惩罚性赔偿而是补偿性赔偿,这与民事责任之补偿性与恢复性功能是相符的。
三、中澳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立法比较
我国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立法规定在《反垄断法》第三章。该法第17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6种表现形式。这种立法方式符合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但与属于普通法系的澳大利亚立法区别甚大。除了立法体例有差异,中澳两国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表现形式、法律责任及其在法典中的地位等是否存在差异呢?
(一)定义及认定标准的比较
1.市场支配地位定义及认定标准比较。与《2010竞争与消费者法》不同,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以及认定标准。澳大利亚法典虽然未直接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但两国对该种行为的理解及其认定标准都是经营者具有独立于竞争者做出价格、销售数量等市场行为的能力;在认定该种行为时,两国都以市场份额、市场行为以及市场壁垒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不同的是,我国立法还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推定条款。而澳大利亚法院认为,不能仅根据市场份额推定市场支配地位,市场份额是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6]。可见,两国关于推定的规定是存在差异的。
笔者认为,两国在推定制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源于两国属于不同的法系,及两国立法价值观的不同。综观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都有根据市场份额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如德国《卡特尔法》第19(3)款,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4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的第五之一条[7];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市场份额在认定时都不能起决定作用。两国在推定制度上的不同体现出两大法系的分歧。前者注重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后者更关注法律的灵活性与自由裁量性。推定制度体现了立法对效率和公平价值的权衡,但这种稍显武断的做法,难免会以牺牲个案公平正义为代价。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尚短,反垄断经验也不丰富,因此,选择推定认定的方法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现实需要。
2.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定义及认定标准比较。我国《反垄断法》没有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与认定标准。《反垄断法》列举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要表现形式,且分别规定了认定和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从法条规定来看,正如学者研究的观点,对滥用行为及其认定可作如下理解: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企业为了维持或增强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的反竞争行为[8]。这一定义具有代表性,该定义也与经合组织及《欧共体条约》的定义相一致,三者都强调滥用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且实施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或说反竞争性。对比澳大利亚的定义及认定标准,可以发现两国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都是从主体的特殊性、行为的违法性两方面着手。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规定更注重行为的目的性,即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法定目的是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标准,而我国的规定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规定主观要件在刑法上比较普遍,大部分罪名的成立都要求主观要件,而世界主要国家的反垄断立法规定主观要件的相对较少,大部分国家和我国的规定一致。例如,日本《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列出16种行为,均以行为“不正当”、“不公正”、或者价格“不公平”作为认定的要件;德国《卡特尔法》则规定了“无实质性正当理由”[9]。澳大利亚对主观要件的规定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归责原则变成过错责任,我国的规定则为严格责任原则,而具有“正当理由”则更像是一种豁免制度。
笔者以为,中澳二国归责原则的相左源于两国对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不同认识。从澳大利亚反垄断实践来看,该国非常重视市场的自由竞争。在昆士兰线业公司案中,法官认为,损害是竞争无法避免的后果。第46节的立法宗旨是通过保护竞争过程最终保护消费者利益,而非竞争者利益[10]。由此可见,法院鼓励自由竞争,并对竞争中产生的损害持宽容态度。保护竞争过程使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法律的天平更倾向于效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要有“法定目的”存在。我国反垄断立法既注重适度竞争的效率性,也注重过度竞争的不良后果,采用严格责任可以有效矫正不良竞争行为,可以说是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来提升效率。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表现形式的比较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在各国立法中都有体现。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了六种典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同时也通过兜底条款揽括了其他未能列举的行为。前已述及,澳大利亚的判例表明,澳大利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包括垄断价格、拒绝交易、搭售、掠夺性定价等。两相比较,两国关于表现形式的规定是一致的,也与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相符,符合世界反垄断法的发展潮流。
(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责任的比较
反垄断立法的法律责任一般分为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我国《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责任规定在第47条和第50条。比较发现,两国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均没有规定刑事责任,处罚方式主要是民事赔偿、行政禁令和罚金;民事赔偿都以损失补偿为限,但两国行政处罚力度不同。澳大利亚规定的行政处罚有上限,有违法所得按三倍处罚,不确定违法所得的按年营业额的10%计算;我国则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澳大利亚行政处罚力度明显大于我国,尤其是3倍违法所得的处罚,有利于打击滥用行为人。我国行政处罚力度虽具有弹性,可以依据行为持续时间、造成后果等因素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处罚幅度;除性质特别恶劣,损害时间特别长的案件,处罚幅度可以低于销售额的10%,这等于相对降低了处罚力度。同时,处罚具有可裁量性也为人们提供了寻租空间,最终有可能导致处罚不公。
(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法典中的地位比较
在反垄断法中,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构成反垄断法三大支柱[11]。对此,因国情不同,各国看法可能不同,立法重视程度也有可能不同。澳大利亚的反垄断制度规定于其法典的第四篇。该篇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单立一章,包括定义、行为效力、行为种类、法律责任和适用除外条款等合计22个条文,为规制该种行为做了详尽规定;从法律责任看,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情节严重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则未独立成章,被放置于该篇“其他规定”中,直接属于规制滥用行为的条款仅有5条。我国《反垄断法》规制上述二种行为均独立设章;二种行为的处罚幅度均为按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罚款,不同的是我国对二种行为均未规定刑事责任。对比可见,与我国不同,澳大利亚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立法并不如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一样重视。
导致以上差异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澳大利亚虽然国土面积770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只有约2100万,其国内市场相对较小,特别从历史来看,小企业远比大企业要多,因此联合行为出现远比滥用行为要多。其二,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进入多元化以及外向化,为更好地维持企业在本国的地位并加大对国外市场的控制,澳大利亚公司洲际间及跨国间的联合行为更加凸显出来,致使澳大利亚修法时持续注重对联合行为的规制。其三,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澳大利亚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改革,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国有电力、能源等方面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则进行了深度改革③。经过改革,澳大利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数量减少,滥用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也许是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被更加重视的另一原因。相比之下,我国人口众多且分布相对集中,国内市场大,改革开放已30多年,至《反垄断法》颁布时,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二,中外大、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均得到了发展,二种垄断行为都经常发生。因此,我国对这二种垄断行为在立法上都非常重视。当然,也许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澳大利亚属于英美法系,判例法为其特征。虽然澳大利亚滥用行为的法条并不多,这种更隐蔽、更复杂、查处更困难的垄断行为由于需要做经济学分析[12],因此,对它的规制只能更多地体现在其判例中。除以上原因外,学界对该种制度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和偏差也会影响该国规制这种行为的立法。
四、澳大利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立法对我国的借鉴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第一天就有了反垄断诉讼,四年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不断出现,虽然数量不及兼并案件,但有几起案件影响颇大。例如,2008年北京李方平律师诉北京网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④,2011年,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宽带接入垄断案⑤。从我国审理这些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案件牵涉面广,影响因素多,调查取证难,审理难度大,因此,必须加强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研究。
首先,我国应坚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独立成章的做法,肯定其在法典中的理论地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为垄断的高级形态,[13]我国当然应重视对其立法,从源头及行为本身规制该种行为。澳大利亚立法及判例法源于并相符于其经济和市场特点,我国应认识到这种立法差异,继续坚持立法与本国国情相符的立场;同时还可借鉴澳大利亚立法完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制度。
其次,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应坚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适用严格责任制度,不需要像澳大利亚那样为其规定主观要件。澳大利亚这样做更重于对市场自由的保护,更重于对个体行为、私权利的保护;由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垄断行为发展的高级阶段,其行为对市场秩序、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福利损害很大,对该种行为采取严格责任制度而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无疑将增强认定及处罚该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再次,尽管澳大利亚法典中没有规定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但两国对该种行为的理解及其认定标准是相似的。在认定该种行为时,两国都以市场份额、市场行为以及市场壁垒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因此,行为人一旦取得这种能力必定在市场份额上有所反应,市场份额应当作为认定该种行为的最重要依据。由于滥用行为较之其他垄断行为具有更隐蔽、更复杂、查处更困难的特点,推定制度将举证责任倒置,对查处这种垄断行为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对我国这种反垄断法执法经验和能力明显不足的国家。
最后,我国应当调整处罚机制,加大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处罚力度。行为人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会考虑违法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如果违法成本远远低于收益,处罚机制将失去威慑效应,因此我国应引入澳大利亚三倍违法所得的罚金制度。我国没收违法所得的现行规定只是没收行为人的非法获利并不具有惩罚作用,如果处三倍违法所得罚金,则法律的威慑作用将大大增加,滥用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我国还应当依据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等因素将“上一年度营业额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划分为不同档次进行处罚,以减少处罚的不确定性,也可使经营者预测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另外,为滥用行为规定刑事责任是有必要的。既然澳大利亚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都规定了刑事责任,而我国立法对规制二种行为同等重视,我国为该二种垄断行为都设定刑事责任应作为将来立法修改的方向。
五、结 论
澳大利亚竞争法的发展历史已有一个世纪,其成熟立法是与其经济和国情发展相符合的。而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才四年,这部历经十余年讨论才最终颁布的法律也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发展的。中澳两国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定义、认定标准及表现形式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基于认识的偏差,二国关于市场支配地位定义及其滥用行为的认定、归责原则、法律责任规定及该制度在反垄断法中的地位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反垄断法》应当借鉴及参考澳大利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继续坚持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制度,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应继续适应严格责任原则。为有效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我国应当加大处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幅度,必要时为其增设刑事责任处罚。
注释:
①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2001~2010年,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4.8倍,而同期中澳贸易额增长了8.8倍;2011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148.4亿美元,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688.1亿元,其中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8.86亿元,在中国对外投资国家中排名第四。
②本文所引用澳大利亚《2010竞争与消费者法》条文的原文参见: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11C00003/Html/Volume_1#param313。
③例如,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澳大利亚电讯公司这些大企业的改革。此外,机场、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也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或承包给一些私营企业。参见:Russell Smyth,翟庆国:“澳大利亚国企改革实践及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启示”,载《财经问题研究》2001第7期。
④朝阳法院网:http://cyq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37。
⑤新浪网:http://tech.sina.com.cn/t/2011-11-09/12106296381.shtml。
[1]Deborah Healey.Australian trade practices law[M].Sydney:CCH Australia Limited,1993.2.
[2]汪素芹.推动中澳经贸合作发展的基础、契机与思考[J].世界经济研究,2005,(5):75-79.
[3]S.G.Corones.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australia[M].Sydney:The Law Company Book Limited,1990:71.
[4]Anne Hurley.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commentary and materials[M].Sydney:The Law Company Book Limited,1995:118-128.
[5]John Duns,Mark J Davison.Trade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M].Sydney:Impact Printing Pty Ltd,1994:158.
[6]Anne Hurley.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commentary and materials[M].Sydney:The Law Company Book Limited,1995:126.
[7]尚明.主要国家(地区)反垄断法律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812.
[8]李小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6.
[9]肖江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正当理由”[J].法商研究,2009,(5):90-98.
[10]S.G.Corones.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law[M].Sydney:The Law Company Book Limited,1994:191.
[11]王晓晔,﹝日﹞伊从宽.竞争法与经济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74.
[12]李小明.论反垄断法理论体系之构建[J].法学杂志,2008,(3):81-83.
[13]李小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