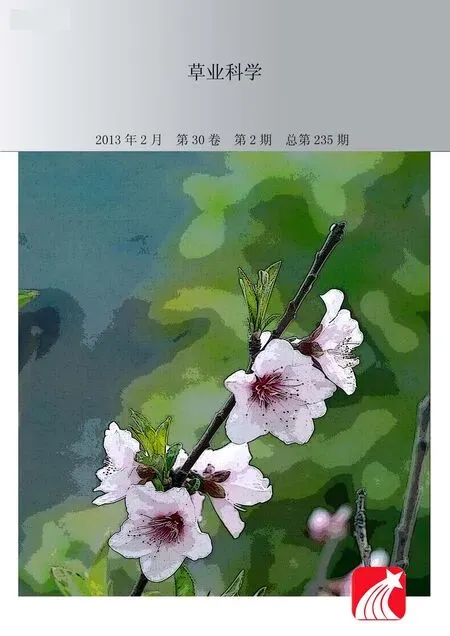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奶业技术扩散及其影响因素
李琦珂,曹幸穗
(1.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 10012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干部和革命青年。因敌人封锁,物质匮乏,边区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供应制。抗日军民由于领到的粮食极其有限,普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为了给中央领导、伤病员及其他抗日军民增加营养,边区政府于1940年创办了光华农场。
光华农场可被视作边区奶业科研的重要“基地”。自创办以来,农场科研人员便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大力开展奶畜育种、饲养、管理、防疫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试验制作奶酪、奶皮、奶油、酸奶等奶制品,并开设奶牛、奶羊养殖场,生产鲜奶,制作奶品,从而极大地满足了边区伤病员、婴幼儿及中央领导的营养之需。尽管抗战时期条件简陋,光华农场科研人员还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研制出一套包括育种、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奶畜养殖技术,积累了奶品加工的初步经验。其奶业技术和经验经边区展览会和《解放日报》的宣传[1],经营养研究会和中央医院的推广[2]和饮奶嗜好者的大力鼓吹[3],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民众的纷纷仿效,不知不觉中引发了民间奶业技术的嬗变。
1 边区奶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的奶业技术服务体系逐渐建立并不断趋于完善,对于边区奶业技术的扩散起到了引导、示范作用。大致讲来,边区奶业技术服务体系包括光华农场等科研机构,家畜防疫委员会等防疫组织,中国营养学会等普及单位,《解放日报》及“科学园地”等宣传阵地,边区展览会等交流平台。
1.1光华农场奶业科研
1.1.1奶牛、奶羊育种工作 光华农场十分重视育种工作,引进黑白花奶牛后,尝试以纯种繁殖的方法来优化种群。1945年美国畜牧专家阳早(1918年11月9日出生于美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学习农牧专业。1946年8月携妻子来延安,为我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到来,给育种工作带来新的技术。为充分发挥良种公牛的配种能力,农场开始使用冷冻精液进行人工受精,使大范围种群优化成为了现实[1]。
光华农场的科研人员还开展了河南奶羊累进育种工作,以河南奶羊改良本地山羊,来实现奶量的不断提高。1944年有第1代累进种奶羊19只,第2代累进种奶羊10只,第1代产奶量平均0.75 kg,第2代产奶量更高[4]。
1.1.2研制牛瘟血清及疫苗 尽管边区养牛业不断发展,但因瘟疫造成的牛的死亡率高达36.4%[5]。据统计,仅1943年就因牛瘟死亡牛7 800头[6]。为此,光华农场与国际和平医院的科研人员合作研制了牛瘟血清疫苗,并进行批量生产,投放边区各地,积极预防治疗,终于在1945年根治了牛瘟。
1.1.3扩大奶畜饲料来源 为选育和推广苜蓿(Medicagospp.)[4],光华农场组织群众在路边大量种植苜蓿,并尝试与大豆(Glycinemax)间种,效果很好。农场还选育推广了金皇后玉米(Zeamays),为边区奶牛提供了质优、量多的秸秆饲料[1]。不仅如此,光华农场积极倡导群众在夏秋之末种植燕麦草(Arrhenatherumelatius),因为燕麦草既可做草,又可做料,喂奶羊最好[4]。秋天割存之后,可储作冬用。为了增强冬季饲料的适口性,农场还推广青贮饲料的制作方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
1.2边区奶业技术扩散渠道
1.2.1边区展览会 为发展经济,推进技术进步,边区几乎每年举办规模不等、内容各异的展览会。据统计,1939-1944年边区开办展览会就有10多次[1]。如在1941年光华农场展览会上就曾展出了农场用牛、羊乳试制成的干酪[2]。1944年卫生展览会曾设想展出以母乳营养、牛羊乳营养、母乳与牛羊乳混合营养不同效果的对比分析材料[7]。
1.2.2营养研究会 1942年7月,中央医院建立营养室,专门利用牛奶为病人调配流质饮食[7]。 1943年2月3日,中央总卫生处成立营养研究总委员会,下设实验组、调查组和宣传组,研究饭菜谱,并送中央医院大灶试验,进而推广到各机关,其中就有以牛奶配餐的食疗法[3]。
1.2.3《解放日报》 抗战以来,《解放日报》及其专栏“科学园地”进行了大量的科技报道,成为奶业科技宣传的一大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3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报道有关奶畜养殖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6],并且有力地配合了营养研究会及中央医院牛奶配餐食疗法的推广工作[2]。
2 边区奶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
2.1奶业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 奶业科研技术的扩散,不仅仅是以扩散源为中心的单向轮状辐射,而是一条“奶科技-奶生产-奶科技-奶生产”的环状闭合链。这一环形闭合链的驱动因素,应该是边区奶需求的不断增长。
2.1.1当地老百姓的日常饮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老百姓物质生活依然相当清苦,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边区的广大农村,也同样发生在“红都”延安。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土壤贫瘠,降水偏少,所种作物多为抗旱耐瘠品种。据边区政府统计,1944年整个边区麦类播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23.4%,而谷子占到22.3%,糜子占到13.9%[8]。加之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边区物质贸易的封锁,当地老百姓的日常饮食,往往是以麦面、小米、黄米为主,辅以豆类、荞麦、高粱等杂粮。在这种情形之下,边区百姓急待肉、蛋、奶的补充,以使百姓身体日渐强健。
在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陕甘宁边区实行粮食供应制度。普遍百姓一年种地所得粮食,除却上交边区政府的之外,剩余已不算太多,因而在百姓的日常食谱中,杂粮粗食居多,很少有细粮和肉食。一旦遭遇灾年,许多农民连一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日常营养需求,对于奶业在农村的扩散是急需的,也是最有潜力的。
2.1.2机关工作人员饮食状况 抗战时期,边区的部队、学校和机关普遍实行供给制,供给粮食以小米为主。按照边区政府的规定,“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9]。即使是对知识分子云集的延安马列学院,日常饮食的供给标准也只能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10]。在供给制下,机关干部的饭菜品质比民众高了不少,但仍缺乏营养,因此,急需肉、蛋、奶的补充。
2.2奶业技术扩散的制约因素 民间奶业技术是相对于光华农场等公营农场奶业科研而言的,是边区奶业技术的扩散场所。就其实际情形而言,边区奶业技术的传播与扩散,因受经济条件、饮食习惯、市场流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
2.2.1经济条件 边区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畜牧业。但就养殖牛羊的目的而言,养牛是为耕地役使,养羊是为了吃肉、剪羊毛,当然,养牛、养羊还同时为了取粪肥田。有一度,边区百姓只能用黑豆糊糊充饥[11],有时连细粮、蔬菜都很难吃到,更难吃到牛奶、羊奶等营养品。在边区,牛奶、羊奶几乎成了奢侈的代名词。除专供婴儿以外,人们在生病时才能够喝上牛奶[12]。
2.2.2饮食习惯 边区以山地为主,老百姓多为汉族,饮食以糜食为主、面食为辅,不大习惯奶(而且山羊奶有膻味)及奶制品。边区自古农业资源贫乏,且自清代以来常罹兵火[13],造就了百姓吃苦耐劳、朴素节俭的精神,表现在饮食观念和生活习惯上,多吃粗粮,少取精食,视饮奶为奢侈。只有在遭遇灾荒时,百姓才不得不以羊奶活命(华池遭灾后许多百姓曾以羊奶充饥[6]),安塞老人方生荣深有感触:“过荒年不要杀母羊,一只羊(的奶)能活两个人”[6]。
2.2.3市场流通 牛奶(奶品)的适量流通,能够刺激奶户养牛的积极性。可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尽管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开办消费合作社,供给群众所需,并且除了边区合作社外,灵活小巧的货郎也在群众生活用品的交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牛、羊奶(及奶制品)在当时很难见于市场流通。这一方面是因为牛、羊奶不耐贮存,另一方面与民间奶产水平低、加工技术与设施落后造成的奶制品数量有限有关。
应该说边区牛、羊的大量繁殖会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奶牛、奶羊养殖科研的发展,可以促进奶牛、奶羊的大量养殖;而奶消费群体规模的扩张以及奶消费数量的增长,也会拉动奶牛、奶羊的大量养殖,这是一条奶业科研扩散的良性路子。可事实上边区的牛、羊奶的产能严重不足,兼之鲜奶及其制品市场流通不畅,奶需求的满足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而奶需求的徘徊不前反过来又影响、制约了奶业科研的继续扩散。
3 结语
在现代奶业发展史上,我们不能忘记光华农场等延安奶业科研单位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在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以光华农场为代表的奶业科研机构,把先进的奶畜养殖、奶品加工技术和科学的奶品消费意识,传播到边区的每一个角落,泽惠了奶畜养殖的每一个农场、每一家农户。
但从另一角度去分析,全新时代风尚与古老饮食习惯的交汇,哺育婴儿需要与经济条件制约的交锋,奶品加工技术滞后与奶品市场流通不畅的交织,使得抗战时期边区奶业科研扩散既呈一种起步、发展的良性态势,又显规模较小、曲折往复的特点,情形比较复杂。无论如何,光华农场奶业科技的发散与传播,毕竟启蒙了边区民众的奶消费思想和习惯,从而为新中国奶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北京:中央学术出版社,1988:58,150,162-163,442-443.
[2] 赵炎.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1939-1950[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175,177.
[3] 中国革命博物馆.解放区展览会资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50,204.
[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室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光华农场过去工作总结(从内容看可能是一九四四年文件)[A].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室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98,746,750.
[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室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三十一年度(1942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A].见: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378.
[6]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室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 人民生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46,172,384.
[7] 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3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150.
[8]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95.
[9]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M].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14.
[10] 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82.
[11]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70-72.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323.
[13] [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