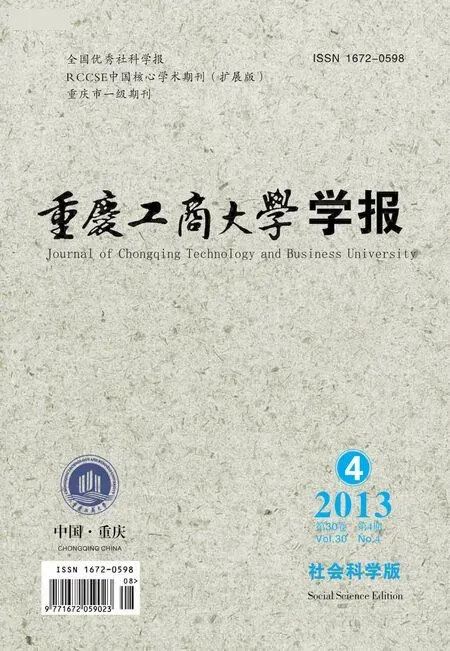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既遂形态*
秦 蜻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重庆 401147)
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具体罪名的犯罪形态,学界大多主张用构成要件既遂说来评断一个犯罪行为是否既遂,该说对刑法中既遂点明确的结果犯、危险犯、举动犯有指导意义,但对刑法中既遂点不明确的某些行为犯如何理解却容易出现争议。刑法法条对本罪只作了行为方式和处罚结果的表述,没有明确规定本罪的既遂形态,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解不一致导致适用标准不一致,这直接影响了对本罪的准确量刑。对此,笔者认为对这类既遂点不明确的行为犯,在司法实践中应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指导,综合考量行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最终确立其既遂点。本文将结合实际案例来探讨如何确立本罪的既遂形态。
一、本罪的犯罪既遂形态争议
对于本罪的犯罪既遂形态的争议目前主要有既遂结果说、既遂行为说、既遂着手说、既遂构成要件说。
(一)既遂结果说
是否事实上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作为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否则便是未遂。[1]其缺陷在于将实际发生了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结果作为本罪既遂标准,按照此学说司法机关耗费高额的司法成本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仍然不能认定帮助犯既遂,显然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查处和对本罪的惩处。对犯罪分子的查处除了在法律上过了追诉时效和犯罪嫌疑人死亡无法追究外,事实上永远存在追究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对犯罪分子无法追究时才能追究本罪既遂责任在逻辑上自相矛盾。
(二)既遂行为说
以行为人实施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行为为构成既遂的标准,并不要求实际发生了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结果。[2]行为说缺陷在于只是笼统地以实施一定的行为作为既遂标准,却没有明确行为达到何种程度为既遂,由于缺乏具体的标准,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三)既遂着手说
本罪是举动犯,即行为人的通风报信、 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一经实施,犯罪即告既遂,并认为由于行为人一着手实施本罪行为,犯罪即成立既遂,所以本罪不存在未遂形态。[3]其缺陷在于,举动犯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法律将预备性质的行为提升为实行行为的犯罪。《刑法》将本属于预备阶段的“着手”行为上升为该罪的实行行为是因为这些预备行为一旦着手实施危害性很大,为了打击和防范犯罪发生才规定这些犯罪为举动犯。如《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二是教唆煽动性质的犯罪构成,如第249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95条传授犯罪方法罪等。这些犯罪的实行行为都是教唆性、煽动性的行为,针对大多数人实施,旨在激起多人产生和实行犯罪。考虑到这些犯罪严重的危害性及其犯罪行为的特殊性质,法律也将其规定为举动犯。很显然,本罪不属于该两类范畴。[4]将本罪定为举动犯,行为标准过于苛刻,不利于分化瓦解犯罪,降低司法成本。此外,该说认为举动犯不存在未遂形态也不恰当,因为举动犯也存在手段不能犯的未遂。[5]
(四)既遂构成要件说
将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是否具备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这是外国刑法理论界中较为通行的观点,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6]按照这种观点,帮助人的犯罪行为具备了刑法417条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就成立本罪的既遂。其缺陷在于: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具备了分则的全部要件就是既遂要件,具备分则具体条款的全部构成要件是评断该罪的成立要件而不是该罪的即遂要件。无可否认,某些犯罪的成立要件和既遂要件重合,如举动犯、危险犯,但结果犯与行为犯却另当别论。犯罪行为是否具备了全部构成要件,在不同犯罪中有不同的表现。以本罪为例,刑法第417条只规定了主体+行为+处罚结果,司法实践中对本条中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是结果、目的、还是行为存在争议,即便是将其当成行为,也存在举动犯、危险犯、过程犯的争议。用既遂构成要件说来解释本罪的既遂形态缺乏具体标准,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司法解释为“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实施的具体行为”模式,该司法解释将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变为主观要件,使其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要件属性,该司法解释虽然方便了实践操作,客观上却改变了刑法对本条的立法模式。刑法对本条款之所以没有规定主观要件,是因为本罪的主体是具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有条件知道查禁方案、有能力辨别是否是犯罪行为,对其主观要件无需再规定。司法解释中“目的+行为”模式立法,忽略了司法实践中主体认识因素及行为、犯罪对象的意志及行为对本罪犯罪形态所产生的影响,不符合犯罪认定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二、对本罪犯罪既遂的理解
本罪属于渎职类犯罪,目前我国渎职类犯罪共有35个具体罪名,从刑法对具体犯罪是在客观行为之外还规定有某种特定要素以及规定何种特定要素来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罪状中规定某种结果要素的渎职罪,称为结果犯;二是罪状中规定“情节严重”要素的渎职犯罪,称为情节犯;三是罪状中同时规定某种结果要素和“情节严重”要素的渎职罪;四是在罪状中于客观性之外未规定任何特定要素的渎职犯罪。[7]本罪属于第四种情况,罪状仅仅是对犯罪构成的描述而非犯罪既遂的表达,因此片面地将犯罪构成中的“行为”理解为既遂的标准是错误的。刑法417条对本罪表述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而非“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或者“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本身就是以“行为”而非“结果”或者“目的”作为本罪构成要件。本罪中行为方式是“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帮助行为达到什么程度方构成本罪,还需具进一步讨论。
根据行为犯既遂的理论,行为一经着手并不一定构成既遂,而是以行为人在着手实行行为过程中,达到了法律要求的程度时作为既遂标准[8]。行为犯并非一旦实施犯罪行为就成立既遂,它也有中止、未遂两种状态。在行为犯的范围内,根据犯罪自然状态中进程时间的不同以及各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紧急程度,规定了不同的既遂时间阶段。这样可以把行为分为举动犯、过程犯、危险犯[9]。举动犯指一着手实施犯罪,刑法就认为是构成了既遂;过程犯是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并不立即成立构成犯罪既遂,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当行为的实施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可以构成既遂;危险犯不但需要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该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还需要达到有出现危害结果的危险时才构成既遂。以贩卖毒品为例,需要买卖毒品成功构成既遂,买与卖系两个行为具有过程性;而运输毒品一旦开始运输即构成犯罪系举动犯。从本罪的自然属性来看,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需要帮助方与被帮助方配合完成,犯罪过程分为帮助方获取信息或者双方共谋——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犯罪分子”积极配合——犯罪分子采取行动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成立未遂、中止的时间性与可能性,其自然属性系过程犯。从本罪的社会属性来看,本罪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举动犯、危险犯那样的程度。列入刑法中的举动犯是为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而将本属于预备阶段的行为上升为实行行为,本罪的预备阶段是“帮助方获取信息或者双方共谋”。列入刑法中的危险犯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虽然本罪的行为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存在侵害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危险,但只是侵害了某一特定的刑事法律关系,并没有达到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将其纳入危险犯的范畴并不合理。从立法上来看,刑法417条只对本罪的行为方式和如何处罚予以表述,没有将本罪的预备行为或者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本罪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决定了本罪属于行为犯中的过程犯,从本罪的具体犯罪过程分析,笔者认为应以犯罪分子获得帮助后着手实施逃匿行为时为既遂点,即当行为人实施的帮助行为可能妨害国家对犯罪分子实施追诉活动时即为既遂。
三、本罪既遂状态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帮助尚在追捕中的犯罪嫌疑人逃避处罚,二是帮助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逃避处罚。在此笔者将结合两个实践中的两个案例具体分析本罪在不同情况下的犯罪形态。
案例一:2009年9月19日,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某派出所上班期间,利用其保管的“数字证书”在公安内网查询到其好友田某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上网追逃,同案人还有黄某、汪某等人,就把田某等人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打印一份。由于张某没有联系上田某,便将追逃信息表交给王某(黄某的姨妈,田某的表妹),叫其通知田某逃匿,王某告知张某其听说田某已被抓获,并拜托张某帮忙打听,张某表示同意。随后王某当着张某的面给黄某打电话告诉其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并叫其潜逃,张某随后也接过电话授意黄某潜逃。经查明:公安机关以田某、黄某等人非法拘禁案于2009年9月8日被立案侦查。同月14日,黄某、田某作为犯罪嫌疑人被网上追逃,田某于17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黄某至今未归案。最终田某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0年3月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决书未认定田某、黄某犯有非法拘禁罪。
张某通知黄某逃匿,黄某最终被证明无罪,如何认定张某行为的犯罪形态。
实务中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黄某既然被证明无罪,则张某帮助的就不是“犯罪分子”,当然就不构成本罪,即“司法裁判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417条的“犯罪分子”应广义理解,对此又有“立案侦查说”“刑事受案说”“材料反映说”[注]“司法裁判说”认为“前案”是否构成犯罪,应以最终司法裁判为准,在此之前,任何个人不得将其确定为罪案。“立案侦查说”认为“前案”只要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进入实质性刑事追究程序即可认定该“前案”属刑事罪案,不必以最终裁定确定。“刑事受案说”认为“前案”只要经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以刑事案件正式受理即可。“材料反映说”认为“前案”只要有举报、自首、报案等材料即可认定。——参见蔡先初、胡金国.渎职罪中“前案”的确定标准[J].人民检察,2002(9):35。几种标准,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应作广义理解,作为具有查禁职责的司法人员认知程度远高于一般民众,只要其知道帮助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有犯罪事实仍予以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则可以推定其主观知晓是“犯罪分子”,至于该“犯罪分子”是否最终被司法认定有罪,不能成为阻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和追诉的理由,如果将此处的犯罪分子作只有经过法院判决为有罪的狭义理解,势必会妨碍对案件的侦查,从而导致放纵罪犯的后果。分析张某帮助行为的过程来看,张某提供的帮助行为得到黄某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由于不能及时查找到黄某,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导致相应的刑事法律关系的待定状态,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侦查和追诉活动,系既遂。用主客观相统一原理分析,张某符合主体、主观、客观要件,尽管最终证明黄某不是犯罪分子,却不能因为事后没有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来否认先前的帮助行为没有给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带来困扰。因为在该行为过程的即遂点上已经侵犯了本罪的客体。
张某让王某通知田某逃匿,而通知之前田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张某虽然有通风报信的行为,但通风报信并没有实际到达田某处,田某在此之前已经被抓获,张某就不存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可能性,因此张某不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张某构成本罪,系未遂。在刑法理论上,以行为的实行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分为:能犯的未遂与不能犯的未遂。能犯的未遂是指犯罪行为实际有可能达到既遂,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达到既遂而停止下来。不能犯的未遂是指犯罪人对有关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而停止下来。我国《刑法》23条第1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从张某帮助行为的过程来看,张某帮助行为尚未实际到达黄某处,黄某就已经被抓获了,张某帮助行为不可能发生致使犯罪分子逃匿的结果,在本罪的既遂点上没有妨害司法机关正常追诉活动,按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张某符合本罪的主体、主观、客观要件,但实施帮助行为时并不能实际侵犯本罪的客体,属于不能犯的未遂。
几种假设:
1.若张某误认为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黄某系自己的朋友黄某,遂通知自己的朋友黄某逃匿,该黄某误以为自己触犯了刑法而逃匿。张某把非犯罪对象当成了犯罪对象,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中的对象认识错误。张某的帮助行为不会对司法机关追诉活动造成困扰,不构成本罪。
2.若张某让王某通知田某潜逃时,田某已经死亡的,田某系公安机关追逃的对象。系对象不能犯的未遂。
3.如果张某通知黄某逃匿,黄某没有逃逸反而自首。这种情况下张某是否构成既遂存在争议。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理论,张某的通风报信行为已经在其主观意志的支配下到达了黄某处,张某的帮助行为已经完成,客观上黄某没有逃匿反而自首,并没有达到妨害司法机关追诉的程度,系未遂。张某类似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被教唆人未犯教唆之罪行,张某系未遂。
4.如果张某通知王某,让王某通知黄某逃匿,王某未通知,成立未遂。
5.如果张某通知王某转通知黄某,随即后悔又骗王某说黄某并没有被追逃,系自己看错了,王某就没有通知黄某,成立中止;如果张某后悔及时阻止王某通知,但王某仍然执意通知到黄某,黄某潜逃,构成既遂。
6.如果张某告知王某,让王某通知黄某逃匿,被蔡某偷听到,蔡某系黄某的朋友,王某没有通知黄某逃匿,蔡某私下通知了黄某逃逸。这属于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即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事实上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行为人误认为是自己行为造成的,行为人应负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即张某构成本罪的未遂。
7.张某未经授权私下通知王某,让王某通知黄某叫他来自首,黄某逃匿,则张某对黄某的逃匿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由于本罪系故意犯罪,所以主观过失不成立本罪。
8.张某在与王某交谈中,谈起黄某被追逃,并没有叫王某通知黄某,王某私下通知了黄某,黄某逃匿。由于张某明知王某与黄某系亲戚关系,交往密切,张某作为公安人员有保密的义务,对王某通知黄某系放任,主观上是一种间接故意,构成本罪既遂。如果张某不知道王某与黄某存在亲属、朋友关系,则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不成立本罪。
案例二:2008年11月李某因涉嫌抢劫罪被羁押在看守所,其亲属买通管教,希望管教能提供帮助,管教帮助其通风报信,由于李某及证人的翻供,本案被退查了2次,最后李某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分析:行为人帮助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处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提供便利条件,帮助犯罪嫌疑人逃离羁押场所,这种以犯罪嫌疑人逃出羁押场所时为既遂。如果帮助人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而犯罪嫌疑人临时改变主意,不愿意逃离羁押场所或者因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无法逃离羁押场所,帮助行为人系未遂。
另一种是通过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或者隐匿、毁灭、伪造证据,致使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疑罪从无”被释放的,帮助行为客观上使犯罪嫌疑人逃脱了处罚,给司法机关的正常追诉活动造成了严重困扰,系本罪既遂。如果因为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或者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但司法机关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收集到了关键证据将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的,帮助人仍然系本罪既遂。如果帮助人通风报信教唆证人或者同案犯作伪证,但证人或者其他同案犯并没有作伪证的,帮助人虽然有帮助行为,但该帮助行为并没有给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带来实质不利影响,系未遂。
[参考文献]
[1] 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2197.
[2] 韩耀元.渎职罪的定罪与量刑[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 2000:557.
[3] 赵秉志.犯罪停止形态适用中的疑难问题研究[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11-722.
[4] 高铭暄.刑法专论(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94-295.
[5] 马克昌.犯罪通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99.
[6] 高铭暄.刑法专论(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90-291.
[7] 肖中华.渎职罪法定结果、情节在构成中的地位及既遂未遂形态之区分[J].法学,2005(12).
[8] 刘沛谞,陈幸欢.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刑事一体化纬度的考量[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9] 魏修臣.行为犯的概念及其未完成形态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