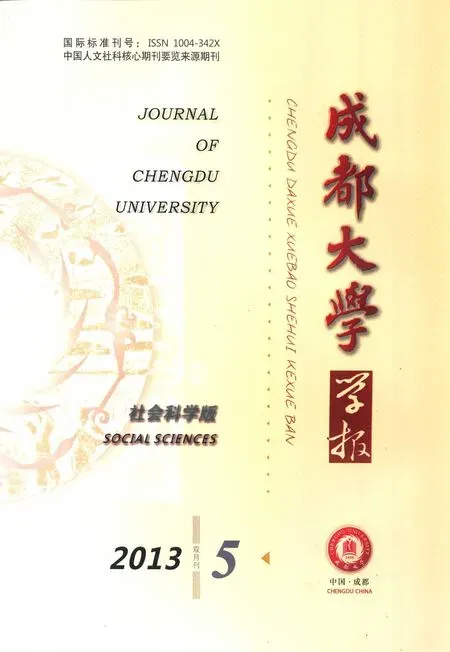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与翻译文学
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与翻译文学
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
留法勤工俭学;法语学习;象征主义;影响;接受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研究,学界取得了很多研究成就,而我们仍然需要寻出李劼人与法国文学的事实线索。1919年12月李劼人赴法国留学,后入蒙北烈大学、巴黎大学。在巴黎通讯社和《华工旬刊》任编辑。1924年9月回国,从1921至1949年,李劼人翻译法国长、短篇小说和剧本20余种。在一些回忆散文中,还可见李劼人一些生活片段的描述,《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生活片断》、《李宁在巴黎时》、《鲁渥的画》、《法人最近的归田运动》、《正是前年今日》、《法之鸡零谭》等叙述了李劼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经历闻见。曹聚仁《海外有这么一个文字知己——曹聚仁谈〈大波〉》写道:“我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李劼人的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李氏,四川人,受法国写实主义大师佛罗贝尔、左拉、莫泊桑的影响甚深。他写了一连串庚子拳变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之迹为主题的小说。”[1]P10
从时间上看李劼人的法语文学翻译,1919年翻译了卜勒浮斯特(Marcel Prévost)《火》(Au Feu)、《忠荩》(Dévouement)、《恩惠》(Grâce)、《酒馆中》(Au Cabaret),1922 年翻译了鲁意士(Pierre Félix Louis dit Pierre Louÿs)《斜阳人语》(Dialogue au soleil couchant,1903)和莫泊桑《人心》(Guy de Maupassant,Notre Cæur,1890),1923 年翻译了卜勒浮斯特《和解》(Renseignments)、歹里野《诺厄尔节之前一日》(Claude Adhemar André Theuriet,La veille de Noël)、都德《小物件》(Alphonse Daudet,Le Petit Chose,1868)、拉魏党(Henri Léon Émile Lavedan)《烦恼》(Tourments),1924年翻译了卜勒浮斯特《妇人书简》(Lettres de femmes,1892)和《斯摩伦的日记》(Journal de Simone),1925年翻译了福罗贝尔《马丹波娃利》(Gustave Flaubert,Madame Bovary,1857)、都德《达哈士孔的狒狒》(Aventures prodigieuses de Tartarin de Tarascon,1872)、保尔·马格利特《离婚之后》(Paul Margueritte,Après le divorce)和《虫》(L’insecte),1926年翻译了爱德蒙·龚枯尔《女郎爱里沙》(Edmond Huot de Goncourt,La Fille Élisa,1877)、罗曼·罗兰《彼得与露西》(Romain Rolland,Pierre et Luce,1920),1927-1928年翻译了马郎《霸都亚纳》(René Maran,Batouala,1921),1931年翻译了福罗贝尔《萨朗波》(Salammbô,1862),1934年翻译了发赫尔《文明人》(Claude Farrère,Les civilisés,1907),1944 年发表出版翻译作品威克妥·马格利特《单身姑娘》(Victor Margueritte,La Garçonne,1922)、左拉《梦》(Émile François Zola,Le Rêve,1888),其中有11个中长篇小说,多位作者(鲁意士、卜勒浮斯特、拉魏党、歹里野、威克妥·马格利特等)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发赫尔《文明人》获得1905年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马郎《霸都亚纳》获得1921年龚古尔文学奖。所涉及期刊包括《少年中国》、《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川报·副刊》、《新新新闻·柳丝副刊》,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重庆作家书屋、人言社、中西书局,舒新城、姚篷子作为李劼人的出版界好友,推荐介绍和接纳了李劼人的多部译作。1937年以前,李劼人及其翻译活动是限于极少数的期刊出版社联系,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一些作品从翻译完成到发表、出版在时间上相距两年,这表明期刊和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者,复杂的人际关系对翻译现象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李劼人法国文学翻译实践中,重译的现象是明显的。1885-1935年法国小说的非写实因素明显进入李劼人的文学视域,但20世纪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确乎没有出现在李劼人的翻译批评中。
一 早期创作与翻译文学
晚清至民国初年,现代中国生起了林林总总的批判思潮和异域色彩的理想主义思潮以及普遍流行的悲观情绪。现代中国似乎完全是一个可恶的、无可救药的、善恶分明的社会,这构成了黑幕小说的一个基本叙事的结构趋向。民国初年,主要在上海,多种现代期刊均刊载游戏的、趣味主义的批判小说,赤裸裸地描绘现实,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好异猎奇的普遍阅读口味以及文学娱乐的一般需求。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写法归于自然主义,但确实与从日本、英语文学中传入的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影响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2]李劼人《〈小东西〉改译后细说由来》回忆道:“更知道了几年前所萦回于脑际,而为主编者不甚重视的《知县下乡》、《猎帽记》两篇,原来也是都德的作品。从此,在未能直接阅读法文之前,都德的文章,已是为我所爱好。及至数年后,能够读法文了,故在中华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作第二部翻译时(第一部译的是莫泊桑的《人心》,曾于民国二十年改译过),便选中了《小东西》这部书。”[3]P590
1913年李劼人在《晨钟报》上发表《游园会》,这是现代中国最早的白话散文(或者短篇小说)之一。李劼人《李劼人谈创作经验》回忆道:“看了《块肉余生述》,颇有启发,就想写回忆。回忆儿时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上私塾、背生书,吃了不少的苦头,我就把这个回忆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儿时影》,以后又陆续写了五六个类似的短篇。”“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看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官场中许多怪事,又读了林琴南译的《旅行述异》,这部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学习他的写法,把我所见的社会生活,写成一个短篇,叫《盗志》,揭露官场黑暗。”[4]P12伍加伦《李劼人与法国文学》写道:“如司各德的《撒喀孙劫后英雄略》、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华盛顿欧文的《旅行述异》等,林译小说引导李劼人跨入了文学之门。通过外国小说的广泛阅读,初步了解了外国作品常用的表现手法,并在外国文学直接启示下,开始了白话文学的写作。”[5]P60
1923年刊载于《少年中国》的《同情》是日记体的(纪实)小说,表现出鲜明的纯客观的描写,李劼人以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亲身经历的一次住院事件和小城养病为素材,近似把实质的对象一丝不走地写下来,心灵的对象却不涉及。李劼人《同情》中的整个罹病事件,虽未与实验医学相关,显然翔实的医护的细节被突出,并追求医学的准确,例如“当医生巡视时,室中清静极了”一段,以极致的客观之叙述笔调,把真实的观察从实质描写、人物的主观和叙述者的情感被有效地涤除,故事的虚构被悬置起来,这些写作的特征在李劼人留法之前创作中是模糊而不可分辨的。在《同情》中,李劼人提到了都德《小东西》(第二部,第六节“皮埃罗特的故事”,第七节“红玫瑰和黑眼睛”)里的情人皮埃罗特小姐,并与看护士沙朗小姐对比。沙朗小姐“漆黑一双眼珠在修长的睫毛里走得和金刚石一样”,“绒花似的一对澄清黝黑的大眼睛”,《同情》中还写到一个看护士玫瑰姑娘,这恰是都德《小东西》的投射形象。在爱情的论题上,李劼人在《同情》中还提到了莫泊桑《人心》中的毗尔伦夫人,当然《同情》中没有出现类似的形象,《同情》没有更多的故事,“他高兴极了——巴黎女子的虚荣心直可称为世界第一,不仅是她们的风致,她们的艳冶,她们的装束——把编贝似的牙齿一起露出,握住我一双手道:‘你真是一个可爱的调皮的少年!你几时出院?’”《同情》中并非偶然一次出现这种反讽的叙述,而往往可以在莫泊桑的小说中不期而遇,叙述者的客观立场和理性的观察——判断是反讽的基础,莫泊桑对李劼人的启发显然并不限于此,莫泊桑提供了太多人物的原型,李劼人显然清楚地认识到了。也就是说,都德和莫泊桑的小说人物已是先决存在的形象,影响了《同情》中的人物和思想,平民家庭与平民医院所表露的同情或者爱心,被细腻不繁地表现出来,或许还有更深隐的启发李劼人《同情》的创作。迄至1923年,李劼人翻译过卜勒浮斯特《和解》、《火》、《忠荩》、《恩惠》、《斯摩伦的日记》、《妇人书简》,莫泊桑《人心》,都德《小东西》,似乎卜勒浮斯特对李劼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作用,李劼人《同情》表现出对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件、平凡的情感之真切叙述,似乎近于福楼拜-左拉一派的主张,但确乎走出自然主义的“感情与理想的歧路”,到此,我们已经无法进行更深的考察。李秀卿、龙岗《李劼人和法国自然主义的关系》认为,“比如1923年的传记体中篇《同情》就是以他在法国巴黎住院期间的经历写成的。伍加伦认为可以把《同情》看作是李劼人从早期的‘漫画法’到后期的‘绘画法’过渡的一座桥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是在他研究了自然主义后完成的,这似乎意味着李劼人开始向自然主义靠拢。其后的作品,这种绘画式描写更为显见突出。”[6]P40
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好人家》收入10个短篇小说,其中八篇作品是1924-1926年创作的,在创作上早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它们可以显现李劼人长篇小说创作之前的种种图景,尤其是与法国文学的关系,李劼人对自然主义小说的选择是一贯的吗?这一考察的发现,将对李劼人和现代小说研究都是有意义的。王锦厚《李劼人与外国文学》认为,“这些作品,无论是短篇、长篇,都与法国文学的影响息息相关。短篇小说,受莫泊桑影响最大。故事都非常简单,但剖析得很细腻,论点摆得很恰当;同时又自然而然地道出一些不经人注意的社会问题。……单就三部长篇小说而言,从酝酿到写作,李劼人都有意学习法国作家大仲马、左拉、巴尔扎克等人。”[7]P55但是李劼人并未提及对大仲马、巴尔扎克作品的阅读。
小说集《好人家》显然包含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的故事素材,可以说是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创作试验,一些人物的基本型态开始形成。《好人家》一篇中的赵幺粮户形象及其家族的命运衍变,叙述的反讽成分突出了些,是莫泊桑式的中国风俗描写吗?人们难于辨别区分这个现象。《市民的自卫》在一次表现了“好人家”的故事,顾老汉的近似形象其后也出现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中,《市民的自卫》表现了纯客观的描写,只是把实质的对象一丝不走地写下来,仿佛编演了一段不加说明的活动电影,而心灵的对象却不涉及,“直到第二次细胞分裂之时,努了许大的力,那经史等旧势力才稍稍让了一点步,许外人进去辟港通商”,科学的词汇与反讽一时增色了小说的叙述。《大防》引入了一些科学(大脑的生物学,拒力的物理学)和新词汇,“它的钢骨是历史和习惯锻炼成的,所敷的沥青则得力于三种原料”,[8]实验小说就是今世纪科学运动的结果,并支持和完成生物学的东西。这种小说即为吾人科学时代的文学……,换言之,左拉的自然主义是全赖实验科学的方法,(利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只重实际的经验,忽视心灵的力量;然而李劼人并没有表现对科学更深更广的运用,这只是一个基础的意象。《只有这一条路!》可以作为一篇问题小说,写作手法上确乎运用电影的蒙太奇成功描写了张桂荪的心理,“张肯堂到底不了解他老二的心志啊!……假使他能设法把桂荪在自己脑里用悬想和感情所制成的电影看一看,他一定不会这样的枉费唇舌。桂荪脑里的电影制片公司,大概成立在一年以前,一切材料,都是国产,尤其是土产。他逐渐摄制,逐渐修剪,到最近两个月,算是大体粗具,……于是他的电影工作方完成了。并且得亏电影的制造,……每夜必将他这精工制成的电影开映一次,一以自娱,一以自励;昨天夜里,因他父亲叫仔细想想,他的电影才映得越有劲。”事实上,小说《只有这一条路!》构成了叙述的预叙,一个故事的开放式结局,虽然李劼人立意在反讽,在现代小说发展中,这无疑是一次有趣的叙事艺术的探索。李劼人在自然主义批评中明显提到“不加说明的活动电影”。1924年,李劼人在小说中成功引入电影艺术,基本具有了现代主义的色彩。《编辑室的风波》选入茅盾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小说一集》,并没有批评的文字,反讽已经作了李劼人一贯的叙述特征,“有人说,这城里的人因为吃得太多太好,一个个都有肠肥脑满的样子,所以无须再拿眼睛来当口,再拿《日日报》来当粮食,再拿头脑来当肚腹了;又有人说,并不是人家的头脑不想容纳《日日报》,只怪《日日报》太缺少资养料,差不多同芜菁一样,惟有肚腹饿到十二万分的饥人才不得已而欢迎它”,隐约现出科学的思维。《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在整个叙述上,以时间作为故事的划分,与《同情》略相近似,并不缺乏反讽。《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表明李劼人已经成熟地移用了自然主义小说的艺术,李劼人虽然以现代中国故事为目标,小说叙述的探索深受自然主义及其后法国小说的启发。值得指出的是,《兵大伯陈振武的月谱》采用了戏剧的结构,故事由序曲部很快进入展开部和高潮部,对话的成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其后再次出现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中,对平庸猥琐、对不幸、对恶的关注,已经不再有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如果对比莫泊桑的战争——士兵小说,李劼人似乎不相信善和高尚,突出了纯客观的描写,并不作出说明。《对门》其后再次出现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中,李劼人把叙述的视角放在叙述者石太太形象上,突出了风俗的意义,成都中上层人物的势利眼光被生动地描写出来,莫泊桑式的反讽被置于时代命运之下,加强了悲惨的氛围。
我们无法确知,1919-1923年李劼人可否阅读过左拉或者龚古尔的作品。小说集《好人家》中的大多数篇目在写作艺术上,确乎表现了自然主义的真实观察。从实质描写,只是把实质的对象一丝不走地写下来,仿佛编演了一段不加说明的活动电影,而心灵的对象却不涉及,顾阅者的心理,不怕社会的非难,敢于把那黑暗的底面,赤裸裸地揭示出来,把社会写得完全是一个可恶的、无可救药的,善恶分明的社会,凭其观察所得,毫无顾忌将种种黑幕尽力地揭破,只是着力在黑暗的正面,只管火辣辣地描写出来;超出小说的时间观念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是漂泊不宁的,李劼人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进化学说的建构影像,纯客观的叙述淡化了善恶的批评,摒除了崇高——英雄的理念,虚构被悬置起来,小说中的一切都是平凡微小的,李劼人着力描述市民生活中的平凡事件。反讽透露出来的被讲述的故事并没有显现悲观与迷惑,它们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目标是“人的教育者”(L’instituteur des hommes,巴尔扎克语),即极力想把人间的事物及肯定的影响,一一呈诸吾人,以做为恶的龟鉴,使读其书的人迁而为善。这些作品中,明显映照了莫泊桑的小说艺术特征、风俗的考察,揭示对善意与乐观追求和企望。
1956年李劼人在《自传》中记述1912年写过两篇讽刺性的速写,而1913-1915年在得到的不少社会知识中了解许多丑恶事件和丑恶情况,对晚清的官场和辛亥革命的成果发生了怀疑,并且其后在《余闲录》上发表的散文作品主要是描写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面。应该说,李劼人的创作一开始就带有怀疑精神和揭露世态风气,如势利、欺骗等等,怀疑精神和揭露世态风习的聚焦,在李劼人的长篇小说中是一贯的,与其早期短篇小说维持了多种一致品质,包括故事和叙述法。
1912-191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李劼人已经表现出着力描写(社会)黑暗的正面,而且与林纾翻译的英国狄更斯小说的事实影响相关,隐约具有狄更斯式的幽默,即以轻松的、活泼的社会丑恶的描写来揭示出社会黑暗的底面,与晚清的黑幕小说潮流相一致。五四时期及其后,中国流行自然主义的前提的要求和文学阅读与创作视野,即现代中国从赤裸裸的揭示黑暗的正面发现了自然主义。在《死水微澜》创作之前,李劼人的短篇小说已经在题材,叙述艺术、构架的观念、思想结构上为此作出了成功的探索试验和充足的准备,一个精致选择的自然主义艺术方案成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的创作基础,李劼人对自然主义的认知表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接受方式和接受视域,非欧化的创作方向在现代小说创作进程中是有意义的。在李劼人的短篇小说中,大大超出了自然主义,而莫泊桑、都德的影响更显著一些。
二 法国文学对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影响
1919-1924年留法之后李劼人接受了法国小说影响,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积极移用了自然主义及其后写实小说的理论:即作出鲜明的社会批判,赤裸裸地揭示(社会)黑暗的底面。李劼人在《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中指出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顾阅者的心理,不怕社会的非难,敢于把那黑暗的底面,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凭其观察所得,毫无顾忌将种种黑幕尽力地揭破,只是着力在黑暗的正面,只管火辣辣的描写出来。[9]也就是说,李劼人明显放弃了幽默的写法,放弃了大多的理想主义成分,而染上了一些悲观主义,普遍运用了自然主义式的反讽,虽然李劼人并没有表现出对社会下层苦难更多的关注,但同情感是一贯的。司马长风认为,“李[劼人]氏的风格沈实,规模宏大,长于结构,而个别人物与景物的描写又极细致生动,有直迫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魄。”[10]P54李劼人指出,马尔格利特兄弟(Paul et Victor Margueritte)合写的《一个时代》(Une époque,Paris:Plon -Nourrit et Cie)是四部避免了自然主义定型上的束缚的爱国主题的丛书,“在一个时代的题目下,做出那几部大书”,《灾害》(Le désastre,1898)写一八七○年摩泽尔省会麦茨的事,《战事之片断》(Les Tronçons du glaive,1901)写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拿破仑第三败后法国防御普兵的事,《勇士》(Les braves gens,1901)写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事中法国民军的逸事,《公社》(La Commune,1904)写一八七一年巴黎与凡尔赛间的事,这四部巨作自然因为普法战争的激刺,十余年后目睹法人的荒嬉堕落,作此以教训国人。李劼人的长篇历史小说似乎与此有近似处。[11]
李劼人《死水微澜》(1937年,1954年修改),《暴风雨前》(1937年,1955年修改),《大波》(1937年,1955-1961年重写)隐约包含着自然主义的成分,尤其是福楼拜、莫泊桑的影响更明显些,“自然主义的反对者和叛徒,如保罗·补尔惹、保罗·马尔格利特等,大抵多保存得有这种精神,彼等之不免走近宗教,不过是向道德方面,进而求善,以救自然主义的偏弊而已。彼等并不欲转而投身罗曼的文学。”[12]P460“卜勒浮斯特的文学才能是独立的、循正轨的、有特质的,不属于哪一派,也无创造什么体系的野心。他只是研究心理学,尤其只是研究妇女心理学,他的作品便是他研究结果的发表,——然而是文学,不是报告书。”[13]P561由此已超出了自然主义。首先我们可以追溯李劼人创作的进程和文体风格的变迁,从《同情》到《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包含有意义的事实和细节,这可以揭示李劼人创作与法国文学的影响的事实性关联。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是相互联系的左拉《鲁贡·玛卡尔家族》式的小说,我将作专门的考察。小说是意识形态(idéologique)的表现,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故事的真实对于小说并不至关重要,只有极少情况,小说具有生活——社会的真实,对此李劼人有自觉的意识,并清楚地认识到小说需要创造形象的典型,李劼人《自传》关于蔡大嫂与罗歪嘴的说明强调了典型形象的意义。考察李劼人的细节描写是必要的。
细节描写。从巴尔扎克开始,细节描写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福楼拜、莫泊桑、左拉等都善用这一技巧。在很多情形下,李劼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这是一个模糊的影射,有着更多似是而非的成见,我不再谈论其中性的描写。李劼人重视细节的描写是无争的事实,在小说叙述中,达到真实的效果的手段便是充满想象力的细节描写,郭沫若、周太玄正是在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的细节描写中发现艺术的力量:成都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生活的可亲近品质或者私人生活回忆的成分,而对于别的读者,细节描写是唯一的发现,而细节描写是法国写实主义小说以来伟大的传统,并不归于自然主义。李劼人长篇小说中的细节大多是生活场景的细节、人物刻画的细节、风俗的细节,如《暴风雨前》中郝又三与叶文婉的婚礼;《大波》中保路运动,分析的、平凡的细节是被怀疑精神映照着,不是为了揭示一个真理,而是被强调可分析的品质,它们使得小说的场景生动起来,明朗细腻。正如福楼拜、莫伯桑反对戏剧化一样,李劼人也努力避免高度戏剧化、典型化(typifié),李劼人努力节制小说的想象力,分析的、平凡的细节激发了读者私人的生活感受的共鸣。李劼人有意放弃了追求情节的真实,在改写《大波》时,李劼人则重申了细节描写的手法,“例如在上半部,尚不慌不忙,反映了一些当时社会生活,多写了一些细节。(也有朋友批评细节写得过多,不免有点自然主义的臭味。)”[14]P952小说批评所指责李劼人的散漫,或者细节的混淆,再一次提出了细节的价值争论和细节的美学争论,如果对比左拉一派的小说细节,李劼人长篇小说的细节描写并没有达到分析的最后深度。中国的美学习惯拒绝细节的、分析的最后深度,而李劼人长篇小说的人物在分析的细节下并没有达到完整地形象感受,形象的重塑的结构特征并没有因此而加强,这些平凡的人物并没有被集中到一个强调的性格上,心理化的倾向不时表现出来,打破了现代中国普遍的阅读习惯,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阅读方向。
时间意识。在一段封闭的、可以经验的时间(1894-1919)中,李劼人长篇小说的时间是向前展开的。李劼人永恒的怀疑精神并没有采取进化论的时间意识,也没有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时间意识。外在的时间不是循环的时间意识,外在时间与事件行为一样运动着,单向地线性运动。然而逻辑的时间和内在的时间,与世态风气、社会丑恶则表现为偶然、模糊、混淆,或者说,世态风气、社会丑恶反复产生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不同时间发生着不同的社会丑恶,这是一种不可回归的重复。普遍的人性并没有为未来投上理想主义的亮色或者解决的希望,我们称为时间的丑恶复制,而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时间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浮现,即浮出时间的流动的晦暗,李劼人长篇小说反复表现了时间意识上的偶然性,或者人物命运的偶然性,这与分析的细节保持着可喜的同构性,打破了人物的主从、情节的层次,实现了小说内在成分的民主状态,在偶然的时间运动中,分析的细节是平等的重要。在时间观念上,李劼人长篇小说确乎与自然主义有一些接近,有两种并行的时间意识,而且逻辑的时间往往被突出,偶然,心理的时间叠加在外在的时间之上。换言之,在时间意识上,李劼人成功达到了社会批判的目标。
小说的场景。李劼人的长篇小说集中于现代中国的风俗研究,考察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的场景是需要的。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分别集中到不同的家庭,近乎左拉式的家庭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如《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的婚姻与爱情,《暴风雨前》中的郝又三的家庭与任情孟浪,《大波》中的黄澜生的家庭与恋情,《天魔舞》中的陈莉华与陈登云同居;从地理上看,所有场景是在成都和城市近郊,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写到一些贫困人们的生活场景,如成都的下莲池,《天魔舞》中的桤木沟,李劼人对此并不缺少同情与批判,近似左拉小说的城市贫民区的描写,除《死水微澜》,《天魔舞》主要写城市近郊,更多的是亦官亦商,成都官宦人家的生活场景描写,如成都的郝公馆、黄公馆、咨议局等等,作了社会丑恶的主要现场,这表明李劼人集中于世态风气的分析,而所揭示的丑恶主要是腐败、势利、虚伪、守旧、封闭等,即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场景是道德与社会理想的审判场所,而不是社会对立,极端贫困所体现的社会丑恶。更为重要的是,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场景往往投上家庭的温情或者爱情的好奇,淡化了道德与社会的尖锐批评,或者说,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场景包含一个心理的层面,包含太多风俗的构造。总而言之,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场景与左拉一派的小说场景有明显的不同,自浪漫主义运动(如雨果)而来,美学上的丑的对象,获得了新的价值,左拉一派显然发挥了美学上的丑的价值,如《娜娜》结尾的天花场景。尤其是在宗教道德方面的反抗性的认知意义,而李劼人并没有自觉运用美学上的丑的价值,由于没有宗教意识的结构性基础,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场景中的丑恶便没有了反抗性的争辩和意识形态的张力。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场景构造显得更加中国化。
三 长篇小说的虚构与社会批评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1937年,1954年修改),《暴风雨前》(1937年,1955年修改),《大波》(第一部,1937年,1955年重写;第二部,1937年,1958-1959年重写;第三部,1937年,1960-1961年重写;第四部,1937年,1961-1962年,未完),《急湍之下》(未写),《天魔舞》(1947-1948年),在事件和时代顺序上是相互联系的,更重要的小说间关联是故事与人物的重现,蔡大嫂——伍大嫂——黄太太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贯品质,和别的事件与人物行为线索上的可连接或连续性。自五四时期以来,严厉的、似是而非的批评影响了《大波》的创作,现代中国对自然主义的误解已经很深,超出这些语言的记载。然而1880年代法国精神世界对科学的信仰出现分歧和动摇,这一思潮,无疑在尚未确立科学观念的现代中国,迎合了普遍的心理,加剧了现代中国文学对科学的隔膜。
一个社会包容太多太复杂的事实或者社会现象,它们并不调和一致,而是表现出矛盾的趋向,甚至无序混乱。当这些现象被纳入小说的创作素材时,事实被创作者驯服了,被赋予秩序和主题思想,创作者为它们提出纪律或者规律,换而言之,一种文艺的理论支配了小说的素材,作者的情感和认识在其中表现出来,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所指涉的是一个变革剧烈的现代中国,李劼人显然对这些现象的认识是倾向于批判社会的丑恶,他认为官场及其周围的世界是荒诞的、无可救药的,善恶分明的社会,与理想主义绝然对立着。李劼人对现代中国的同情,加强了现象分析的深透力量,尤其是在风俗方面的深度,李劼人似乎一直没有依赖唯物主义,这使他的认识保持了相当的独立品质,法国自然主义及其后的小说为李劼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故事结构和叙述模式。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并不是自然主义小说,左拉一派的小说中的社会批判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目标和认识理论,也就是说,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只是一种社会研究的小说,而不是社会的历史小说,共和国时期,李劼人的重写活动事实上是努力把社会研究的小说改造成社会的历史小说。如果社会的历史小说是力图展示社会历史的广阔的事件和对事件本身的最大同情,而社会研究的小说只是对一个或者更多的主题现象进行分析,现象的考察作了它的核心目标。对李劼人的小说批评,最大的误区应该在于对这一事实的不恰当的混淆,我不能多谈这个论题。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并不是反映现代中国的想象世界,尤其是《大波》写到了极丰富的历史事实,我们的研究首先考察的是李劼人小说的事件或者现象聚焦是什么。李劼人并没有完全运用进化论,因为永恒的怀疑精神,在长篇小说的虚构世界中,辛亥革命并不比晚清显得更进步更良好,人只是替换,混乱事件只是更迭,丑恶一样发生,世态风气一样迁衍,在李劼人的叙述中,早期的幽默写法到随后的讽刺与研究,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就在于李劼人把社会黑暗面作为一种社会研究、一种风俗的研究,事件的原因和过程成为李劼人长篇小说的叙述主要的目标。我们发现,在李劼人的长篇小说中,说理的分析成分往往与现象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着自然主义之后的心理小说影响的加强,分析成为李劼人长篇小说的核心叙述法,换而言之,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的叙述不再是现象与形象的描写,而是事件过程与人物心理的发生,即揭示社会黑暗面的发生,普遍人性的丑恶行为,恰是普遍的人性作了李劼人永恒的怀疑精神的聚焦目标,从世态风气的角度,考察和发现现代中国的漩涡式的运动,一切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沉没在改革之中。自然主义小说的启发似乎在于泰纳(Hippolyte Adophe Taine)的环境决定论在叙述中的运用,标志着英雄主义消失了,平凡人物成为小说叙述的主要形象,蔡大嫂与罗歪嘴,郝又三与伍大嫂、黄太太与楚用、陈莉华与陈登云是李劼人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是反英雄主义的,无力改变社会,只是一时在巨大的变革潮流中浮现,然后消失其形象,尤其是《天魔舞》中的陈莉华与陈登云形象鲜明地表现了无始无终的善恶分明的游戏,叙述的首尾所表现的陈莉华,构成一个完整的戏剧化行为进程,漩涡式的回归。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着力描写(社会)黑暗的正面,作为社会的批评,一方面与自然主义的正义的批判有近似的品质,另一方面,19世纪法国在意识形态上,丑与恶的分离,引发了深刻的变革,自然主义发挥了美学上的丑的价值,对丑作出分析的表现,引发宗教道德、意识形态的反思性的变革,而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没有自觉到丑在美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与自然主义明显悬殊。李劼人对自然主义小说的接受是中国化的选择,是一些技巧和局部观念的移用,至今中国尚未完成意识形态的丑恶分析性的独立。
四 结语
李劼人在《李劼人谈创作经验》中指出:“解放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提出来以前,我不打算动笔。我觉得今天写作不能像以前那样了,今天有今天的一套。我过去学的文艺理论是资本主义理论,不适用了。”[15]P131956 年李劼人在《自传》中详细写到所接受的旧教育,在别的地方,李劼人一再强调旧教育这一事实,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李劼人似乎确认自己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影射李劼人在解放后时期里心灵的紧张,心灵改造带来的焦虑。在旧的社会,李劼人确乎看到和经历了一些社会的丑恶,以一种进化观和理想主义投射到现代中国上,于是便有了批判。而且李劼人明确指出一种文艺的理论(自然主义及其后的小说理论)是小说创作的结构性的基础,更为宏大的背景力量。
李劼人法国文学翻译的译者附言、译后记、译序,其中一些表现了深刻独立的批评品质,法国写实小说是李劼人的翻译批评主要的选择,它们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启发。李劼人写道:“[《单身姑娘》]对于第一次欧洲大战后一般法国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和少数出风头、无常识、专爱操纵政客的一些女人,稍稍作了一点不客气的描写,于是引起了一场不寻常的风波,由最高检察厅提起公诉。”[16]P599《大波》中的黄太太、《天魔舞》中的陈莉华则隐约可见近似的批评意图。
:
[1]曹聚仁.海外有这么一个文字知己——曹聚仁谈《大波》[J].郭沫若学刊,2011(4):9-13.
[2]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275.
[3]李劼人.李劼人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54.
[4]李劼人.李劼人谈创作经验[A].草地,1957(4):12-14.
[5]伍加伦.李劼人与法国文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4):60-65.
[6]李秀卿、龙岗.李劼人和法国自然主义的关系[J].西昌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9):39-41.
[7]王锦厚.李劼人与外国文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52-60.
[8]李劼人.大防[A].李劼人选集·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47.
[9]李劼人.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李劼人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54.
[10]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54.
[11]李劼人.《离婚之后》后记,李劼人选集·第五卷[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568.
[12]李劼人.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李劼人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60.
[13]李劼人.《斯摩伦的日记》译者附言[A].李劼人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61.
[14]李劼人.《大波》第二部书后[A].李劼人选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952.
[15]李劼人.李劼人谈创作经验[A].草地,1957(4):13.
[16]李劼人.《单身姑娘》译者序言[A].李劼人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99.
I206.6
A
1004-342(2013)05-45-08
2013-07-03
彭建华(1970-),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