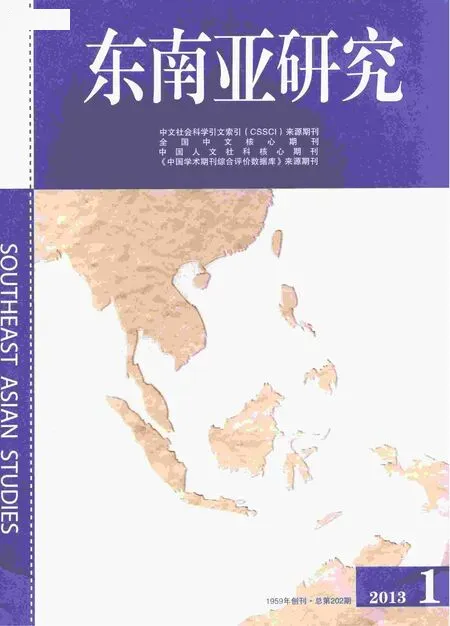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探析——基于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考察
檀江林 李 莉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230009)
后金融危机时代,“重返亚太”成为美国实施全球战略调整的明显标志。2009年奥巴马上台伊始,发出了回归亚洲的信号,并以首位“太平洋总统”自居。国务卿希拉里接连在夏威夷发表“美国的亚太接触政策”、“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等演说,反复阐述其称之为“前沿部署外交”的(“forward-deployed”diplomacy)的亚太举措。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由政策宣示加速向具体的行动转化。如在军事调整方面,奥巴马政府奉行有缩有进,军事关注点向亚太集结。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发表新国防战略,放弃了在中东和亚洲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两条战线”战略,把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以实现牵制中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利用韩国“天安号”事件与北朝鲜延坪岛炮击事件进一步密切与韩国、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奥巴马借出访澳大利亚之机宣布在澳北部的达尔文港实施驻军计划,并于2011年底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经济议题上,美国高调宣扬和推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试图把TPP打造成高标准的亚太自贸区,成为美国掌控亚太区域统合主导权的机制安排。在推进民主与人权方面,奥巴马政府充分展现其政策灵活性,在对待缅甸议题上,2011年希拉里访问缅甸,成为50年来首访缅甸的美国政府高官,由以往单纯的冷落、制裁向接触政策转移。在参与地区机制方面,奥巴马一改小布什单边主义作风,积极参与亚洲地区多边机制。2009年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以东亚峰会正式成员身份与会。除此之外,面对亚太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全面深化与中国的工作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和助推“南海问题”,挑动矛盾的小动作不断,2012年8月,在论述美方对中国设立三沙市的立场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名道姓地抡起大棒,将“有违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风险”的责任推给中国[1],以策应其亚太战略的需要,扩大与激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矛盾,营造有利于美国实施平衡举措的紧张环境。总之,从高调的政策宣示到大刀阔斧的行动,奥巴马政府妄图打造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体系,国务卿希拉里更信誓旦旦地指出,在20世纪美国成功缔造了跨大西洋体系,在21世纪美国也有能力构建跨太平洋体系,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
作为冷战后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化趋势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重大战略决策的转变是复杂变量作用的结果。而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重要工作就是找出涉及国际关系中的两个或多个变量,并发现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效的方法是在诸变量之间发现有序的内在关系,层次分析法正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建立变量之间关系的工具,并使国际关系研究更趋科学化。因此,运用层次分析法探究影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具有可行性和可信度。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由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首创,后由包括戴维·辛格、詹姆斯·罗斯诺以及布鲁斯·拉西特等在内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与丰富。其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层次分析方法的使用,分析层次越来越系统,层次间隔越来越小。但是,学者们对于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时到底应该划分多少层次并非完全一致,关于层次的数量、层次的具体内容都存在分歧。本文拟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系统结构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嬗变)、国家间互动 (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国内因素 (美国国内发展面临的困境)等三个层面出发,分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
一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嬗变:亚太经济的崛起
现实主义论者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政府需要根据外部客观环境及他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对本国对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因应外部的压力。国际政治理论只是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解释,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3]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首先是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嬗变的一种客观反应与主观调适。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加速加剧了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了大变动、大调整的新时期。2008年底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欧洲亦深陷债务危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态势下,亚洲经济发展傲人,成为全球经济新崛起的发展引擎,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稳步上升,从1980年的7%上升到了2008年的21%。目前,亚洲股市的市值占全球总市值的32%,领先于美国的30%和欧洲的25%[4]。根据预计的发展态势,在今后五年内亚洲地区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总量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增长50%左右,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1/3,足可与美国和欧盟相抗衡。预计到2030年,亚洲地区的GDP将超过七国集团(G7)[5]。另一方面,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2009年,美国GDP增速-2.4%,欧洲-4.8%;印度7.3%,中国高达8.7%[6]。2010年,世界商业服务出口平均增长率为9%,按区域计算,2010年,欧盟商业服务出口增长率为3%,北美增长率为9%,中南美洲增长率为12%,非洲地区增长率为10%,中东地区增长率为3%,而亚洲地区商业服务出口增长率却达到22%。自2005年以来,亚洲地区的商业服务出口平均以每年13%的速度扩展,大大超出世界平均增长率,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区[7]。
经济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力量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格局的变化意味着潜在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及经济增长意味着其影响力的加强。七国集团炉边谈话式的旧有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诞生的20国集团(G20)中,就有六个来自亚太地区。在IMF的投票权中,目前亚洲所占比例仅略超过20%。但随着IMF改革的继续推行,亚洲地区在IMF投票权中的比例必将进一步增加。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认为,“新兴亚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亚洲,尤其是向“新兴亚洲”转移。这个模式至少会持续到下一个五年,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改变[8]。依据美国学者奥根斯基建构的“权力转移”理论,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他认为,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是权力的国际分配的关键,工业化必然出现并导致权力的转移和世界范围内权力分配的变化,权力的转移会造成新的权力大国或新的权力中心,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而原因在于,工业化在全球的进展是不均衡的,这就注定了国家间的权力会出现转移和此起彼伏的变化[9]。国内学者指出,由于世界经济力量和财富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东移,区域综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亚太地区不仅有比欧洲——大西洋地区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空间,而且具有有效利用这一空间的能力,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10]。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于2011年11月撰文指出,“不论21世纪是否成为另一个‘美国世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21世纪将会成为亚太世纪。”[11]
美国对于由于经济增长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权力转移极为关注与敏感。冷战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保持和巩固自身单极霸权地位是美国始终不渝的全球战略,而紧控热点、关注和主导新兴经济区则成为其保持全球霸权的重要路径,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有一个缓慢的进程: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冷战后一段时间,美国趁着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以及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战略机遇期加紧“北约东扩”;克林顿时期美国开始显现了对亚太地区有所重视的迹象,但小布什时期的“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战略重点的轨迹,扛起全球反恐的大旗;及至奥巴马执政,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泥沼,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强劲,加剧了美国“重返亚太”的紧迫感。认定未来世界权力的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这是美国决策层近年来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对21世纪国际经济与权力重心发生变迁的客观反应,是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重点,使之与亚太地区长期的重要性相符。美国唯有“重返亚太”,从安全、经济、外交、资源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的“前沿布署”,才能主导亚太地区的发展轨迹,维持和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具有“顶层设计”,其目的是通过掌控亚太这个“未来世界权力的中心”,借以维持和加强美国相对衰弱的全球霸权地位。
二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2008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截止到目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仍旧复苏乏力。而中国率先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超过8%的经济增长率超出了人们的预期,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近些年来,中国与东盟实现了区域经济整合;通过ECFA的签署,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实现了经济融合,台海两岸开启了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局面;中国与韩国、日本自贸区议题的商谈亦在进行之中。通过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与实践,中国周边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正在趋于改善。经济实力的增长无疑成为增强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助推器。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缴纳会费的金额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以及支付能力等确定。截止到2011年,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从2007—2009年的2.667%增长到3.189%,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列第8位[12]。2010年,中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3];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08年进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正式生效,根据该方案,中国在IMF的特别提款权 (SDR)份额占3.72%,投票权占3.55%,居第六位;而根据尚未生效的2010年改革方案,中国的SDR比重将升至6.39%,投票权跃居第三[13]。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当局的警惕与担忧。快速发展的中国一旦实现真正的崛起,必然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形成重大的挑战。具体说来,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自从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纵览19世纪与20世纪,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是追求“门户开放”政策,防止任何单一强权控制亚洲。美国学者认为,由“敌对”势力控制亚洲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的根基。因此,和19世纪之交“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前后相比,在21世纪的今天防止亚洲地区由任何单一强权主宰变得更为刻不容缓[14]。美国在亚洲的重要角色是担当地区平衡者,即美国是既有能力又有历史记录的担任地区平衡者与“诚实经纪人” (honest broker)的唯一国家,成为亚洲地区稳定的关键[15]。而中国快速的崛起与持续上升的影响力,显然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不相容。亚洲地区是中国的战略基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首先在亚洲地区具有扩散效应,从而直接挑战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领导力。对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叫嚷,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拥有最大的潜在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和安全动态的能力,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形成对区域准入的限制[16]。
其次,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华盛顿共识”或“美国模式”的衰退。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主流派,以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为代表,倡导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全盘西化来实现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又广为传播。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作为全球主流发展理念的“华盛顿共识”日益受到“北京共识”的挑战。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17]30多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实施渐进式的改革,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日益引起世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瞩目,国外出现“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语的评析与热研。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促使西方一些媒体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同时也驱使它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在危机中的表现。西方国家认为所谓“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全世界效仿西方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将颠覆一切西方话语体系中“现代”内容,甚至需要重新界定“现代”一词的含义。尽管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能否复制存有争议,但不容质疑的是,中国的成功实践颠覆了“华盛顿共识”的普世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18]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也承认,中国在创建国家级冠军品牌、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提高管理水平与增加公共商品等方面更新其发展模式,如果中国成功地更新其发展模式,这将对美国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各地推动市场和民主的目标构成新的挑战[19]。
再次,中国的崛起挑战着美国的制度霸权。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必然会带来国际秩序的变更,权力的转移造成的新的权力大国或新的权力中心,不仅会对邻国或别的国家构成威胁,而且会动摇现存的国际秩序[20]。霸权稳定论亦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新兴国家或曰挑战国家的出现导致霸权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从而对霸权国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提出挑战,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21]。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消蚀着美国的制度霸权,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理念的实施。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高举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旗帜,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又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在政治上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2011年12月2日,在联合国有关叙利亚人权形势的决议问题上,中国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表明了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坚定立场。在对外援助方面,截至2009年,中国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累计免除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对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22]。中国坚持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坚持外援不与他国内政相联系。而美国希望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的价值观,像美国人那样行事。冷战后时代,美国把拓展民主与人权作为历届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之一,把实施对外援助与附加政治条件以及改善他国人权相联系。2011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出台的研究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对外援助的增强,很有可能造成中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战略目标,这可能会潜在地削弱包括促进民主治理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内的美国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23]。美国学者艾伦·沃奇曼认为,中国给美国及其盟友所带来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是与北京关于“核心利益”的冲突,而是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北京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上的道德权威和影响力作斗争[24]。
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群体性崛起。通过上述种种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新兴大国的身份尤为警惕与担忧。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网络威胁论”充斥美国各大媒体,在美国官方和学界亦有广泛影响。显然,中国因素无疑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成因。美国意识到,对中国实施单纯的遏制既不可行亦无成效,因而就针对中国而言,其“重返亚太”的重要目的是直接进入中国所处的战略依托地,通过主导与加强亚太地区的双边与多边机制,构建影响中国决策的压力环境。
三 国内因素: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发展困境
“宣称只考虑国家内部条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国家外交行为,并不是说对外交行为的解释无需考虑国内因素。”[25]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亦出于国内因素的考量。与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持续的经济繁荣不同,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美国就深陷金融危机,联邦财政赤字加重,债务缠身,通货膨胀,市场消费意愿持续低迷,国内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此起彼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彰显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其实早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内部治理的潜在弱点已经逐渐暴露出来,至奥巴马执政时已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摆脱危机、重振美国经济成为奥巴马政府优先关注的任务。对此,奥巴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出台金融监管法案、削减国防预算、促进就业等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由于受到党派政治的牵绊,奥巴马的国内改革举措举步维艰,调整经济结构、重构经济增长模式的任务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放眼海外”,在全球战略上有缩有进,“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军事重点向亚太集结。在经济上强化出口促进战略,即在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支撑与提供的空间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更多的把希望寄托于海外,企求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为美国经济复苏与促进就业搭桥。为此,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内使出口翻番的目标。在欧盟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欣欣向荣、后劲十足的亚洲经济势必为美国所青睐。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目前占到全球GDP的55%,拥有27亿消费者市场,并购买58%的美国出口商品,美国最大的15个贸易伙伴当中,7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26]。在美国看来,在今天的世界,亚洲已不仅仅是美国商品的市场,更成为美国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亚洲有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实体。亚洲融资是美国财政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是美国国债的重要买主。同时,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与北美、欧洲相比有更多的专利申请,亚洲又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世界电脑芯片的大部分在亚洲生产[27]。显然,亚太地区经济体将在美国摆脱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新的增长与繁荣的目标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国家出口计划”与五年之内美国出口翻倍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目标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亚太地区。而其高调宣扬的TPP与出口促进战略遥相呼应,其目的就是打造有利于美国的亚太经贸机制安排,并以此掌控亚太区域整合的主导权。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实力达到顶峰。通过扶持日本以及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确立了以跨大西洋机制为基础的世界霸权。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昔日的辉煌不再,实力相对大大衰落。与跨大西洋机制以美国较多的“付出”和提供集体公益相比,美国梦想构建的跨太平洋机制却以更多的“索取”和“利用”为特点。美国希望搭乘亚洲这趟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为国内经济复苏乃至快速发展注入强心剂。
结语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必然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单位层次上的单一变量无法全面解读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首先是对亚太经济崛起所导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现实和潜在嬗变的客观反应,而国内面临的发展困境无疑加剧了实施此战略调整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当然,中国因素虽然不是唯一但无疑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动因。但21世纪的今天,与美国构建跨大西洋体系对抗与遏制苏联的冷战时期毕竟不同,全球化的发展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造成美国在对华策略上整体战略与国家利益重叠的趋向。美国妄图构建的跨太平洋体系难以达到遏制与对抗中国的意图,只能通过双边与多边机制构筑影响中国决策的亚太环境,美国对此洞然于心。美国官方一再声明,美国“重返”亚太的目的不是遏制中国。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军队并不想用冷战的方式“遏制”中国,但这可能有助于营造未来中国领导人作出自己选择的环境[26]。美国“重返亚太”必然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和行为规范产生一定挤压,但中国无需因“狼来了”而过分担忧或焦虑不已。在坚持“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前提下,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方针,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对我国仍有指导意义。
【注 释】
[1]温宪: 《美国有关南海声明难掩虚伪、荒谬与阴险》,《人民日报》2012年8月4日。
[2]Hillary Rodham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美国国务院网站,November 10,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
[3]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4]Robert B.Zoellick,“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Modernizing Multilateralism for a Multipolar World”,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April 14,2010.
[5]Anoop Singh:《亚洲引领全球经济发展》,《金融与发展》2010年第2期。
[6]《朱民论亚洲经济及相关议题》, 《金融与发展》2010年第6期。
[7]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1,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1_e/its11_toc_e.htm.pdf,p.15.
[8]朱锋:《“权力转移”理论评述》,《欧洲》1998年第1期。
[9]俞正梁:《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6期。
[10]Richard N.Haass,“Re-Orienting America”,Project Syndicate,http://www.cfr.org/us-strategy-and-politics/re-orienting-america/p26490
[11]《联合国称中国已缴清7490万美元联合国会费》,《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日。
[12]《中国成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网,2010年4月27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4/27/content_1814092.htm
[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中国份额暂居第6》,中国新闻网,2011年3月 4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3-04/2882932.shtml
[14]Dean Cheng and Bruce Klingner,“Defense Budget Cuts Will Devastate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he Asia-Pacific”,The Heritage Foundation,December 6,2011,pp.2-3.
[15]Patrick M.Cronin ed.,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The U.S.,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2.
[16]〈英〉马丁·雅克著,王瑾译《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17]朱可辛: 《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18]Bruce J.Dickson,“Updating the China Model”,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1,pp.54-55.
[19]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7-304页。
[20]胡锦涛:《同舟共济共创未来——在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09年9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24/content_1210 3701.htm
[21]Jonathan Weston,Caitlin Campbell,and Katherine Koleski,“China's foreign assistance in review: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网站,http://www.uscc.gov/index.php.pdf,p.2.
[22]Alan M.Wachman,“China's current and emerging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manuscript from the USCC hearing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Challenges and Players,http://www.uscc.gov/index.php
[23]同 [3],第34页。
[24]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局:《美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21世纪实现增长与繁荣》,美国国务院网,2011年5月1日,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amgov/294130/tsangk/APEC%20One%20Pager%202010.pdf
[25]Dean Cheng and Bruce Klingner,“Defense Budget Cuts Will Devastate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he Asia-Pacific”,The Heritage Foundation,December 6,2011,p.2.
[26]Joseph S.Nye,“Obama's Pacific Pivot,Project Syndicate”,2011-12-06,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101/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