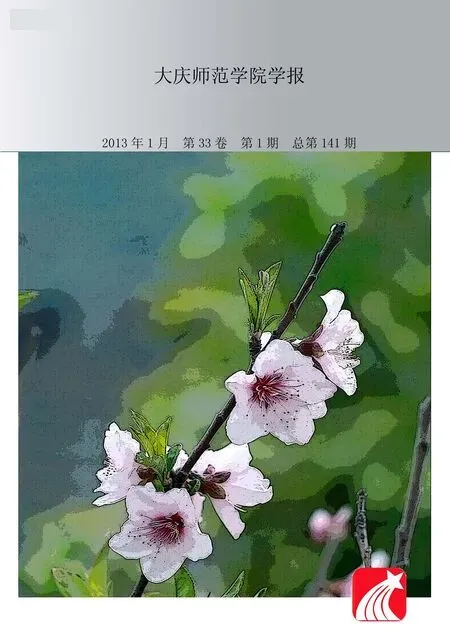《庄子》拟人修辞景观探微
陈启庆
(莆田学院 中文系,福建 莆田 351100)
拟人是比拟之一,它是一种以人比物的修辞方法。《庄子》不仅善于比喻,而且长于拟人。《庄子》拟人既形态别致,同时又承载着特殊的修辞功能,具有别样的修辞韵味和独特的修辞魅力。
一、《庄子》拟人的修辞形式
在《庄子》拟人的园林里,可谓景色绚丽,异彩纷呈:不但以人比物,而且以人比理;既有自然物的拟人化,也有非自然物的拟人化。
1.以人比物
在客观世界里,有情的人和无情的物是各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的,为了表达的需要,更为了言语交际的需要,人们常常根据想象把物当作人或把人当作物来写。对此,庄子也不例外。庄子为了实现言说意图的需要,常常运用超现实的想象让物人相通——物具人情,物具人性,即常说的以人比物。庄子笔下的“物”不但如人一样会说话、会思维而且还和人一样会争论、会争辩;不但具有人的丰富表情,而且具有人的丰富情感。
(1)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庄子·秋水》)
有学者认为其中“旋”字当训为“还”,系还返、回复之义;“面目”当指与神情有关的面容。“旋其面目”,即是回复其面容,而并非“转过脸”或“转过头来”之意。[1]如此,从“欣然自喜”到“旋其面目”再到“望洋而叹”,三言两语,便把河伯这一形象的表情与神态的变化栩栩如生地凸现在人们面前。
(2)罔两问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发,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问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无有待者乎!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庄子·寓言》)
其中,“景”,即影;“罔两”,指影外微阴;“括”,指括发,意为把头发束起来;“强阳”,意为徘徊。[2]339这里不仅赋予影子及影子的影子以人的种种行为动作,并且二者还能像人一样会发问、会辩解,既奇异又生动。
(3)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庄子·秋水》)
其中,“怜”,意为爱慕[2]188。这里把人的情感行为“怜”移植到“夔”、“ 蚿”、“ 蛇”、“ 风”等身上,从而不也就赋予了它们人的禀性?
(4)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若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庄子·人间世》)
这是栎树在作理性的辨驳,在阐述无用之用的道理,同时表达对匠石的不满与愤慨——一棵人格化的栎树不正活灵活现地屹立在人们眼前!
(5)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云将见之,倘然止,贽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为此?”
鸿蒙拊脾雀跃不辍,对云将曰:“游!”
……(《庄子·在宥》)
其间,“云将”指云主将,“鸿蒙”即自然元气。“游”,指游历、游玩。“拊脾”,意为拍大腿。显然,这里又把“云”与“鸿蒙”这两种自然之物拟人化了。不仅如此,通过“拊脾”“雀跃”这两个形体动作,更是把鸿蒙那种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2.以人比理
《庄子》是一个寓言的世界,《庄子》也是一个拟人化的世界。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庄子》拟人化的世界里,庄子不仅把动物、植物以及其它自然之物等人格化,而且庄子还常常把某些抽象理念或哲学概念予以人物化——让它们像人那样活动着,也让它们像人一样具有理性与智慧,这便是以人比理或称概念的人格化。而这或许也是庄子对拟人这一修辞方法的一种创造性发挥!
(6)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庄子·德充符》)
有学者对“伯昏无人”这一名字是这样注释的:伯,长也,大也;昏,不精明,无作为也;无人,忘己忘人,物我同一。[3]249显然,这里作者把复杂而深奥的得道之理寄寓在一个虚构性的人物命名上,既巧妙又极具神韵。
(7)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庄子·天地》)
根据陈鼓应所引,这里“玄珠”便是“道”,“知”为“智”,“喫诟”为“言辩”,“ 象罔”乃“无心之谓”。[4]302-303而“道”、“智”、“言辩”、“无心之谓”不都是抽象的概念吗?然而,经过庄子的创造性处理,同样把“有心失道”“无心得道”这一深刻的思想理念隐含在这一人格化的寓言故事之中。
(8)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曰:“其数若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
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中而叹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
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庄子·知北游》)
成玄英注曰:“泰,大也。至道宏旷,恬淡清虚,囊括无穷,故以泰清、无穷为名也。”又曰:“至道玄通,寂寞无为,随迎不测,无终无始,故寄无穷、无始为其名焉。”[2]257可见,“泰清”、“无穷”、“无为”、“无始”原来都是“至道”这一抽象的哲学概念的化身,加上它们之间理性对白的设计,这样也就把原本看不见的抽象概念与抽象道理得以直观化与形象化。
二、《庄子》拟人的修辞功能
我们认为,《庄子》的作者之所以对拟人这一手法如此痴情,并因此开辟出一片诱人的修辞景观,这是因为借助它可以达到别的手法所无法达到的功用与效果。
1.有助于提高言说信息的可读性
谁也无法否认,《庄子》是一部言“道”之书、传“道”之书,而且《庄子》所言、所传之道更多的是老子所说的“常道”——具有宇宙本源性的永恒之道,其深奥性与抽象性由此可见一斑。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言说意图、达到理想的言说效果,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即言说信息的可读性——形象性、生动性乃至于趣味性。显然,拟人这一修辞手法对此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作者(庄子)以生花的妙笔,用拟人手法,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以生命,让它们从思维世界的逻辑轨道上跳到人间舞台,像人那样活动着。如泰清、玄冥、知、满苟得、无足等,都是‘无状(现实中不存在)之状,无象(非人的耳目所感知 )之象’,转而寓托为人名,思想被穿上外衣,赋予血肉,完全形象化了。”[5]这里尽管只是对概念的拟人化所作的评定,可是物的拟人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2.有利于传达言说者的情感信息及其思想
陈汝东先生对拟人这一修辞手法的功能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无论是把物当作人来写,还是把人当物来说,运用比拟建构的话语较之平铺直叙的话语,其情感信息有显著增加。拟人是把物当作人来写,从说写者角度来看,是把用于人的词语用来描写事物,其动机就是为了更有效地传达出作者的情感信息,表现说写者的爱憎。”[6]228-229的确,当言说者在对各种各样的事物给予人格化处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这些事物进行重塑——即“人化”:或者赋予人的形貌,或者赋予人的品质,或者赋予人的思想,或者赋予人的情感等等。如此,重塑后的“人化” 形象也就有高大与矮小、美与丑等等分别,而这些分别实际上也是言说者爱与憎、褒与贬等情感的直接投射。换句话说,读者同样可以通过那些重塑后的人化之物的种种样态与性状,感悟到言说者所流露出的情感信息。在《庄子》的拟人世界里,人们正是从河伯的反省、海神的包容、蜩与学鸠的自适、鲲鹏的高远、东海之鳖的质朴、井底之蛙的憨厚、魍魉的思辨、髑髅的深刻、栎社的睿智等,品读出作者对种种自然之物与非自然之物的喜爱之情,进而领悟到庄子借此所要表达的物无贵贱、人与物齐、道通为一的思想内涵。
3.有益于强化言说信息的可信度与接受度
《寓言》篇云:“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意思是说:父亲不替自己的儿子作媒;父亲夸奖自己的儿子,不如不是他父亲的人容易取信于人;这样运用别有寄托的话,并不是我的罪过,而是别人的罪过;一般的人对于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相同的就应和,和自己不同的就反对。可见,正是出于对听读者接受心理的熟谙,并从接受效果的最大程度这一角度出发,庄子常常不得不采用寄托式——“藉外论之”——的言说策略。而拟人化的大量使用,恰恰是这种言说策略的最佳选择。庄子或借助动物、或借助植物,或借助自然之物、或借助非自然之物等予以言说,而这些自然物与非自然物无不是庄子思想的代言,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言说效果的最大化。事实也是如此,“罔两问景”、“髑髅见梦”、“云将问鸿蒙”、“象罔得珠”等等,通过它们所传达出的道理乃至哲理,比起由庄子自己作直白式的告知或说教,听读者对其信息的相信程度与接受程度无疑都要高出许多。而这也是《庄子》拟人的又一功能。
三、结语
《庄子》是一部大迷宫,也是一座大宝藏。说《庄子》是迷宫,是指《庄子》这一文本确实不易读懂;说《庄子》是宝藏,则是因为无论你从何处掘进,都将收获一份不小的惊喜。而今,我们透过《庄子》拟人这一扇小窗口,便也领略到了一片奇异的修辞美景——既有以人比物,又有以人比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庄子》而言,拟人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修辞方法,它更是庄子的一种言说策略,可以较好地为庄子言道、传道服务。
[参考文献]
[1] 郭剑英.《庄子·秋水》“旋其面目”考辨[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26.
[2] 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孙雪霞.文学庄子探微[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249.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302-303.
[5] 熊宪光,陈劲.庄子命名艺术试探[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84.
[6]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2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