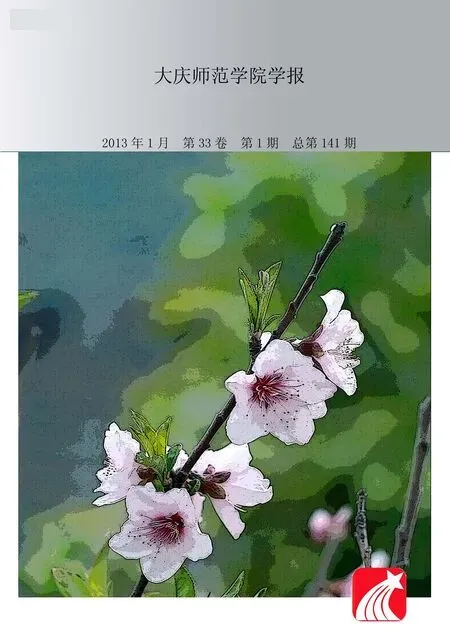宗白华对李白滋菡艺术形象的感性认识
何长仁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在李白诗篇中,月、水、山、绿等意象几乎都是围绕“春”之“生”而诞生艺术心灵的。“春”意味着滋菡,意味着无限发展的蓄意之“生”,最高境界是与“道”共舞。宗白华先生特别嘉许李白,把他排在世界八大天才人物(李太白、杜甫、哥德、萨士比亚、拜伦、叔本华、康德、黑格尔)之首,认为“太白的情调……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1]374而“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1]364由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的节奏相适应”[2]432,诗人的“‘移情’就是移易情感,改造精神”。[2]441也即诗人艺术人格、艺术心灵的自觉。《楚辞》曰:“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是说即使是“滋菊”(做隐士)也要把“春”的芳香留给人间;明朝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谓:“‘九龙吐水浴身胎,八部神光曜殿台,希奇瑞相头中现,菡萏莲花足下开。’迨至菡萏成花。”是说含苞待放的莲花象征神圣之爱的希望和“生”的创造精神。宗先生认为:“太白登华山落雁峰……‘恨不携谢眺惊人句来,搔首问晴天耳。’”诗人热爱“春”的山川水月,概因“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极易唤起宇宙意识;诗人具有这“‘禅’的心灵状态”也即对滋菡的艺术追求,方能“直探生命的本原”。宗白华曾写有一首小诗:“莹白的雪,深黄的叶,盖住了宇宙的心。但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你心中的热烈,在酝酿着明春之花。”[3]400在宗先生看来,因为有了“心中热烈”的“酝酿”,“春”象征蓄意之“生”,艺术家做到心物合一,便会创造出滋菡艺术形象。基于此,他认为“太白的情调较偏向于宇宙境象的大和高”;而滋菡之“春”作为复合意象,在李白那里可谓是“一方表现其天才自然流露,一方表现其智慧之整体或结构”[3]490。“概彼之思想为有意义的、有组织的,可成功为宇宙观及人生观”[3]487。我们不妨以李白的《关山月》一诗为例加以说明。诗曰:“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宇宙之“春”的创生之力惠及“玉门关”,春风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界无比蓄意之“生”的强大力量。但诗人的观照却急转为“以大观小”[4]103,“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5]219诗人欲将这人间之“小”回归于宇宙之“大”:他对征战带给人民的离愁悲恨深表同情,实际在张扬宇宙的创生之道、好生之德。这些真情流露,既复现了儒、释、道的人文精神的主旋律,又集中反映了诗人宏阔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人民需要仗义报国的勇士,也需要救苦救难的“菩萨”,“济苍生”当是诗人的本分。李白自诩肩负“谪仙”、“居士”双重道义,他的一生,就始终朝着这个既定目标挺进;他的诗篇融合儒、释、道哲学精神于一体,创造了滋菡艺术形象,赢得了历来人们的喜爱。对此,宗先生将其视为“天才的创造物”,认为“天才为直觉之智慧,并非纯由经验得来者。”[3]487-489意思是李白的天才创造,得力于李白本人对“涤除玄览”、“忘我”、“禅意”的感悟实践。他的“有意义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契合道、儒、释有机哲学方法论,具有集大成的创造特点。剔除李白的宗教色彩,所剩全是人文关怀、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
以上,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宗白华先生对李白滋菡艺术形象的肯认,现就其感性认识论方面作如下解读:
一、“缘起性空”的象征主义文学观
宗白华受柏格森影响形成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美学理论,在纯文学观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被关注的重点。宗白华较早地将艺术的定位偏重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艺术的过程终归是形式化。”然而,“伟大的艺术是在感官直觉的现量境中领悟人生与宇宙的真境,再借感觉界的对象表现这种真实。”宗白华对李白滋菡艺术形象的判断,就是要求在“现量境”中领悟“缘起性空”的“真境”,赋予生命真爱以象征意义的形式。“缘起性空”的“性”,指的是生命的本源;“缘”,即“关系”。这里指“现象、实在和存有被限定在一组本质上不可分离的关系结构中”[6]78。在宗白华看来,只有把“关系”置于生命本源中才会体现生命真爱,而生命体验达到亦真亦幻的“真如”(象其所象)境界就是“性空”;象征主义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实写的“艺术之世界,乃另一世界,介乎真假之间,名曰艺术之真实”[3]442。倘若执著于“真”必然偏执于内容优先,“如蜡人院及假山水等,几如真者一样,反不觉其有艺术之价值”;而对虚写的象征界,倘若执著于“如”,“纯粹幻像,反不足引起美感。”[3]447“所以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超俗凡近,深深地深深地坠入这世界人生的一层变化迷离。”[1]407他指出:“形式主义的美学说,谓内容绝无关系……内容主义的美学说,谓一切美不外表现其内容,高等的美术,皆为美术人格之表现。缺点在谓‘表现即是美’,实不可视为定论,因纯粹表现,有时不能算美,表现能入轨道,方可谓美也。”
宗白华强调,考察诗人的艺术行为表现(形式)须紧密联系其艺术精神的思想意涵(内容),“实则形式与内容,并不可偏废也。”[3]436而“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2]270。因此,用“真如”的象征境界来表现“缘起性空”的价值意义,主要取决于“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1]345这里,“艺术心灵”就是诗人要有“‘禅’的心灵状态”。惟其如此,才能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表达的沉思,无可解答的疑问……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1]408。
总之,宗白华的象征主义文学观,主旨在于“缘起性空”。他对盛唐诗人,尤其是对李白的首肯,都是建立在这一文学观基础上的审美判断。
二、“浑然一体”的印象主义批评观
宗白华对李白诗的评价,基本上采取的是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一是侧重于对李白的象其所象的整体感悟和把握。在艺术创造中,象其所象就是诗人在对经验世界的整体把握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宗先生说:“‘象’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创造的技术的(美术的诗学)的知识对象’”。[3]591“象”本身是宇宙真相,而“我们所能直接认识的始终是个浑然一体的经验世界”,它离不开人的主体之“象”(心象)。宗先生说:“从这心象的绵延创化推断生物现象的绵延创化以至于大宇宙全体的绵延创化。……哲学家大半融科学家及诗家的天资。”其“无意识的直觉,渐渐光明,表现出来,或借说文章,或借图画美术,使宇宙真相得显示大众,促进人类智慧道德的进化。”[3]67-79总之,宗先生实际是打破了艺术同哲学等其它学科的严格界限,认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都应善于借助艺术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在宗先生看来,李白诗的“宇宙境象”归功于诗人象其所象的艺术感悟和创造,而批评家也需投入全部的感觉、情感和理智,并在艺术体验中把心灵融进去,才能从诗人创造的艺术形象中把握其整体的艺术精神;二是主张摒除成见,赋予艺术同情。他认为,艺术同情是社会的存在根据和完善,“艺术世界的中心是同情,同情的发生由于空想,同情的结局入于创造。于是,所谓艺术生活者,就是现实生活以外一个空想的同情的创造的生活而已”[3]318-319。他称赞“苏格拉底所重视的是艺术的精神内涵”,“希腊的哲学是世界上最理性的哲学,寻求纯粹论理的客观真理”,赞美荷马史诗“描绘了一部光辉灿烂的人生与世界”,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给予艺术较高的地位”,“他能注意到艺术在人生上净化人格的效用,将艺术的地位从柏拉图的轻视中提高,使艺术成为美学的主要对象”[1]54-59。在宗先生看来,艺术同情不仅适用于诗人,同样适用于哲学家和批评家;三是多采用一种诗性的表述方式,用感性的富含形象和情致的语言,将自己对作品的整体阅读体验凝成一个或一组鲜明的意象。如说:“李太白的诗也具有这高、深、大……都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就是用一两句话,概括一篇作品、一个作家的风格。概而言之,宗先生的印象主义批评,不仅是感性的、非逻辑的、形象的,也是经验比较的、富有同情心的整体把握和领悟,它实际融入了宗先生的自我和艺术人生体验的心得。
三、建构艺术精神之体系的美学观
在对文艺功能的梳理中,宗先生认为,“民族的盛衰兴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自信力’”。“这种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熏陶。”“初唐诗人的壮志,都具有并吞四海之志,投笔从戎,立功塞外,他们都在做着这样悲壮之梦,他们的意志是坚决的,他们的思想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诗人才可称为真正的民众喇叭手。”[1]121-123由此可见,宗先生的美学主张,主旨在于建构艺术精神之体系。他的六境界说,客观阐释了李白滋菡艺术形象的精神意涵。而李白滋菡艺术形象的历史成因,亦可在宗先生的学术观点中见出端倪。一是宇宙观。老庄,言恻隐之心、思无为之治、行退隐之道。恻隐之心主张贵生、同情;无为之治,缘于天人和谐之玄思;退隐之道,在于返归自然本真之玄朴。比照中西,宗白华考察其言、思、行、止,乃高远之道玄境界。他精研《周易》,首推“气韵生动”之宇宙观,其次是生命观。孔儒,言仁爱之心、思有为之行、行禅让之道。比照中西,宗白华考察其言、思、行、止,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主张,乃是艺术人生雄伟奇秀之境界。结合艺术人生实践,比照中西,复验“刚健清明”之生命观;三是艺境观。释佛,言之于口(佛咒、禅语)、解脱于头(破除色空谜团)、获证于心(思维修),思“灭苦”之行,行忍让之道。主张万物皆空,静照在心。比照中西,宗先生考察其言、思、行、止,放下即同情,舍身即精神,其“物我两忘,梵我合一”的宗教境界或通于艺术创造,遂悟得“静照现量”之艺境观;四是审美观。在处理宇宙观、生命观、艺境观三者之间关系时,宗先生把道玄、圆融的宗教境界实际看成是艺术境界的精神来源。在他看来,艺术体验以艺术理论来指导实践,便沟通了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进入了“艺术境界”的最高层次:禅悟的灵境。宗先生认为“艺术境界主于美”[1]357-358。揣摩宗先生的意思,学术是一种理性思辨境界,宗教是一种感性直觉境界,而艺术境界就是将此二者沟通起来的一种圆融境界。宗先生就是要用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哲学的审美观,来唤醒国人对艺术哲学和艺术生命意识的觉醒。他所推崇的李白,“实际上是以胡地的风气、胡化的气质和长江文明的气象,改造了盛唐的诗坛”[7]。在李白身上非但有艺术人格的价值取向,更凝聚有滋菡艺术形象的精魂。
结语宗先生对李白艺术形象的感性认识,滋菡与“救赎”实际成了他思想的主旋律。铅华洗尽返真本,他要用这种扎根于本土的蓄意发展的“生”的力量全面推动民众的艺术生命自觉,决意用艺术的人生感动中华。在他那里,我们能感悟到李白滋菡艺术形象实际已不属于学术境界之存在,而是活化于人生“至善至安”的艺术境界之中。李白滋菡艺术形象的概念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唯有感性形象中那种深邃的艺术人生之道,那种伟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才具有永恒的生命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卷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卷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3]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卷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4] 沈括.梦溪笔谈校证:卷之十七[M].胡道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卷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罗嘉昌.关系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M]// 罗嘉昌,郑家栋.场与有:第1 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7] 杨义.李白诗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分析[J].新华文摘,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