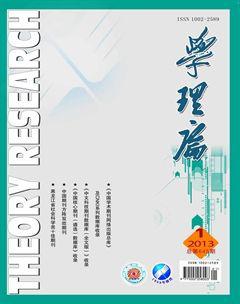浅析汉代《诗经》学与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的关系
桂珍明 楚宝阳 尹学敏
摘 要:《诗经》与其他四经相比是“五经”中能够更直接、全面了解汉中及其他地域文化的文本。以汉代《诗经》学中关于汉中所在地域的文化地理背景为基础,着重分析其中涉及到汉中地域及其他与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特征形成、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探求汉代《诗经》学与汉中文化之间关系,并揭示汉代《诗经》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汉代;诗经学;《韩诗外传》;《毛诗正义》;汉中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2;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78-03
“汉代诗经学”源于先秦儒家《诗》学,历经秦火之后,汉代各家对《诗》的文本传承、经义解释、学术研究而形成一项专门学问,又因汉代“五经”地位定型,故称“汉代《诗经》学”。《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薮和地域文化之结晶,“其中汇集的传说、神话、巫术、祭典、信仰、艺术原型、语言表象、名物制度、生活习俗、社会家庭组织形态等等”,都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它像《伊利亚特》《奥德赛》《旧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万叶集》等民族原典一样,是展开‘释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合适文本”[1]1,其中又包含了大量的地域民风民俗等文化因素,也是研究地域文化的重要文献。学术界多从学术史、《诗经》学与宏观文化层面进行论述,对于汉代经学中的《诗经》学与小区域文化的形成、流变关系研究,目前成果颇少,因而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探求汉代《诗经》学与汉中文化的关系。
一、汉代《诗经》学视域下汉中文化地理背景
“汉中府,《禹贡》梁州之域”,①可知汉中在古“梁州”之域。“周、召者,《禹贡》岐阳之地名……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2]8,再者《尚书·西伯勘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3]248,文王“兼梁、荆”与“文王典置南国江、汉”均证明汉中在南国王化之地。据《公羊传》载:“天子称三公……天子三公何?天子之相也,则何以称三?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4]49,“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阳承天、德安、光黄、汝、颖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顺庆、保宁是已”[2]10,“十五国风首为《周南》,次为《召南》。周南地区在汉中盆地西部及汉水上游一带,召南地区在汉中盆地东部及南阳一带,号称‘二南。”[5]83可见“汉中”所在的地域必是《周》、《召》二南之地,故其文化地理基调必是《诗经》“二南”国风。
二、汉代《诗经》学视域下汉中与周边地域的联系
(一)汉中与周边地区的政治联系
十五国风中的《秦风》、《豳风》、《魏风》、《王风》、《桧风》、《陈风》与汉中所在的周、召“二南”在政区上有联系。《秦风》的地域“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抚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故秦地于《禹贡》时跨有雍、梁,诗风兼秦、豳两国”[6]306《秦风》所处地域和《豳风》在一起,南兼雍、梁,故汉中必与《秦》、《豳》二风有直接的地域联系。《魏风》的地域“魏国……在晋之南河曲”[6]308,其地在山西南部、山西陕西交界处,即与《秦风》、《豳风》、《召南》地域相邻。《王风》地域“周地……今之河南雒阳、■城、平阴、偃师、巩、缑氏。”[6]308,在今之河南,居《诗经》周南之北。《桧风》“桧者……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7]105,“洧水出自河南密县西南马岭山。水出山下,亦言出颍川阳城山,山在阳城之东北,盖马岭之统目。……洧水又东流与黄水合”[8]333-335,其地域在颍川,今之河南登封市、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市以南,叶县、舞阳以北等地。《陈风》“陈者,太■氏之墟。淮阴,古陈国,舜后胡公所封也。”[7]98,其地域“今河南陈州府治附郭淮宁县,陈故都也”[9]462,《陈风》之地域在今河南南部且与《周南》之地毗邻。以上这些相邻区域与汉中在政治、地理上紧密联系,故汉中“夏时,汉中地区属梁州。……殷商时期,属巴方。……西周时期,将梁州并入雍州。……春秋时期,本区是蜀国的一部分。战国时期,为秦、楚、蜀、巴争夺之地。”[10]8-9从先秦到两汉,汉中郡先在东西方向上受巴蜀节制,后在南北方向上归秦管辖,至汉代亦如秦置汉中郡。
(二)汉中与周边地域的经济联系
汉中在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上,又在荆楚、巴蜀地区的中点位置,《史记·货殖列传》:“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唯褒斜绾毂其口。”扼南北交通要道,足见“汉中”为战略交通枢纽。《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足见汉中为其战略核心。同时汉中物产丰富,故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苏秦说:“取其(汉中)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也。”汉高祖刘邦以汉中为基地,萧何留守汉中源源不断地将汉中、巴蜀物资运给刘邦,成为其开大汉四百年基业之先河,即“汉中开汉业”。“自古以来,(汉中)就是连接西北与西南、东南的通道和辐射川陕甘鄂的主要物资、信息集散地之一。”[11]两汉时期汉中因商业发展与巴蜀、秦陇、荆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在本区域自西向东的汉水、沟通南北的秦巴栈道则起到经济动脉之作用,因此汉中文化形成与发展必得益于与周边区域的经济交流。
三、汉代《诗经》学视域下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特征
《诗经》之中,《周》、《召》二南系直接产生在汉水流域的诗篇,《大雅》、《小雅》则从汉水流域外的视角来刻画汉中文化,因而立足《诗经》来看两汉时期汉中域文化之特征,则必从汉水流域内、域外两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诗经》“二南”国风所体现的汉中文化特征
1.关雎之道,礼乐之行,彰显女性之德行。观“二南”之诗《关雎》、《汉广》等十二篇皆言女性,《关雎》为国风之首,“‘《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北自南,无不思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诗》曰:‘钟鼓乐之。”[12]165孔子将“关雎”提升到“生民”、“王道”的重要地位,足见其意义之重大;而良士求偶,因“钟鼓”礼乐之道为之,更著女性之尊,彰显女性之德行。“战国时代,是一个封建政治解体,大一统专制尚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代,妇女的地位,有相对提高。……韩婴在上述各种背景之下,《诗传》中特别注意到女性在社会、人生中的意义”[13]42-43。故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两汉时期)“穆姜温仁,化继为亲。……泰瑛严明,世范厥训。……杜氏之教,父母是遵。……礼■肃穆,言存典韵。……文姬■敏,宗祀获歆。……陈氏二谦,或智或仁。……礼修顺姑,恩爱温润。……树南悼夫,轻死重信。……祈祈令姬,如玉如金。允矣淑媛,齐德姜、任。总赞此九人也。述汉中列女”[14]607-609。
2.建功立业与宁静守虚。《周南·兔■》:“肃肃兔■,■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汉地“武夫”为公侯之腹心,彰显了士人建功立业开拓进取之决心。故汉中张骞万里凿空,立功绝远之地,尽显汉中士人建功立业开拓进取之精神。东汉末年,老将黄忠刀劈夏侯渊,诸葛武侯屯兵汉中,锐意北伐均体现了两汉时期汉中文化中的“建功立业”的特征。汉中文化存在“建功立业”特征的同时,“宁静守虚”又为另一特色,汉初张良归隐紫柏山;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号谷口子真”[14]597上述材料展现了两汉时期汉中文化“建功立业与宁静守虚”共存的特征。
3.忠诚正直勤政。《召南·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甘棠》歌颂召公勤于政务,故民怀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茏”,《小星》:“■彼小星……夙夜在公,实命不同!”《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又曰‘■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9]103,为讽刺之诗。反映“召南”之人鄙小人与君子同列于朝,颇见忠直之义,更见政风淳朴,为汉水流域忠直勤勉政风之开端,故屈原与张仪、靳尚等人抗辩于朝堂;延及两汉,汉中李固中正直行,与权贵、宦官抗争,为“北斗喉舌”,最后为正道献身;诸葛武侯,勤勤恳恳“夙兴夜叹”、“奔走驱迟,六出祁山”,告诫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更为历史上忠正勤劳之典范,乃汉中汉魂中正人格之源。
4.多元兼容。“汉水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我国自然地理南北差异的过渡带,既是我国南北两大文化的结合部,又是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15]3,“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发轫于南国楚地的《楚辞》风格迥异,前者尚实质朴,后者浪漫华丽,极其生动地展示了两大地域文化风貌特质上的差异。但非常有意义的是,《诗经》和《楚辞》所描写的地域文化恰好在汉水流域重合”[15]3《汉广》与《楚辞》之风格甚近,汉水流域婚恋爱情诗亦多委婉,不似北方直率,而多南国柔和之美;而《楚辞·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其气度甚大,视野更开阔,于南方阴柔之中多了一份阳刚之气。两汉时期,特别在高祖二年,关中饥荒,下令迁民蜀、汉就食。这从移民的角度为汉中文化发展奠定了多元兼容的基因,在这之后,特别在东汉末年,外籍人士大量入汉,张修、沛国曹操、张鲁、涿郡刘备、琅琊诸葛亮、荆州魏延、西凉马超、南阳黄忠、巴西宕渠王平等一大批外来人士均在汉中留下了辉煌的足迹,这对汉中“多元兼容”特征的形成与发展作用甚大。
(二)《诗经》其他篇章所体现的汉水流域文化特征。在《诗经》“二南”篇章之外,《大雅》、《小雅》亦有关于汉水流域之记载,即汉水流域外对“二南”和汉中地域文化的观照
1.敬天保民,天人合一。《大雅·旱■》中记载周王,“瞻彼旱■”,备“玉瓒、清酒、■牡”祭祀旱山。其一体现了周人敬天,以敬天而求民之福禄,“周族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9]840;其二祭祀地点在“旱■”,今之汉中汉山,从另一层面体现汉中之汉山是祭祀中心。此处重祭山,具有楚地“重淫祀”的特点,故在两汉时期汉中“重祭祀”的文化背景下,五斗米道在汉中应运而生。抛开迷信成分,可以看出,人们“重祭祀”体现了此阶段汉中文化“敬天保民,天人合一”的观念。
2.汉水汤汤,南国之纪,朝宗于海——礼乐隆盛。《大雅·江汉》:“江汉浔浔,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恍恍。”《大雅·常武》:“王旅■,如飞如瀚,如江如汉。”以武夫与江汉相比,江汉气势之盛大以凸显周宣王南征之师旅斗志高昂,也反映出汉江威武盛大之貌。另一方面,《小雅·四月》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传》曰:“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纲纪一方”,汉水汹涌,其气势可威震南国,故可纲纪一方;《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荆及衡扬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注:郑康成曰:‘江水、汉水,其流湍疾,又合为一共赴海也。犹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3]163,可见“江汉朝宗于海”更超越其本义而具诸侯朝宗天子之大义。从礼、乐的角度看,“江、汉”之形象大矣,天下江河不独“江、汉”,而以江汉喻之,足见其地位之隆尊。
四、结论
两汉时期汉中文化多姿多彩,然据汉代《诗经》学可看出其文化具有“尊崇女性德行”、“建功立业与宁静守虚并存”、“尚忠诚正直勤政”、“多元兼容”、“敬天保民,天人合一”及“礼乐隆盛”的地域文化特色。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首先汉代《诗经》学为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理基础;其二,汉代《诗经》学与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的关系进一步体现在汉代《诗经》的基本思想与汉中地域融合,从浅层次文化逐渐影响到两汉时期汉中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先秦时期,《诗经》中“风”、“雅”、“颂”三部分保存了大量的地域文化信息,而在经历汉代儒家整理之后,则奠定了地域文化在汉代《诗经》学中的文化地理背景模式,便于人们充分发掘和研究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政.《诗经》文化人类学[M].合肥:黄山书社,2010.
[2]李勇五.《诗经》“周南”“召南”地域及时代考[D].太原:山西大学,2005.
[3][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李学勤.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唐]孔颍达.毛诗正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8][北魏]郦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清]王先谦,著.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杨起超.陕西省汉中地区地理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1]汉中市政府网.汉中概况[EB/OL].http://www.hanzhong.gov.
cn/hanzhonggov/72340168526266368/20051205/10738.h-
tml,(2005-12-30)/[2012-11-20].
[12][汉]韩婴,许维■.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
[14][东晋]常璩,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梁中效.试论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特征[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责任编辑: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