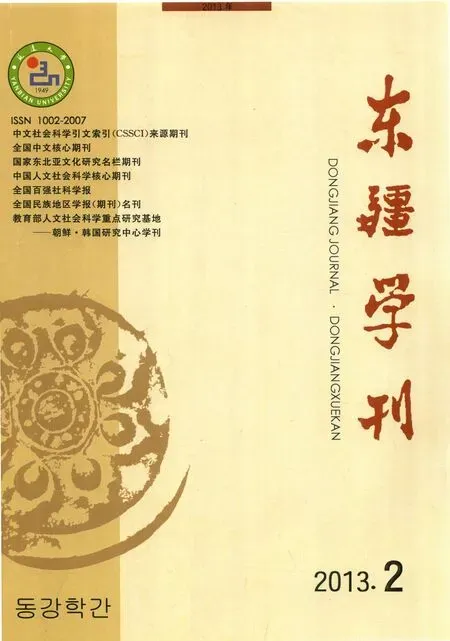庄子与卢梭的自然观比较及其文化意义
董 晔
庄子和卢梭是东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家。虽然时代、地域不同,但二人在哲学、美学思想方面,尤其是在自然观方面很相似。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他们追求二者的和谐统一;在社会理想方面,他们追求自由、平等;在审美态度方面,他们追求本真、拒绝人为。当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二人的自然观在哲学基础、社会理想和审美态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根本不同。这些异同点为二人及其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阐释的有效空间。
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基本哲学问题上,庄子和卢梭均主张二者和谐相处,而反对将其对立起来。原始的自然崇拜、天人感应思想,在老庄的道家学说那里被提升为整体的哲学认识。在庄子看来,“天”与“人”是统一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人”与“天”都统属于宇宙之“大全”,“人”如果从“天”中分离出来,“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宇宙也就不具有整一性。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①本文所引《庄子》原文均出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只标篇名。(《齐物论》),就是说天地虽大,乃与“我”共同存在;万物繁多,却与“我”并无差别。庄子站在物性平等的立场上,主张天地万物的同生同体,所谓“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可见,庄子主张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推动、相互依存的关系。
相比之下,“欧洲人从来不委身于自然”[1](118)。从古希腊直到近代,西方文化中一直在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近代以来流行的功利主义、伦理主义,更是片面强调人的价值,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甚至弱肉强食的法则。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导致自然被过度开发索取,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紧张。直到 18世纪,卢梭呼吁“回归自然”,才启发西方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卢梭说:“在宇宙中,每一个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作是所有一切其他存在的共同中心,它们排列在它的周围,以便彼此互为目的和手段。”[2](394)他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实体之间是美妙和谐的关系;事物发展是无数生生不息的因果链条,在特定的因果联系中,每个事物又互为目的和手段,紧密联系与配合。正是在这种整体论自然观的基础上,卢梭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谐的,其“回归自然”的口号便有了东方哲学的思维特点。
当然,尽管庄子与卢梭的宇宙自然观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而反对将二者割裂开来,但由于东西方哲学思维模式不同,又使他们对人与自然做出了相异的价值选择。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哲学偏向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一向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和谐相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人也不主张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二元划分,而强调认识主客体间的依存与包容,表现为一种不可做物我分离的一元论。比如,“心斋”、“坐忘”作为庄子哲学中最重要的体道方式,就避开了心物之争,要求尽可能地淡化主体意识,从以“我”为中心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在与万物的交融共存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因而具有典型的一元论特征。
与东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专注于认识与找寻“自我”,导致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原始混沌状态逐渐向物我分离状态演化,最终将“自我”从外在事物中分离了出来。“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3](179)。尤其是近代的笛卡尔把世界区分为心与物两种实体,更是对机械论自然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成为卢梭全部思想的一个当然前提。尽管他极力回避并消除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但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还继而在这种模式下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范畴。
所以,庄子与卢梭在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上存在先天的差异:前者在物我不分的思想前提下领悟自然的存在,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天”对“人”的包容;而后者则在主客二分的理论前提下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和自然视作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强调它们之间的平等。从根本上说,这是东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差异,亦即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难免不造成价值判断上的非此即彼,而且很容易导致对问题的实质作形而上学的分析。所以,尽管卢梭竭力通过自然教育、社会契约等方式来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但却一直周旋于自身学说的二律背反之中。实际上,他只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转化为人性演进中的感性与理性、社会契约中的个体自由与社会必然、文明发展中的自然与文化冲突等问题,而并没有在根本上脱离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
二
探索人性的自然、本真,是庄子与卢梭自然观念的又一个共同特征。在他们那里,“自然”一词均具有人性的本然、天然、自然而然等含义,所以,这一范畴不仅与宇宙认识观相连,而且还有着伦理的、审美的内涵。生活于当时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庄子与卢梭,认为文明发展戕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因而对历史的前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文明发展不仅使人性失去了原初的真实,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罪恶,因而主张自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遂以“自然”作为标准来衡量现存的伦理秩序。实际上,庄子与卢梭正是基于对一种完全未经文明浸染的人性“自然状态”的预设和追溯,批判了伴随社会文明进步而来的人类生存境遇的异化状态。当然,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所以其批判的对象不尽相同。这意味着面临社会文明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庄子与卢梭必然选择不同的解决路径。
先秦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反对人为。所谓“人为”,即用外力强行干预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庄子的学说中,这类非自然、反自然的“人为”活动,既包括“落马首,穿牛鼻”(《秋水》)等野蛮行为 ,也包括“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天地》)等技术行为,还包括儒家的“杀身成仁”、墨家的求道于“义”等忽视个体生命自然存在状态的礼乐仁义与赏罚刑法等。具体地说,庄子一方面抨击了仁义礼乐制度对人之自然本性的背离,认为这些制度毁弃了自然人性,倡导仁义礼乐将最终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所谓的“……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在庄子看来,自黄帝倡导仁义始,人之自然本性就已散乱;随着儒、墨成为显学,人们越发追求巧智,各种刑具和惩罚制度亦逐渐兴起,所以猜疑、欺诈、责难、讥刺等淆乱人心,天下渐趋衰败。另一方面,庄子还揭示了礼义仁德的虚伪,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知北游》)。认为儒墨两家倡导的礼义仁德是在失却“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不但遮蔽了人性的自然本真,还内化于世俗人的各种形式化、工具化行为,成为“道”的伪饰与乱之祸首。他提出“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并且认为真正治天下的理想境界是顺应人性自然,实现人与万物同生同存的“至德之世”,所谓“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
如果说庄子面临的是中国农业文明早期人为的“凿木为机”的状况,那么,摆在卢梭面前的则是像“矿坑、矿井、熔炉、锻炉、铁砧、铁锤、弥漫的煤烟和熊熊的炉火”[4](92)等西方工业文明初期的机械化作业。卢梭极力反对人类的“胡作非为”,即理性之误用,认为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不但破坏了人们的自然生活图景,还造成了自然人性的扭曲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不仅如此,他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伴随科技发展而生的私有制社会,认为其所孕育的专制政体戕害了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在卢梭看来,处于人类社会“黄金时代”的人们依照本性生活,人与人之间既没有相互的奴役和剥削,也不存在道德意义上的不平等,彼时的人性呈现出原初的自由和本真。然而,“那些在自然状态下几乎不存在的不平等,随着人的能力的开发和思想的进步而扩大、加深,随着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而稳定下来,变得合法”[5](138~139)。在私有制出现后,人类的天赋自由消失了,人与人之间逐渐沦为统治与服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过去处于自然状态的自由的人现在成了受人支配的奴隶或支配他人的主人。为了改变这种异化状况,卢梭指出,以往的社会公约只是为一个人的专制制度服务,无法保障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平等,而疗治时弊的唯一办法就是平等地签订社会契约,转让个人所有的权力甚至财产,使“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6](24),由此产生一个公意指导下的政治国家。
因此,尽管庄子“所采取的方式非常完整地预示了卢梭后来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论科学和艺术》中所采用的方式”[7](237),但二者却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庄子的社会理想是万物各适其性的“至德之世”,即人与禽兽同乐、与草木同生的原始社会状态,而这种状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么至少从表面上看,卢梭也同样追怀纯朴的太古时期,只不过他的“回归自然”并非真要人们退回到身穿兽皮、手拿石斧的蛮荒时代,也并非主张“毁灭社会”、“返回大森林和熊一起生活”[5](155)。在此问题上,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并不是想要作为一个关于过去的历史记事,它乃是一个用来为人类描画新的未来,并使之产生的符号建筑物。在文明史上总是由乌托邦来完成这种任务的。”[8](78)所以我们认为,卢梭批判人类社会的历史,但并不否定历史的发展;他反思理性的误用,但并不否定理性的作用。卢梭思想的关键点不是破坏而是重建,这突出表现在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设计中,即通过契约转让重塑社会历史秩序,让每个人在契约社会中重获自由与平等。
三
由上可知,庄子与卢梭分别从不同的路径找寻自由和平等,即前者是“顺应自然”,而后者是“回归自然”。如果说庄子向往的是“织而衣,耕而食 ,是谓同德;一而不党 ,命曰天放” (《马蹄》)的无为境界,是一种取消个体自我意识的消极存在,那么,卢梭追求的则是致力于建立符合自然本性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有为状态,是一种凸显主体自我意识的积极存在;如果说庄子把个体养生当作最重要的生活目标,而将国家帝王之事视为“绪余”、“土苴”,难免有否定人类文明的虚无主义嫌疑,那么,卢梭则强调主体创造历史的能动性,试图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来尽可能地还原理想的自然生活,从而具有重塑人类文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进一步说,如果说庄子“顺应自然”的虚无主义对于实在的个体生命而言是最真实的,所以可被视作一种有意义的虚无,那么,卢梭“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对于现实的社会制度而言却是最浪漫的,以至被看作一种消极浪漫主义。当然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无论“顺应自然”还是“回归自然”,都是不切实际、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二者那里的“自然”反而具有更重要的文化意义与审美意义。
在庄子和卢梭那里,“自然”都具有一种返朴归真、淡泊宁静的意味,所以他们同样将本真、素朴作为艺术审美的最高原则。如庄子强调“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倡导“无以人灭天”(《秋水》);而卢梭也认为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真正的美,是美在它本身能显出奕奕的神采”[2](551)。相应的,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贬抑人为造作的艺术美,如庄子指出“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扌丽工亻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月去箧》);卢梭则借以道德纯朴著称的法布里修斯之口呼吁:“赶快拆毁这些露天剧场,打碎这些大理石像,烧掉这些绘画,赶走这些征服了你们并以他们那些害人的艺术腐化了你们的奴隶吧。”[9](36)在此,我们不能因为庄子和卢梭学说中的反文化倾向而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应从他们批判的精神实质以及所构建的艺术理想中发掘某些新的文化与美学的内涵。
首先,就批判的精神实质而言,二者文艺批判的主要针对点仍是工具理性之运作。在庄子看来,巧智的行为只会淆乱人心、自绝于“道”;卢梭也认为,工具理性的滥用将导致人性的异化和生存环境的恶化。当然,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历史语境,所以批判的具体所指亦不相同。庄子主要针对的是儒家的礼乐文化,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五趣”皆是“礼”的化身 ,它们皆使人“失性”,“皆生之害也”(《天地》)。由于人为法则只会让文艺离“道”越来越远,所以他提出“自适其适”与“灭文章,散五采”等。卢梭更多地站在民主、大众的立场上,批判路易十五时代遍布法国的矫揉造作、卖弄式的贵族艺术。由于此类艺术满足的是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精神需求,所以在艺术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上流社会及宫廷生活,而平民百姓则往往被排斥在外,“这种收费的现代的戏剧演出到处都助长财产不平等的增长”[10](116)。所以在卢梭看来,“艺术”是不平等的象征。
其次,虽然二者均以“自然”作为标准批判当时的艺术和审美观念,然而他们在构建新的文艺理想时,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庄子的艺术理想可谓“技进于道”,即像庖丁解牛那样地“游刃有余”。最好的艺术不只是技术,更应以技彰道、顺应自然,通过技艺的解放带给人更多的自由感。这必然要求艺术主体“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庚桑楚》)。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疑通向的是与道合一的“逍遥游”境界,即在简单、质朴、自然中体验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因此,有学者指出:“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11](44)反观卢梭,他一方面把情感视作文学艺术的本质,从而抓住了文艺区别于科学、哲学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艺除了自身形式上的纯粹审美意义之外,还应具有作为升华人性、教化风俗的道德载体的价值。换句话说,卢梭始终站在一个道德家的立场上,把是否有助于促进人的幸福、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以及培养纯朴的民风与自然的人性作为评价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所以他不会幻想通过艺术审美解决人性和社会问题,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政治、社会制度的变革解决艺术审美问题。总的来说,庄子与卢梭在审美态度上的不同表现为:前者是以“道”观物,后者则是以“善”观物;前者追求有大美而不言的天道与无为精神,后者追求个体情感的真实流露与主体精神;前者向往“乘物游心”的人生境界,更加接近纯粹的文学艺术审美,后者主张美与善的结合,具有更强的社会功利目的。
综上所述,庄子的自然观念更多地指向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当然,这里的“道德”与其说是伦理,毋宁说是人为,他的“自然”所包含和意味的种种非人为、反人为倾向,并未妨碍其关注个体的存在意义与生命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庄子的虚无主义自然观指向一种有意义的虚无,可能暗示着某些极为深刻的人生价值规律;而卢梭的自然观念更多地指向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只不过他的“自然”包含、意味着太过理想的道德设想和太过直接的功利目的,所以他实际上走向了文化浪漫主义,虽然于社会现实是最理想化、最不切实际的,但其在艺术审美领域中却有着最积极、最发人深省的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12](179)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过程中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虽然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但它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导致了如道德败坏、人为物役、精神焦虑、生态危机等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诸多问题。有学者指出:“卢梭提出的问题,是 18世纪思想生活的中心问题,也是19世纪哲学探索由此出发的理论前提。”[13](146)从文化价值层面上说,庄子的“顺应自然”与卢梭的“回归自然”在本质上都是寻求一种回归,即共同呼唤人性与社会的返璞归真,均将目光投向人类的前社会阶段,希望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以此克服理性文明带给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端。尽管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对于如何实现目标的认识和手段亦有差异,却都呈现出一种典型的价值秩序与理想追求,足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仍在检讨文明与异化问题,思考如何处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人从自然中确立,既与自然对立,又与自然无限亲近,这说明“作为自然的参与者,我们引起它的平衡和不平衡,我们是自然建筑的调节者和建设者”[14](286)。
[1][法 ]克洛德· 德尔马:《欧洲文明》,郑鹿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法 ]卢梭:《爱 弥儿》 (下卷 ),李 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3][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 (上卷 ),何兆武、李 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4][法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5][法 ]让-雅克·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6][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北京:商 务印书馆,1980年。
[7][美 ]欧文· 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德 ]恩斯特·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9][法 ]让-雅克·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法 ]卢梭:《卢梭论戏剧》(外一种 ),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14][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黄玉兰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