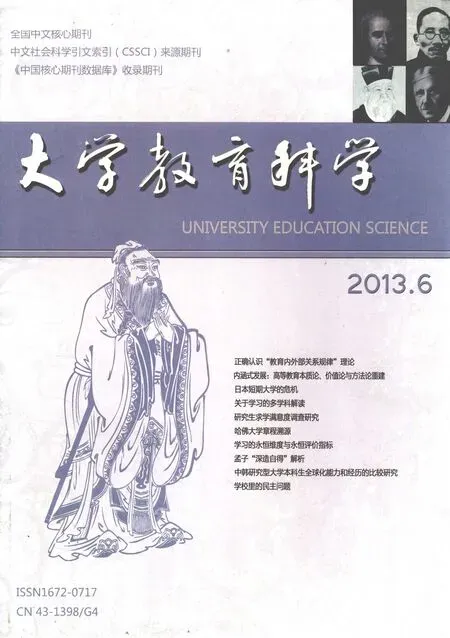孟子“深造自得”解析
□燕良轼 卞军凤
“深造自得”一语最早出自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名轲,前372~前289)。其原文是“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P189)其意是说,君子要达到高深的造诣,进入精深的境界,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以道”),从而获得有自我体验、自我感悟的知识。只有自我体验、自我感悟的知识,才能够掌握牢固、积累深厚;积累得深厚,运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古往今来,有学者对之进行了释义和解析。如赵岐注:“造,致也。言君子学问之法,欲深致极竟之,以知道意。”朱熹(字元晦,1130~1200)集注:“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李贽(字宏甫,1527~1602)《复京中友朋书》:“有顿入者,有渐入者。渐者虽迂远费力,犹可望以深造。”我们认为,“深造自得”泛指学习者在学习中对学习内容在内心不断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加工,以达到精深的境地的学习策略。对“深造自得”这一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命题进行诠释与解析,对当下人们的学习仍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深造自得”是向内心求索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学习者自觉向内心求索的学习。在孟子的学习视界中,学习有两种,一种是“外铄”,即从外部世界获取知识或信息;一种是“内求”,即向内心世界去求索、探究、体验。孟子虽然继承了孔子的“多闻”、“多见”的“外铄”思想,但他更重视内求在学习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内求才真正体现了他“深造自得”的主张。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P259)。学习是一种内心求得的过程。按照孟子的理解,“自得”之学来源于“深造”,“深造”不是向外部世界去索取,而是向内心世界去探求。为什么要向内心世界探求呢?因为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的资质与潜能,只要学习者能够向内“扩而充之”,就能够使这种资质和潜能变成实际的品质和才能,这就是“深造自得”的过程。在孟子看来,外铄虽然也可以获得某些功利性或实用性信息或知识,满足人们眼前某种实际生活的需要,解决人们实际生活中某些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继承了孔子“多闻”、“多见”、“每事问”等向外获取知识的传统,提出了“博学详说”的主张,要求学习者主动获取信息,积极观察,从而从外部世界广泛地获取知识),但是要提高道德境界,获得人生的感悟,解决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就需要向内心求索的“深造自得”。要主动利用与发挥“思”的作用,向内心深处探索,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求则得之,舍则弃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圣人之学一定是自得之学,仅仅向外部世界下功夫,而缺少向内心世界探索的功夫是不可能获得圣人之学的。北宋二程(程颢,字伯淳,1032~1085;程颐,字正叔,1033~1107)认为,要获得圣人之学,就必须要有向内心世界探索的功夫:“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1472~1528)以饮食消化作比,认为“记诵词章之学”,“习训诂,传记诵”之学是没有“消化”的学问,虽然“博学多识,皆伤食之病也”,只有得之于心之学才是被学习者“消化”的学问。在此基础上,王守仁进一步提出,即使消化,也有两种,一是依赖他人点化,二是自家解化。在他看来,自家解化才是真正的“深造自得”之学。他说:“学问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传习录》下)王守仁认为,自得不是得之于口目,而是得之于心。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
二、“深造自得”是自觉与自悟的学习
梁漱溟(字寿铭,1893~1988)说:“凡自觉之所在即心之所在”[3](P67),“凡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3](P68),“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心之所以为心在自觉”、“人惟自觉乃临于一切动物之上而取得主动地位也。”[3](P71)所以说,有了自觉性就必然有主动性,主动性是自觉性的表现。自得之学也是自觉自悟之学。王守仁认为,自得之学要通过自觉才能获得,“学无难易,在自觉耳。才觉退便是进也,才觉病便是药也。”(《与湛民泽·五》)王夫之(字而农,1619~1692)认为,深造就是“自悟”。他说:“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四书训义》卷五)在王夫之看来,“善教”只有与“善学”相匹配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同样的教学水平,学得好与不好、精与不精关键在于学习者的“自悟”能力。“学,觉也”(《姜斋文集》卷三)。《说文解字》说:“斅,觉悟也……学,篆文斅省。”班固(字孟坚,32~92)也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白虎通义》卷六)朱熹在《孟子·万章上》说:“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王夫之说:“随见别白曰知,触心警觉曰觉。”(《读四书大全说·中庸序》)如《说文·心部》云:“悟,觉也。”《玉篇·心部》说:“悟,心解也。”总之,在王守仁、王夫之看来,深造自得的学习虽然也需要师友的帮助和指导,但最终都是要依赖学习者自觉自悟。
三、“深造自得”是质疑问难的学习
质疑问难精神是深造自得的心理保障,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学习的一种重要策略。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学习要达到或实现“深造自得”,就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和善于对问题进行层层追问;敢于对已有结论或定论进行质疑问难。所以,自得之学又是自立之学,即独立思考之学。自立之学表现为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教师的独立思考之学。汉代的王充(字仲任,27~约97)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以一个乡村教师的身份跻身于古代思想家的行列。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他不仅敢于向当代帝师董仲舒发出挑战,甚至向中国的头等圣人孔孟质疑问难,敢于《问孔》、《刺孟》。他以遗世独立的精神批判“世之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他认为圣贤所写的文章即使是“用意详审”也不一定“尽得实”,如果是仓促所言则更“不能皆是”。他认为“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缺乏“考实根核”、“核实道义”、“证定是非”的精神,那种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是不能获得“自得”之学的。
我们的古人认为,质疑与学习具有等值性。有学习发生的地方就一定有质疑,没有质疑的读书、背诵那不能称作学习,更不可能成为自得之学。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质疑而获得自得之学呢?张载(字子厚,1020~1077)说:“在可疑则不可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按照这样的标准,一切缺少问题意识的学习都不能算作学习。在值得怀疑的地方一定要质疑。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那就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在学习和思考中遇到障碍的时候,用现代语言诠释就是在给定与目标之间遇到障碍时一定要质疑,在没有可疑之处也要进行质疑。张载说:“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1139~1193)也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陆九渊集·语录下》)我们的古人已经意识到,质疑的根本作用是防止和克服心理定势。吕祖谦说:“学者不进则已,欲进之则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则不可进乎道矣。故成心存则自处不质疑,成心亡,然后知所疑。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吕东兼文集·杂说》)这里的“成心”就是先入之见和心理定势。在吕祖谦看来,防止和克服心理定势,策略就是质疑,甚至在无疑处质疑,先入之见就无从产生。
按照这样的观点解读学习与教学的结果不是导致学习者疑问的减少,而是导致疑问的增多。准确地说,学习是使旧疑问消除的同时又增加了更多新的疑问。如果一个学生来的时候是一个问号,学业结束时是一个句号,那是很危险的;真正的好学生应当是来时有很多问号,离开学校时应当有更多的问号。在学习中,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字慎修,号杲溪,1724~1777)从小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10岁时,师傅向其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下,他便问师傅:“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著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1929)认为,这故事不仅可以说明“戴氏学术的出发点”,而且“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4]由此可见,质疑问难是深造自得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条件和方法。
四、“深造自得”是自我反省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自我反省式学习。孔子就提出了在学习与道德修养中要“自省”、“自讼”。孔子之所以获得那样多的人生感悟、人生哲理,在其好学、乐学的同时,也在于他善于“自省”,通过自省获得了许多“自得”的知识、智慧和道德。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5](《论语·里仁》)他的高足曾参(字子舆,前505~前432)更是具体实现了孔子的自省理念,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唐代的韩愈(字退之,号昌黎,768~824)也继承了这种自省自讼的思想;“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原毁》)由此可见,学习中善于自我反省是“深造”的重要表现,只有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才能获得许多“自得”的知识。
戴震将孔孟这种自我反省称作“反求诸己”。深造自得是一种“反求诸己”的学习,就是一种内省、反省式的学习。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智仁不智,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静。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其意是说,如果自己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那自己就应当反躬自问:“我对别人的仁爱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如果自己管理别人,别人却不服从自己,那自己也应当反躬自问:“我的智谋还有哪些缺欠?”当自己对别人很有礼貌,别人却不予理睬,那自己也应当反躬自问:“我的恭敬还有哪些做得不够?”孟子就是在学习与品德修养中不断进行这种自我反思、自我反省而走上至圣之路的。与孟子同时代的思想家荀子虽然就主要倾向来说是“外铄”学习论的提倡者,但是他并不否定内省在学习和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见善,修然必以自存(察)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
五、“深造自得”是虚心涵泳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虚心涵泳的学习。什么是虚心?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对“虚心”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荀子(名况,字卿,约前313~前238)看来,所谓“虚”心就是“不以所藏害所将受”[6]。“所藏”,即是人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将受”,是人们将要接受的新知识。那所谓“虚心”就是学习者不应该让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干扰和阻碍即将学习的新知识。也就是说,在学习和生活中不能以已经形成的定见(“成见”、“私主”)来阻碍新知识、新观点、新行为的获得。朱熹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与践行。他说:“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晦庵文集》卷四十八)
什么是涵泳?朱熹回答得很明确:“所谓涵泳者,只是仔细读书之异名也。”他还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虚心涵泳?因为在朱熹看来,许多聪明人难读书,因为聪明,所以常常自以为是,在没有搞清文本原意的情况下,就自立己意,穿凿杜撰以求惊世骇俗。所以他反复讲,“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言杂语,则久久自然有得。”(《朱子语类》卷十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大部分人读书时候先有私意成见,对书里意思的理解很容易就走样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似读书不少,但始终气质变化不大、见识不高的原因,因为读来读去,还是一个成见在作祟。他认为,真正“深造自得”的学习,应当虚怀若谷、静心思虑、仔细研磨、反复体会,从而“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学贵类编》)。在他看来,虚心,才能“濯去旧见”,涵泳,才能获得新意。“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来新意”,只有把虚心与涵泳结合起来,“方能辨其曲直”(同上),使学习得到成功。怎样虚心涵泳呢?按照朱熹的意见,主要有五项[7]:即“不要先立说”(《朱子语类》卷十一)、“不得有自足心”(《文集·答胡季随》)、不能穿凿附会(《学贵类编》)、“不可先责效”(《朱子语类》卷十),即不要主观确定要达到的效果,不应“心粗性急”,而“须要细看”(《朱子语类》卷十一)。
六、“深造自得”是自我体验的学习
“深造自得”是自我体验的学习,就是“切己体察”的学习。“自得”之学必须经历观察、体验的过程。如他所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意即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诗人的本意。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
“深造自得”本身就是孟子自我体验的结果,孟子就是以自己切身体会说出这番话的。我们相信,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学说的领军人物,获得名声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地位,一定从“深造自得”的学习策略中得益不少。孟子不仅在自己的躬身实践中运用“深造自得”的学习策略,将自己塑造成胸中充满“浩然之气”的伟丈夫,而且还将自己的体会写在著作中,供后学者学习、借鉴和发扬光大。朱熹认为:“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学规类编》)他认为,“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明白道理;反之,如果学习停滞于“纸上求义理”、“文字上做功夫”,“不于身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朱子语类》卷九)怎样切记体察呢?根据朱熹的意见,主要有三点:即要“自求自得”,“自用力去做”(《朱子语类》卷八);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学规类编》);要自信不疑,“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朱子语录》卷十一)
七、“深造自得”是自然真乐的学习
孔子就非常重视“乐学”。他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论语·雍也》),主张“学而不厌”,认为“学而时习之”是非常快乐的事,体验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孟子的“三乐”之一(《孟子·尽心上》)。孔孟的乐学之道为后世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明代中叶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1428~1500)认为,自得之学是对见闻知识的超越,“读书不为章句缚”,是情与理的高度融合。具体体现在:首先,自得一定是在快乐的心境中实现的。在痛苦、烦恼中是不会获得自得之学的。“其自得之乐,亦无涯也。”自得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之乐,“自然之乐,乃真乐也”(《与湛民泽·九》)。自得是一种超越,自得者“鸢飞鱼跃,其机在我”(《赠彭惠安别言》)。明代思想家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认为,只有在快乐的情感中才能获得自得之学。他说:“学不至于乐则不安,终非己有,故作乐以安之,如田之入为己有也。此自得之学也。”(《圣学格物通》卷二十七《进德业二》)他甚至提出:“读书遇厌倦时,便不长进,不妨登山玩水,以适其性。”他非常赞赏《学记》中“游焉”、“息焉”的思想,认为“使人乐学鼓舞而不倦,亦是一助精神。”此外,他还指出这种乐学鼓舞而不倦的精神可以防止心理定势“防夺”,克服心理束缚“处处皆梏亡矣”(《甘泉文集》卷六《大科书堂训》),“教者,所以觉人之良知,而归于中正者也”(《圣学格物通》卷四十八《立教与化下》)。
八、“深造自得”是日新日进的学习
学习“日新日进”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礼记》。在《礼记·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千古不朽的名句。显然,古代先哲已经认识到“深造自得”的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进取、天天进步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我们过去对于“循序渐进”的理解仅限于按照知识的逻辑体系和个体的智能水平,有系统、有次序、有步骤地进行。如二程就认为,学习不能操之过急,“学欲速则不得,然亦不可怠”(《二程语录卷十一》)。朱熹说:“读书之法,循序而有常”,《学规类编》有云:读书必须“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此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朱子大全·读书之要》)事实上,我们在理解这些观点时重心偏向了“循序”,而忽视了“渐进”。从二程、朱熹等一系列的言论综合来看,他们所说的“进”,不仅仅只是按顺序向前推进,而是每天都有新收获,每天都有新体验。二程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这里强调的是学习者天天都有新收获、天天都有新观点、天天都有新体验,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朱熹集注云:“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这句话一语中的,深造就是不停地进步、不停地进取,不断创新。自得之学不是通过简单的表面观察就可以获得的,而是通过深思熟虑才能获得。所以他说:“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再有“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没有经过深思的记问之学不能“体味”书之真谛。正如二程所认为,一个学习者如果真正做到“日新者日进”、“进而不已”,还怕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吗?
九、“深造自得”是居敬持志的学习
“居敬持志”是指学习者要独成一家之言,达到自得之学的境界,其心态必须“专静纯一”,且拥有坚定持久的志向。“专静纯一”就是要保持心态的宁静,宁静则能致远,为心中所持之志而长久地保持宁静的心态。“居敬持志”最初是由朱熹提出的,他认为:“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朱子读书法》)但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用二人学下围棋的故事生动形象地阐释了注意力集中、专一和坚定志向即“居敬”与“持志”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孟子的这一思想为后来者不断发扬。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所编著的《淮南子》一书就提出了这一主张:“昔者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荻作酒,奚仲为车,此六子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做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在《淮南子》看来,即使是中国历史传说中六位有重大发明创造的人物,尽管他们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但他们也不可能一人兼有其他五人的成就,每个人也只能“做一事而遗后世”。二程认为,学习者要盯住某一事件潜心积虑,一个人只要能坚持长时间思考某一问题,就会“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不曾见人有一件事终思不到也。”(《二程遗书》卷十八)靠泛泛地、浮光掠影地思考是很难获得自得之学的,必须选择一个有价值的事件或问题“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深入的体验和独特的收获。在二程看来,深造的途径是“贵一”,“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约。”(《二程语录》卷十五)当然,二程也认识到“学不博者不能守约。”(《二程粹言》卷一)
宋代与朱熹、吕祖谦(字伯恭,1137~1181)齐名,时称“东南三贤”的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字敬夫,1133-1180)也认为,“持志者主一之谓。若曰欲持志之时,二者犹交战于胸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南轩集》卷三十二)“使其志常定于内,昭然不乱,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则必须自知,以心验之,未见其为私。”(《南轩集》卷三十二)著名元代理学家吴澄(字幼清,号草庐,1249~1333)也认为,“静而安”是“圣学之基”(《静安堂说》)。所谓静安,就是学习中保持“不为外物所动”的专一的心理状态;静安亦即“常定”,就是“事物不挠心”,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学习。只有专一常定,才会“为外物所实”、“须臾不离道”(《静居敬持志渊说》)。为了确保学习能够专心致志,虚心涵泳,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具体办法,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主张学习者要“各专一事”,不要“多歧而亡羊”。明清之际思想家、教育家颜元(字浑然,号习斋,1635~1704)认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试观虞廷五臣,只各专一事,终身不改,便是圣;孔门诸贤,各专一事,不必多长,便是贤;汉室三杰,各专一事,未尝兼摄,便是豪杰。”(《颜习斋先生演习录》卷上《学须》)因为“各专一事”才能谈得上“深造”,只有“深造”才能获得“自得”之学。
总而言之,“深造自得”这一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学习策略,对于当下人们的学习仍具有启发与借鉴的价值。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王阳明.传习录[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1:176.
[3]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 2010:58.
[5]毛子水.论语注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58.
[6]王先谦.荀子集解[M].台湾:艺文印书馆,1988:386.
[7]燕国材.中国教育心理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