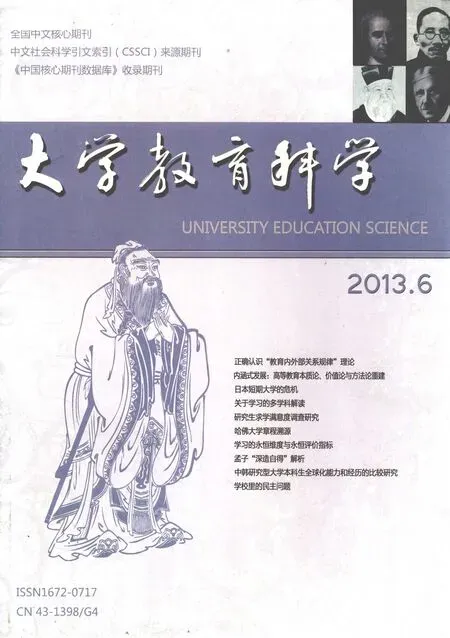正确认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方泽强
展立新、陈学飞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文章“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以下称“理文”)。该文从工具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等五方面进行分析,批判了关于高等教育“两个规律”的理论(该文将之概括为“适应论”),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坚称“从理性分工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活动,其首先应该符合的是认知活动合理化即认知理性发展的要求”,因而,“回归认知理性,建设完善的学术市场,是我国高等教育摆脱‘适应论’思想束缚、稳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客观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通读全文,笔者产生若干疑惑:该文列举的工具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实践理性与认知理性存在什么关系、能否在同一范畴中使用?认为“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活动”,该“本质”如何使高等教育与科学院、研究所从事的活动区分开来?等等。总之,笔者对该文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特别是该文对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的认识有误解、偏颇之处。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探讨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及其应用的正确认识问题。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提出的背景及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恢复并有所发展。1966年,文革发生,政治运动和阶段斗争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括经济规律、教育规律,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提出了按规律办事的愿望,探索教育规律、促进教育发展成为教育研究者的期盼。1979年,余立和刘佛年先后在《教育研究》发表了“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探讨教育工作规律”和“三十年来我国对教育规律的探索”的文章,拉开了探讨、研究教育规律的序幕。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980年,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到湖南大学讲学时正式提出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另一条是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合称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此规律的要旨是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适应分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起作用。简言之,“适应”就是“受制约”和“起作用”。
第二,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是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教育内部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此规律的具体内容包括:教育与教育对象身心发展以及个性特征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各个组成部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之间的关系;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教师)、教育对象(学生)、教育影响(教育载体、媒体)等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就教育的两条规律的关系来讲,内部关系规律的运行受外部关系规律制约;外部关系规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相互起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支持下,培养人的工作才能够实现;反过来,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第四,在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时,特别是处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时,要求教育应“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被动适应”。
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在教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议,其中不乏有一些质疑之声。有学者提出,规律是本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必然联系,提出外部关系规律不妥。对此,潘懋元先生进行了系统解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规律的定义是: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外部’一词,指的是范围、系统的外部,而不是相对于内在本质的表面现象的‘外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的正是教育系统与本系统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活动、现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非本质的不稳定的联系’”[1]。自此以后,学术界基本上对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了共识,尤其是教育实践工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论证了它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揭示了教育发展所应遵循的原则和逻辑: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又要遵循人的成长要求,更重要的是,教育发展要把社会和人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唯有如此,才不会导致畸重畸轻,顾此失彼,才能保证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的系统解读及“理文”的误解
(一)应充分认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中的“适应”
“适应”,一方面是指教育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约”;另一方面是指教育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起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教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持、财政投入,需要在经济制度的规制下运行,脱离了经济来发展教育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政治方面,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为国家所规制,教育体制决定于政治体制;在文化方面,教育发展受国家、民族文化等影响。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教育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制约都是必然的现象,而教育要脱离这些因素的制约而独立存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对此,布鲁贝克在考察高等教育发展史后指出,高等教育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历史时期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如中世纪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则把其合法地位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上;德国的大学是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合法地位的;美国“赠地”大学的合法地位则依赖于它们把人力用于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2]。事实上,对于大学和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早已有定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就强调,“在以变革和以知识与信息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为特点的经济背景中,应当加强与更新高等教育与劳动界以及社会其他组织部分的联系”,“高等学校要经常性地考虑科学技术、经济与生产领域的变革。为了适应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和劳动界应当共同确定和评估教学过程,使之融合理论和培训”[3]。无独有偶,阿什比也指出,“它(大学)必须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社会,不管它是由美国的专家治国论者构成还是由哈米特牧民构成”[4]。
除了“受制约”的一面外,教育还存在“起作用”的一面。事实上,“起作用”蕴含着“教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命题。也即,教育要对经济社会起作用,是建立在教育是符合自身规律、逻辑的基础上的。例如,大学的发展必须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如此,大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大学发现市场上对物流专业人才有潜在需求,于是开设了物流专业,最终促进了“物流行业”的大发展。这就反映了高等教育对经济的反作用力。再例如,在五四运动时期,大学提出“民主”、“科学”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高等教育对文化“起作用”。总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在指出教育“受制约”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教育不需要“独立性”。正是教育存在“独立性”,才可能对经济社会“起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教育,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起作用”能达到什么程度和效果,大致上取决于两点:一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赋予教育的“能动性”有多少,二是人们对教育按自身规律运行的认识和运用程度。
反观“理文”,认为高等教育不应该受社会制约而应自由发展。该文列举文革时期教育遭受破坏作为“教育坚持适应论”所造成的后果。按“理文”的逻辑,认为高等教育坚持“认知理性”发展,就会避免遭受“政治”破坏,实现独立发展。但是,这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实,文革时期教育受破坏并非是按照两条规律办事所导致的后果,而恰恰是违反该规律所引发的苦果。这一点在第三部分再展开论述。另外,“理文”误认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适应”忽视了高等教育的“独立性”。实际上,它狭隘地理解“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中“适应”的含义,没有认识到该理论包含了“教育具有一定独立性”命题,以至错误地指责该理论无视高等教育需要“独立性”,但事实并非如此。至于高等教育是否应该不顾社会需要而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则是另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不可简单归纳为“适应论”
第一,就“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而言,探讨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两者的互动关系:“受制约”和“起作用”。归纳为“适应论”在中文语义上很难揭示、反映出两者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无法准确突显、概括“起作用”的内涵,因而不适切。
第二,就“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而言,其包含的内容涉及教育与人的关系问题、在人的培养过程中德智体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教育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提出,教育要适应人的身心发展需要。从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视角看,该规律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在教育的过程中,无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培养素质,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就此而言,将教育要适应人的身心发展需要归纳为“适应”勉强可以。但“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还包括在人的培养过程中如何处理德、智、体、美的关系,以及教育者(教师)、教育对象(学生)、教育影响(教育载体、媒体)等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存在着德育适应智育、还是智育适应体育的问题。可见,“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不能简单地用“适应论”来归纳。
第三,就两条规律的关系而言,“教育内外部关系”理论指出:首先,内部关系规律的运行受外部关系规律制约。“如果只考虑教育的内部规律,也就是就教育谈教育,哪怕谈得再好,想得再美,但社会条件不具备,或者是培养出来的人不适合社会的需要,教育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不能实现。”[5]其次,外部关系规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内部关系规律实现。“就教育谈教育是行不通的,但是,只就社会的各个因素来谈教育,只就生产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来谈教育,不顾教育自身的特殊性,违反教育的内部规律办事,也是不全面的。”[5]可见,两者的关系显然并不是用“适应论”就能归纳的。
概言之,“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不仅涉及教育与教育外部的关系的勾勒,而且涉及教育内部的关系的揭示,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如何处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关系问题。“理文”把“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归纳为“适应论”显然不太适宜,无法反映出该理论蕴含的完整内涵。
(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折射出认识高等教育的全面性和辩证性
关于如何发展教育的问题,需要用复杂性思维进行认识。复杂性思维是指要用系统、联系、背景化的方式认识事物和问题,这种认识方式有利于全面认识事物。莫兰指出,“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的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或问题愈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合理的认识大体是这样一种认识,它能够把任何信息都在其背景中和(如果可能的话)其所属的整体中加以定位。人们甚至可以说认识主要不是依靠精确化、形式化和抽象化而进步的,而是依靠实行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而进步的”[6]。与复杂性思维对应的是简单性思维,体现为用线性、分割、片段化的方式认识事物和问题。它表现为:对事物的认识缺乏系统把握,从某一角度得出的认识结果就认为是事物的全部;对问题进行认识往往缺乏用联系的思维开展,孤立地就问题谈问题。简单性思维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方式,是我们应该反对和规避的。
不难发现,“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充分体现了复杂性认识思维。具体来说,该理论既指出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要求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又指出了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要求教育发展应遵循人的成长要求;既阐释了这两条规律的关系,要求教育发展应把社会和人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进行考虑,又强调在运用规律时应“主动适应”,避免“被动适应”。这一高度精炼的理论是在“社会—教育—人”的研究框架下谈论高等教育,无疑很好地突显出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系统性和辩证性。它让人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发展教育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以及教育内部的教学内容、方法等因素,从而有利于指导人们更好地推动教育的发展。
反观“理文”,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发展认识理性的活动,不应当适应社会发展,这无疑是采用简单性认识思维所得到的分割的、片段化的认识结果:既没有勾勒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又没有勾勒出高等教育与人的关系,而只从所谓的“认知理性”的视角探讨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就高等教育谈高等教育的认识。可以断言,按“理文”的“高等教育不应当适应社会发展,而只是一种发展认知理性的活动”的思路来设计、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迎接我们的必将是一场沉重的高等教育“灾难”。当前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阶段,如果一味地要求高等教育“为学术而学术”,要求应用型大学、职业型大学无需适应社会而应从事发展“认知理性”的活动,那么,这种脱离实际的高等教育除了迎来遭受社会各界的“痛批”、“责骂”以及高等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的后果之外,还能有其他“收获”吗?很显然,大学和高等教育的举办绝对不能脱离社会。
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运用:“主动适应”以及“内外部关系协调”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违背的,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应该注意,人们在按规律办事的时候,可以主动运用好规律,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这里主要谈论两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适应”问题;二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协调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应该“主动适应”而非“被动适应”。事实上,潘懋元先生早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中就提出这个思想了。他在评价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时指出:“当年那种‘左’的错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的。虽说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很难不受其消极、错误的影响,但有的跟得很紧,甚至推波助澜;有的则跟得不那么紧,尽可能减轻某些‘左’的消极影响。”[7]也就是说,在文革那种特定的政治年代,教育适应政治是必然的,但教育者在推动教育发展可以“跟得不那么紧,尽可能减轻某些‘左’的消极影响”。这种就是“主动适应”。反之,“跟得很紧,甚至推波助澜”则是“被动适应”了。“主动适应”是“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所提倡的,而“被动适应”则非“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的应有之义。当前,人们在遵循“教育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时候,应推动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发挥积极方面的作用,规避消极方面的作用。例如,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经济服务,可以充分调动高校的办学积极性,提高教育资源效率和效益,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面向市场经济办学也可能会带来高校大量发展短平快专业而不举办基础专业,造成专业结构畸形,这是消极的方面。为此,高等学校办学者在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时应“主动适应”,想方设法减少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采取一些措施和方法来减少专业结构畸形等负面影响,并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推动高校的发展,此才是“王道”。而千万不可“因噎废食”,仅仅因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就作出“高等教育不应适应市场经济”、“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是致命错误”等类似的论断。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高等教育适应外部关系规律发展不能违背内部关系规律。事实上,高等教育在文革遭受破坏不在于它“适应”社会,而在于教育在适应社会的同时违背了人的身心发展,把教育过程“政治化”、把人“政治化”了。也即,这种适应在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同时违背了内部关系规律,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受挫。这恰恰是没有运用好“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表现。当前,社会需要大量人才,继而要求高等教育进行培养。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根据现有办学条件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年增长速度。如果无视这一点,不顾条件地扩大学生规模,那么必将有违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人才质量下降,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从1999年起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大扩招,高等教育规模增量过多,增速过快,而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没有相应配套,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好在不久之后,政府加大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高等教育质量才有所保障,高等教育在适应外部关系规律的同时也遵循内部关系规律,从而使高等教育健康向前发展。此外,高等教育适应内部关系规律发展不能违背外部关系规律。具体而言,高等教育根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培养人才,但培养人才必须适合社会的需要,否则,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无法实现。
简言之,运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指导、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遵循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主动适应,又要遵循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突出人的成长和发展逻辑,还要把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很好地进行协调。
四、结语
“水本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针对“理文”的误读,笔者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进行了系统剖析,以期深化对该理论的认识与践行。当然,“理文”所表达的个别观点,如“大学发展应遵循学术性”值得肯定,但对于高等教育应如何发展学术的问题应有辩证思维,既应认识到其独立性,更应认识到其社会适应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的‘靠拢’,可以说是大学在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而且这是大学在信息时代面对社会现实必须秉持的理性态度”[8]。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规律,引导高等教育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避免不利因素的影响。同时,对于高等教育应如何处理学术自主和适应社会的问题应有辩证思维,特别是不能过分地强调大学(高等教育)“为学术而学术”而置社会需求于不顾。毕竟,现代大学(高等教育)已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焉能不顾外界要求而“独善其身”、“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正如有学者所言,“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够自治学术,就是因为大学一无所有,因为一无所有,大学才不至于怕这怕那。学术自由与自治的传统是大学在远离社会的边缘和在一穷二白的生存条件下逐步培育起来的,当一切都有了改变的时候,过分地迷恋传统或许就是一种保守或倒退”[9]。“大学的合理与合法性,表现在对不同时期社会需要的满足上。如果大学脱离政治、脱离社会,那么,大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任何社会和政权机构都不会以更多的人才、物力和财力去支持一个对国家政权巩固不起任何作用而仅仅具有学术价值的大学组织”[10]。所以,高等教育应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不能够为了所谓的高等教育独立而置社会需求于不顾。当前尤其必须牢记:适应、服务于社会发展是高等教育应有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
[1]潘懋元.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A].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27-141.
[2][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
[3]吴松,沈紫金.WTO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15-117.
[4][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
[5]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A].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13-126.
[6][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1-103.
[7]潘懋元.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J].教育评论,1989(1):1-4.
[8]王长乐.构建大学内在逻辑与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7.
[9]陈廷柱.大学的理想:价值取向及其言说立场与限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99.
[10]刘少雪.略论大学的学术自由[J].上海高教研究,1997(7):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