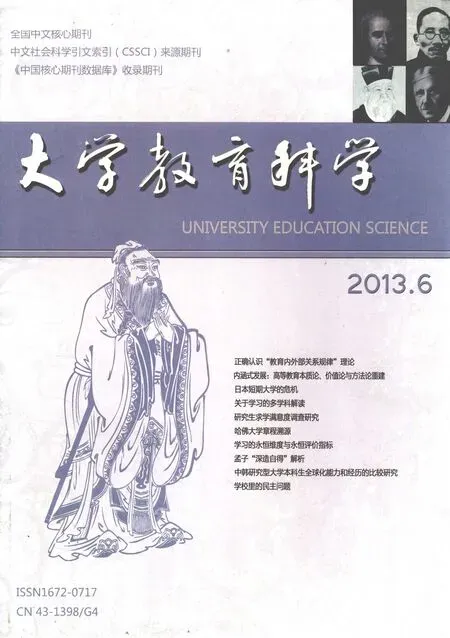中世纪大学的“场所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肖 维
人总在一定的场所中生活。场所包括空间和特征两方面的因素。“场所精神”(英文称为genius loci或spirit of place)是20世纪末出现的建筑学术语,但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这种说法。古罗马人认为,一个场所的“守护神”就是“场所精神”,它决定场所的典型特性[1](P18)。在现代建筑学中,“场所精神”是指某个地方蕴含的人文思想和情感,它是构成一个场所的典型氛围和核心精神的原因,是一个场所的象征和灵魂[1](P20)。“场所精神”为置身于场所中的人带来“方向感”和“认同感”[1](P23)。大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场所,具有独特的环境和特征,能带给置身此处的人特定的“场所精神”。这种“场所精神”不仅体现大学这一类型机构的特性,还代表着某所大学的个性和品味。大学“场所精神”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作为源头的中世纪大学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一、中世纪大学“场所精神”的载体
“场所精神”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容纳场所活动的空间,这是产生场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一是场所活动,这是赋予空间意义的核心要素[2]。
(一)中世纪大学场所的建筑:“场所精神”的物质基础
中世纪大学早期没有自己的不动产,最先出现在大学的建筑是12-13世纪的寄宿学院建筑物。寄宿学院大量借鉴修道院的建筑元素,凸显教堂的中心地位,最典型的格局是牛津的莫顿学院(1379年)——回廊围绕的大方形庭院,钟楼居高临下,四周为规模宏大的教堂、教室与会堂、图书馆、院长的住宅和学生的宿舍、花园、墓地[3](P151)。
中世纪后期,停止迁移的大学获得了自己的建筑和资产。第一座由大学设计建造的建筑物是牛津的集会大厅,其他较为重要的建筑包括了神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建筑。与之相似,剑桥大学的建筑项目(四方形校舍)建立于14世纪末和15世纪。巴黎大学在15世纪不仅拥有了在麦杆街的演讲大厅、寄宿学院、礼拜堂,而且还使得拉丁区成为巴黎的大学区[4](P150)。1420年后,在意大利出现的、以博洛尼亚大学西班牙寄宿学院为原型的“智慧之屋”类建筑,承接了早期寄宿学院的建筑传统的同时加入了中世纪后期的奢华元素:围绕着有拱顶的庭院,设有演讲厅、讨论室、图书馆、膳宿室与管理室和档案室,以及一个举行毕业典礼的大厅。自此之后,“智慧之屋”成为华丽的大学建筑的通用名称。这种大学建筑,尤其是带有图书馆的建筑,在15世纪末遍布整个欧洲。
(二)中世纪大学场所中的人物:“场所”中的活动主体
中世纪大学中活跃着不同的人群:教师/教士、学生、仆人、执礼杖者、差役、抄写员、书商等,他们都在大学的管理和保护之下。大学最核心的人群是教师和学生。没有教师和学生就无所谓大学或学校的存在,他们的品性和活动塑造了大学的特性。
在中世纪的大学,教师主要来自社会中下层,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是必要条件之一,其次是教长授予的资格和大学同辈的承认。获得教师职位享有教皇和国王们给予的荣誉和特权。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提高。中世纪大学有招聘它所希望的任何人的自由,这是当时大学独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世纪大学的教师待遇有较大差异,大多数教师需要通过兼职或出租房屋等获得非校方提供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
学生是由一名教师、学者或学派而组织起来,这是中世纪整个欧洲大学的常见模式。中世纪大学对学生唯一的入学标准是道德品质,实际上通常只需要一个人的合法出生证明。学生成为一所大学的正式成员的前提是在某一特定的教师名下注册。整个中世纪,大学的注册学生数持续增加。保守估计,从14世纪中期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大约有75万学生进入大学[4](P204)。早期大学的学生大多是神职人员,随着时间推移其比例不断减少。学生基本上是来自城镇的男生,所有学生无论贵贱贫富在大学章程面前都平等。学生中只有少数人能毕业,毕业生部分成为大学教师的补充,更多的人则为教会和宫廷提供服务。
(三)中世纪大学场所中的活动:“场所精神”的意义赋予
中世纪大学的师生们既要完成学业又要履行宗教义务,他们的教学、典礼仪式、社群生活、抗争迁徙等活动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特有的生活模式。
首先,中世纪大学将教学变成一种真正的职业工作,从而赋予大学以独特使命。中世纪大学推崇文明和理智的教育,采用讲座和辩论两种紧密相连的方式来给学生传授教学内容,其教学法则要求向学生提供纯粹的智识习训并教导学生学会思考和工作。然而,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性”的教育,而是被灌输一种由公认权威的著述和评注堆积而成的知识传统,例如,无论哪所大学都需要教授和学习基督教经典文献。
其次,中世纪大学中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往赋予大学以独特的社群文化。教师社团不仅是职业性的组织,也是类宗教团体。成为教师社团的成员不仅意味着享受行会的特权,还能保证其成员间的友爱互助。作为同事的教师内部鲜有冲突,冲突往往来自于世俗教师和修道士之间由于职业身份和知识之间的差异;在师生之间,学生一旦注册成功,教师需要对其行为负责:首先是确保学生学习的进步并获得学位,在适当的时候教师还有责为“学有所成”的学士推荐参加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考试。在寄宿学院,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给予更多的指导,学生经常拥有与教授非正式接触的机会,如共进午餐、一起运动、相互走访等。学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大学内部,学生一般基于民族、地域、地位以及兴趣不同组成各种团体。这些社团都有自己的领导人和管理者,有自己的印章、庆典、注册制度和预算以及特别的入会仪式,最重要的是这些社团成员在彼此遇到困难时给予援助,形成亲密的同伴关系。
再次,中世纪大学有经常性的宗教活动和各种典礼仪式以强化大学师生的身份意识。中世纪大学始终与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师生都是广义上的神职人员。教师有义务参加定期和偶然的宗教仪式;学生被要求每日做弥撒,每周做一次布道,至少在每次宗教节日时做一次忏悔。大学自身还有许多特殊的典礼和仪式,如学生注册宣誓、学生毕业典礼、教师就职礼等[5]。
最后,中世纪大学师生经常性地采用罢课和迁徙等抗争行为来巩固其自治的地位。中世纪大学与市镇当局和地方教会时有冲突,其结果往往是学生被杀死或受到严惩,对此大学教师常见的做法是以停止授课的方式表示抗议,如果“罢课”措施并不奏效,更加极端的挽救措施就是遣散整个大学或者整体迁徙。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巴黎大学1228-1229年的大骚乱和剑桥大学的诞生。
二、中世纪大学“场所精神”的解读
当我们追溯中世纪大学的“场所精神”时,既发现了与现代大学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也呈现了中世纪特有的精神和风味。中世纪大学的“场所精神”集中体现在它的神圣使命、独立地位以及和睦氛围方面。
(一)中世纪大学的神圣使命:“求知”与“朝圣”共荣之地
中世纪大学建筑的最大特点是修道院建筑风格,它反映的是基督教宗教观下的理想人类环境特征。一方面体现了修道院文化的延续,有利于培养适合基督文明的青年,另一方面又将“求知”和“朝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象征欧洲文明最高追求的哥特式教堂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物,反映最普遍的宗教或人文精神和意向。人们置身于这样的宗教建筑和环境中能获得对求知信念的支撑、对至高无上的存在的谦卑之心以及致力于崇高事业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值得注意的是,刺激大学出现和成长的根本原因是探索知识的欲望,是学习和了解世界的需要。中世纪大学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它的使命不止于阐释和宣扬教义、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它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为知识而知识”的自觉和追求。这种意识与年轻学子的求知和探索欲望汇合,使大学教师自觉成为“探索真理和无私的教学”的工作者,并赋予且坚定了大学“为知识而知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中世纪大学的独立地位:“自由”和“自治”共享的王国
直到中世纪结束,罗马教廷一直扮演大学最主要的财政支持者、安全保护者和毕业生接收者的角色。教会庇护下的大学享有许多特权,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权利是自治权,即大学作为法人团体有权处理与外部的关系、监督成员(包括教师和学生)的录用、制定章程并通过一定程序的内部管辖强制实行。大学和学院自治的特权造就了中世纪大学的弹性和多样性。也正是这种自由和自治,使得中世纪大学既不完全受控于教会控制,也不受地方当局的过多干涉,保障了大学“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和自由。
然而,中世纪大学并非我们想象中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带着枷锁的舞蹈者”。在中世纪大学,没有任何东西比教学内容及其形式受到更多的审查。大学的各学院把教学大纲写进了章程,经院理性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被禁锢在一个几乎永久不变的教条框架之中,这使得教师的“学术个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学内容和传授方式,教师们在这种教学体系中的教学自由是极其有限的,教师往往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三)中世纪大学的社群文化:“平等”且“友爱”的智慧家园
中世纪大学的生活模式受当时特有的一种行会理念(或相同从业者宣誓为兄弟的理念)影响,大学的师生组成了类似行会性质的联盟。师生向大学宣誓,在个体与组织之间建立了一种永久的成员资格和合法关系。中世纪大学教师不仅在生活上建立了较亲密的关系,他们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摒弃了社会出身和民族差异,促进了同行者在知识和真理面前的平等和团结。事实上,平等的水平越高,对知识进步的共同责任就会导致参与越多,大学就会更好地履行责任。中世纪那些销声匿迹的大学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由于中世纪大学的师生关系建立在自愿选择和正式宣誓基础之上,这种契约关系使得师生之间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是紧密联系的。较之现在,中世纪大学教师对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责任感,他们给予学生更多的个人指导和阐释。这种个体之间的交往能产生即时的思想碰撞以及最高层面上的精神和智识熏陶。
中世纪大学的学子们带着求知的热情和对教堂的渴望聚集起来,在由众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的社群中,学生们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寻的生命体验:一种众多身份迥异但意气相投的同道们共同构成的、令人如沐春风般的社群生活。“根据正义的此意可看出生活的法则”这句格言,没有何处能比中世纪的大学理解得更加透彻了[6]。
三、中世纪大学“场所精神”的现代启示
大学需要“场所精神”,这种“场所精神”使你一走进去就能获得与其他场所截然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一种大学独有的认同和归属感。我国大多数的大学校园景观几乎可以与国外大学相媲美,其豪华程度甚至超过国外大学。然而,多数大学在形象上缺少教育建筑的优雅性,在环境上缺少人文性,在空间上缺少教育的规律性和本质性[7],大学人对大学的疏离感油然而生。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中世纪大学的经验,加强现代大学“场所精神”的建设。
(一)大学“场所精神”的延续:纯粹智识追求和平等自由交流之所
中世纪大学通过那些神圣优雅的建筑、师生活动、古老仪式、学术术语以及操作规程形成了大学的“场所精神”——纯粹智识追求和平等自由交流之所。大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演变出不同的形态,但其内在意蕴却大致相同:一是为学生提供纯粹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其可以是几个年头,也可以延绵至全部的学术生涯;二是在这段生活期间,大学应致力于保障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亲密、自由地交流和栖居。唯有此二者,才是大学亘古不变的真谛,也是大学的“场所精神”所在。当然这种气质也并非千篇一律,不同的大学有着自己独具的风格和面貌,各有更具体的“场所精神”。
如今,弥漫在中世纪大学上空的神性光芒早已淡去,但大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象牙塔”的象征屹立不倒——她代表着一种纯粹的智识习训、一种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想象、品味与感知。这种探索精神和责任使得赋予大学的特权与自由具有超越时代和现实的意义,也确保大学在其最基本的学术和研究活动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
(二)大学“场所精神”建设的基础:建筑和环境与使命的统一
“场所精神”的获取源自文化或地域特征的文脉内涵。大学通过形象化和象征化的建筑和环境赋予其特有的“场所精神”。中世纪大学优美、和谐、实用的物质环境和细腻深邃的文化景观彰显了其特定的使命——大学“犹如站在高塔的卫士”,“大学与上帝的事业融为一体”[3](P155)。尽管近现代的大学很少提供中世纪大学的惊奇和神圣,但其建筑风格和结构布局的转变与大学的使命变迁相一致。正如克尔所言,大学在中世纪是一个僧侣居住的村庄,教堂是基本元素;近代大学是“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图书馆、实验室必不可少;当代大学则是“一座无穷变化的城市”,校园更宏大、更开放,承担的使命更多: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探索真理的“象牙塔”,还是社会的“动力站”和“服务站”。
人们能利用“主题与变异”的形式使变迁与过去场所发现的公分母(即场所的共同意义)产生关联,同时在这个系统中容许独特认同性的表现,由此既坚持类的“场所精神”又不至于使特定场所丧失个性。大学作为一种场所,不仅为大学里的人提供一个学习和生活的空间,更通过其独具特色的建筑布局、人文景观、校园文化提供一种独特的“场所精神”来体现每个学校特有的文化和理念。同为“欧洲大学之母”,巴黎大学的尊贵不同于博洛尼亚大学的敦实,一个神圣肃穆,另一个则更显独立自由;北大的古朴肃穆不同于清华的庄严凝重,一个更强调自由包容,一个更注重严谨创新。这些大学都是其建筑和环境与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和使命完美结合的产物。事实上,只有把校园本身建设成为一种教育资源,才能让人真切地感觉到大学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只是一种场所类型的存在,还是富有鲜明个性的具体场所的存在。
(三)大学“场所精神”建设的实现:人与场所的互动
“场所精神”的形成不是个别个体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特定的群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共同生活来确立的。大学自在环境固然重要,但大学人回应与塑造自己大学的能力,即大学人与大学场所的互动才是“场所精神”建设的关键——通过学习如何去做,在与人交谈、共同进食、一起感受和阅读文字、欣赏音乐以及使用场所来体验并建设“场所精神”。
人与大学的互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对特定传统的坚持来延续大学的“场所精神”。传统通过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塑造“场所精神”,每一所大学和学院都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其二是通过给场所添加更多的人文特征以更新大学的“场所精神”。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诠释既有的大学文化,也可以通过注入新的元素建构新的大学文化[8]。唯有如此,才能有活的“场所精神”,而活的“精神”才符合生命的发展规律。更新大学“场所精神”离不开大学人对大学的“认同性”与“自由”:“认同性”意味着引导大学人回到起源和本质;“自由”意味着一种对大学的选择与参与的权力。毋庸置疑,“自由”并不是任意地玩弄,而是具有创造性的参与:“川流不息于这所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一代一代精雕细刻,匠心独具地去建设”——这种“建设”也不只是“传承”和“说教”,更需要“艺术的”和“人文的”加工[9]。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人不只是“建造”了大学这个场所,形成了特定的“场所精神”,同时也建造和完善了“自我”,这恰好是大学场所的最高目的和意义所在。
[1][挪威]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2]Vaclav Smil.Genius loci[J].Nature,2001(1):21
[3][法]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M].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瑞士]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5][英]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在上帝与尘世之间[M].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34.
[6][英]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博雅教育的兴起[M].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262.
[7]邬大光.大学与建筑[J].教育研究,2009(12):25-29.
[8]张文强.网络科技时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弱化与提升[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5):96-99.
[9]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