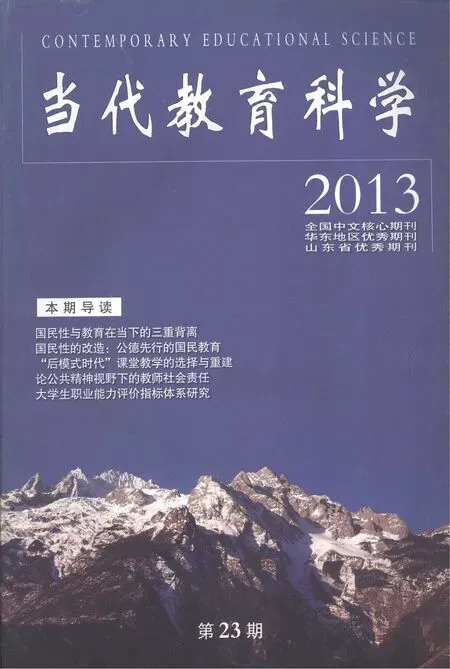论负面教育中尊重的在场*
● 董吉贺
在德育领域中,显然存在两种教育。一种是正面教育,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面引导,主张用优良的行为和榜样来教育儿童,这类教育主要指向表扬、鼓励、赏识、宽容等手段;另一种是负面教育,它或者通过强制性的要求对儿童进行限制,或者通过批评性的方式给儿童施以压力,从而使儿童避免或改正不当行为,这类教育的主要手段包括约束、批评、惩罚等。如果说正面教育已经受到了当代教育者足够的重视,那么负面教育远非如此,其正当性甚至常常遭受来自不同学者的质疑。论及负面教育的正当性,尊重是一个首要的话题。这缘于20世纪以来人们对儿童人格和权利的史无前例的重视。负面教育的手段很容易使人把它们和规训、压制、打击等联系起来,即便不是如此,也常常被怀疑丧失了对儿童的基本的尊重。这一点,是凡支持负面教育的人们不得不花点力气进行讨论的。
一、对负面教育中尊重缺失论说的反思
在负面教育的手段中,惩罚当属一个伦理难题。由于文化的惯性和习俗的力量,在蒙台梭利时代,体罚以及残酷的惩罚仍然存在。针对这种情况,蒙台梭利为儿童的权利的奔走呼号,然而她并没有对惩罚进行区分,从而将那些有害儿童身体的、侮辱性的惩罚连同其他一切责罚都驱除在教育之外。在她看来,儿童不小心打坏了小物件使他失去了心爱的东西,就已经是惩罚了。蒙台梭利将成人施加的惩罚视为奴役,“奴役对儿童和成人同样会孕育低级的情操,并且发生绝对丧失尊严的情况。”[1]体罚以及残酷的、侮辱性的惩罚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这些惩罚正如蒙台梭利所认为的那样,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横加于儿童,无视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是对儿童人格尊严的直接侵犯,最终使儿童丧失自尊。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所有的惩罚都是对儿童尊严的侵犯吗?如果儿童的过错严重到不得不给他一点严厉的惩罚,那么,在独善其身的尊严和责使其承担道德责任之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在对惩罚的指责方面,相对于蒙台梭利,法国“现代”学校的理论奠基人塞勒斯坦·弗内核更加激进:“‘种种惩罚总是一种错误,它们让人感到屈辱并且从来也达不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必须结束这种惩罚和控制的逻辑。(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或是处分,这常被视为有损尊严,尤其是被当众控制或处分。)”[2]他认为,没有人喜欢被命令,孩子并不比成人更喜欢被命令,并且应围绕不让儿童承受失败来组织教育。如果这种观点针对的是知识的学习,那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若把儿童行为中的过错也算进去,则是值得怀疑和讨论的。惩罚最为主要的、直接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为了预防和威慑,它重在使儿童承担责任。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尚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的意识,惩罚是在这时才出现的必要的手段。如果惩罚是一种错误,那么,舍弃了它,什么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呢?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果真只是给儿童以屈辱吗?如果对儿童的过错不管不问或欣赏、表扬乃至鼓励才是尊重吗?尤其是,如果没有对犯错者的惩罚,受侵犯的一方的尊严又何在呢?更值得玩味的是功利主义的观点。边沁一方面指出惩罚是必要的,因为惩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更大的恶。惩罚犯错者完全是为了威慑步其后尘者,使他或他们望而生畏。但是另一方面,边沁又认为,所有的惩罚都是一种恶。[3]惩罚既然是一种恶,那当然是对其对象的一种损害,也就难免使受罚者丧失尊严。
应该承认,体罚、残酷的惩罚以及侮辱性的惩罚的确是恶,因为暴力就意味着丢弃了行为的道德性。但是,在此不得不进行思考的一些问题是:所有的惩罚都是一种恶吗?惩罚所包含的恶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对于犯错者和受侵犯者,惩罚的含义是一样的吗?惩罚能不能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教育手段?与惩罚一样,强制性、批判性、施以压力是约束和批评等负面教育手段的共有特征。虽然约束和批评不像惩罚那样更容易受人指责,但其固有的属性仍然让人怀疑是否能够使儿童的尊严得以保全。如果约束儿童不得玩暴力游戏,是不是没有尊重他的选择权?假若批评儿童课堂上乱说话,是不是没有顾及他的言论自由?类似这些问题,都是负面教育无法回避的。而且,要使人们认可负面手段的运用就是教育,它们必须得到正面的回答。
二、有关尊重的检视
要解答上述负面教育中的疑问,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尊重的内涵,去考察人因何需要受到尊重,以及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尊重。在一般的语境中,我们说一个人值得尊重,大概是说值得我们尊敬和敬重。然而,尊重一词不仅含有“值得”的意思,有时它还含有“应该”的义务。比如,“尊重人权”一方面是说人权是重要的,它值得我们尊重;另一方面,承认人权是维持现代生活秩序的基本条件,它不应受到侵犯,这就有应该受到尊重的含义。
当我们说尊重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和这个人的尊严联系起来。什么是尊严呢?1980年版的《辞海》将之解释为“独立不可侵犯的地位或身份”。[4]这种说法强调了有尊严的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就应该有尊严。按照这种解释,地位和身份越高、越重要,他拥有的尊严就应该越多。2009年版的《辞海》则扩大了尊严的内涵,第一项为“庄重而有威严,使人敬畏”;第二项为“可尊敬的身份或地位”;第三项为“对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自我肯定或不可贬损性”。[5]这种解释不再强调地位、身份的不可侵犯性,也不再单独强调附属于人的外在属性,而是侧重于人的内涵。一个人之所以有尊严,不仅因为他拥有令人尊敬的身份和地位,还因为人自身的价值以及令人敬畏的固有属性。当然,按照马斯洛的意见,人有受到尊重的需要,这也可以构成尊重人的理由。但马斯洛也承认,“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于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6]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尊重作出进一步的理解。尊重不仅是说 “我要尊重”,它还必须弄清 “我如何尊重”。一般来讲,有尊严就意味着要受到尊重。在一些情况下,尊重是有条件的。低劣的品行无论如何都难以得到他人的尊重。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尊重则是无条件的。比如,对于人的基本权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哪怕是强盗也有生存权,这已经得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认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就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7]目前,这一宣言已成为一部习惯法,是人们维护和争取权利的重要证据。在这层意义上,儿童的人格尊严和诸如生存权、学习权、发展权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这些应受到尊重,则是无条件的。
然而,怎样才算是尊重了他人呢?这就引出了尊重的方式问题。通常,我们在描述尊重的对象时,会用到“不可侵犯”、“不可贬损”、“不得歧视”等词汇。这就意味着,只有承认、认可、赏识、赞扬、佩服、肯定、支持、高度评价等态度才符合尊重的定义。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理解的正派社会是“不羞辱人”,不论文明社会的成员之间还是正派社会的制度下,尊重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羞辱人。尤其对待弱者,不羞辱是第一原则。[8]应该说,这些都是尊重的基本方式。如果说这些方式是肯定性的,那么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尊重就需要排除那些与此相反的,也即一切否定性的方式。
既然尊重就是肯定,我们对当前的教育强调正面教育并且排斥负面教育的做法,似乎也就有了相应的理解和同情:儿童需要受到尊重,教育就要以肯定的方式来进行。因此,赏识教育、成功教育、愉快教育等也就有了顺势而起的“理论基础”。儿童犯了错误,批评是不对的,惩罚也是有问题的。怎么办呢?那就要诉诸说教,那就要发现闪光点予以鼓励。这就是当前某些教育者只要正面教育的逻辑。单纯的正面教育果真就是尊重吗?不管是出于意愿还是非意愿,纯粹的正面教育把儿童完全置入一种温情的场域之中,使得教育趋向软弱无力,给儿童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这一点就说明教育者并没有尊重教育规律,没有尊重儿童发展的规律,甚至没有尊重儿童成长的需要。尤其那些放纵、放逐的做法,表面上没有损害儿童的尊严,其实是对儿童、对教育的不负责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不尊重。
笔者并不否认肯定性是尊重的主要方式,甚至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此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有问题的行为,即儿童的不当行为,怎么样才算得上尊重?进而,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尊重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三、负面教育蕴含另一种尊重
负面教育的手段,诸如约束、批评、惩罚,是否定性的。结合对尊重的理解,人们往往把它们和对儿童人格尊严与权利的侵犯联系在一起,也即把负面手段作为一种非尊重的方式。然而,否定性的方式就一定不包含尊重吗?
马卡连柯在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时曾说,“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9]马卡连柯是在纪律的意义上来理解要求的,他认为没有要求就不可能建立集体和集体纪律,而且要求之中就包含了尊重:“这二者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是一回事。并且,我们对个人所提出来的要求,表现了对个人的力量和可能性的尊重;而在我们的尊重里,同时也表现出我们对个人的要求。这种尊重并不是尊重外表的什么东西,并不是尊重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尊重令人愉快的、美丽的东西。这是对那些参加我们的共同劳动、共同工作的同志的一种尊重,这是对活动家的一种尊重。”[10]在这里,马卡连柯提出了对个人的要求和对个人的尊重相结合的原则。在他看来,要求就意味着尊重,尊重就暗示着要求,这两者是二而一的事情。要求之所以是尊重,就是因为它承认了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潜能,而不是对儿童的贬低;尊重之所以有要求,是产生于集体教育中对全体成员利益的关照,以及这是文明社会的生活所必需的。这对我们全面理解负面教育是有着极大帮助的。
其实,在一般意义上来讲,约束、批评、惩罚等手段就是一种要求。只不过这种要求是以“不得做某事”的方式提出的。因此,根据马卡连柯的观点,负面教育和尊重并不矛盾。针对儿童的不当行为,负面教育并不是对儿童的侵犯、贬损或者其他,而是适应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的需要的手段。这种教育手段对儿童的能力包含着期待、认可与促进,它并不违背尊重的原则。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马卡连柯把犯错的孩子置于中间,周围站满了对他进行指责的同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犯错者人格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见解还不足以说服人们,即负面教育本身就是尊重的表现。要证明这一点,还必须去寻找其他证据。
负面教育有一个必然的前提,即应以儿童为目的。像功利主义那样把惩罚儿童作为预防和威慑的纯粹手段,其直接的损害就是儿童自身。因为在这样的逻辑里,惩罚的力度越大,其威慑力也就越大。功利主义考虑的是惩罚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效应,在这一惩罚理论里,儿童的遭遇可能是无辜地成为教育的牺牲品,没有人会顾及到他的尊严。杜威曾说,“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11]杜威并非反对教育应该有目的,而是反对在教育之外去强加一个目的。事实上,杜威认为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目的的行动和明智地行动是一件事”,[12]有目的就是增加了对未来可能性的预见,使得行动有了计划。但真正的、能够为行动提供力量的目的只能是教育自身。而外在的目的往往使教育活动沦落为达成目的的手段,让有意义的教育和学习变成人的苦役,“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都变成机械的、奴隶性的工作”。[13]杜威的话并不是直接针对负面教育的,但这对思考负面教育是有益的。教育者不能把负面教育作为达成改善儿童以外的目的,否则的话,违规者就会被贬低为其它什么东西的手段,从而就违背了教育的原则。应该承认,负面教育对其他的儿童具有警示作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把违规者作为手段吗?这种反对意见看起来很有道理,但这种警示作用只能作为负面教育附加的影响。在集体中,这种影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产生的,并非刻意而为。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在集体中发生的,就不能不重视它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这是教育者必须考虑的事情。但是,教育者应该秉持一个忠实的原则:负面教育对其他儿童的作用始终是从属的、次要的,它永远不可能上升到主要的目的。任何教育者都必须在这样的原则下展开负面教育。
我们不能离开当前所讨论的话题太远。将儿童作为目的,就是一种尊重。负面教育最为直接、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善有着不当行为的儿童自身。这就是说,教育者必须尊重儿童的需要、心理特点等一切教育所要求的东西,而一旦这样做了,就是对儿童的尊重。
如果承认了负面教育必须将儿童作为目的,我们的讨论就会有更大的进展。将人作为目的,这是一个富含德性的表达方式。人必须道德地活着,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康德的伦理学为人们找到了一条摆脱经验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则。绝对命令告诉我们的是,我能不能这样做取决于别人能不能对我这样做。在绝对命令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将他人作为目的,因为每一个行动者都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这被斯特赖克等人称为“平等尊重每个人的原则”。[14]人应该是一个道德的行动者,这就意味着人有道德地行动的义务和担当行动后果的责任。负面教育的手段是对儿童不当行为的回应,这种回应即为儿童应该担当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比如惩罚就是对自然后果的替代责任,并且这种替代难以再找到另外的替代物。对有过错行为的儿童施以惩罚,在告诉他不应当如此行动之外,是让其承担一个道德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相反,如若一个儿童没有为他的过错行为受到任何惩罚,在他者那里,将会积聚怨恨甚至是愤怒——这对犯错者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惩罚之后,则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消除这种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惩罚的另一个功用就是能够为犯错者恢复名誉。一个主动为过错承担责任的儿童能够消除不良影响,为自己赢得声誉。惩罚也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惩罚的实施不是让儿童的境况变得更糟糕,而是在于让他从过错行为的后果中摆脱出来。而对于有过错行为的儿童,他既不会也不能认为惩罚就是无理的,因为只要他认为别人应该为过错承担责任,那么他自己也必须承担。一个能够接受的惩罚,怎么能算得上是侵犯或羞辱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惩罚其实是对一个道德主体的承认,是对儿童的尊重。在这样的思路上继续下去,我们就能看到,约束和批评也是一种尊重。同惩罚一样,约束和批评也是出于对道德主体的认可与尊重。不管是危险行为还是不良行为,在教育者那里,此时所拥有的观念是 “你必须为此负责”。这样的态度,是有别于放纵和放逐的,是尊重对方的表现。
至此,我们也许还不能确保人们会收回对负面教育缺失尊重的种种成见。但是,作为教育者,应该有理由相信,负面教育中包含的是另一种尊重。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90.
[2][法]阿尔贝·雅卡尔,皮埃尔·玛南,阿兰·雷诺.张伦译.没有权威和惩罚的教育?[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5.
[3][英]边沁.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6.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300.
[5]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 4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3088.
[6][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
[7]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Z].1948-12-10.
[8]Avishai Margalit.The Decent Society[M].Fir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edition,1998,22-27.
[9][10][苏]马卡连柯.吴式颖等编.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02,402.
[11][12][13][美]约翰·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8,114,122.
[14]肯尼斯A.斯特赖克等.洪成文等译.教学伦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