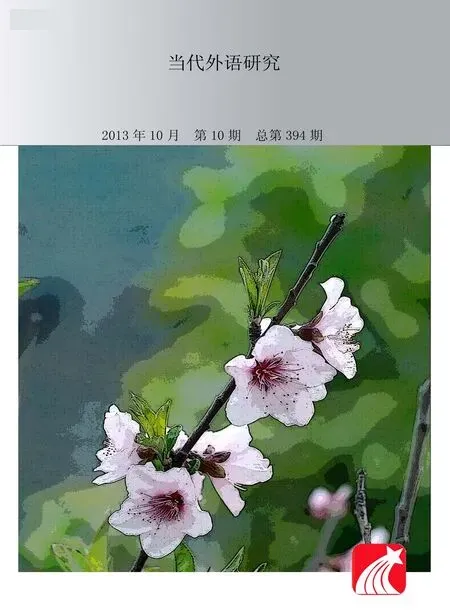论《贝利小餐馆》中的黑人男性气概建构
武玉莲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089)
1. 引言
当代非裔美国女作家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擅长从黑人女性经历中挖掘写作素材,探索女性世界,文笔波澜不惊,却韵味十足。《贝利小餐馆》(Bailey’sCafé,1992)是其继处女作《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WomenofBrewsterPlace)之后又一部以布鲁斯为基调的力作,讲述发生在贝利小餐馆和夏娃旅馆的故事,时间为1948年夏到1949年夏。小说主要由夏娃旅馆里的女性讲述自己饱受种族歧视和男权压制的辛酸历史与悲惨经历,每个故事都充溢着一种悲戚的忧郁,娓娓道来,宛如一首布鲁斯乐曲。小说中穿插着一位很独特的人物——“梅普尔小姐”,但他不是女性,他真名叫斯坦利,实为男性。他虽有高学历,但在求职过程中,因自己的黑人种族身份屡屡遭受拒绝。后来他无意中来到了夏娃的小旅馆,得以暂时栖身。由于天气炎热,他喜欢穿女士裙子,既舒适又防暑,被众人称为“梅普尔小姐”。
内勒的大多作品一向以描写黑人女性为基调,相对而言,其笔下的黑人男性人物往往比较平面化,但在本小说的倒数第二章,内勒以大篇幅描摹了一位黑人男性形象。对于本部作品的研究,大多评论均从女性研究视角关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对“梅普尔小姐”的着墨却不多,散见的评论认为他提供了“黑人男性气概的一种不同理解”(Byerman 2005:90),代表了“男性气质的正面典范”(Erickson 1993:201),但对于他的男性气概与前人的男性气概有何不同及他是如何建构自己的男性气概等问题却详解不多。
那么,什么是男性气质与男性气概呢?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与认识一直比较模糊、不太明朗,有关它的学术之争到现在依然在持续。其中,康奈尔的男性气质观被广为接受,他认为男性气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构建的过程,并因阶级、种族、历史、经济等因素的不同而各异。男性气质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分为支配性、从属性、边缘性、共谋性等不同类型,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是一个核心概念,具有浓厚的男权文化和性别角色色彩,同时也是特定文化环境中男性品质的理想类型(康奈尔2003:104-111)。
后来曼斯菲尔德提出了男性气概的概念,在他看来,男性气概是“一种德性”,是“勇敢或绅士风范(gentlemanliness)的德性”(曼斯菲尔德2008:4)。由此,男性气概有着与男性气质不同的内涵,更强调一种勇气和品德。“男性气概不是某种所有男人都具有的性质,也不是大多数男人和少数女人所拥有的,而是少数男性以一种高级的方式具有的品质。”(同上:57)对黑人这个特殊的族群而言,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及之后的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影响了黑人男性气质的构建,导致男性气概的缺失,如康奈尔所说,白人为黑人男性施加的“制度压迫和肉体摧残作用影响了黑人社会中的男性气质构成”(康奈尔2003:110)。男性气概中“蕴涵着超越男权文化观念和性角色理论的精神诉求,突出的是一种精神品质”(隋红升2011:17),所以很多作家用文学作品来构建黑人男性气概,传达自己对黑人男性的期望,“梅普尔小姐”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本文将参照男性气质和气概理论,通过分析“梅普尔小姐的布鲁斯”这一章节中祖孙三代的男性气概,尤其是“梅普尔小姐”的黑人男性气概构建,考察作家对黑人男性气概想象模式的转变历程,其中重点考究暴力在黑人男性气概构建中作用的消减过程,以期了解黑人男性气概构建的整体脉络,把握作家对黑人男性气概的不同阐释。
2. 传统黑人男性气概中的暴力因子
男性气概的内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差异,它是一种社会构建,是社会对男性的期望。在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下黑人男性气概的构建困难重重,因为白人主控了判定男性气概标准的权力。在此之下,男性气概被视为造成权力关系不平等的过程与结果,其中既有性别上的权力不平等,也有种族上的不平等。为了厘清黑人男性气概的风貌,在这里需要将黑人男性放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在主流男性气概模式的脉络里面,来解析被边缘化的黑人男性气概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男性气概的。
美国是一个有着暴力传统的国度,从拓荒时代的暴力情愫和牛仔精神中可略见一斑。在西进运动中,拓荒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在凶险莫测的原始森林、大草原与河流面前,人们需要果断、勇气和力量而不是犹豫、懦弱和恐慌。只有充满力量和侵略性的人才能战胜对手以取得生存的权利,而犹豫、斯文和礼让意味着失败和死亡。“暴力成为北美移民维持安全生存、扩展自己领地、增加财富、显示自我的手段。”(张立新2007:237)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中,人性遭到压抑,暴力成为“人们反对专制和禁锢、摆脱孤独与封闭和争取人身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方法”(同上:243)。因此,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崇尚暴力、有着暴力神话的国家。暴力基础上的男性气质得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可,甚至赞许。
就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来看,正如朱小琳(2008)所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张扬暴力的因素。在十八、十九世纪,黑人男性被刻画为“未开化的野兽,不能体会复杂情感、不能感受恐惧或懊悔”(Hooks 2004:44)。与白人暴力不同,黑人男性暴力使他们成为“失控、狂野、野蛮、天生的掠夺者”,被斥为“野兽、怪物、魔鬼”(同上)。这种对黑人形象的扭曲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对黑人男性的偏见。“野兽”成为黑人男性挥之不去的阴影,阴影下的黑人男性不仅被剥夺了各种权利,更被完全排除在了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导致的后果是黑人男性不再努力改变这种固化印象,而是将其视作“优于白人男性的标志”(同上:45)。暴力成为黑人男性获得人身自由和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许多黑人作家笔下都极力渲染以暴制暴的方式,以此体现黑人种族的勇气和耐力。
再者,随着奴隶的解放、南方棉花歉收以及北方劳动力的需求,获得人身自由后的大批黑人奴隶陆续北迁,到大城市中谋生。在大都市里,挣取薪水,养家糊口的一般是女人,因为女人可以做一些比较低级的体力活,如作保姆、当洗衣工等,而黑人男性一方面被排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又因未能接受较好的教育而不能获得体面的工作,所以,黑人男人无法通过事业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随着白人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黑人女性受其影响而逐渐觉醒,她们走出家门,正如《紫色》(TheColourPurple)中的西莉那样,争取自由独立,摆脱父权和男权压迫。失去了对女性支配的黑人男性在潜意识深处埋藏着对“不像一个男人”的深深恐惧,他们变得越发脆弱。
为了显示自己的男性强者形象,黑人男性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彰显自己的男性气概,这不仅包括种族暴力,作为暴力历史受害的黑人又沿着施暴者提供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对白人种族与社会实施暴力;也包括家庭暴力,凌驾于女人之上,从而使女人蒙受伤害;还包括犯罪暴力,走上街头打架斗殴,甚至杀人越货;更有性暴力,不仅猥亵黑人女性,也“对白人女性实施性暴力,藉此报复白人社会”(Leiter 2010:133),从中获得满足感,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综上所述,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下影响下黑人男性气概的建构是狭隘的,实际上是暴力基础上的支配式男性气质的体现。
小说中,“梅普尔小姐”(斯坦利)的祖父于1849年穿越亚利桑那州大沙漠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娶了一名印第安女子为妻,当时两人语言不通,祖父教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由此,祖父骨子里透露出支配性男性气概的因子。他们生有八男二女,多年以后,他们在当地拥有三千英亩肥沃的土地。故事中斯坦利提到的几位叔叔均粗犷不羁,暴力十足。有一次,一个男人喊利昂叔叔为黑鬼,于是被他一顿暴打。在西部拓荒的过程中,这种暴力能有利地凸显男性气概,使黑人免受白人种族的掠夺,保护自己的领地。当然,这种暴力基础上的男性气概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孩子们的游戏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男性暴力的烙印。过圣诞节时,众多堂兄弟收到的都是牛仔服或者手枪等礼物,而斯坦斯的父亲送给他的礼物却是书籍,为此他耿耿于怀,由于没有这些衣服或装备,他在游戏中只能扮被人用枪打倒的小丑角色。在黑人传统男性气概观的影响下,小时候的斯坦利潜意识中有着对暴力为基准的男性气概的强烈渴望,对自己不能成为像叔叔或堂兄弟那样的男子汉而心存焦虑。
3. 消解传统黑人男性气概中的暴力因子
以暴力为核心理念的支配性男性气概不仅不会促成种族问题的解决,还会对黑人女性造成危害,更不利于黑人男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身份的构建。所以,黑人男性要想摆脱种族桎梏,构建新的男性气概,必须先解构掉传统黑人男性气概中的暴力因素。为此,黑人男性需要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消解掉白人种族视黑人男性为“野兽”的定式思维;同时在两性关系中,尊重女性,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在这两个方面,文本中斯坦利的父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换个时间与地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名诗人或哲学家,但是他却只是一位农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期望他日后能成为具有儒雅气质的新黑人,这从他给儿子取的名字(Stanley Beckwourth Booker T. Washington Carver)就能看得出来。斯坦利的名字中包含着一长串黑人历史人物的名字。其中,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是著名的政治家,1890~1915年之间美国历史上重要的黑人领袖人物之一。他倡导“以实用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为标志”(屈书杰2004:87)的工业教育,培养黑人的职业能力,同时加强道德教育,以提高美国南方黑人的综合教育水平。他还认为黑人要想在美国社会取得进步、获得尊敬,首先必须在经济上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在政治上取得平等。为此,黑人要积极地把握能得到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机会,增加基督教文明的修养,养成勤俭节约和善于理财的习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名字不是空洞的能指,而是一个社会符号,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父亲为斯坦利取得这个名字体现了父亲希望“通过自我克制与约束,而不是诉诸报复手段”(Pochmara 2011:23),通过自我鞭策,摒弃暴力,加强以意志力控制、禁欲、冷静沉着等强调诫规的自身修养,来实现黑人自我价值的思想。为此父亲饱读史书,满腹经纶,从西方文化经典作家莎士比亚、但丁到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伊斯,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父亲不仅通过教育来提高文化水平和修养,在对待女性上,他与其他叔叔的择偶标准不同,他是八兄弟中间唯一一位真正为了爱情而结婚的人,妻子漂亮热情,夫妻感情笃深,妻子死后,他终身未娶。他在妻子的墓碑上刻下了“沙漠之花”、“风之女儿”、“我之爱妻”等字样,如果墓碑上还能写得下,估计他还会继续刻下去。与通过对女性的暴力来彰显男性气概的传统黑人男性气概观不同,父亲用爱颠覆了黑人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的观念。
除此以外,父亲身体力行地践行非野蛮与非暴力的主张。妻子是被人奸杀弃于山谷中的,在凶手被捉拿之后,父亲固然爱妻心切,但是无意去阉割并活活烧死凶手,拒绝成为白人种族想象中的野蛮的“野兽”形象。另外,父亲一直以坚忍的态度对待白人种族歧视与暴力,拒绝传统黑人男性气概的界定,以此来教育影响儿子。他看起来软弱无能,一幅被动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在以自己高傲的姿态藐视白人的歧视,但是儿子斯坦利起初并不明白这一点,一直以父亲的斯文为耻辱。后来,一场父子与白人的正面冲突彻底改变了斯坦利对父亲的看法,并最终认同了父亲的生存哲学。父子两人在邮局遭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骚扰,被关进了货运室,剥光了衣服,遭至白人的羞辱与嘲笑。直至这时,当众受辱的父亲也没想动用武力,他原想逃出去之后去报告警察。但是在暴徒们毁掉了他送给儿子的莎士比亚作品全集之后,对视书如命的父亲来说,他再也忍无可忍,在货运室找了几件女人衣服穿在身上以遮羞,而后他冲出去,盛怒之下,他将暴徒们击倒在地,让他们一一就范。站在一边的儿子惊得目瞪口呆,对父亲肃然起敬,彻底改变了父亲懦弱无能的看法。但事后父亲告诫儿子,施暴是不对的,黑人不能拿暴力来彰显男性气概,父亲的举动展示了他的“绅士风范”。
斯坦利父亲形象的刻画质疑了以暴力为核心的男性气概观,转而注重道德修养和自我素质的提高,传达出自我要求的内敛形式,希望通过文化地位上的提升来提高政治地位,实现与白人的平等的愿望;同时他尊重女性,消解了男性气概中通过对女性施暴让她们屈服于自己的男权主义思想,从而超越了传统黑人男性气概中暴力、征服等不合理因素。
4. 构建新的黑人男性气概
新的黑人男性气概的建构绝非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期间困难重重。小说中,父亲的教育极大地影响了儿子,斯坦利认识到,除了暴力之外,男性气概的实现方式有很多。黑人男性一方面可以“坚守自己的个人和文化身份”(Nash 1997:220),另一方面通过实现美国梦来体现自己的黑人男性气概。
4.1 历史创伤与种族智慧的融合
斯坦利在大学期间,遭遇到种族歧视的层层壁垒。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数学专业,最后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数学考试答案是固定的,只要答对了就能得到分数,而对于文学和哲学这样的学科,不管答卷上写什么,教授们总认为是空洞无物、没有思想内容,成绩永远是不及格或者刚及格。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后来发现其他的黑人学生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种族歧视不仅在大学里深深扎根,在军队亦是如此。斯坦利在校期间,二战爆发,他满腔热情地到红十字会义务献血,却被告知血库不接收黑人献的血。种族歧视让斯坦利深感愤怒、彻底绝望。当政府宣传鼓励黑人入伍参战时,斯坦利毅然决然地拒绝去前线当炮灰。传统男性气概观认为,战场上的暴力厮杀能让男性“重拾男性气概”(Hooks 2004:48)。然而同父亲一样,斯坦利拒绝通过暴力来凸显男性气概。
由于拒绝被征兵,斯坦利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如同非裔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恶作剧精灵一般,他学会了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策略。恶作剧精灵如猴子、兔子等在非洲裔美国民间传说中一直是重要的角色,它们机智圆滑,“通过愚蠢、傲慢或勇敢的方式,恶作剧精灵总能应对可怕和混沌的局面”(Smith 1997:2),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机灵处处化险为夷,恶作剧精灵的双面技巧成为黑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生存的必要技能。在监狱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面对典狱长的骚扰、狱友的威胁,斯坦利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绝不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是用智慧周旋在他们中间,从容应对,最后得以安全地度过在监狱的漫长日子。
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给斯坦利造成了难以抚平的种族创伤,但他承继了父亲非暴力的生存理念,用黑人种族智慧哲学与白人社会相博弈,体现了新的男性气概观。
4.2 白人教育与种族自信的结合
斯坦利在斯坦福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正统的白人教育武装了他的头脑,让他获得了先进的知识。他的儒雅气质使他不同于其他黑人男性,只要他“一张嘴巴讲话,就知道他不是从哪个穷乡僻壤来的,一听就很有文化,显然,他接受过教育”(Naylor 1992:164)。斯坦利还熟稔自己的种族历史,不像小说中的其他黑人男性人物那样对自己种族的历史一无所知。
博士毕业之后,斯坦利去应聘统计分析师的工作,却被给予保管员的岗位,负责拖布和扫帚。后来,他来到丹佛、堪萨斯、芝加哥、费城,能接纳他的岗位基本是服务生、脚夫、电梯操作工等工作。他跑遍了全国大中城市,他的市场分析计划备受众多公司的青睐,但他们都不想以影响公司形象为代价去招聘黑人。处处碰壁的斯坦利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如同海明威笔下的老人,表现出了超强的意志力与重压下的优雅。“具有意志力的男性气概”(曼斯菲尔德2008:125)虽不是男性气概的全部,却是一种勇敢的德性。虽然工作失意,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而是始终满怀信心,“拥有自信”(同上:26)使他成为有男性气概的人,因为自信让他独立于他人。在夏娃旅馆的工作很轻松,他有大把的时间搞投资,另外他还参加一些公司的广告词征集大赛,由于对市场非常熟悉,他的广告词一举获得大奖。“梅普尔小姐”以积极的行动践行美国梦,即使一再受挫,但自信心与灵活性依然让他最终得以成功。在小说的结尾,他挣的钱足以让他离开夏娃旅馆,成立自己的公司,所以他准备迎接新的生活,实现自己的黑人美国梦。
4.3 男性气概与女性特质的糅合
有学识、有能力的斯坦利由于黑人身份而屡屡受挫,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黑人种族身份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像先辈那样通过施暴的方式来表现男性气概,而是秉承了父亲的非暴力思想,用教育武装自己,施展自己的才华,用实际行动实现美国梦,以积极的心态参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展现了种族自信与坚强的意志力,充分展示了新的黑人男性气概。
与此同时,斯坦利的别名“梅普尔小姐”意蕴深远,表现出拥有男性气概的黑人男性能够尊重黑人女性、与黑人女性和平共处的理念。父亲的培养让他具有阴柔的气质,在以男性身份活于世界的斯坦利屡遭失败的打击之后,他以女性身份获得了事业的巨大成功。他放弃男士着装,身着女士衣服时更感到自在。虽有女性的装束,但精神上却是男女的混合体。在夏娃旅馆,他主动保护那些深受父权压制的弱小女子。“梅普尔小姐”这一名字超越了单一性别,兼具两性特质,体现了男女两性的互补,进而消除了男女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这种观念颠覆了父权社会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对立模式,融合了作家希望拆解父权社会性别神话、消除性别霸权、希望男女和谐共处的主观愿望,也即作家憧憬的“雌雄同体”境界。推崇性别平等、一个融合可取的阴柔气质及阳刚气质的雌雄同体社会。
5. 结语
男性人物是“民族的具体形象”(Mayer 2000:6),男性气概观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一个民族发展的整体面貌。本文的分析表明,作家内勒对黑人男性气概的想象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摒弃了传统男性气概中暴力、征服等不合理因素,赋予狭隘的男性气概观以新的内涵,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男性气概模式。在男性气概的建构中,重视美国教育和黑人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将二者与种族自信统一在黑人男性的成长过程里,还把历史创伤与种族生存智慧融合在一起,并将男性气概的建构与女性特质糅合在一起,成为主人公男性气概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作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探索男性气概的构建,藉此传达出了对黑人男性的理解、尊重与期待,表达了作家对种族与两性乌托邦的渴望。但小说对男性气概中的暴力因素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暧昧的态度,如父亲虽然践行非暴力的主张,但最后还是通过必要的暴力手段获得了儿子的钦佩与尊重;在夏娃旅馆,斯坦利还担任保镖的职务,专门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男性客人。有关暴力的蛛丝马迹的刻画凸显出在种族歧视重重的美国社会,黑人男性气概构建中所陷入的尴尬境地与作家的矛盾心理,体现出种族与两性乌托邦的虚幻性,实现真正的种族与两性平等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尽管如此,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相比,“梅普尔小姐”积极面对种族歧视的阴霾,以新的姿态迎接未来,这种新型的男性气概观有利于黑人男性自我身份的构建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Byerman, K. E. 2005.RememberingthePastinContemporaryAfricanAmericanFiction[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rickson, P. 1993. Canon Revision Update: A 1992 Edition [Thulani Davis, Rita Dove, Gloria Naylor, Alice Walker, and Toni Morrison] [J].TheKenyonReview(3): 197-207.
Hooks, B. 2004.WeRealCool:BlackMenandMasculinity[M]. New York: Routledge.
Leiter, A. B. 2010.IntheShadowoftheBlackBeast:AfricanAmericanMasculinityintheHarlemandSouthernRenaissance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ayer, Tamar. 2000.GenderIroniesofNationalism:SexingtheNation[M]. London: Routledge.
Nash, William R. 1997.The dream defined:Bailey’sCafé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ies [A]. In S. Felton & M. C. Loris (eds.).TheCriticalResponsetoGloriaNaylor[C].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11-25.
Naylor, G. 1992.Bailey’sCafé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ochmara, A. 2011.TheMakingoftheNewNegro:BlackAuthorship,Masculinity,andSexualityintheHarlemRenaissance[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 R. 1997.WritingTricksters:MythicGambolsinAmericanEthnicFic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W·康奈尔.2003.男性气质(柳莉等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维·C·曼斯菲尔德.2008.男性气概(刘玮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屈书杰.2004.美国黑人教育发展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隋红升.2011.危机与建构:欧内斯特·盖恩斯小说中的男性气概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立新.2007.文化的扭曲: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黑人形象研究(1877-1914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小琳.2008.扭曲的生命,不屈的灵魂:论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暴力禁忌意象及意义[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0):17-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