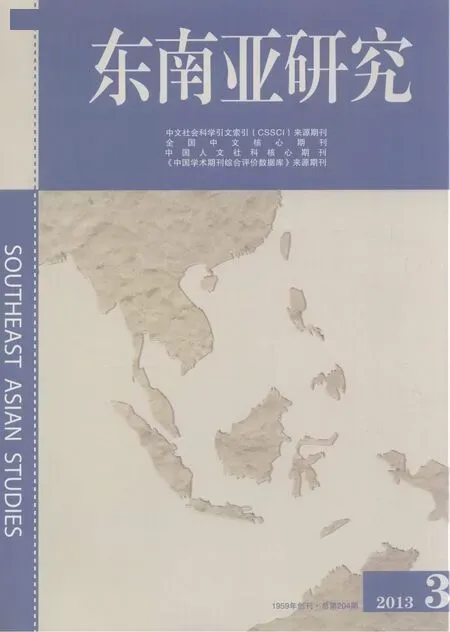越南汉文历史小说 《皇越春秋》的文化研究
吕小蓬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北京100089)
由于中越两国紧密的地理、历史、民族渊源,古代越南深受中国文化浸润,在其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汉文文学一直占据着文坛的重要地位,并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汉文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皇越春秋》便是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一部杰作,其作者、创作年代虽不可考,但从成书来看应是现存可见最早的一部越南古代长篇汉文历史小说,对越南后代同类型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全书分为初、中、下三集,每集二十回,共六十回,记述天圣元年庚辰 (1400年)至顺天元年戊申 (1428年)年间的越南史事。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载,该书今存印本1种及抄本7种[1]。此外,陈庆浩、王三庆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和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均收录有校点本,是目前所见最完备的两种通行本。
在现存越南古代汉文长篇历史小说中,《皇越春秋》因其突出的虚构性和文学性而备受学术界关注。其中,陈默的《论越南汉文小说〈皇越春秋〉》(载于《北方论丛》2000年第6期)通过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指出《皇越春秋》在创作上受到《三国演义》的直接影响,剖析了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及艺术得失。陆凌霄的《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和任明华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是国内学术界目前仅有的两部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专著,从小说体制、艺术特色与文化特征等多个角度,对《皇越春秋》做了精彩论述。本文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皇越春秋》独特的题材和话语方式,因为黎利集团、胡季犛集团与明朝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中国史籍笔记中亦不乏记载和描述。历史书写是有文学性的,“历史讲述的就不仅是事件,而且有事件所展示的可能的关系系列。然而这些关系系列不是事件本身固有的;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思考的历史学家的大脑中。这里,它们存在于被神话、寓言和民间传说及历史学家自己文化的科学知识、宗教和文学艺术概念化了的关系模式之中。”[2]倘若不囿于历史语境与文学语境的束缚,那么无论是中国史籍笔记还是越南历史小说,其实质都是叙事性散文话语,含有同样的文化研究价值,即同样承载了中越两国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特定“关系模式”。特别是由于书写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越两国叙事文本具有突出的互文性特征。本文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不做辨别真伪的历史考据,而是力图进行中越两国叙事文本的互文性对比,通过分析双方文本表述的重复现象,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皇越春秋》的话语特征及其对中越历史事件所做出的文学虚构和文化阐释,剖析其体现的越南文化的民族性格。
一 “真理”的对话:越南文化的话语独立意识
《皇越春秋》是以陈朝王室后裔陈天平在失国的危急时刻向明成祖求援的情节展开故事的。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中越两国文本的叙事话语呈现出趋同倾向。《明史》记载永乐二年“故安南国王陈日煃弟天平来奔”[3]。《明史纪事本末》则记述了陈天平“叩头流涕”,奏请明成祖“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职贡”而协助讨贼复仇[4]。《皇越春秋》第二回“陈天平乞怜上国”对此描述为:
明侍郎王俊引天平跪于龙墀,奏曰:“臣陈家后裔,声教外臣,恭遇天朝,率先归顺……伏望陛下天地父母生成之德,恤及微臣,世守南邦,恭修职贡。季犛父子罪逆滔天,臣与此贼誓不俱生。”因叩头流血。[5]
这处书写与中国文本相近,陈天平跪称“外臣”、“微臣”,叩请明朝顾念陈家世守安南、恭修职贡而出兵助其复国。对此,《皇越春秋》不仅未加贬斥,还在对明朝出兵讨伐胡季犛父子的叙述中,更鲜明地显示了与中国文本的趋同性。例如多次在回末诗中指斥胡氏“贼子乱臣天共怒,弑君篡国地难容”[6],蔑视其“不觉偏方诚地窄,敢将群小抗天兵”[7]的对抗行动,甚至直接借黎利属下之口称赞“明朝遣将,伐罪吊民,救弱扶衰,正为顺道”[8]。可见,《皇越春秋》肯定明军入越伐胡的正义性,希望借助明朝之力正纲常、锄逆贼,实现封建正统王朝的回归。邱浚的《平定交南录》也记述了越南百姓对明朝军事干预行动的反应:
初,交人闻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闻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见榜末云:“待黎贼父子就擒之后,选求陈氏立之。”莫不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9]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皇越春秋》所传达出的越南古代社会对中越关系的基本定位,即接受宗藩关系中的外藩地位,以政治及军事上依附宗主国来维护自身社会的稳定。
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一部作品和孕育、渗透它的文化之间的趋同效应体现在很多方面,互文的互异性深融于文本的个性中”[10]。在宗藩关系的语境下,在叙述明朝讨伐逆胡的互文性文本中,《皇越春秋》体现出与中国话语的趋同特征。但随着明军军事行动的升级,它的叙事话语逐渐呈现出与中国文本的互异性,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了越南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格。
明军出征前,明成祖誓师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此,中国文本多有重述,叙述话语也大致相同,即如《殊域周咨录》中所述:
上幸龙江。禡祭誓众曰: “黎贼父子必获无赦。胁从必释。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恣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降。有一于此,虽功不宥。毋冒险肆行,毋贪利轻进。罪人既得,即择立陈氏子孙贤者,抚治一方。班师告庙,扬功名于无穷。其共勉之。”
按观誓众之词,俱平定安集之略。与古帝王神武不杀,真有光哉![11]
《皇越春秋》同样以宏大叙事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
成祖幸龙江禡祭,誓众曰:“胡贼父子,必获无赦,胁从必释。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廛行,毋害稼穑,毋肆取财货,毋掠人妻妾,(二句是徒誓耳。)毋杀降。有一犯者,虽功不宥。毋冒险肆行,毋贪利轻进,罪人斯既得,必拜陈氏子孙贤者,统治一方。(如此不敢奉诏)班师告庙,以次定功。”[12]
《皇越春秋》和《殊域周咨录》均以批注和按语的形式,对事件做出了直接的解读和阐释,然而两者的叙事话语却是互异的。严从简身为明代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给事中,其按语以臣子讲说圣朝君主的语气,赞赏明成祖的英明神武,是“我者”的主体性表达与自我认知。而《皇越春秋》的按语则是置身事外式的调侃,与天朝圣主誓师的庄严语境形成强烈反差,不仅从叙事语气上颠覆了话语的庄严性,使明成祖的誓词由我者的源话语演变为对他者话语的讽刺性模仿,更直接否定了正义誓词的真正动机和实际效果。“话语在穿过他人话语多种褒贬的地带而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情味深入时,要同这一地带的种种不同因素发生共鸣和出现异调”[13]。换而言之,《皇越春秋》与中国叙事文本间的异调源于其话语独立意识,是独立的“我者”话语在深入阐发时,与“他者”的话语在褒贬地带上出现差异化造成的。
明军入越的军事行动在实际效果上不尽如人意,甚至加剧了越南社会的动荡。《皇越春秋》多处叙述了明军贪暴、为害百姓的行径,如“美女三十余人,乃是梁成胁取民女,充为己有”[14];“北将李彬督后部,凡所到之处,胁淫妇女,掠取货财”[15];“友坠下,被北兵生擒,并得其党二千人,张辅深恨,命悉坑之,筑为京观”[16];“李彬、马骐索民供贡,马骐墨而残,定一而取十,要索百姓以金银代纳……残虐日甚,浚尽民财”[17]等。并写乡村耆老因不堪忍受而泣求黎利:“今北国索民贡献,有不及者,杀戮甚酷,请黎公起兵讨贼,以救生民”[18],明确地将明军的贪暴作为民族起义的直接导火索。虽然中国文本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平定交南录》等对此也有述及,但却将张辅坑卒筑尸、马骐墨残的事件作为个案,而将越南的抗明斗争解读为风俗教化之争,如“盖新设州县军卫太多,交人久外声教,乐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首所至,辄为之供亿隐蔽。以故贼溃复聚”[19]。作为叙事主体,《皇越春秋》与中国文本间呈现为对立的他者关系,双方不仅互称为“贼”,而且各自以我者的口吻对他者进行声讨。
平定逆胡后,明朝并未履行立陈氏子孙的承诺,反而郡县安南。对此《明史》仅以“求陈氏后不得,遂设交趾布政司,以其地内属”[20]做简略叙述。《明会要》则增加了越民请命的细节,称“陈氏子孙耆老千余诣军门,言:‘陈氏已灭,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辅等以闻”[21]。而《平定交南录》的叙述最为详细:
先是,王等受命时,诏令求陈氏子孙立之。至是平定,王遍访国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称:“黎贼于己卯年杀光泰王颙,立其子 而杀之,遂篡其国。前后杀其近属五十余人,及其远族又千余人。血属尽绝,无可继立者。请依汉、唐故事,立郡县如内地,以复古。”王疏闻,上从其请。[22]
以众多越南官吏耆老人主动请求的细节,强调郡县举措是顺应越南人民的意愿。《皇越春秋》却写张辅不顾黎利请立陈氏后人的提议:
密使喻百姓请立郡县。及宴罢,见帐外三四耆老伏地啸曰: “陈氏不存,乞设都护,如汉唐故事。”辅曰:“民心如此,诸将如何?曷若奏捷回朝,献俘传命,此时立与不立,方可议定。”[23]
可见,《皇越春秋》的有关叙述几乎与《平定交南录》针锋相对,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三四耆老”使“遍访国中官吏耆老”失去了代表性,“密使喻百姓”使“立郡县如内地”的请命沦为一场阴谋,中国文本中的正义征伐被阐释为恃强凌弱的穷兵黩武,中国话语中民心所向的收复外藩被阐释为失道寡助的侵略扩张,并成为促使越南有识之士“扶正统”、“奋中兴”,走上越南民族独立之路的直接动因。
正如巴赫金所说,“说话主体的每一具体表述,都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施力点,集中和分散的进程,结合和分离的进程,相交在这话语中。”[24]《皇越春秋》不是对中国叙事文本的重述,而是以离心力的话语进行主体性表达,其与中国叙事文本在互文中的互异性则进一步彰显了“我者”话语与“他者”话语相遇的特征,即“作者在他的真理和他人的真理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特殊的相互联系。作者是相当活跃的,而他的行为具备一种特殊的对话特性”[25]。《皇越春秋》便是这种作者的“真理”,即越南民族文化语境下的“真理”。它是处于宗藩关系的历史框架下,在封建时代东亚、东南亚强大的汉文化场域中,越南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对话”。尽管由于文化的长期弱势地位,《皇越春秋》只能借用中国的文字书写方式和文学形式,但它却试图以自己的独立话语阐述自己的“真理”,并以此与中国话语中的“真理”形成一种全新的联系,传达越南文化的独特声音与独立精神。
二 话语的“转移”:越南文化的民族独立精神
《皇越春秋》与中国文本在叙述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具有明显的互文特征,但其文化阐释却往往是属于越南民族的。正如互文理论家所说:“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26]《皇越春秋》的互文实现了对中国文本的话语“转移”。例如,“画狮蒙马”是中国古代文本多有重述的明军征战安南的经典战例,《明史纪事本末》便写到了张辅率兵与胡军进行的这场激战:
贼复巷战,列象为阵,辅等督游击将军朱广等以画狮蒙马,神机将军罗文等以神铳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铳箭,皆退走奔突,贼众溃乱。[27]
《平定交南录》也写到:
都指挥蔡福等数人先蹑梯登城……贼于城内列阵,驱象来冲我军。乃出内府所制狮子象蒙马,象见狮形惊畏而颤,又为铳箭所伤,倒回奔突。贼溃乱,自相蹂践。[28]
《皇越春秋》也记述了这场富于传奇色彩的战役,写黎利之子黎钦率兵协助明军与胡军交锋,他面对敌军象阵施展奇谋:“将马蒙以画狮埋伏,闻号抄出左阵击之……以虎皮蒙马首,见号抄出战右阵击之”。战斗中黎将“产容各以狮虎翼而前,象皆股慄,多中炮箭,缩鼻便走”。黎钦卓越的军事谋略不仅扭转了战局,还令明将沐晟赞叹“如此将才,我诚不及”[29]。在这段互文性文本中,《皇越春秋》将以奇谋妙计克敌制胜归功于黎钦,使中国文本对明军神武的称道转移为赞颂黎军将领的军事智慧。再如黄福是中越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不仅作为明军主将出征安南,还在当地出任行政长官长达19年。他为官正直宽厚,“治交趾,视民如子,徇其所好,祛其所恶,劳辑训饬,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抚字之政,新造之帮,政令条画,无巨细咸尽心焉”[30],不但受到明成祖的褒奖,同时也在越南社会享有赞誉,《大越史记全书》称其“为人聪慧,善应变,有治民才,人服其能”[31]。《皇越春秋》中对黄福也多有叙述,并以与中国文本同样的话语记述了黄福归国时“交人有何盛恩者,扶老携幼送之”[32]的情景。不过,《皇越春秋》建构的黄福形象毕竟与中国文本有了重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在黄福奉诏回国的原因上,《明史纪事本末》中因“上念其久劳于外,召还”[33]。而《皇越春秋》中黄福因感悟“南国必生圣君矣,久居,祸必不浅”,从而主动萌生去意,临行前还透露了“子国已有圣君,虽欲坐固,不能得”的天命[34]。二是在黄福被俘后获释的原因上,《明史纪事本末》中载:
工部尚书黄福为贼所得,皆下马罗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谕以顺逆,贼终不忍加害[35]。
《殊域周咨录》也写到:
福为贼所得,皆下马罗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谕以顺逆之理,贼终不忍加害。[36]
《明史》记载黄福被俘后:
欲自杀。贼罗拜下泣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闻之曰:“中国遣官吏治交趾,使人人如黄尚书,我岂得反哉!”遣人驰往守护,馈白金、餱粮,肩舆送出境。[37]
而在《皇越春秋》中黄福战败被俘,黎利本欲斩黄福,只因与黄福有师生之谊的爱将公僎、少碍情愿替死,黎利才义释黄福。黄福非但没有“斥之,谕以顺逆”,反而回报了黎利的不斩之恩:
黄福入谢,言曰:“南国之民,劳于兵革,请大王班师释旅,回守南帮,致某回朝,奏请息兵,得两国安然无事矣,则天下之大幸也。”[38]
显然,《皇越春秋》中黄福的形象发生了“转移”,由中国文本中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忠臣义士转化为识时务、知大体的智者。这一“转移”并不单纯出于文学作品刻画人物的需要,而是越南文化想象下的文学虚构的结果,通过民族文化语境下的阐释,重塑了黄福这位在中越两国均享有盛誉的历史人物,借此传达、强调越南民族独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从《皇越春秋》与中国文本的互文特征来看,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上的“转移”,归根结底都是双方民族文化阐释的结果。由于胡季犛集团与黎利集团都未经宗主国册封而擅自宣告政权,因此中国文本将其统统阐释为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叛乱,而将明朝的军事行动称为“平定交南”或“安南叛服”,也就是在天朝上国的文化语境下叙述宗主国起兵平定外藩叛乱的话语。《皇越春秋》对此做出自己的民族文化阐释,叙述黎利集团在铲除逆贼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勇敢机智地与外敌斗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建国事迹,从而将中国文本的平叛话语“转移”为捍卫民族独立的爱国史诗。
《皇越春秋》中话语“转移”的文本现象张扬了越南文化中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不过其独立观念却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例如在明成祖向群臣征求安南事务国策时,黄福提出“立陈氏后,统治交人,永为臣妾”,而张辅主张“郡县其地,以绝后患”。客观地说,黄福、张辅的策略异曲同工,都是站在明朝统治的立场上获取对越南社会的控制权。不过,《皇越春秋》对黄福的“永为臣妾”之说未置一词,而在批注中痛斥“张辅狼心已露于此”[39]。再者,黎利虽然击溃来犯明军并宣告了政权,但随后便以臣子的名义求封纳贡。可见,黎利集团争取的仅仅是使越南不必沦为郡县,而并非彻底摆脱纳贡称臣的附属国地位。从这一角度上看,《皇越春秋》传递出越南文化阐释的独立观,其立足点是可为外藩、不为郡县,即接受以中国作为宗主国,但拒绝纳入中国的疆域版图。这一独立观深刻映射出越南民族的自我形象认知,“我兵微将寡,国小民贫,欲提数千乌合之师,而抗百万熊桓之众,正犹以鸟卵而斗泰山耳”[40]。可以说,越南民族建构了“兵微将寡,国小民贫”的自我形象认知,并与熊桓之众的中国他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而《皇越春秋》在高唱民族独立史诗的同时,其阐释的独立观正体现了越南民族基于这种自我和他者形象对比而做出的现实性的选择。
结语
“每一文化的因素各有其特殊的意义,对这些因素的评价,只能站在该文化的立场作判断,而不能以他一文化的观点来论其好坏,这也就是说文化之间的价值判断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41]本文将《皇越春秋》与中国文本做出互文性对比,也绝非意在进行价值高下的判断,而是力图揭示其话语蕴含的越南民族文化特征。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在域外汉文化圈的延伸,《皇越春秋》以汉文的书写方式、中国历史小说的惯常体制展开叙述,以越南民族的独立话语和独特的文化语境阐释中越历史上的斗争事件,既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又张扬了民族独立的精神。可以说,它体现了越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反馈,其独特、强烈的文化对话意义无论在文化人类学还是比较文学的视域内都值得研究者予以关注,即使是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引人深思的。
【注 释】
[1]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897页。
[2]〈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3]《明史》卷6《成祖本纪》,第81页。
[4][27] [33] [35]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2《安南叛服》,第345页,第348页,第356页,第360页。
[5][6][7] [8] [12] [14] [15] [16] [17][18][23][29][32][34][38][39][40] 《皇越春秋》,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132页,第132页,第149页,第167页,第149页,第283页,第180页,第238页,第261页,第268页,第208页,第178-179页,第304页,第304-305页,第338页,第134页,第168页。
[9][19][22] [28] (明)丘浚:《平定交南录》,载于 (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4页,第1869页,第1867页,第1866页。
[10]〈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1][30][36](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5《南蛮·安南》,中华书局,1993年,第178页,第193页,第196页。
[13][24]〈苏〉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页,第50页。
[20]《明史》卷154《张辅列传》,第4221页。
[21](清)龙文彬: 《明会要》卷78《外藩二》,第1510-1511页。
[25]转引自〈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26]〈法〉菲力普·索莱尔斯语,转引自〈法〉蒂费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1]〈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9,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刊行委员会,1984年,第497页。
[37]《明史》卷154《黄福列传》,第4226页。
[41]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