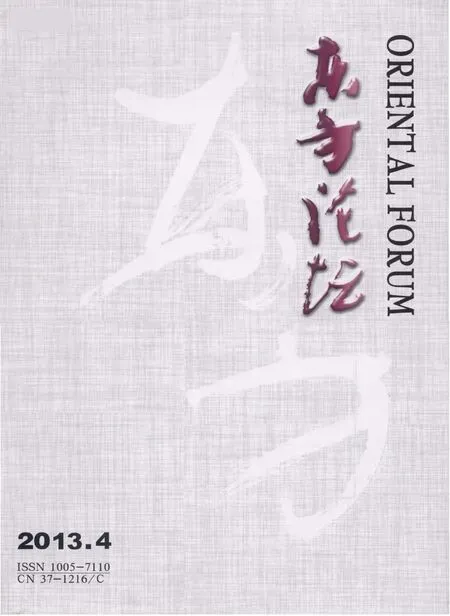英国后殖民作家的流散书写特征
杨晓红 李升炜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英国后殖民作家的流散书写特征
杨晓红 李升炜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当代英国后殖民作家用英语写作,他们都熟悉英国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双边甚至多边文化综合的优势。他们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站在本民族的立场,描述本民族的生活,用文本的形式来演绎被歪曲的历史并表现出明显的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是通过使用寓言体的叙述形式和对欧洲文学传统的颠覆表现的。同时,他们还表现出对人类共同命运与未来的关注,表现出探索人类文明之旅的努力。
全球化;流散;流散写作;后殖民;文化研究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写作①流散“diaspora”一词来自希腊语“diasperirein”,其中“dia”意为“分开或穿越”,“sperein”代表“播种、播撒”,表示植物借花粉和种子的传播而繁衍生长。国内学者对“diaspora”一词有多种翻译:飞散、流亡、族裔散居、离散等,鉴于在全球化语境下流散作家离开本土大多属于自愿,且在居住国并没有被居住国的文化完全同化而是采取借鉴糅合的方式共生共存,本论文作者赞成王宁教授的说法,亦称之为“流散”。关于流散、流散文学的由来已有多位学者做过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对流散文学的研究也已成为一个热门课题。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深入,学界对流散现象格外关注。流散批评也应运而生。国内对流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流散写作理论;2)对世界不同地区流散文学的研究,包括美国华裔、加勒比流散作家、非裔流散作家、犹太裔流散作家的研究,其中对美国华裔流散作家的研究成果最多。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欧洲流散作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当代英国流散作家较为全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论文通过细读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英国后殖民说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钦努阿·阿契贝、布奇·埃默切塔、本·奥克利、纳丁·戈迪默、J·M·库切、维·苏·奈保尔、卡里尔·菲利浦斯、迈克尔·翁达杰、萨尔曼·拉什迪、韩素音、提摩西·莫、石黑一雄、巴里·昂斯沃斯、克里·休姆等人的代表作品,用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分析其中与欧美文学传统相异的流散写作特征。
一、流散文学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流散文学这个由来已久的世界性学术命题,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义。流散文学作为伴随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而出现,并以文学的形式对流散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诗性表征的文学事实,有其悠远的历史传统,有其特定、丰富的文化与诗学内涵[1]。流散文学之滥觞可追溯到希伯来圣经和圣经后典。长期以来,流散文学专指自两次犹太战争,犹太人进入世界性大流散以来的犹太文学。除犹太人以外,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如非洲人、印度人、加勒比人、墨西哥人、华人等族裔也有类似于犹太人流散的现象,在世界各地的流散。所以,“流散”是一种世界性现象。流散文学相对于居住地主流文学而言,无论书其作者本身还是其作品,明显处于边缘的、少数的、非主流的状态,因而这种文学亦被称为“少数族裔文学”。
二、后殖民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
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尼日利亚的杰出作家、批评家希努亚·阿契贝在他的主要论著《后殖民批评》中,他揭露了一个真相:西方批评家用所谓文学普遍性的观点来包裹自己文学的民族性,排斥其它民族的文学,实质上是带有殖民性的批评[2]。另外,他在一系列文章如:“非洲作家和英语语言”、“一个关于非洲的形象: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中,强调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赛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东西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体系,指出所谓的东方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2]。赛义德后来所著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进一步审视了十九、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霸权,从根本上颠覆了长久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体系。因此,赛义德被另外两名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誉为“开创了后殖民批评研究的领域的大家”。
斯皮瓦克以她的《贱民能说话吗?》(1988)一文和相关著作把后殖民批判引入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层次。霍米·巴巴在《民族与叙事》[1](1990)和《文化的定位》(1994)中对殖民主义文化话语进行了深入、有力的分析和批判。在后殖民批评思潮中,也有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其中最嘹亮的当数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和美国的弗·詹姆逊。尤其是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3]。这样,第三世界的文化传统将面临威胁,母语流失,文化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并发生改型。针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文化应该与第一世界文化进行对话,以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打破欧美文学传统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及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的力量。
三、英国后殖民作家的流散书写特征
英国后殖民作家指的是从1980 年代以来在英国文坛具有较大影响的来自大英帝国前殖民地或其他国家与地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后殖民特征的作家。这些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用英语写作,不仅在英语中注入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还将其他民族的文化带进文本中,创造出了一种跨文化的“世界小说”文本,使当代英国小说由于具备了丰富的跨民族性而引起世界的关注。本文作者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在这些英国当代后殖民作家的作品中在以下八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与传统欧洲文学传统相异的流散文学特征:
(一) 语言
对于大部分英国后殖民作家来说,英语是他们继承的语言,是父语,同时也是他们的隶属母语,而民族语言是他们的“根”。他们流散到这样一个“阈限空间”,在这个语言交接点构成的空间中,英国后殖民作家创造着一种新型的“流散语言”,这种流散语言,表现的是一种由流散者的“流散语言”维系的“根”与“流散”的关系。处于边界写作状态下的流散作家虽然使用英语写作,但他们所使用的英语不再是大写的English,而是小写的english,或englishes。这是颠覆传统与中心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及再表义(resignification)的一种方式。用重新定义的词语开拓空间,不仅是为了表现无法名状的、审慎压抑的感觉和情感,更是为了冲出殖民者的语言牢笼,为流散族群赢得商讨和重新书写的空间。当这些身份模糊、文化心理分裂的被殖民阶层彻底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句法与句法的帝国主义二者之间并行一致时,他们毅然崛起,打破帝国主义句法的束缚,将模糊、含混、支离破碎的流散文本转变为反霸权力量的源泉。这就是边界写作的缘起,无拘无束的边界写作形式打破了句法、语法和逻辑等语言规则的限制,从而将英语转变为一个再表义系统。
(二) 文化认同与身份危机
文化认同是一种共有的情感和信仰,是把某一文化系统内置于自己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并据以评判生活和和规范行为的人类文化倾向,也是一种方向感,是寻找价值方向、生活方向、行动方向的心理诉求,其根本目的是定义自我[4]。文化认同是流散文学表达的主要主题之一。流散作家提倡多元文化中的自我认同,藉此强调认同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位置和地域所形成的地域认同,甚至进一步挪用后殖民研究的论述,强调一种交混杂糅的认同位置。
英国后殖民作家中的奈保尔,是“文化无根”精神悲剧的重要“表演者”,他的在世状态——因为拒绝了特立尼达而造成自己的文化悬挂;因为疏离了母国印度而无文化落根之处;因为无法真正“抵达”英国而飘浮在欧洲文化之外;因为精神性危机而寻找不到灵魂归宿——使他更具“无根”特色:他是精神上的流放者、印度母国的海外浪子、欧洲文化的私生子、特立尼达的“文化弃儿”、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公民”,哪里都没有他的根[4]。流散作家库切笔下的人物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总是有一种欲望,想成为某种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最终他们发现只能成为自己主观创造出来的外在世界的变形系统中的一部分[5]。旅居英国的日本流散作家石黑一雄也是身受英、日两种文化的熏陶,却对两者都有一种疏离感。提起日本人和英国人,他都用“他们”这个人称代词来指称,而不是“我们”。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漂泊无根的感觉。他的主人公都抱着怀旧的心情回忆往昔的岁月,被孤独错位的情绪所萦绕。他既非日本的,又非英国的。
(三) 文化杂糅
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是当代英国小说又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它不仅是当代英国后殖民作家刻意描写的主题,而且还是他们创作活动本身的一部分。与其先辈作家相比,当代英国后殖民作家的创作意识具有独特的一面,即特别关注英国身份的多重性 (a range of British identities)和多元文化语境( cultural contexts)[6]。后殖民批评家喜欢用“杂糅”这个概念来描写流散作家由于跨文化疆界引发的时空关系和身份归属问题,并将它看作是“由殖民引起的不同文化接触区域内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跨文化创作”[7](P118)。
印度裔英国后殖民作家拉什迪在其作品《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92)中声称自己写作《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 的动机是要找寻并恢复童年时代的家园,以便能让自己疲惫奔波的灵魂有一个歇息之地。但他发现时空的断裂己使得“家园”遥不可及,只存在于梦想之中。《午夜的孩子》这部小说从印度电影、报纸、街市文化、巫术、妖术、神话、传说及各种政治历史事件、文化习俗以及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中提炼了各种复杂的历史意象,形成了一个大杂烩。这里,历史真实与流言蜚语相互掺杂,传统迷信与民主政治,原教旨主义与多元文化混杂一起。这种内容上的“杂糅性”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小说独特的叙事空间,构成了由诸多小叙述交织而成的蜂窝状结构,也让整个叙述在精英与通俗、过去与未来、上层与下层之间来回穿梭。埃默切塔1983年的短篇小说集《阿达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写的是移民到英国伦敦的尼日尼亚妇女。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度里,她拼命挣扎以求自身的独立,含辛茹苦抚育自己的子女。在白人眼中,黑人是二等公民。但黑人妇女的地位更低,她们还要受到男人的欺凌。该故事集表现了作者对于处于双重压迫下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关注。
(四)重新书写历史
流散作家能够用一种“外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母国的历史,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重新书写历史表现出对本国历史重新审视、对落后现状的担忧或正在改变的欣喜以及对未来给予的希望。
在书写《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时,奈保尔从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转变成怀着期望去关注母国前程的当事人,在他以口述历史的方式为血缘母国印度的现代史书写了恢弘的一面、充满活力的一面,把印度的历史从古老得像“废墟”一样的沉静与恒定中剥离出来,为更多的当代及后来的印度人增加思考和前进的勇气与力量,表现了作者对于母国当前所发生的变化的无比欣喜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拉什迪的小说创作也是通过滑稽模仿、演义、讽喻、戏说等各种方式来“解构”业已被定型的历史,通过他的处理,历史呈现出开放的特点,这给文学作品及其读者提供了可以无尽想象的空间。在他看来,小说总是要否定官方政治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记述,他的作品意图打破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故事之间的既定界限,在其小说中,故事是历史,历史也是故事。拉什迪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而不是史诗时代,他打破历史与故事之间的界限,其用意并不是要回到史诗时代,也不是为了戏弄历史,而是以反政治、反历史的姿态来建构新的政治和新的历史[8]。
阿尔马赫长篇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淋漓尽致地彻底揭露了加纳的腐败现象。奥克利的小说《饥饿之路》中描写了发达国家在非洲推行西方式民主和政党制度,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阿契贝的代表作“尼日尼亚四部曲”的第三部《神箭》揭露传教士在非洲的罪恶活动。英国殖民者利用传教士作开路先锋侵入非洲部落,在非洲人内部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冲突,然后用武力镇压非洲人的反抗。这无疑是对殖民历史传统的颠覆。
库切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乡》描写了两个故事,两个主人公。两位主人公的共同点在于,不仅入侵或侵占别人的土地,而且还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且都采取了一副君临天下的傲慢态度,把当地人视为虐等的“他者”。小说将战争和殖民行为并置,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
戈迪默1981年出版的《朱赖的人》构建了在未来南非白人几乎是死路一条的情景。读者从中不但可以窥见种族仇恨的底蕴,并且证明了白人一旦失去特权,便无种族优越可言。菲利浦斯1987年发表的旅游散文集《欧洲部落》分析了当前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历史根源。在他看来,欧洲大陆不是人类文明和人道主义的摇篮,而是剥削压迫的渊薮。在《渡河》(1993)这部作品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辈分人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揭示了被掠夺、被奴役黑人的血泪史。昂斯沃思1992年出版的《神圣的饥饿》也是一部重写历史的小说,揭露了奴隶贩卖的丑恶历史。同时,这部作品证明,当代英语小说已经拓宽视野,愿意涉及公众行为的私人后果,并且与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相结合,重写历史并对以往的历史作深刻的反省。
(五) 寓言体叙述
寓言体叙述是后殖民文学叙述的常见方式。詹姆逊曾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民族寓言的观点。他列举现代中国文学中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为例说明了“民族寓言”所表现出的第三世界民族被剥削、受压迫的真实境遇。寓言体叙述不仅反映了作者所生活的殖民地人民被压迫的境遇,也体现着作者对处于边缘状态中个体的关注,对中心压迫的强烈反叛。
对流散作家而言,采用寓言体叙述是一种他们常用的文本叙述方式。奥克利的代表作《饥饿之路》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生死之间轮回的幽灵儿童“阿比库”,是一个隐喻。它象征着非洲各国不断产生又一再夭折的对于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期望。《等待野蛮人》 是库切的第三部小说,故事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像是一篇寓言,讲述了可能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国家的故事。拉什迪第二部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们》也是用寓言的形式,通过萨利姆和湿婆的故事来审视印度的命运,试图证明印度教关于“末世”的宿命观,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
(六) 对殖民的反抗
人类理性对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一直非常自信。但是实践证明,文明在有人性的人手里可以促进其进步,而在邪恶人的那里则会变成野蛮的工具。在部分英国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警示:人类应该对自己创造的文明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自大。当强者趾高气扬地站在文明的土丘上颐指气使时,弱者必然会对他进行必须的、忍无可忍的反抗,让强者清醒一下,低下脑袋。暴力便是这种反抗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在库切的多部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对暴力中的人性缺失的失望①关于库切小说中以暴力形式对殖民的反抗参见王宁教授2006年指导的王敬慧的博士论文《永远的异乡客》,其中对库切多部作品中的暴力反抗有详细的论述。鉴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再赘述。。另外,在库切的小说中,读者明显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努力塑造一种独特的非洲精神,编织一个和西方神话迥异的非洲神话。作为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抵抗,非洲后殖民文学往往表现出一种制造神话的热望,以非洲古老传说为基础运用想象力创造性地修复出一个古老的非洲神话。制造这种神话不仅出于心理上一种自然的、直觉的、追忆过去的要求,也不仅出于一种对群体归属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用以对抗白人殖民者以他们的话语编织的非洲神话[2]。
翁达杰1992年的小说《英国病人》小说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立场。翁达杰本人也有很强的反殖民主义意识。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大多数历史著作将那场战争描写为白人之间的战争,有意忽视亚洲人的贡献。我对此很反感。实际上,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反对压迫的意识也非常强烈。例如,《我饮雨水》以马来亚为背景,《年轻的山》以尼泊尔为背景,记述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亚洲地区激烈的矛盾冲突。《四副面孔》则具有强烈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另一位华裔作家提摩西·莫198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糖醋》中借书中华人的眼光来打量、评估白人。这些白人都没有姓名,用广东话称之为“番鬼佬”、“番鬼婆”、“番鬼妹”之类,同样表现出了对殖民中心的一种反抗意识。
(七) 反传统
流散作家奈保尔说:“我阅读过的所有小说,都描写安居乐业、井然有序的社会。如果使用这种社会所创造的文学形式,来描绘我自己看到的污秽不堪、杂乱无序、浅薄愚昧的社会,我总感觉有点儿虚假。”因此,他在努力寻找适合于反映他那个社会的文学形式。《达到者之谜》是他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的例子。或许奈保尔觉得对此还不满意。他在1994年推出的《世界上的道路》让评论界感到困惑,因为它既非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亦非历史、自传、游记或回忆录。实际上它包含了上述各种因素,这就是后殖民作家挑战、颠覆欧洲文学传统的一种策略。
作为流散文学和后殖民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品,拉什迪《午夜的孩子》应和了西方后现代所谓的开放的、不确定文本的说法。它表现的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将历史变成了脱离中心、四处流散的碎片,它具有历史性宏大叙事的表象特征,同时又使尼赫鲁、甘地等人的“自传”性宏大叙事破碎了,随着殖民帝国的崩溃,一切历史的或官方的关于真理或真实的权威说法也随之崩溃[8]。
库切的第二部小说《内陆深处》主人公玛格坦在日记中所书写的南非,也可以看成是对18世纪英国白人文学传统中的非洲田园诗形象的颠覆。库切的第五部小说《福》是作者对欧洲18世纪流浪汉小说的戏仿,也是对欧洲文学传统颠覆的很好的例证。翁达杰1970年出版的《小子比利作品选集》是一本奇特的书。它打破了文学体裁的界线,把诗歌、散文、照片组合成小说,运用意识流艺术手法,剖析了用左手打枪的美国19世纪草莽英雄小子比利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
(八) 探索人类文明之旅
在当今世界,先进的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代言人,与之相比,东方的国度变成了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国度。西方世界以长者自居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这种高傲的姿态长久以来一直伤害着在物质文明上欠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东方世界虽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缓慢,相对比西方世界,它们拥有着更悠久的历史、神秘的宗教和完整的处世哲学体系,这使得它们安于现状,鄙视异族势力、洁身自好,不与西方世界走同样的道路,东方世界的行为难免有些顾影自怜,不思进取。
后殖民文学“教父”、流散作家拉什迪在他的文学评论集《想象中的故国》(1991)中反对种族隔离的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反对地域上的人为障碍,反对文化宗教的褊狭心理和唯我独尊。他的作品“赞颂弘扬混血杂交、不纯粹、混合形式,以及由于人类、文化、观念、政治、音乐歌曲意外的重新组合而衍发的演变”, 探索人类文明之旅。
流散文学的迅速发展,标志着盎格—撒克逊民族唯我独尊文化垄断地位的失落,以及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这种文化多元现象已经成为21世纪英联邦文学发展的显著趋势之一。
当代英国流散作家用英语写作,但他们已在这语言中注入了本民族的色彩和韵味,从而改铸了这种语言。作为少数民族移民,要在一个以白人为主流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殊属不易,必然要经历一番极其艰苦的奋斗拼搏。因此,这些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和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心态。流散作家都熟悉英国文化传统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双边甚至多边文化综合的优势。在不同的文化夹缝中生存,他们在保存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有借鉴、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杂糅现象。流散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们站在本民族的立场,收回了自我阐释权,用自己“未经过滤”的声音,来描述本民族的生活,用文本的形式来演绎被歪曲的历史并表现出明显的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是通过使用寓言体的叙述形式和对欧洲传统的颠覆表现的。同时,作为严肃作家,流散作家在重写历史、颠覆传统、反抗殖民的同时还表现出对人类共同命运与未来的关注,表现出探索人类文明之旅的努力。
[1] 刘洪一. 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 机理及联结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2).
[2] 王敬慧.永远的异乡客[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6.
[3] 陈茂林. 新世纪西方文论展望: 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 [J]. 学术交流, 2003,(4).
[4] 梅晓云. 文化无根——以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 [D].西安: 西北大学, 2003.
[5] 任一鸣. 构筑后殖民文学的神话——J. M. 库切的小说艺术 [J].社会观察, 2003,(4).
[6] 杨金才. 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 [J] . 当代外国文学, 2008 ,(4).
[7]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k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1999.
[8] 石海军. 故事与历史:“流散”的拉什迪 [J]. 东方丛刊, 2006(4).
责任编辑:冯济平
Diasporic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Post-Colonialist Writers
YANG Xiao-hong LI Sheng-w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
Contemporary writers from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write with English. These post-colonial writers are all familiar with British and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ossess bilateral or even multilateral cultural advantages. With stro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y depict their national lives from their national viewpoints. They show the distorted histories through their texts, expressing clear consciousness against colonialism, which is conveyed through allegoric narratives and anti-European literary traditions. Meanwhile, they also show great concern about the common fate and future of human beings, expressing their efforts to explore human cultures.
globalization; diaspora; diasporic writing; post-colonialism; cultural studies
I106
A
1005-7110(2013)04-0091-06
2013-03-05
杨晓红(1976-),女,重庆彭水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讲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与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李升炜(1978-),男, 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英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