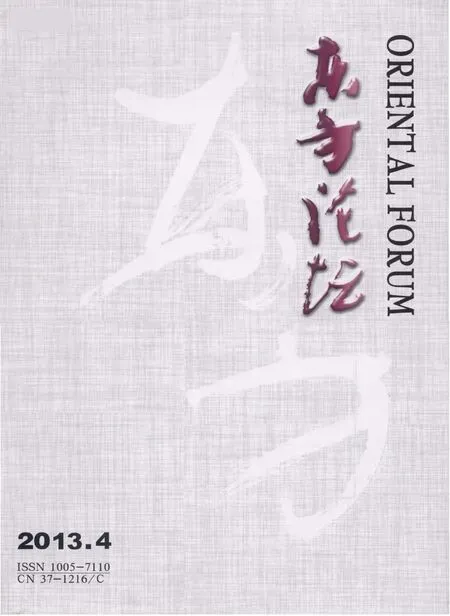网络穿越小说:当代文化镜像的反讽性文本
李盛涛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网络穿越小说:当代文化镜像的反讽性文本
李盛涛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网络穿越小说是最具有网络文学特征的小说类型,它以现实的缺席作为结构文本的潜在性小说要素,主要从两个方面与当代社会构成了反讽关系:一是作品文本层面生活景观的史诗性与戏剧性和当代实存层面的散文化生活景观构成了反讽关系,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匮乏与欠然状态;二是穿越主人公的高大完美与当代主体性的悲剧性处境构成了反讽性关系,动摇了传统的小说创作理论。这使得网络穿越小说有着潜在的文化建构功能。
网络;穿越小说;文化镜像;语境反讽;文化建构
可以说,网络穿越小说是最具有网络文学特征的小说类型,它动辄以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天马行空的想象与非凡的故事情节构造而不同于传统的小说。不管是有着蛛丝马迹的历史碎片,还是子虚乌有的纯粹虚构,网络穿越小说无不以现实的缺席作为结构文本的潜在性小说要素。因而,网络穿越小说可视为当代文化镜像的反讽性文本,体现了对当代文化重建的一种思考和努力。
一、对当代社会散文式生活景观的反讽
在网络穿越小说中,遥远的历史空间(甚至是纯属虚构的历史空间)、匪夷所思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形象都使文本中的生活图景与当代散文式生活景观相去甚远,因而有着强烈的现实反讽意义。
首先,这种反讽体现在小说中生活景观的史诗性上,这种史诗性体现了网络穿越小说结构的宏观性特点。穿越小说主人公往往因偶然事故(科学实验、车祸、昏迷或死亡)而进行穿越,而穿越后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甚至推动了历史进展。男性穿越主人公常涉足宫廷权力斗争或是朝代更迭,如项少龙(《寻秦记》)、林晚荣(《极品家丁》)等。而女性穿越主人公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宫廷内闱,她们不仅卷入宫廷的权力斗争之中,亦陷入自己的情感纠结之中,如花木槿(《木槿花西月锦绣》)、小薇(《梦回大清》)、慈禧(《末世红颜》)等。所有这些人物的人生历程都使网络穿越小说极具有史诗性。当然,这种“史诗性”不同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史诗性。五四以来,小说的史诗性多指涉长篇小说,既强调社会史实与历史精神之真,又强调艺术之美。但对网络穿越小说而言,由于小说所写的历史空间是虚构的,甚至是子虚乌有的,它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学者这样认为两者的区别:“与传统历史叙事不同的是,这种叙事并不是要顺向地重述或转述某段历史撰述(历史记载、家族记忆、民间传说、考古发现、文物凭证等),也不是逆向地思辨历史的有无、对错及叙事本质,而是在既定的历史记忆基础上,人为地增加历史变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历史推理,使历史在叙事者的观念引导下戏剧性地虚拟演进。它的叙事对象建立在已有的历史撰述上,但此时的历史撰述却是作为被影响和被改变的对象而存在。”[1](P77)但也不尽然,有的网络穿越小说并未完全建立在已有的历史撰述之上,如《极品家丁》便是纯属虚构之作。严格地说,两者的区别在于:传统历史叙事重史实之真,网络穿越小说重当代精神之真。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历史”只是一个空洞的外壳,重在演绎一种“民族精神”或“人类精神”,即穿越主人公身上的那种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创造历史的人类精神。于是,网络作者站在当代精神与文化的制高点来俯瞰历史,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任意择取古今中外之事进行叙事,使网络穿越小说宛如一个“时空浓缩”的文本,让读者在极富传奇性的文本中感受着一种创世纪般的冲动。
其次,这种反讽还体现在小说中生活景观的戏剧性上,这种戏剧性体现了叙事的局部性特色,增强了文本的阅读效果。禹岩的《极品家丁》极具有代表性。该作品约三百万字,在情节构造、场景设计、人物刻画和细节安排上,都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如有几处作者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古人所用的“消闲之笔”,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提出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的技法,使本来略显单调的叙事节凑突生变化,充满情趣。如在380章《摸错了》一节中,写林晚荣到济宁侦查官府丢失的官银时,遇到了朝思暮想的洛凝,晚上幽会洛凝,却错进了军师徐芷晴的房间;在419章《我要和你师姐睡觉》中,当林晚荣把阔别几月、朝思暮想的肖青璇接回家准备就寝时,却遇到了不谙男女之事、赖在肖青璇床上不走的小师妹李香君;第268、269两章,写萧玉霜因姐姐怠慢林晚荣离家出走,心急的林晚荣找到栖霞寺,没看到萧玉霜,而是先看到了跪在菩萨面前表白心迹的萧玉若,然后才看到了萧玉霜。……所有这些都使平淡的生活情节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也为人物的关系增加了许多变数,更有力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可谓“一石多鸟”。当然,作者增加戏剧性的因素很多,此处不逐一枚举。戏剧性的主要动力来自穿越主人公的现代认知水平、当代文化个性同古典环境与古典文化人格的历史性差距。对于当代人来说,一件平常不过的举动在古代环境中却能引起酣然大波,而古代最平常不过的举动却在穿越后的当代人心理掀起波澜。可以说,网络穿越小说中戏剧性的构成,使作品产生了强有力的阅读效果。
在叙事的故事层面,网络穿越小说与当下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关系。就小说叙事的“故事”而言,它实际涉及实存形态的“生活景观”与文本形态的“生活景观”两个方面。前者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各种事件的无焦点性、共时性和并存性,在时间形态上表现为每个事件都沿着自己的时间轨迹向前发展,呈现为一种杂态的、无序的、无中心的网状结构;后者是被结构的、有序的、存在聚焦的意义事件。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但它们的关系是考量文学作品与现实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且对文本的形成、形态与意义构成非常重要,通常所谓的“真实性”、“写实性”皆源于此。而当代实存的生活景观具有非史诗性,这种生活状态被德路兹和瓜塔里认为当代是个“散文时代”:“人们已越来越无法忍受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灰色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散文的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规范体的、被剥光了的宇宙里……”[2](P281)因而,人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必然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匮乏和欠然状态。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史诗性的生活建构让读者从主人公身上获得了一种阅读补偿,如在《末世朱颜》中,穿越后成为慈禧的主人公后改变了现有正史和野史中的所有“慈禧”形象,写她为圆明园立耻辱碑、对同治皇帝实行现代教育、卖给美国人武器、建造汽轮装甲船等。这种个人与民族的密切关系,既使个体人生具有了某种崇高感和神圣性,亦使民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召唤性。从而,这种生活包含某种终极意义的东西,而这恰是当代散文化的社会所缺少的。网络穿越小说对这种终极性意义的书写恰恰反讽性地彰显了当代社会精神中的欠然状态。当代社会精神的匮乏已是个全球性的事件,难怪尼采痛言:“精神在从前是上帝,之后变成了人,如今则变成了乌合之众。”[3](P3)
二、主体文化人格溃败感的反讽
在网络穿越小说中,主人公高大而近乎完美。男主人公往往文武双全,建奇功,立伟业;女主人公往往才貌双全,亦能在穿越后的历史时空有所建树。即便个别主人公看上去不够完美,反而更具有一种悲壮性,如《木槿花西月锦绣》中花木槿。花木槿起先爱上了原非钰,却又被原非白所深爱;当它移情爱上原非白时,却被段月容所掠并失身于他;当它为了生存与段月容假扮夫妻亡命天涯时,尽管世人都认为曾痴情于原非白的华西夫人花木槿已跟随了恶魔般的段月容,但她依然坚守着她的清白;逃难途中,还先后被太守张之严和二哥宋明磊所劫,但仍守身如玉;……所有的人生遭际和情感纠葛都使花木槿具有人生的传奇性和性格的深渊性,使她在精神层面获得了一种完美和崇高感。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完美形象通过人物的关系集中体现出来,即“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模式。在文化层面,这种模式可视为对当代社会“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模式的想象性突破,却没有当代婚外偷情模式中的迷乱与堕落。它又不同于古代文学想象中的“三妻四妾”模式,在传统文学中,人物关系往往被想象为争风吃醋或倾轧陷害(苏童的《妻妾成群》),而穿越主人公则凭一己之魅力令“众男”或“众女”倾倒并能和睦相处,这在男性穿越主人公身上表现尤甚。因而,穿越主人公的这种爱情模式是当代人的本我在穿越各种道德屏障后的最浪漫的想象表达。
尽管穿越主人在穿越前是凡俗之辈,甚至处境尴尬,如身为特种士兵却受排挤的项少龙(《寻秦记》)、出发归来碰到丈夫偷情遇到车祸的孟颖(《木槿花西月锦绣》)等形象,但在穿越后却无所不能。如《极品家丁》中林晚荣通过制造香水、肥皂、女性内衣让萧家在金陵取得商业的成功,运用水的浮力捞起了湖中藏匿的官银,根据现代记忆中的丝绸之路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沙漠奇袭突厥王庭等行为。从中可看出穿越主人公制胜的诀窍:现代知识、技能和人格在历史语境中的非对称性操演。主人公以强大的生存优势存在于某一虚构的历史时空中,他的胜利就是当代对历史的胜利,是科技对人文的胜利。
穿越小说主人公不论在现实意义、美学意义或文学性上,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首先在现实意义上,现实人生和穿越人生构成了绝妙的互文关系。主人公穿越前表现凡俗,在穿越后却是非富即贵且惊天动地,这可视为当代草根族文学上的“黄粱梦”。在深层次上,当代人缺乏深刻的文化反抗意识和伟大的文化创新精神。当代主体陷入了一种沦陷或堕落状态,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甚至悲观地认为当代主体连异化的机会也没有了:“异化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且异化现在已经是一个极为奢侈的享受,因为异化还可以让主体想象自己还可能与原来的样子有所不同。可是,现在,异化已经完全屈从于‘个性身份认同逻辑’(identity logic):千禧年时期的主体已经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它只能通过个体间的差异而不是通过本质上的极端的他者性(otherness)来跟其他主体发生联系。”[4](P115)因而,当代历史主体很难承担起反抗与创新的重任。而且,当今所有值得文化反抗的东西都被各种方式掩盖了起来:体制不能反抗,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禁区;命运不能反抗,因为它已被科学理性界定为子虚乌有的东西。可见,当代社会是个不需要悲剧的时代,“确实,随着现代的开始,政治基本上不再为悲剧提供合适的内容。悲剧不再是封建或专制主义英勇、壮观的要素,而变成不流血和官僚化的,是一个关乎委员会而非骑士制度、关乎化学战争而非十字军东征的问题。”[5](P101)作为悲剧匮乏的“后悲剧时代”,种种可能的文化反抗命定是孱弱的,仅停留在学理层面。而在网络穿越小说中,主人公获得了一个强大的主体形象。在哲学意义上,穿越主人公似乎无意中反拨了后现代哲学中的悲剧性主体,而体现着现代哲学意义上主体的强大性。所以,网络穿越小说主人公在古典语境中的非凡成就,曲折地暗示了当代生存环境的非人化以及与主体的异质性关系。因而,从这种意义上看,网络穿越小说是对现实凡俗人生的补偿性表达,是当代人的文学白日梦,是一次文学上的达人秀。
在人物塑造上,穿越主人公对传统小说人物塑造的艺术规范造成了冲击。传统小说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认为性格是本体性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而穿越主人公并非如此,他(她)的性格表现是语境性的,说白了就是其现代文化人格同古典文化语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在较为保守的古典历史环境中,具有现代文化人格的主人公身处其中,只需保持本色不变,便能获得一个特立独行的形象。因而,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本色的,而是时空错位造成的,是语境性的。因此,人物形象不仅获得了外在于性格的叛逆性和文化反抗的功能,也获得了突出的戏剧性。因而,在网络穿越小说中,穿越主人公与传统人物的关系,是一种文化人格与本初性人格的关系问题,是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传统人物在穿越人物身上得到的是对理性与智慧的崇拜与迷恋,而穿越人物从历史人物身上得到的是人性的淳厚与美善。这种人物性格与人性的互补与弥合隐含地表达了作者对当代文化人格建构的思索。
三、潜在的文化重建行为
既然网络穿越小说与现实构成了一种反讽关系,它必然对现实发挥着某种文化功能。
首先,越界行为体现了对当代生存困境甚至人类生存困境的超越。现实生存的困境给人们带来的局限性往往是巨大的,是个体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无法克服和逾越的。这种局限性是多面的,有心理层面的,有文化层面的,也有时空层面的。其中,生存时空的限制尤甚,甚至以人类毋庸置疑的方式存在着。然而,人类的本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意味着自由,是主体对自由的向往,正如伊格尔顿所语:“主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像一个流亡君主一样,它没有真正的王国可以统治。”[5](P229)于是,禁锢与自由、疆界与穿越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生存永恒的动力。穿越行为在两个方面对现有的文化规范进行了颠覆。
一方面穿越行为是对传统时空观念的颠覆。在现有时空观念中,人们坚信生存的时间维度具有不可逆性,坚信生存的空间维度具有不可选择的唯一性。而这种时间的线性关系和空间的唯一性就构成了人们对现有时空观的经验性认识,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大局限。而穿越小说的文学想象打破了这一生存困境,认为时间可以逆行,认为人可以两世为人。在网络穿越小说中,人可以像穿越空间一样自由地穿越时间,这就使传统的时间观念具有了某些空间性的特征。D·哈维将这种时空的变化称为“时空浓缩”:“时空浓缩这个概念暗示着使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属性发生变革的那些进步,变革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改变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有时采用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采用浓缩这个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以生活节奏的加快为标志,空间障碍被大大克服,以至有时觉得世界向内倾塌在我们身上。”[6](P312)网络小说中的“穿越”具有后现代时空观的影子,但似乎比之更大胆、更激进,也暗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念,表达了对人与宇宙关系的重新思索和定位。
另一方面,穿越行为也可看作是当代人对死亡观的文学阐释。死亡是不是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人们对死亡既满怀好奇,又充满困惑。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死亡意味着经验的空缺和断裂,使得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不论是从个体经验层面还是从哲学层面都是一个令人类永远困惑的未知之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死亡不仅是一个人不能不猜的谜,一个人若不猜或猜不着便会因此失去生命(像一些底比斯人那样被斯芬克斯吃掉)的谜,而且又是一个永远让人猜不透的谜,一个永远摆在人的面前、至死都困扰着人的头脑的谜,一个只要你活着,你就得不停地把它猜下去的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越来越深的层面猜度死亡之谜的历史。”[7](P5)因而,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到海德格尔,从中国的老子到当代哲学家,都对死亡做出了不同的阐释。然而,网络穿越小说却以自己的方式十分形象地对“灵魂不死”说法进行了文学性的阐释。其中,天夕紫紫的《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写得最具有戏剧性,主人公先后进行了三次穿越,且穿越后的情况各不相同。第一次穿越后的身份是康熙皇帝的启蒙教养姑姑苏嬷嬷,记忆是当代人“叶茉儿”的,肉体却是古代人苏嬷嬷的,主人公穿越后被皇帝康熙深爱着。第一次穿越结束是因生阿哥大出血而死,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医院里躺了两个小时。第二次穿越是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龙钦寺,在一个活佛的帮助下进行了穿越。这次穿越后竟是上次离别的十年之后。这次主人公既有着当代的记忆也有前次穿越的记忆,而身体又是当代自己的,因而穿越后年青美貌的主人公更赢得了康熙的爱。第二次穿越结束是因为自己以为康熙遇刺而死,于是殉身自杀。第三次穿越是主人公阳寿已尽,在阴间孟婆的帮助下把康熙的阳寿续十年给主人公后又穿越复活了。而这次穿越后主人公的意识完全停留在当代,失去了前两次穿越的记忆,康熙认定她不是自己以前深爱的茉儿。最后主人公的记忆慢慢恢复又赢得了康熙的爱。因三次穿越后的情况各不相同,使人物之间的关系、情节设置和走向发生微变、突变甚至逆转,这使得叙事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更奇妙的是,当穿越后的主人公最终寿终正寝后,又在当代复活了,而康熙也追随着自己穿越到了当代,演绎了一段跨世之恋。可以说,穿越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越界冲动的方式表达了当代人对死亡这一生存局限的想象性的客服与超越。
其次,越界行为表现了现实与历史的一种互文性关系。穿越行为作为情节要素并非网络小说独有,在中国传统小说已存在,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中。《红楼梦》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也经历了穿越行为,从仙界穿越到凡间,但主人公在穿越后都忘记了前世,穿越后和所穿越的世界处于同一个认知水平。而网络穿越小说不同,穿越后仍带着前世的清醒记忆和认知水平。因而,穿越主人公实际上是作为当今世界的文化代言人而出现在虚拟的古典历史语境中的。可以说,在网络穿越小说中,作者对于历史的想象以及对主人公形象的设置,都体现了作者当下生存境遇中对未来想象的历史性的移植,使网络穿越小说文本成为作者当下生存意向在历史化语境中的成功操演,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耶尔恩·吕森所语:“今天,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主要是以对未来远景进行批判的形式中造就的。”[8](P194)因而,穿越主人公与传统历史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两个历史时代的错综复杂的互文性关系。
这种互文关系改变了传统文学中历史因素和当代因素的功能性关系。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使历史一直以来成为中国文学的精神土壤,为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资源。在作品中,历史因素往往是作品中的审美想象空间和精神增长点,它构成了人物的文化底蕴,构成了情节的演化,也融入了对主题的构造之中。同样,穿越小说再次证明了历史时空是一个能量巨大的审美形象空间,再一次为文学展示了它的魅力和神奇性。但网络穿越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在传统作品中,历史因素往往成为文本的参照性因素被作者通过古今对比而抒“借古讽今”之意;但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当代因素成为作品主要的结构性要素,“历史”只是一个貌似陈旧的文学容器,里面承载着对历史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而在传统的历史性小说中,“历史”只是作为一个人类经验的符号,为文学的当下性思索提供智力支持。因而,当代和历史的关系,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得到了新的阐释,也是今人与古人在文学想象中的一次亲密的接触。
总之,网络穿越小说通过对当代散文式生活景观和当代主体文化溃败感的反讽,隐含地表达了对当代社会欠然性的思索。穿越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对历史的能动创造性以及对历史和当今关系的重新思索,对当代文化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 许道军, 张永禄. 论网络历史小说的架空叙事[J]. 当代文坛, 2011,(1).
[2]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陈清侨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3] 尼采. 戚仁译. 上帝死了——尼采文选[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4] 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 鲍德里亚与千禧年[M]. 王文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英)特里·伊格尔顿.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 方杰方宸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 乔治·拉伦. 文化身份、全球化与历史[A]. 包亚明主编. 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7] 段德智. 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8] 埃娃·多曼斯卡. 邂逅: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 彭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冯济平
NetworkT ime-travel Novels: the Ironical Tex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Image
LI Sheng-tao
( Chinese Dept, Bingzhou University, Bingzhou 256600, China )
Time-travel novels on the Internet are the genre of novels with the most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literature. They regard the absence of reality as the potential fictional element of the structural text, and establish the ironical relationship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y from two aspects. The epic and dramatic features of the life landscape reflected by the text form an irony with the prose-styled life landscape. The perfection of the tall time-travelers form an irony with the tragic p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counterparts. This endows the network time-travel novels with a fun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twork; time-travel novel; cultural image; contextual irony; cultural construction
I207
A
1005-7110(2013)04-0086-05
2013-03-26
李盛涛(1972-)男,山东滨州人,滨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网络文学。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态视野中的网络小说叙事研究”(11CZW074);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09YJC751008)“网络小说的生态性文学图景”;滨州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网络小说的生态性叙事”(bzxy0904);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十二五”重点学科“文化生态学”建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