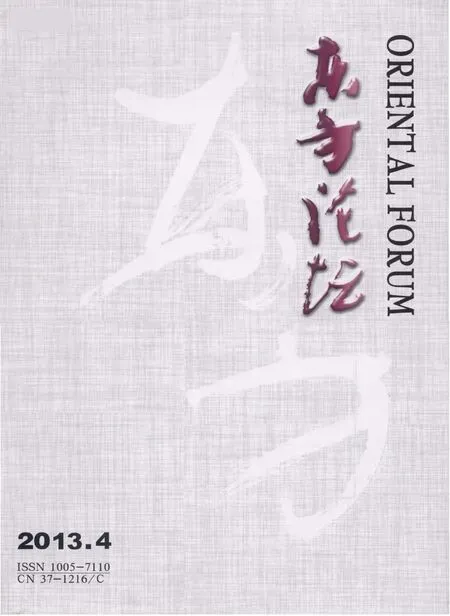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孙立涛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孙立涛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我国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其兴盛原因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汉代;谣谚;兴盛;传承;政策;精神
我国谣谚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兴起应在文字产生之前。先秦时期,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很多谣谚作品亦见载于各类典籍中。汉代继承了这一趋势,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谣谚文化的盛世。汉代谣谚不仅数量多、类别多,而且涵盖时间长、地域广。汉代出现谣谚文化的繁盛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谣谚艺术本身、官方相关政策、民众对其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一、谣谚文化在民众间的自发传承
汉代谣谚文化直接承前世而来。从具体的文化作品上来说,有传承,则不可避免遗漏。尤其像谣谚这种主要靠口耳相传的艺术,遗失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是新作品、新特点不断涌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前世文化对后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谣谚文化从先秦到汉代是一个怎样的传承方式呢?下面具体来分析。
(一)具体谣谚作品的传承
谣谚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口头文学,其流传方式主要是民众间的自发传播。因缺少文人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具体的谣谚作品即会渐渐亡佚。尤其是那些时事谣谚,主要反映一时一地的情况,时过境迁,这些作品也就失去了魅力所在。
但是,随着文人文学及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与政治事件相关的歌谣作品,开始记录在了典籍中,并一直传至汉代。如周宣王时的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郑语》),到了汉代,在《史记·周本纪》、《汉书·五行志》、刘向《列女传》 中都有传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载师已引文武之世童谣:“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鸲鹆跦跦……”,在《史记·鲁世家》、《汉书·五行志》中也有引录。此外,还有一些前世的歌谣作品,首次见载于汉代的典籍中。如春秋时期晋惠公时童谣:“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记录在《史记·晋世家》、《汉书·五行志》中;战国时期赵国百姓间流传的童谣:“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上生毛”,记录在《史记·赵世家》、《风俗通·黄霸篇》中;楚人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记录在《史记·项羽本纪》、《风俗通·王霸篇》中,等等。从此类情况中,更可以看出谣谚文化善于口耳流传的特性以及在自发传播过程中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能够在历史中保持着长久传承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哲理性和长期应用性的谚语。它们往往形式短小、琅琅上口、易于记忆,更有利于口耳相传。所以我们能看到更为久远的谚语,如《国语》、《左传》、《孟子》、《韩非子》、《战国策》等典籍中保存下来多首先秦时期的谚语作品。其中像《孟子·梁惠王篇下》晏子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羽父引周谚:“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春秋左传·桓公十年》虞叔引周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等等,都是流传更为久远的谚语。到了汉代,人们从这些典籍中,同样能窥测到这些谚语所反映的信息。当然,这些谚语虽被记录于书面中,但不一定只是靠文字来传播的,也很有可能会是靠口耳相传流至汉代的。首次见载于汉代典籍中的前世谚语,如周谚“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见于《新书·容经篇》),周谚“囊漏贮中”(见于《新书·春秋篇》)等,这些就很可能是靠口耳相传流至汉代的作品,到了汉代得到文人的记录。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很多谣谚作品,都流传到了汉代。这是我们从典籍考察中,直接看到的情况。具体到实际中,因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可获知,但可以想象,民间口耳相传流传至汉代的谣谚作品应该更多。这些作品在汉代的传播,不仅直接丰富了汉代社会谣谚文化的内容,而且为汉人创作新的谣谚作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样式。
(二)谣谚艺术形式的传承
谣谚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谣谚作品本身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谣谚这一艺术形式上的传承。一个具体的作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是渐渐亡佚了,或是渐渐失去了继续流传的可能。但某些谣谚的艺术形式,包括其中运用的艺术手法,在民众心中会永保活力。人们受其影响或启发,会创作出越来越多的谣谚作品。
谣谚在其简洁的体式内,其创作一直保持着灵活多样的句式与结构。考察汉代谣谚的形式、风格及艺术特征,其中一些与周秦时期几乎没有区别。从句式上看,从一句一首、二句一首,到多句一首皆有。先秦时期一句一首的短谚有:“狼子野心”(《春秋左传·宣公四年》)、“老将知而耄及之”(《春秋左传·昭公元年》)、“臣一主二”(《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等。而汉代则有:“利令智昏”(《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赞》)、“欲投鼠而忌器”(《汉书·贾谊传》)、“盗不过五女门”(《后汉书·陈蕃传》)等。谣谚作品中较多的四言二句体,先秦时期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春秋左传·桓公七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春秋左传·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春秋左传·昭公三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等等。而汉代则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史记·白起王翦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传》)、“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汉书·薛宣传》)、“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后汉书·曹褒传》),等等。其他三言体至多言体,相似的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句式与结构的多样性,使谣谚创作更显得灵活有趣,人们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也往往会刻意追求作品的形式美、韵律美,以便使作品更具感染力。从上面涉及的谣谚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偶、对仗、押韵等手法应用非常普遍。人们在刻意追求着这些相似的东西,所以谣谚的创作在保持着语言简洁、短小精悍、指意明确这些总体性特征的同时,随着创作过程的继续发展,逐渐表现出趋同模式的创作倾向。还是从句式上看,先秦时期即有模式相同的谣谚作品:“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春秋左传·闵公元年》)、“心则不兢,何惮于病”(《春秋左传·僖公七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礼记·缁衣》)。而到了汉代,谣谚创作除前面提到的多用对称、对偶的创作结构外,像“前有赵张,后有三王”(《汉书·王吉传》)、“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前有管鲍,后有庆廉”(《后汉书·廉范传》),“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史记·酷吏传》)、“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汉书·酷吏严延年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汉书·王莽传》)等,这种“前有……,后有……”、“宁……,无(不)……”的具体创作结构和“道德彬彬,冯仲文”(《后汉书·冯衍传》)、“问事不休,贾长头”(《后汉书·贾逵传》)、“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五经从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传》)之类表现出的语言惯性传承等,逐渐在人们心中形成共同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风气使谣谚的创作表现出大众化的特征,更能为时人所理解、所接受。
形式上的传承,也使得某些艺术特征继续保留在固定的样式上,为汉人的继续创作提供了便利。除以上叙述外,汉代谣谚艺术在其他方面也与先秦有着很多的相似。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廖传》),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援列传》)的记载。可见,汉代人不仅在谣谚作品的形式上借鉴了前世,而且在社会意识或社会心理上,也与前世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三)社会心理的传承
社会心理,是在民众社会生活中,因自然现象、社会情景或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人们之间潜移默化演进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和普遍的心理倾向。具体到谣谚文化上来看,人们普遍地用谣谚艺术抒发情感、发表看法、总结经验等,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期民众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心理作用。
某些谣谚作品之所以具有流传的“市场”所在,也正是因为作品的内容或功能适应了一段时期的社会心理。如果再具体一点的话,我们从具有预测性功能的谶谣(或曰童谣)上更容易看出社会心理的形成对谣谚文化的影响作用。历代谶谣的兴盛不衰,正是我国早期神秘文化在各个时期社会心理上影响的结果。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这种社会心理已经普遍形成。从周秦时期一些谶谣的创作中可以得到直接的证明。如《国语·郑语》 载周宣王之时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这是周宣王时期一则预言西周灭亡的童谣;《史记·晋世家》载儿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这则儿谣预言晋惠公必将衰落,要振兴晋国,只有晋文公登位。《春秋左传·僖公五年》载卜偃引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这是春秋时期,预测晋国必灭虢国的一则童谣。这些预言能为当时人所接受并产生“震慑”作用,可见谶谣在当时已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做基础。
从对谶谣的具体应用上来看,秦末大起义的发起者陈胜、吴广利用谶谣发动群众,半夜篝火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迁在书中详细揭示了这一伪作谣谚的过程、动机。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与此相似。《论衡·卷二十六·实知篇》载孔子将死,遗下谶书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1](P1069)预示了秦始皇将死于沙丘。孔子虽被称之为圣人,也不可能具有预知未来的“神力”,明显是后人的伪作。又如,《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师已引文武之世童谣:“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鸲鹆跦跦……。”这则童谣预示着鲁国将会发生灾难,鲁昭公攻打季氏将会失败出逃,鲁定公继位。这则童谣出现时间比较早(文武之世),预示事情的应验却很晚(春秋时期),可见比附成分更大。
拿汉代谶谣与周秦时期谶谣相比来看,二者本也无异。谶谣与国家政治、政权、国运紧密相连,具有“极强的预示效果”,充满着一定的神秘色彩。再往前推,谶谣应与原始的卜筮、巫术文化有关。从此类谣谚作品上也可以看出,在周秦时期谣谚艺术并不仅仅是在下层民众中创作、传播。一些谶谣,具有整齐的句式,从用词、造语及所反映内容上看,明显是文人化的作品。①这里涉及到一些作品的真伪问题,关于先秦时期部分歌谣的真伪,可参考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汉代某些政治家、阴谋家为某个政治目的也比附或伪作了很多的谶谣。举例来看,《汉书·五行志二》载元帝时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这则童谣的意思是:“井水溢出,浇灭了灶里的烟火,灌进了殿堂,流进了金门。”成帝继位后,果然有童谣里出现的现象,北宫中井泉稍向上溢出南流。于是便有人揭示它的预兆:井水象征着阴,灶烟象征着阳,玉堂、金门象征着黄帝的至尊之居,井水灌进玉堂也就是阴盛而灭阳,有臣下要篡位,占据宫室,并以此比附王莽篡位。又如《汉书·五行志二》记载成帝时的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从字面意义上看,这则童谣是对进谗言的邪佞之人的诅咒,对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同情。但也被人解释为预言:“桂,赤色,汉家象。华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头也”。同样被认为是汉室衰落、王莽篡权的征兆。与这两首谶谣相似的还有很多,如成帝时童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汉书·五行志中》),用来预言赵飞燕姊妹的后果;王莽末谶谣:“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宋书·符瑞志上》),用来预言刘秀将做天子;更始时期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汉书·五行志一》),用来预测更始政权覆灭,刘秀政权将建立;公孙述割据称帝时期蜀中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后汉书·公孙述传》),用来预兆汉朝的复兴;灵帝末年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后汉书·五行志一》),用来预测东汉末大动乱。
以此可以看出,汉代不仅在谶谣称谓上直取周秦的“童谣”,而且也传承了周秦时期的文人、官吏比附或伪作谶谣之风。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汉代民众传承了我国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的社会心理,即神秘性观念影响下的心理。从谶谣产生时期始,就给人们的心理和思想上造成了阴影,这一阴影一直传给后世,使得后人也自发地对灵异现象产生敬畏心理。这才是谶谣继续生存壮大的土壤。
可见,一方面是具体作品的传承,直接丰富着汉代的谣谚文化内容;另一方面是艺术形式(包括艺术特征)的传承,为汉人的继续创作提供了便利;再一方面则是社会心理的传承,谣谚作品在社会流传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造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在谶谣的流传中尤能看出。这一切,为谣谚文化在汉代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谣谚文化盛世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官方相关政策对谣谚文化的影响
一个文化现象能在社会中繁荣起来,并给后世带来重大的影响,除这种文化艺术本身的魅力之外,还与一个时期国家的相关文化政策分不开。汉代谣谚文化的兴盛即与此有关。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采诗制度,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杜预注解:“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2](P929)虽然传统称法为“采诗”,但真正采集到的应多是包含“谣谚”性质的作品,因为这是“遒人”于民间之路上采得的。上面所提到杜预注中也认为是“采歌谣之言”。正是这一制度使散落全国各地的诗歌、谣谚汇聚到王庭。也许《诗经》总集的出现确实与此制度存在着不可否定的联系。通过这项以歌谣进行规劝的制度,统治者欲达到“观风俗、知得失”的目的。这项制度在给政治带来一定影响的同时,又在客观上使我国先秦诗歌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汉代多数学者都相信周代的采诗制度及其带来的政治效果,这从一些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如《礼记·王制》载: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
《孔丛子·巡守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3](P152)《汉书·食货志》载: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此外,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汉书·艺文志》、刘歆《与杨雄书》也有相似的记载。周代这一文化制度的政治功效,必定会给后世造成一定的影响。秦代已建立了乐府机构,但由于史料缺乏,这一机构的具体运作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汉代的乐府机构,则继承了周代这一文化制度,承担了“采歌谣,观风俗”的任务。《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亦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汉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是为他的政治统治服务,制作许多新的祭祀歌曲以配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但宫廷的娱乐活动则需要一些世俗之音来满足他们的享乐需求,所以汉乐府机构又仿效先秦旧制到各地采集歌谣,这在客观上也达到了“观风俗、知薄厚”的社会效果。同时,这一举措采集和保存了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歌诗作品,其中也包含一些谣谚性质的作品。这必会使得各地谣谚艺术得到发掘、保存、改制,从而扩大了传播范围,提高了影响力。
除此之外,据史载,汉武帝时期还实行有“巡行”制度。这一制度直接促成汉代官僚集团对民俗风情的重视,尤其是对民间谣谚文化的看重,这与周代的“采诗”制度更为相似。如果说汉武帝立乐府对汉代谣谚文化影响还不算大的话,那么其后汉代官方受“巡行”制度的影响,而实行的直接的谣谚文化政策,可谓使汉代谣谚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载: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
韩延寿为治理好颍川,而“略依古礼”,采取了一些深得民心的措施,其中包括“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颜师古注曰:“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4](P3210)可想而知,这种措施客观上会使得颍川之地的谣谚文化时兴一时。
《汉书·王莽传》载,王莽篡位前,为制造民意根据,派“风俗使者”到各地考察民情民俗,并伪作民间歌谣颂扬他的功德。这说明“采歌谣、观风俗”这一文化政策在当时应该非常普及,以致被政治家、阴谋家所利用。同时,这一政策客观上也定会促进谣谚作品的继续创作,尤其是文人的创作。
东汉时期,谣谚艺术更加为官方所重视,通过谣谚考查政治得失的措施得到更大的发扬,同时打开了社会各阶层共同创作谣谚的局面。《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载:
(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
这是叙述光武中兴的一段史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光武帝所采取的政治措施有“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以此了解各地的吏治情况。并且“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也就是通过谣谚对时政的反映情况而选拔黜陟官员。《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载:“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又载:“(范滂)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这里提到三府掾属举谣言,通过这一措施,范滂弹劾“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欲达到“忠臣除奸,王道以清”的政治目的。另外,《后汉书·陈蕃传》还载有三府为朱震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所谓“三府”,即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或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司马、司空、司徒”三公并列,这是汉代吏治实行的三公制,以宰相为首,职责权限极大,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由此可见,官方在以谣谚文化“治王道”的同时,还会给自己带来新鲜的创作体裁,这反过来又给时兴的谣谚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与谣谚相关的文化政策在东汉非常普及,除以上记载外,我们在典籍中还能找到很多相关证明。如《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惲列传》载:“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争臣七人,以自鉴照,考知政理,违失人心,辄改更之”;《后汉书·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载:“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又载:“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三国志·卷八·魏书八》亦载:“(公孙度)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另外,文人著述中也有所体现,如班固《两都赋》:“采游童之讙谣,第从臣之嘉颂。”可见,这一文化政策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之深。正是因为这一文化政策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汉代社会兴起了“谣谚热”,谣谚创作、传播深入人心,文人也因此大量引用谣谚进行应对或说理,谣谚艺术逐渐有了更多的社会功能。于是便有一些政治家、阴谋家利用这一文化现象和政策,伪作谣谚,欺罔世人,为自己的政绩或阴谋制造舆论,上面我们提到的王莽派遣风俗使者“诈作谣谚”即是证明。但这客观上有利于文人谣的创作与发展,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化政策给文化事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与东汉这种谣谚文化政策紧密相连的,则是汉代选拔人才实行的“察举制”、“征辟制”。这种制度在西汉到东汉初的一段时间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但随着社会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日渐严重,尤其到了东汉晚期,以致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篇》)的现象。选拔官吏中弄虚作假、结党营私,察举制、征辟制逐渐成为豪强、大族安排亲信的工具。与之相配的一个手段就是伪作谣谚,互相标榜,因为以此形成的舆论效果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声誉和前程。而被排挤在外的知识分子也会结成阵营,利用谣谚相互标榜与其对抗。从此在社会中形成了人物品评的风气,由此衍生出众多程式化的俗谣谚语。如:“间何阔,逢诸葛”(《汉书·诸葛丰传》);“欲为论,念张文”(《汉书·张禹传》);“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汉书·楼护传》);“夜半客,甄长伯”(《后汉书·彭宠传》);“五经复兴,鲁叔陵”(《后汉书·鲁丕传》);“道德彬彬,冯仲文”(《后汉书·冯衍传》);“前有管鲍,后有庆廉”(《后汉书·廉范传》);“问事不休,贾长头”(《后汉书·贾逵传》);“殿中无双,丁孝公”(《后汉书·丁鸿传》);“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五经从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传》);“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汉书·荀淑传》);“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后汉书·党锢传序》);“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后汉书·贾彪传》);“说经铿铿,杨子行”(《后汉书·杨政传》);“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等等。这些具有随意调侃性、标榜性的流行语,大部分出自东汉,因是品评人物时所用,其中有些不免脱离实际。但这客观上增长了文人官吏创作谣谚的风气,有助于谣谚文化的繁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谣谚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相关的政策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载艺术表达方式,一般都是文人化的,如寓言、赋诗言志等,这些不能真实的反映民声。而谣谚艺术则是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艺术表达方式,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们在民众中代代自发的创作与传承,其中所透露出的民风与民情,会引起政府的重视,把其看成是考察政治得失的工具,因而促使统治阶层的人采用相关的文化政策加以利用。这些文化政策的实行,不管意图如何,反过来又促进了汉代谣谚文化的创作和传播。
三、社会各阶层对谣谚文化的精神需求
我们知道,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短秦,再到汉代大一统局面的完成,也是西周宗法制度和封建领主经济逐渐破灭,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最终得以确立的过程。这一时代巨变,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各类社会文化现象产生重大的影响。汉代新的统治秩序建立后,在新的时代、新的气象之下,谣谚文化也有了十足的发展。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 社会环境的转变对民间谣谚文化的促进
在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下,农奴完全依赖于封建领主,并表现为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对于广大农奴来说,根本没有过多的自由而言,且生活面非常狭窄,所以民众间不可能形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较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随着封建地主制社会的建立,西周宗法制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和世袭尊卑关系逐渐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相对独立的以个体家庭为主体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经济关系。历经春秋战国和短秦,到了汉代,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已经普遍确立,广大民众有了更多的自由。随着汉代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及宽松的惠民措施的实行,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进步、手工业发达、商人活跃、民众富足。随之而起的则是人们交往的扩大和精神需求的提高。在广大民众社会意识逐渐增强的环境下,人们急需在群体交往生活中建立一种共享的精神文化。当然,他们没有能力去享受大型歌舞艺术,摆在广大民众面前最直接、最适用的就是谣谚文化艺术。经过民众间的代代积累、传承,谣谚文化已不仅是人们最熟悉的艺术样式,而且它的艺术性及应用性也逐步在增强。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式下,谣谚艺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其地位逐渐在汉代广大民众间得以确立。
汉代之前,谣谚艺术在民众间虽然也有着一定的发展,但因为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原因,社会上彰显的是贵族的诗歌艺术。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因缺少人身自由和社会交往,谣谚文化没有在民众间得以广泛施展的可能。正因得不到广大民众的共同“经营”,谣谚文化只能于群众间小范围内流传,表达的是人们一时一地的情感。所以,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作品也很快消亡了。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反映民俗民情的谣谚作品,而只是一些具有生活经验性的谚语。而到了汉代,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人们精神需要的提高,谣谚文化逐渐发展为风靡全国的文化艺术,其特点是: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而且具有更为广阔的流传地域和广大的适用群体。
由此看来,汉代谣谚文化兴世的到来,与社会环境的改变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汉代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促进了汉代民众对精神文化的进一步需求。谣谚艺术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又适应了群众的口味,所以很快得以在民众间广泛地确立。谣谚艺术在汉代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又取决于汉代较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文化发展、兴盛与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所在。①当然,到了社会动乱时期,人们利用早已成熟的谣谚文化艺术来表达所思所感、是非爱憎,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亦是精神需求的表现。
(二) 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对谣谚文化的认定
新的社会性质和统治秩序的建立,也必定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民众来说,多表现的是人身的自由、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这为民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对于统治阶层的文人官吏来说,则更多的表现为思想的自由、艺术审美对象的扩大,这为民间文化得到认可及各类文化艺术的共同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我们知道,在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文人官吏对这种民间文化载体也有着充分的认识与了解。他们不仅把谣谚用来应对或说理,而且利用谣谚来“观风俗、知薄厚”,甚至他们自己也是谣谚文化的直接创作者。谣谚为什么能得到汉代文人官吏的如此青睐呢?最根本的就是谣谚艺术也适合了他们的口味,谣谚艺术也能满足他们某方面的精神欲求。
从谣谚的艺术特征上来看,从先秦到汉代,谣谚文化一直保持着其发展特色,保持着短小的结构形式,直露的表达方式。相对于文人诗来说,这类艺术创作随意、运用自由,没有严格的规定性。文人在枯燥的政治生活和繁杂的诗文创作中,轻松自然的谣谚能使得他们得到轻松一憩。从文人官吏间那些品评性、调侃性的谣谚作品所传达出的幽默与风趣上,也能看出这一点。
当然,文人官吏能对谣谚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关注,除了谣谚艺术本身的魅力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对谣谚文化的认可。先秦时期,在宗法制社会和礼乐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处处受“礼”的制约,文化交往中也多单一地“引诗说理”,而且“歌诗必类”。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享用谣谚艺术的权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人们的思想也逐步解放,文人官吏在日常交往间开始突破“礼”,走出“诗”的规范性,而向民间俗文化倾斜,并引用谣谚进行说理。②查阅《左传》,我们能看到许多引谚说理的情况。如“羽父引周谚”、“虞叔引周谚”、“士蒍引谚”、“宫之奇引谚”、“孔叔引谚”、“乐豫引谚”、“子文引谚”、“伯宗引谚”、“羊舌职引谚”、“刘定公引谚”、“晏子引谚”、“子产引谚”、“子服惠伯引谚”、“魏子引谚”、“戏阳速引谚”等。从这些人的身份上来看,都属于士子、官宦阶层的人。可见,此时期的谣谚艺术已经深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当然,与他们并存的还有更为重要的“赋诗言志”传统。统治阶层的人对俗乐也产生了由衷的偏好,但毕竟正统的礼乐思想影响力还很大,这会受到某些“正统人士”的批判。所以,谣谚艺术在文人官吏间不可能有更大的施展余地。
而到了汉代,文人的思想更为自由。先秦的宗法精神已经破灭,代之而起的则是汉代个人私立观念的增强。人们在个体人格和个体意识上做出了更多的思考与追求,社会环境中流露出一股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倾向。翻阅汉代文人的诗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中所体现的那种慷慨激昂、为宗族国家献身的群体精神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从一己利益出发的喜怒哀乐之情的描写。与之相连的则是他们对平民大众生活的普遍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色人物,如失意文人、游荡浪子、歌妓舞女等都是他们在诗文中描写的对象。他们还把笔触深入到下层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贫民百姓的生活也做出生动的描写,并抒发着强烈的感慨。如《富病行》描写一个病妇家庭的不幸;《孤儿行》描写遭受兄长压迫的孤儿;《东门行》描写走投无路的穷汉,等等。除此之外,汉代官僚文人之间还擅长即兴抒情、即兴演唱,如高祖酒酣击筑而歌《大风》(《史记·高祖本纪》),东方朔酒酣而歌“陆沉于俗”(《史记·滑稽列传》),商丘成醉歌“出居安能郁郁”(《汉书·景武昭宣元功臣表》)等。此外,文人士子间的离别赠答,平民百姓间的感于哀乐,也多诉诸于歌咏来抒发情感。
可见,汉代文人官吏的思想观念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能对下层贫民的生活进行广泛的关注并诉诸诗文,且能即兴运用小韵小调来抒发情感。以此看来,他们也没有理由拒绝民间反应时俗与真情实感的谣谚艺术。而事实上则是他们对谣谚文化非常地青睐,他们不仅对谣谚艺术进行各种应用,而且赋予谣谚更加广泛的社会职能,并且自身也参加到谣谚文化的创作队伍中。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汉代统治阶层的人来说,他们不只需要雅的文化,俗文化对他们也有充足的诱惑;文人官吏既可以做诗,也可以作谣谚,既可以在雅文化中逞才,又可以用俗谣谚语来陶冶性情。正如《古谣谚》序中所说:“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涂。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呜,直抒已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舆风雅表裹相符。”[5](P1)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汉代社会环境的转变、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确立,使得下层民众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统治阶层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民众思想意识的提高,对谣谚文化有了更直接的需求。文人官吏思想观念的转变,对谣谚艺术也有了充分的认可。从此,在汉代较长的历史发展中,汉代各界人士都能从谣谚文化中得到精神的需要,这才是汉代谣谚文化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1]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2]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书社出版, 1999.
[3] 傅亚庶. 孔丛子校释[M]. 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5] 杜文澜. 古谣谚[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Yao Yan Culture in the Two Han Dynasties
SUN Li-tao
( Dep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The Yao Yan ( ballads and proverbs ) culture thrived in the Han Dynasty, partly because it developed as an art, and part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highlight its function through policies. Naturally, as a realistic art in human life, those ballads and proverbs had the function of meeting people's spiritual pursuit.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existed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people to satisfy their spiritual demands from the ballads and proverbs.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ir prosperity.
Han Dynasty; ballad and proverb; thrive; inherit; polity; spirit
G112
A
1005-7110(2013)04-0053-08
2013-05-29
孙立涛(1982- ),男,汉族,河北省河间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