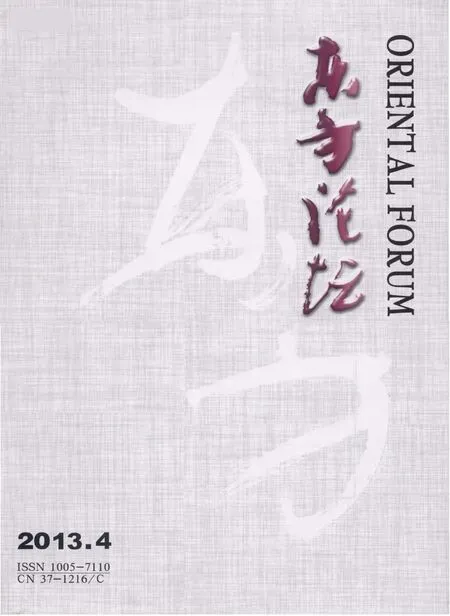清末政治思想中的民论探析
王兆刚
(青岛大学 法学院,青岛 266071)
在中外政治思想中,“民”自古以来是一个核心的命题。在人类历史上,围绕民的地位、民的权利、民的特性、民与统治者的关系等问题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形成了丰富的民论思想。人们对于民的认识,一方面受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民的认识的变化又常常成为时代变革的前兆和政治蜕变的先导。在清末这一变动剧烈的时代中,人们对于民的认识发生了诸多变化,构成了清末政治改革思潮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本文重点探讨清末民论的内涵、特点及影响。
一、民之地位
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如何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出地位,曾出现了“富民”、“善民”、“牧民”以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关于民的思想。尽管如此,对民的重视并不意味承认民的主体地位。各种重民思想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稳固等级统治秩序,是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有识之士们越来越多的开始从民的角度来探讨国家兴衰,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对民的地位的认识与古代民论尚无根本不同,仍是传统重民思想的延续。如王韬提出:“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1](P528),“在抚字以结其心,勇敢以作其气”[1](P18);郑观应认为,议院设立以后,“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2](P237)郭嵩焘指出,“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3](P214);冯桂芬认为:“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教不养有以致之”。[4](P83)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有关民的言论中,民还是被作为被统治者的的庶民百姓整体来看待的,并没有赋予民以新的意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和各种政治思潮的澎湃激荡,思想界开始从新的角度来认识“民”的问题,“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这首先可以从有关“民”的一些新词语的出现而体现出来。
(一)公民、国民等新名词的出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在谈及民的问题时,开始使用“公民”、“国民”、“平民”等新的名词,旧有的“民”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名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强调“民”的权利主体和国家主人地位。其中梁启超提出:“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是之谓国民”[5](P116);有人将国民与奴隶进行了对比,认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国民有责任,喜自由,言平等,尚独立;[6](P72)康有为使用了“公民”的概念,提出“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国民”;[6](P173)有人提出了“平民”的概念:“一国主权平民操之,……政治之主权则属一国之平民”;[7](P584)还有人对“民”和“人”的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如有人认为“有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民”,[8](P458)“权利不保,人性不全,可谓之人乎?”,[6](P484)“权利也,幸福也,非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元气也?”[7](P587)。“公民”、“国民”等有关民的新概念的出现,反映出思想界对民的地位认识的变化,即民不再是完全被动的统治对象,而是可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独立、自由的社会成员。与过去相比,这种新观念已突破了传统民论的思想框架,具有了近代的色彩。除上述内容外,清末民论中民的地位变化又可以通过这一时期思想家对民与君主、民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中体现出来。
(二)民与君、民与国关系的变化
君民关系是中国古代民论中的重要主题,其核心理念是:君主至高无上,君国一体,国家和百姓都是君主的私有物。在清末的民论中,民则完全摆脱了这种依附地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首先,关于君权的来源,认为君权是来自于民,为民而存、依民而存的的,而不是源自于天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君若不能造福于民则可以将其废除。如有人指出:“天子之权得诸庶民”,“天下之权,惟民是主。然民亦不自为也,选立君上,以行其权”,“乡选于村,郡选于邑,国选于郡,天下选于国,是为天子”,”“选于国者不善,则天下废之”[9](P327)。严复认为,君臣“皆源于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民不出十一之税,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强梗,防其患则废”。[10](P334、335)这些言论将传统民论中君与民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其次,在民与国的关系方面,不再把民作为国家消极的附属物,而看作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国家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梁启超指出,“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共有也”,[5](P124、381)汉驹提出,“人民为国家之主人,国家为人民之产业”[7](P580)。
除上述内容外,很多人更进一步的把民看作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如严复认为:“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10](P309);梁启超提出了类似观点:“其民强者谓之强国,其民弱者谓之弱国,其民富者谓之富国,其民贫者谓之贫国”;[6](P135)康有为提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6](P174),“国民之资格日进,中国之资格自进矣”[11](P556)。对民的地位的观念的转变,促使思想家们进一步从民的角度来思考革新政治的方案,他们把民意政治看作是新型政治的重点。梁启超提出:“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5](P302、237)郑观应认为要消除中国上下不通的弊病,“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12](P31)有人指出民意乃宪法的基础,“宪法者,以国民之公意立之,亦得国民之公意废之,以国民之公意护持之,亦得国民之公意革除之”。[7](P635)汉驹认为,中国主权自应中国人握之,中国政务自应中国人公治之,因此中国新政府建设应以国民为基础,即“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7](P580、593)可以看出,清末的思想家并不是单纯抽象谈论民的地位,而是将民与政治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围绕民意设计相应的政治方案,可以说是把握住了政治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
二、民之权利
在中国传统民论中,与民在现实中的无权地位相对应,民一直被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很少有对民的权利的论述。而在清末民论中,则出现了对民的权利问题的种种思考,构成了清末民论超越传统思想框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一)民的权利的内容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末思想界已出现了民之权利思想的萌芽,但尚不够明确。如冯桂芬提出恢复过去的陈诗之法,“无效者无罚”,[4](P35)倾向于保障民的言论自由权。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潮涌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民的权利的论述更加明确和丰富。归纳起来,这一时期所论及的民的权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利。首要的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康有为提出由海内士民公举议郎组织议会,不论“仕与未仕”都可以充选,[12](P135)后又主张公民可以选举其乡、县之议员,有权担任乡、县、府、省的议员,也可被举为乡、市、县、府的官员。[6](P176)严复主张由民众地方官,即“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13]何启、胡礼垣提出:“无论科甲之士,商贾之家,皆得为议员,但须由民公举”。[9](P329)其次,为监督官吏权,梁启超提出:“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5](P150)其三,为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郑观应倡导言论自由,提出广设日报,“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不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12](P142)康有为说,“近开报馆,名曰新闻,……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14](P302)有人指出,“于一国之内,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迁徙自由、集会自由、本身自由、家室自主,下及诉求请愿、秘密书函、干涉行政之得失、选举议员之资格,无不有焉,此自由也”。[7](P526)相对而言,思想家们对结社自由更为关注。宋恕主张,“许官民男女创立各种学会”,“学会最多者,其国最治”。[15](P136)秦力山认为应允许国民组织政党,“政党不能禁一国之有党者”,“党也者,所以监督政治之得失,而保其主权,使昏君悍辟,无所得而行其私”。[16](P46)康有为说,“泰西国势之强,皆借民会之故”。[11](P155)钟天纬认为,西方商业发达,一个重要原因是设立很多商会对商业加以保护,中国也应效法西方,让各行业组织商会,“遇有商务,许其直达有司。凡有益于中国商业,听其设法保护”。[17]梁启超则主张通过办学会来培养议员,提高国民程度。他认为兴民权应先兴绅权,兴绅权应以办学会为起点,吸收绅士加入学会,“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另一方面,推行立宪必须提高国民程度,而政治团体是达此目的最有效的手段。[5](P75、76、541)
第二,平等权。梁启超说,“天之生人,权利平等”,“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5](P381)何启、胡礼垣说,人人有自主之权,“则不问其居之位何位,所为之事何事,其轻重皆同,不分轩轾故也”。[5](P347)汉驹提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率一国之民无强无弱,……均受治于法律下而无稍偏颇”。[7](P586)有人指出,“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应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6](P78)有人指出,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并立于大地之上,谁贵而谁贱,谁尊而谁卑?[6](P480)
第三,经济、社会等权利。郑观应反对妇女裹足,抨击男尊女卑的传统,主张女子入学接受教育。[18]康有为也反对妇女裹足,说:“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14](P396)宋恕主张婚姻自由,认为要消除夫妇怨气,挽人伦之败坏,“必由使民男女自相择偶始矣”。[15](P136)张百熙提出应给予人民一定的经济自由,可在四川、云南等省,“听民开矿,以广利源也”。[19]胡燏棻主张允许民间设厂造机器,“令民间自为讲求”。[20]钱智修提出应由社会对个人进行辅助,“授人以从事竞争之能力”,实行义务教育,提供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事有关公共健康之危害,及个人之力所不及备者,则当由社会任之”。[21](P775、776)
(二)民之权利的特点
综观这一时期思想界对民之权利的论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于民之权利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来源问题,有的是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论述,更多的则是从富国强兵的方面理解。严复曾大力宣传天赋人权论,说:“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13]何启、胡礼垣说:“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此性命之权”,“自主 之权,赋之于天”。[9](P350)有人指出,“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自有天然之权利”。。[7](P480)杨笃生认为,“个人权利者,天赋个人之自由权是也”,“天赋人权者,生人之公理,天下之正义也”。[7](P632、633)另一方面,有的思想家从国家兴亡角度讨论民之权利的合理性。汪康年说,中国如果要改变数千年形成的积弊,“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22]陈天华认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23]有人提出,“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者,蹱相接,背相望”。[6](P70)何启、胡礼垣虽认同天赋人权论,但也承认民权的强国功能,“中国之不能富强者,由不明民权之故”,“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9](P342、348)天赋人权论的提出和宣传,是清末民论中的新元素,它表明思想家开始注意民的权利问题,这是古代民论中没有的新内容,因而是对传统民论的超越。而从富国强兵角度对民之权利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解读,则显示出时人民之权利观的现实性和依附性,即民之权利在很多人眼里还没有被看作一个独立问题。这的确是时代使然,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国家独立民主根本无法顾及个人权利。但从理论上看,赋予民以权利短期内很难说会直接带来国富民强,因此思想家所加给民之权利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实在是它的不能承受之重。这也说明,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观念与实践中,民之权利向个人的真正回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强烈的整体主义色彩。在清末思想家眼中,作为权利主体的民所指的主要不是个体的民,而是整体的民众,这类似于今天所说的集体人权。何启、胡礼垣说,“民权者,以众得权之谓也”。[9](P346)梁启超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22](P102)陈天华认为,“吾侪求总体之自由也,非个人之自由者也”,“惟欲求总体之自由,故不能无对个人之干涉”。[23]这里的“团体“、”总体“所指的乃是国家、民族,因为这样可以“利国善群”,“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23](P96)这种集体权利观念有其时代合理性,但也反映这一时期的权利思想与近代西方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政治观念不同的发展理路。这种倾向说明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还没有根本完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一时期权利观念中重整体轻个体的倾向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一直绵延不绝,而且不时被强化,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特点。
第三,从这一时期思想界所主张的民的权利内容来看,主要是政治权利和平等权,对民的人身人格权、经济、文化、社会权利涉及不多。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政治权利与人身人格权属于第一代人权,是与18世纪后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相适应而产生的。相对而言,人身人格权属于较纯粹的公民个人权利,而政治权利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与所处政治体系的关系。清末民初思想界对政治权利的重视,反映出思想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来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从西方借用来的政治权利观念从新的角度阐释了民与国、个人权利与国家强弱的关系,为设计新的政治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人身人格权主要属于个体权利的范畴,与新的政治设计及急迫的救亡任务关系不大而暂时被忽略。
三、余论
(一)如上所述,清末民初思想家普遍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对民的地位、民的权利进行了不同于传统民论的新的阐释。但对于民的能力却大多抱以悲观的态度,因此在是否给予民以充分的自由权利、提高普通民的政治地位问题上显现出迟疑和保守。
积极主张开议院的郑观应认为,公举议员之法不能在当时实行,“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议员乃贤”,“否则徒滋乱萌”,应从开学校、教育人才,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开始。[12](P40)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中国人的缺点在于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不具备实行议院政治的能力,没有可作为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5](P433、482)麦孟华认为,“中国之民不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权”。[25]有人指出,“以如是国民,而与以莫大之权,使之与闻国事,是何异使蚊负山以虻距海也”。[26]面对低下的民众能力,思想家们主张不能消极等待民众能力的自然提高,必须采取措施增进民众能力,从而为政治革新创造条件,这反映出思想家对民众态度中积极的一面。如当时人有的主张以议会开民智,有的主张以革命开民智,有的提出通过办报,兴学来开民智、培育人才,还有人提出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建设新政府来开民智等。鉴于民众能力暂时无法提高,而政治改革又势在必行,有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过渡方案,即先由士绅等社会精英来代替民众行使其政治权利。如张謇主张,设立府县议会时,“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必绅士也”。[27]梁启超也提出,欲兴民权,先兴绅权。[5](P75、76)
(二)清末民论是近代中国启蒙与改革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民的地位、民的权利等方面超越了传统民论的思想框架,改变了人们对民的认识,促使人们重视民的作用,从民的角度去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在清末民论中,民不再是完全被动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地位的提高与权利的获得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主动地位,这些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民论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民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民的理解侧重于作为整体的民众,注重的主要是民与国家富强的关系,对民的价值的判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对国家民族的作用,民在一定程度上被工具化了,因而很少关注民的个人价值与自由权利,对民的能力普遍持怀疑的态度。这些特点体现了与传统民论的某种继承,古代民论中不乏重民思想,重民的主体是君主,民仅是被重视的对象,而在清末民初的民论中,君主变成了国家,民并没有因此根本改变从属者的地位,获得彻底的个人权利与个人价值。这种倾向反映出后进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政治思想的普遍特点,如中日两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颇为相似,即都是从一种民族危机出发,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振兴民族,推动国家近代化而开始启蒙的。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及其后的启蒙运动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论缺少对个人价值、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权利的体认与宣传,对自然权利观、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等近代政治的核心命题也只是简单论及。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民论还显得比较单薄,没有形成一种以尊重人、解放人为中心的思潮。这的确是时代使然,但作为后来者,我们仍有必要认真梳理前人走过的思想轨迹,清醒认识其中的价值与不足,因为传统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民论中的上述局限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的改良或革命运动影响深远。在戊戌变法中,当事者将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及部分帝党官僚,无意于发动民众,终因势单力薄而归于失败。其后的辛亥革命虽发动于底层,但主要依靠的是新军士兵和会党势力,对下层民众和社会也基本没有触及,因此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的气象,开始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宣传个人价值,但不久因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及国民革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仍没有完成对传统民论的彻底颠覆与新民论的全新建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民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获得了空前的主人翁的地位,从实践中改变了人们对民的看法,形成了以人民主权论为代表的新的民论思想,民的整体地位得到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对民的个人价值与自由权利的思考则时断时续,在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革命、建设与社会改造运动中,民的个体色彩是微弱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目标,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尊重则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反思近代民论的发展历程,认识我们政治观念中的各种基因,对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必要的。
[1]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2002.
[2] 郑观应.议院[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郭嵩焘.上合肥李伯相书[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2002.
[5]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C].北京:三联书店,1960.
[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C].北京:三联书店,1960.
[8] 阙名.革命之原因[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10] 严复.辟韩[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3] 严复.原强[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 谢遐龄.康有为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5] 胡珠生.宋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6] 彭国兴,刘晴波.秦力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 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8] 郑观应.女教[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9] 张百熙.上条陈时务疏[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 胡燏棻.上变法自强条陈疏[A].郑振铎.晚清文选(上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C].北京:三联书店,1977.
[22] 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中)[A].郑振铎.晚清文选(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3]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A].郑振铎.晚清文选(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4] 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5] 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A].郑振铎.晚清文选(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C].北京:三联书店,1963.
[27] 张謇.变法平议[A].郑振铎.晚清文选(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