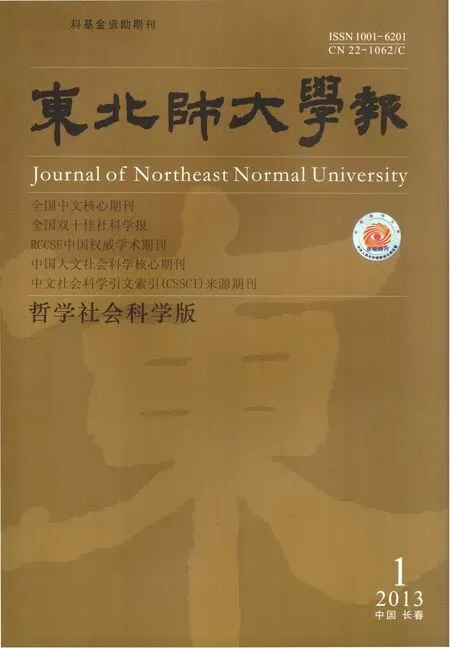现代空间与女性问题
史 巍,枫 叶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现代性与其说是被时间性所标识的,不如说是被即刻性和间距性所标识的。或许可以这样说,现代性本身是围绕着理性主体与非理性主体、边缘与中心、控制与反控制、国家与社群、资本家与工人、生产领域与家庭领域、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等所标识。理性主体与非理性主体、边缘与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为后现代理论所重视;控制与反控制、国家与社群、资本家与工人为自由主义理论所推崇;而生产领域与家庭领域、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等问题就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感兴趣的话题。现代空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现代空间与女性问题究竟有何种关联,本文试解之。
一、空间与女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空间并不是中立的,具有性别特征,空间建构和再现的性别关系、地位是典型的隐性歧视,空间以男性的需要和要求为主要的考虑标,女性则像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始终处于空间的组织、规划和构造的边缘状态。”[1]如果恰如这样的话,那么现代空间是具有性别性的,从现代空间的基本特性出发,或许更能体味现代空间之于女性的意义。
现代空间是具有层级性的空间,而层级性的划分则被艾萨克·牛顿、勒奈·笛卡尔等哲学家试图掩盖,但事实上空间特别是现代空间总是与现代空间中的生活紧密相关。如果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看待现代空间,那么在现代空间内部,空间被分为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赖以存在的城市空间和作为次生性的城郊空间,前者作为经济空间存在,后者仅仅作为居住空间存在。这一空间上的划分一方面使得女性的空间被更多地理解为家庭空间、邻里空间,而男性空间则被理解为经济空间、工业空间、商业空间。前者是与消费、情感、私生活等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化空间,只能依靠消费来满足。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指出,只有当女性被定位在消费者的层面,在对现代社会商品和资本循环做出消费性的努力的时候,才能短暂地被纳入城市空间中来。她们必须被限制在家庭当中,一方面为积极工业文明的主力——男性提供后援;另一方面不断激发难以满足的消费欲望,从而对现代社会的再生产起促进作用。
现代空间使男性——作为“思”之理性主体成为“主宰空间”的代名词。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疑确定了现代空间从“思”到“我在”再到“它在”的基本路径,那么无疑“我在”是理性——男性主体的存在,而“它在”——女性客体则是依靠“我在”得以确证的,而“思”本身作为宇宙间唯一的无形力量应该是“男性”化的。至此自我/他者,客观/主观,理智/情感,抽象/具体,事实/价值,文化/自然的区分,就天然地划定。这些特点与其说是为笛卡尔的主体建构了一个男性身份,倒不如说是为其建构了一个主宰身份,即自我、客观、理智、文化等因素是与男人相联系的,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而他者、主观、情感、自然则相应地与女人相联系,受到贬抑与排斥。这就造成了主体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逻辑进路。这样一来,现代空间使得男性被预设为绝对化的“强大的”、“主导性的”、“攻击性的”具有霸权地位,而女性自然处在“柔弱的”、“消极的”、“被动的”、“非存在的”边缘化、次生化和弱化地位。
女性主义者波伏瓦曾经说过,女性之于女性不是先天造成的,而是后天生成的。与女性的生成性相互联系的就是女性如何在现代空间生存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空间之于女性的意义是通过资本主义予以呈现的。女性空间通过消费将自身的私人空间纳入资本主义体制当中成为公众空间,女性看似作为积极的参加者并表述为多重空间,这些空间分别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同环节,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但事实上,女性仅仅作为男性的衬托,仅仅是为了使男性空间更为充实、更为积极而存在。无论女性被理解为以往的绝对脆弱和空虚的空间,还是在这样一种理解方式中被视为相对的空间,实际上,女性都是通过结合一种本体形态——或为男性、或为资本——而被定位的。
现代空间所导致的权力结构无疑将女性的恶化推至顶峰。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权力关系——“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2]如果现代空间的权力性特点正如福柯所说建立在规约和惩罚基础上的话,女性无疑是规约与惩罚中最为典型的牺牲品。现代空间中的女性时刻处于被窥视和监视的境遇当中,她必须使自身的行为富有“女人气”,否则就会得到“形形色色”的残酷和野蛮对待作为惩罚。这样,“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3]如此的权力关系使得监视和控制沉入到女性的意识当中使得即使监视是断断续续的,而女性在潜意识中也总是沉浸在这一被监视的境遇中,从而丧失了对权力的反抗。
二、现代空间的现代性特点
现代空间之所以能够对女性问题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最核心的根源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特点。如果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4]那么现代性在时间上就代表断裂性与传承性的统一;在空间上则代表一种边缘与中心、在场与出场的统一。女性正是在现代性中才不断陷入被动、消极的境遇的。
现代空间的现代性特点体现为层级性。现代性的空间概念起源于中世纪。中世纪的空间即某种具有层级性的空间,天堂的场所保证了人间的场所的存在,圣地的场所又赋予了非宗教场所以某种特定的空间性。但较之前者,后者的真实性是“存疑”的,只有前者才是确定无疑的存在或空间,空间就被这样按照层级和对立被部署。应该看到在现代空间概念中,除了在康德等有限的形而上学家那里将其看作“先天”的纯范畴或将空间作为纯物理学的广延研究之外,特别是在社会领域研究空间的概念的时候,空间仍然是具有层级性的,如理性主体之于非理性主体、边缘之于中心、城市之于乡村、国家之于社群、生产领域之于家庭领域,而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现代空间的现代性特点体现为主体性。后现代思想家詹姆逊在现代性所应遵循的“第三个准则”中提出“不能根据主体性分类对现代性叙事进行安排”[5]45,似乎在现代性中不存在有主体性之间的分类而导致的不同的现代性,仅仅存在的是现代性的不同场景。现代空间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也应该与主体相互区别并保持距离。但事实上,早在笛卡尔哲学那里就已经奠定了现代空间不可与主体性相互分离的命运:主体与客体/我思与我在之间体现的就是一种现代性——我思就是现代性的主体,我在无疑作为一种客体是由现代性的主体建构出来的。客体作为主体的生产物而存在,“表征客体在建构中呈现为可以辨认,这在形式上开辟了一个地点,使感知从中产生:这种结构的或者称之为形式的地点,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物质或实质,构成了主体。”[6]现代空间在其现代性的起点那里就是与主体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思”为“在”和“他在”确立标准和合法性基础也使得“思”——理性成为主体性分类的划分标准,自然也成为现代空间的划分标准。
现代空间的现代性特点体现为结构性。“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人们有可能确定一些个人和一些事物的位置的真空中。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5]45虽然空间就其本身来说一个自然或原始赐予我们的存在,但空间的结构及空间自身的意义却总是随同社会历史和人类经验不断发生变化和转型的,如果说空间是一段历史的话,那么这段历史并非是作为时间之附庸的自然空间的历史,而是作为不同社会、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在构建整个群体、社会、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历史;空间总是根据时代、社会、生产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构成其自身在不同时间性中的特殊性,“是在接受者头脑中建构的意象。”[7]而这种特殊性对于现代空间来说,无疑就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空间”。
现代空间的现代性特点体现为权力性。如果说“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作为控制的工具的话,那么现代空间无疑是具有权力性的,甚至可以说作为权力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它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的较量之下,在各种斗争中获得自身的现实存在。“今天。阶级斗争比以往更加被铭刻在了空间之中。真的,单单是着重斗争,就防止了抽象的空间盛行于整个星球所掩饰所有的差异。”[8]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权力性是确证无疑的,在这样的现代空间中,个人生活也被权力所包围,监视和约束最终导致一个在权力监控之下的、区别于以往的新个体的诞生。正是现代空间的封闭性使得监督和约束成为可能,而监视和约束又是以空间的区别为其先决条件的,权力总是借助于城市中的空间和建筑的范围划定而发挥作用的,特别是空间之间的区划能够很好地达到限制人们活动,并对人们活动予以控制的目标。不仅如此,现代空间与权力之间的伴生关系使得空间的权力要求由个体的、部门化的、局部的现象成为一种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作用。
现代空间正是通过四方面的特点对女性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着重影响反过来又强化了现代空间,使得现代空间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在场”,而成为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看似出场但却永远在场的永恒存在;它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容器”,而更多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重塑的现代空间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批判现代空间、重建现代空间、重塑现代性精神的主力和生力。她们在对现代空间的层级性、主体性、结构性和权力性展开现代性批判并认为其是女性问题的重要原因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精神展开研究,认为现代性更应该被看作一种置身于时间洪流之中永不停息地追求现代之义的永恒冲动,一种在空间中有“在场”与“出场”所共同架构的关系、意义、境界的网络。
现代空间不应是上层与下层对立的、主体与客体二分的确定性,更应是一种关系性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空间对空间的理解仍然沿袭着“场”的概念,空间意味着“实体”的在场:从早期起,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从在场者方面来表象,在场就成了超出一切的在场者,从而成为至高的在场者了[9]。正是基于“在场”的概念,而场所和位置就意味着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事实上,真正值得构建的现代空间应该是通过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处于不断地形成当中的关系空间。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理论中得到佐证: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空间,但事实上马克思唯物史观体现为这样一种空间:通过能动的、历史地构建创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帝国主义,使得所有的事物和观念都是建构当中、所有的事物都被保存在相对的状态之中。
从本质上来说空间绝不仅仅是事物存在的场所,也不仅仅是组合起来接纳事物的一种环境。空间应该是由旧的空间结构与新的空间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形成的一种境界,境界才是空间的真正内涵:空间不是恒定在地面上的固定位置或者坐标系,而是呈现为天空、匀和和开放。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动态的思想空间本质上不同于领土空间。……动态的空间是匀和的,或不固定性的。一个物体可以出现在任意点,而且可以移向其他的任意点。它的分布方法遵循这样的规则和理念:把自己安顿在开放的空间里,而不是作茧自缚的在封闭空间里。”[10]99这种对空间的假定,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研究,原子运动的无序性和开放性就表征了这样一种开放和自由的空间形态。在新的空间概念中,重要的不在于定位和发现,而在于重新的探索和发明上——对现有空间的潜在客观事物进行想象的对话。
现代空间的关系性对空间的结构性和权力性无疑是一种克服。现代空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用“空灵”这一概念加以表述:“空灵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空间。……空灵不是一个本源,不管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它也不是一个会导致可预知结果的原因。正好相反:作为不确定物,空灵是一个拥有纯粹机会的天使。”[10]101如果对“空灵”概念用一个词加以概括莫过于“道”,而且空灵只是取“道”这一万物之母的特性,却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它只是使位置成为可能的空间,是介于无空间形式和空间化的实体之间的过渡部分,是使自己向着空间化开放,使自己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通道。在“空灵”之内,现代空间就不再是单一的城市空间、不再是单一的以消费为基础的空间、不再是单一体现生物繁殖功能的空间、不再是在以往的空间下只能体味到的,“个人好像不是去占有资本而是被资本占有”;其也不再存在有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对生活领域的绝对的权力、不再是以经济领域对生活领域的绝对权力、不再是以往能够体味到的个人被整个社会所“监视”的状态,每个人都在这一空间中处于“相对”的中心和边缘,“空灵”的不确定性正是对结构和权力的破坏。
这样现代空间概念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才能将属于女性的灵动空间还给女性。这样做的更为积极的意义在于,空间本身不再是实体的“容器”,而成为开放性的领域,其所孕育的生机和潜力无论是对现代性本身、还是对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无疑都是具有及其重要意义的。
[1]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菲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2]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
[3]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226.
[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
[5]詹姆逊文集:现代性、后现代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Rene Descartes,Western Classics-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John Cottingham.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1999:36.
[7]孙影,成晓光.隐喻象似性的三维阐释[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14-117.
[8]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7.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578.
[10]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权主义批判[M].陈冬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