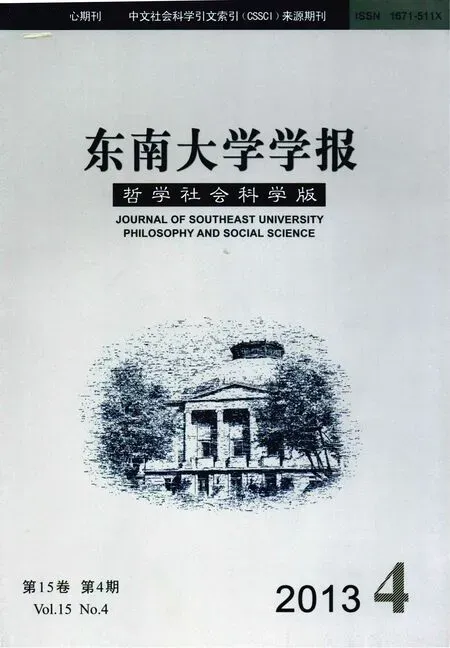探索“中欧融合”的集大成之作——陆志韦《杂样的五拍诗》平议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陆志韦的新诗探索有两轮高峰,一是在东南大学时期的诗集《渡河》(1923),二是燕京大学时期的《杂样的五拍诗》(1937-1940)。1947年6月,陆志韦重钞旧作《杂样的五拍诗》二十三首,发表于《文学杂志》二卷四期(1947年9月)。这二十三首写作于1937年春到1940年春,其中一至五曾经发表于《文学杂志》一卷二期(1937年),十五到十八发表于《燕园集》1940年卷;十九到二十二发表于《燕京文学》(1940年12月)。《文学杂志》1947年发表的全本重抄版本,诗作次序有变化。本文所论诗作顺序,均取1947年6月重抄版。这二十三首诗歌,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有微弱的联系。《杂样的五拍诗》既可以说是一组诗,也可以说是一部诗集。
这部诗集仅仅23首,陆志韦却耗时整整三年苦心孤诣地制作。如果计算一下从动笔的1937年到重抄出版的1947年,那么就是整整十年。陆志韦非常珍视这部诗集。他在重抄的序里写道:“人死了,留下来几根骨头,我想总应该有个权利希望聚在一块儿让人家烧毁。老实说,我对于这几首小诗比这几年来粗制滥造的好些所谓科学的,考据的文章还来得爱惜。就好比生了一个又驼背又拐脚的女儿,人家不疼她,我偏疼她,还想把她嫁出去。所以越是忙忙乱乱的,越想抽点儿工夫把他们抄在一起,交孟实代我付印,并且有几首还得重印一次。我不愿意一把骨头散在好几处。不愿意同一个女儿嫁了驼背又嫁拐脚,要丑就尽丑这一回。”[1]55
很可惜,这部重要作品却备受文学史冷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时代语境。诗集创作于1937-1940年间,这时候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三年,整个文坛尤其在诗坛都将文学的战斗性、工具性、政治性发挥到极致,文学和诗歌的自身属性暂时被实用功利性遮蔽了。而《杂样的五拍诗》无论诗歌内容的表达,还是艺术形式的探索,都与时代语境构成了悖离。《杂样的五拍诗》内容上立体繁复,形式上融中欧元素进行节奏探索,风格上呈现出现代主义欧化特点,实乃一部“中欧融合”的集大成探索之作。
一、超越战争思维的个体表达
《杂样的五拍诗》极富阐释空间。在诗歌的内涵表达方面,它绝对不是直白的战争宣言品,而是深邃的、多声部的、复杂多义的立体结构,甚至是含混晦涩的。他自己在小序里也说:“按内容来说,我不会写大众诗。有几首意义晦涩,早已有人说过俏皮话。经验隔断,那能希望引起共鸣。现在我不怕寒唇,加上一点注解,并非自登广告。一个人太寂寞了,年纪又快老了,自言自语是可原谅的。”[1]56为此,他在每一首诗的后面,都加了注释。
在这部诗集里,诚然有陆志韦个人生活的影子,比如:他出生在“没落的书香门第”(《杂样的五柏诗·一》,下文只引序号),他所见到的尝遍酸甜苦辣的“慈祥的老人”(《二》),“跟自己的思想告别”的自我审视(《十六》)等。但它毕竟创作于抗日战争初期,必然地带有时代磨难的痕迹。《二》以变形意象状写尝遍了酸甜苦辣,还是那么一团和气的“一位慈祥的老人”。《三》以破败的大车在没有尽头的岔路上奔波,隐喻“民族求生存的途径”。《四》是潜意识流泻。《五》以浮苏维(Vesuvius)毁灭城池的典故,写出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手所造的东西会叫人发抖”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同时也道出了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我要创造”的民族精神(《六》)。《十二》中“敌人”作为异己力量的象征,深化了内涵。《十五》则是直接描绘日本和汉奸一起淫乱的丑态。《十七》写战争后的祭奠。《十九》写乡下人匍匐黄土的艰难生活。《二十三》讽刺了纳粹主义者刚愎自用的虚饰和帮闲文人们的肉麻。陆志韦还把笔触探向底层人群的生活。《八》写了留过洋、喝过浑水咖啡、吃马拿(mana)和面包的“小天使”对于吃锅饼、吃大米饭、喝酸豆汁的那些喊着“镰刀、锤子”的贫民生活的不理解,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群,截然不同。《十三》和《十四》写的是流落中国的俄罗斯妓女的不幸生活。
与当时流行的抗战诗歌极其不同的是,陆志韦虽然在诗中显示出抗战时期的一些背景,但没有任何的宣传目的,而是维护诗歌自身的纯粹性。他没有陷于简单的民族危亡的抒发,而是以形而上的抽象的力量,试图抵达人生的一些命题。《五》、《六》不是简单控诉战争,而是写出了战争主体自身的悖论,一方面,人是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破坏者。《七》由“赶着自己的尾巴绕圈儿的狗”的命运,隐喻“有的人到死还跳不出自己的梦圈儿。”(陆志韦诗末自述)我们看《十二》:
我且不走呐,这儿是我的家呀!
敌人也带不走这点儿破东西
好比这碧桃树给砍了一半
我解下裹伤的带子来裹你的伤
别从寡妇的怀抱里抢走孩子
我且不走呐,我是野猪,我是豹
他在诗末自述里阐释:“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没有敢把这一首写下来。其实这并不是所谓抗战诗。谁,任何势力都可以是‘敌人’”。[1]63这里的“敌人”就不是具体意义上的“日本侵略者”,而是与“家园”相对立的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异己力量。“家园”和“敌人”构成了一对范畴。再看《十七》:
纪念屈死的,造一个观音像
废铜烂铁,这年头贵得离奇
用死人的天灵盖好充象牙
慈悲的菩萨原先你裸体而来
白衣是我们献奉的,象看护打拌
如今又归于裸体,我们的骨头
这首诗已经超越了道德的善恶是非的二元对立思维。他诗末自述道:“胜利以后,白布写挽联,纪念‘剿共’的将士,‘光荣’的英雄,双方面都用中纺公司的出品。”在抗日战争期间,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改造,向人民群众看齐。而《十八》写战争年代的庸众表里不一的人性丑陋,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大相径庭。
二、新诗形式的试验
陆志韦不止一次口口声声地表达对这部诗集的珍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反观陆志韦的诗学与诗歌实践之路,就可以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杂样的五拍诗》承续了他在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渡河》(自印诗集《不值钱的花果》增订版)中显示的对于节奏苦心孤诣的探索精神。如果说《渡河》是陆志韦第一轮的新诗形式试验,那么,《杂样的五拍诗》是他的第二轮新诗形式试验。从1920年1月开始写白话诗到1947年辑录《杂样的五拍诗》,前后跨越27年,可见陆志韦对于新诗形式的探索是异常坚定的。
早在1923年,他在第一部诗集《渡河》的自序和《我的诗的躯壳》里就指出白话诗的文体最主要的有两大因素:“节奏”与“韵”。他直陈自由诗破坏节奏的弊端:“自由诗有一极大的危险,就是丧失节奏的本意。节奏不外乎音之强弱一往一来,有规定的时序。文学而没有节奏,必不是好诗。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然而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2]可以说,他一直在这两大因素上进行探索。1937年,他发表《论节奏》,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声音节奏的外界物质原理和生理学原理,并且对于白话诗与自由诗、散文诗的文体差异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所谓白话诗就是根据语调,加以整理,叫他变成有节奏的。……假如每行没有一定的节数,那诗就变成近来通行的自由诗。”[3]10陆志韦特别重视诗歌的文体形式,而诗歌文体又聚焦于语言,因此他特别重视语言的锻炼。他认为白话诗必须创造新的有节奏的诗,否则是很危险的。
当别人都在视诗歌为战争工具、把诗歌当作宣传口号的时候,陆志韦在潜心于诗歌的节奏。陆志韦本来专注于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因为战争年代的学术条件困难,他在1938年开始学术转型,由心理学研究转向语言学,致力于音韵学与语法学研究,开始从王静如学习清代古音学和“高本汉学”,完成了《汉语和中国思想正在怎样的转变》。陆志韦对于节奏的探索可谓是孜孜以求。他在《论节奏》把自己早期的探索完全否定了,认为“那一番功夫算是白费了。”[3]18朱自清认为由于时候太早(格律诗的实验尚未引起注意)而被忽视,陆志韦自己认为是“由于我的南腔北调”,对节奏的尝试不成熟。《杂样的五拍诗》是陆志韦关于节奏的新的尝试。
《杂样的五拍诗》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节奏”。他在序言里说:“这几首诗是节奏的尝试。好多年以前,听元任说,北平话的重音的配备最像英文不过。仔细一比较,他的话果然不错。当时我就有一种野心,要把英国古戏曲的格式用中国话来填补他。又不妨说要摹仿莎士比亚的神韵。我从小就说吴语。学英文,学国语,都不很容易。可是这几首诗决不是填字眼儿。我是用国语写的,你得用国语来念。不得已,只可以把重音圈出来,好比姜白石的《自度曲》。”[1]55-56陆志韦为自己做的圈注重音情况,我们列举其第一首和第七首,如下:
一
是一件百家衣,矮窗上的纸
苇子杆上稀稀拉拉的雪
松香琥珀的灯光为什么凄凉?
几千年,几万年,隔这一层薄纸
天气暖和点,还有人认识我
父母生我在没落的书香门第
七
赶着自己的尾巴绕圈儿的狗
一碰碰倒了人家龈光了的骨头
黄昏是梦打扮出门的时候
露着满口的金牙对人苦笑
虚空呀,空虚!李夫人刚又过去
谁不赶着自己的梦绕圈儿?
1940年,他在《燕园集》发表的《白话诗用韵管见》里,就发现“汉语句式,以语助词收脚者,重音不在末一字上。”[4]9因此,“狗”与“骨头”,就不是押韵。会说官话的人知道,“骨头”的重音在“骨”,不会说官话的人,则往往会误认为“骨头”重音在“头”。
朱自清曾专门撰文《诗与话》对《杂样的五拍诗》进行评论和解读。朱自清谈到《杂样的五拍诗》的形式试验和探索。他根据陆志韦的语言学论文《用韵》,来分析《杂样的五拍诗》的白话试验。
《杂样的五拍诗》作为陆志韦第二轮新诗形式的探索,他的结论是“中国的长短句”加上“英国的轻重音”。朱自清在《诗与话》里论及陆志韦诗歌的现代性与英美近代诗对他的影响:“这二十三首诗,每首像一个七巧图,明明是英美近代诗的作风,说是摹仿近代诗的神韵,也许更确切些。”[5]陆志韦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还是深谙语言运用的内在发生学的心理学家。所以,他的“中国长短句加英国的轻重音”,是化中为欧,又是化欧为中,二者的结合就使得他的诗歌具有出色的母语运用能力,他的欧化没有破坏母语的节奏和韵律。他的“中欧融合”,与中国的汉语智慧、诗学传统、思维国情有机结合。解志熙在《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里,将陆志韦置于40年代富于现代性的新古典主义思潮之中,充分肯定了陆志韦《杂样的五拍诗》的形式探索:
30、40年代他特别注重化欧为中的创作实验……“五拍诗”即英语诗歌中的“五音步”诗行,一般采用“抑扬格”、重音音律,由于它与英语词汇的自然节奏相吻合,所以是英语诗歌中最普遍、最常用的节奏形式。陆志韦是语言学家兼新诗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新诗探寻“诗的躯壳”,尤其是节奏形式。据他自述,“好多年以前,听元任(指语言学家赵元任——引者按)说,北平话的重音的配备最像英文不过。仔细一比较,他的话果然不错。当时我就有一种野心,要把英国古戏曲的格式用中国话来填补他。又不妨说要模仿沙士比亚的神韵。”……这二十三首诗也确实值得特别珍惜,因为它们在化用欧洲诗歌的形式来建立中国现代诗的节奏方面,确实相当成功,以至于人们读这些非常口语化的诗时几乎完全不觉得它们利用的是外来的形式,随便翻开一首都是那样地道的口语而其节奏也都是那么抑扬自如。[6]50-51
三、欧化的现代主义文本
在具体表现手法上,《杂样的五拍诗》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文本。它集象征、变形、隐喻、典故、潜意识等各种手法于一体,构成了立体丰富的、含混多义的艺术世界。朱自清在《诗与话》里也论及陆志韦诗歌的现代性与英美近代诗对他的影响。朱自清说:“这二十三首诗,每首像一个七巧图,明明是英美近代诗的作风,说是摹仿近代诗的神韵,也许更确切些。”[5]解志熙的《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中这样说:“朱自清的判断非常准确,他所谓‘英美近代诗的作风’即是指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风,而T.S.艾略特在英语诗歌史上恰恰是开创了以口语化的、反浪漫主义的作风表达复杂的现代经验而同时又特别注重接续古典人文传统和诗学传统的大诗人,一个带有显著的新古典主义格调的现代派诗人。”[6]51
在这组文本中,诗人的思维汪洋恣肆,时空腾闪跌挪,思绪错接,陆志韦的诗思确实是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他在诗末介绍第十三、第十四首时说:
所要说的,仿佛是 Goethe的das ewige Weiblich。“天下的女人只是一个女人”,也许是母亲,是情人,是坠落的“花”。乱七八糟的,想到《琵琶行》,皇甫松的《天仙子》,李商隐的《碧海青天》,西洋歌剧里 Thais的《忏悔曲》,II Trova tose 末一幕母子二人临刑的前一夜唱ai nostril monti(《回我们的家山》)。第十四首可说是第十三首的下场。我并不知唐朝的长安有波斯女子。李白诗“吴姬压酒劝君尝”,小时候把他错误成“胡姬”,到如今还是胡思乱想。前些年,有人专嫖白俄妓女的,丑不可言。汉人在保儸区域里,男人当奴才,女人不当妓女。[1]65介绍第二十、二十一首时说:
以上两首不妨说是题画诗。极无聊之中,买了一张陈白阳的《百合花》斗方,一个徐青《藤墨荷》手卷,《百合花》叫我想起“公孙娘子”,也不知是杜甫《剑器行》里的舞女,还是蒲榴仙描写的《公孙九娘》。第二十一首断不是荷花引出来了。徐文长这人,(《徐文长传》)里的人),我在别处见过他画的像猫头鹰似的乌鸦,几年前在Yosemite乌黑的潭水旁边,清早起来静坐,这些鬼趣叫我觉得士大夫的生活的可笑。我常把徐文长比袁小修,陈白阳比李流芳。我最爱李流芳的画,最讨厌他的人头。[1]69-70
古今中外的资源共时性地呈现在他的脑海里,任其驱遣调用,又杂以国外很多文化资源。他的诗歌后面的自述文字里频繁出现了西方经典文人和学者Freud、Adler、Vesuvius、Napoli、Ibsen、Montmartre、Goethe、Thais、Naroisus等,这便形成了晦涩难懂的风格。
陆志韦在写作《杂样的五拍诗》过程中,有一篇重要的长篇论文《汉语和中国思想正在怎样的转变》写道:
语言不但是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势力所产生的。社会的势力改变了,语言也得改变。社会上要是发生了很剧烈的变化,最后思想和语言也得发生剧烈的变化。语言的格式也许是社会势力最后才能达到的一种现象。因为在过渡的时候,我们每每看见有的新的思想内容包含在旧的语言格式里。这种情形,好比是中国现今交通工具的杂乱状态。旧的小车可以运输外洋输入的汽油。可是到了有一天我们会用新的运输工具载运汽油,并且那运输工具本身也是得用汽油的,这一段社会的变化可算是完成了。现今的汉语和中国思想可以说是在同时用小车和汽车载运汽油的阶段。[7]1
陆志韦这一段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分析,其实正折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在语言载体方面中西碰撞的状态。“小车”即喻指汉语,而“汽车”则喻指西方语言。陆志韦的理想是“旧的小车可以运输外洋输入的汽油。”而前提条件是“我们会用新的运输工具载运汽油,并且那运输工具本身也是得用汽油的”。也就是说,文言这辆运载旧思想的“旧的小车”必须转化为白话这辆运载新思想的“汽车”,并且白话与西方语言在内在相通。因此,陆志韦才坚决舍弃了文言用白话写诗,并且在白话诗的语言节奏、韵律、格式等方面做到与西方诗歌融通。《杂样的五拍诗》即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尝试。就像朱自清所说:“《杂样的五拍诗》正是‘创造’,‘创造’了一种‘真正的白话诗’。”[5]
[1]陆志韦.杂样的五拍诗[J].文学杂志,1947,二卷四期.
[2]陆志韦.我的诗的躯壳[M]//渡河,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3]陆志韦.论节奏[J].文学杂志,1937,一卷三期.
[4]陆志韦.白话诗用韵管见[M]//燕京大学燕园集编辑委员会.北平:燕园集,1940.
[5]朱自清.诗与话[M]//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6]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7]陆志韦.汉语和中国思想正在怎样的转变[J].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社会学界,第十卷单行本,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