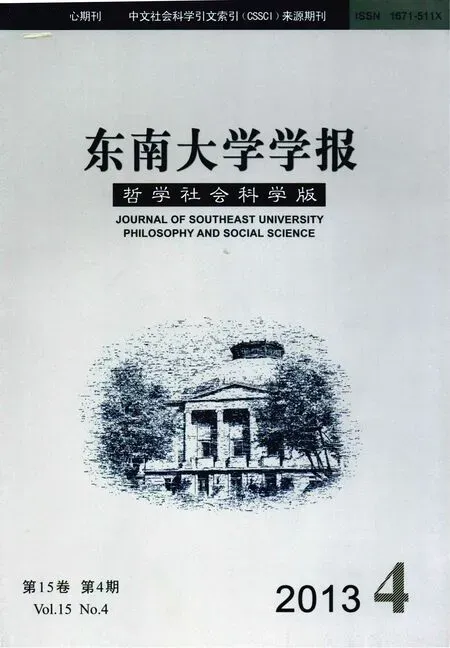元刊杂剧《诈妮子调风月》会校疏证及元杂剧原貌考论
许并生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诈妮子调风月》,王季思先生认为是不见于《元曲选》及《脉望馆抄校本杂剧》的优秀剧目,对其详加校订,并根据曲词和删节后的科白,探索剧中人物故事梗概,写成定本,不仅有便于探索元杂剧源流的学者,对改编优秀古典剧目,使之在今天舞台和银幕上的重现同样有用①王季思为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1980年6月6日所作的序,书第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先生注重文献整理和研究,重视其现实意义,在对待古籍的当代认识里是最全面的,也指出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诈妮子调风月》的校注和写定本在时间顺序上,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出版于1962年;王季思先生的写定本,发表于1958年的《戏剧论丛》第二辑,又经修改,收入《玉轮轩曲论》,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徐沁君先生《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也于1980年出版。宁希元先生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也作于1980年,《元刊杂剧三十种》多种校注成果几出现在同一时间,颇有意味。据宁希元先生校注本的吴小如先生的序,因徐先生的同书出版,宁先生原被允为付梓的书被退稿,直到1988年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年间对原稿重新修订增删,参考和吸收了诸校本的优点、纠正了其缺陷,用吴小如的话说是“譬如积薪,后来者自然居上”。由此宁本可视作这个时期本校注本最后成果②本文论证以宁本为的本。,然而吴小如先生仍在序里提出四个可商榷和可补充的方面,我们在学习阅读中也注意到仍有需订正之处。由此,对此做会校疏证是需要的,并可借此对元杂剧的多方面问题展开实证性探讨,这是本文所做的工作③各校注本所校一致,且语义文字通顺者不作讨论,如[那吒令]“等不得水温,一声要面盆;恰递与面盘(盆),一声要手巾;却执与手巾,一声解钮门。”此为顶针格,“盘”,各本校作“盆”,义通,不再讨论。。
一
《诈妮子调风月》开头相当于标示语的“老孤、正末一折”“正末、六儿一折”,以及第二部分套曲前的“外孤一折”“正末、外旦郊外一折”,第三部分套曲前的“外孤一折”“夫人一折”“末、六儿一折”,其用法表明“折”指人物出场后再回去,此语当代口语中仍使用,如“折回来”“折回去”用于指出来再回去,或出去再回来。“折”在本剧中并未用于剧本的内部单元和单元分隔名称,用“折”指杂剧的单元见于明代,如《元曲选》,对此有学者有专门的讨论④戚世隽《“折”的演变——从元刊杂剧到明杂剧》,中国古代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曾永义先生有专论。,杂剧剧本不分“折”,也不必分“折”,原因是四大套曲子自然形成分隔,一目了然,其二是用人物上下场的标示,将结构之间间隔开来,如果要称呼的话,称作“段”,理由是南宋官本杂剧称作“段”,如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元杂剧不分“折”当有剧本文学创作的原因,容后述。
标示语的第一部分“卜儿”,第二、三部分作“六儿”,宁本改为“六儿”,认为原本“六儿”误作“卜儿”,元曲中多称书童为“六儿”,有其依据。王定本、徐本仍依原本。然两者不矛盾,前者指示角色,后者指人物,诚如宁校所云“犹丫鬟之称梅香”,有其合理性,应从原本。由此表明,元代早期杂剧在叙事文本与戏剧文本上尚未融合,剧本尚未完全戏剧化。原因容后述。
前语后的宾白:“交燕燕伏侍去”,“交”各本均失校,原本“叫”,音假作“交”。“叫”义为使、让,今北方口语仍用。徐本注释五云:本剧“教”作“交”,所释不当,“教”虽有使唤之义,然与“叫”有语义、用法上的差异。“伏侍”,王本为“服侍”,符合语言规范,然“伏侍”意通。宁本“则你去”,王本作“只你去”,意为“只”假作“则”。然音假作“则”,本字当为“着”,两字皆通。全句为“叫燕燕伏侍去,别个不中,只(或着)你去”。
文本第一部分,仙吕套曲[点绛唇]文,“不曾交夫人心困”,“交”如上。全剧“叫”,音假作“交”;“跤”音形也假作“交”。如[油葫芦]“直到说得交(叫)大半人评论”,[天下乐]“合下手休交(叫)惹议论”。[后庭花]“这一交(跤)直是狠”。
曲[混江龙]文,“不抢白是非两家分”,宁本校作“一个”,语义不通。王本、徐本允当。宁本“普天下汉子尽他都先有意”,“他”,王本为“教”,徐本为“做”,据上下句文应为“普天下汉子尽(净)[叫]他都先有意”。“净”义只、光,句义:要使,假设句。
曲[油葫芦]文,“大刚来妇女每常川有些没事狠”,“大刚来”,失注,义但凡、基本上。“妇女每”,“每”失校,原本“们”,音假作“每”。“常川”失校,重文字符误为“川”,应为“常常”,重文符号见宁本注76。句为“大刚来妇女们常常没事狠”。宁本、徐本“更怕我脚蹅虚地难安稳”,“蹅”,王本为“踏”,当为“蹅”。“心无实事自资隐”,“资”各本均失校,原本“知”,音假作“资”。至今北方大多数地区团尖音不分。宁本“那时节旋洗垢求瘢痕”,王本、徐本为“不盘根”,宁本校注依据充分,意通,为是。
曲[鹊踏枝]文,元刊本“厅独”句,宁本“一个独卧房窄窄别别”,不当,“厅独”后应顿,句义为厅独、房窄。“窄”,北方音读“ze”,“窄别”两字皆入声字,现在口语仍用,故周德清《中原音韵》方有“入派三声”的规划意愿。“燕燕一身有甚末(么)孝顺”,“末”各本失校。
曲[寄生草]文,“诵的典谟训诰居(据)尧舜”,“居”各本均失校,语义不通,也不恭,本义为依据尧舜为模范来行为。
曲[村里迓鼓]文,宁本“见他语言儿栽排的淹润”,原本“裁排”非形误,宁本、王本校误。“栽”贬义,如栽跟头,栽赃。“栽排”义捏造、责怪。“裁排”意编造、编制、组织,当为“裁排”。此句义为说让人喜欢听的话。
曲[上马娇]文,“是他因子(只)管交(叫)话儿因”,王本“是他亲只管教话儿亲”,元刊本“因”,宁本注:因字古有亲义,见马致远小令[寿阳春],似可不改,这个意见是妥当的。本剧“子”作“只”。宁本[赚煞]曲文中的插白“油手巾”,校作“紬手巾”,当是。王本作“绸手巾”也当。
第二部分,中吕套曲[粉蝶儿]文“邻姬每(们)斗(逗)来邀会”,王本、徐本本失校。宁本校作“邻姬每斗草邀会”,不当,元刊本下句有“闲斗草”,上下重复,本句有引逗、邀请之义。元刊本“打千秋”,宁本作“打秋千”,义通,然平声阴阳不同,“千秋”北方口语仍用,似可不改。“早晨古(孤)自一家一计”,各本均失校。[朱履曲]“面没(音mo)罗呆答、孩(还)死灰堆”,王本、徐本校为“面没罗、呆答孩、死灰堆”均不当。元刊本上句“又不风(疯)又不呆痴”,故上下句均云两个方面的事。本句义为满脸呆滞而且难看。
曲[快活三],原本[江水儿],宁本从郑本改,当是。“老阿者使将来伏侍你”,“阿”语助词,作衬词。“展(沾)污了咱身起(体)”,徐本、宁本失校,王本作“展污了咱身己”,元刊本不会将简笔体刻成繁笔体,“身体”北方方言仍有读“shen qi”,“起”假音字。
曲[上小楼]文“玳瑁纳(紬或绡)子(只)交(叫)石头砸碎”,“纳”古字写作“内”,故与此无关,当为形误,这里指手帕。“铺持”,徐本注释云即指铺鞋底的布。语义较近,本义指裁剪衣服剩的废布块,以备做补丁用,也用来用浆糊多层拼接粘贴成稍厚的大布块,晾干后照鞋底样剪成,以多层合在一起用来纳鞋底。今北方口语仍用,“持”音“ci”。“粉各(圪)麻碎”,“圪麻”语助词,义颗粒物。“各”宁本校作“磕”,虽有征,然不贴切,注释云:粉团、胡麻,都是至脆之物,一经磕碰,即成齑粉,故借以为喻,非是。
曲[幺篇]“撚绡的”,宁本作“撚捎的”,注释语义明晰,即指手帕,则不必校改。“到(倒)重如细搀(缠)绒绣来胸背”,各本均失校。
曲[五煞]文“沙糖”,语义易明,应作“砂糖”,今韩国语中仍保留此古音读。[四煞]“打也阿儿包髻真加要带(戴)”,宁本校云:“打也阿儿”疑为女真语,待考。若头上包包髻为“打包髻”,则“也阿儿”为衬词。徐本“真加”注释作真的、真正的意思,当是,今韩国语中仍保留此古音读。“与别人成美况团衫怎能勾(够)披”,各本均失校。
第三越调套曲[斗鹌鹑]文“干支剌”语义一点也,完全。[紫花儿序]“好轻乞列”,“乞列”语助词,义费力气;“热忽剌”,“忽剌”语助词,义辅助强调特别、非常。“短古(祜)取恩情”,语义没福气。[幺篇]“怎当那厮大四至(肆)铺排”。“四至”合为一字。[紫花儿序]“铺(噗)的吹灭残灯”。[调笑令]“我说波(破)娘七代的先灵”。[天净沙]“我便似(窃)墙贼蝎蜇噤声”。各本均失校。[收尾]“不似这调风月媒人背厅(听)”,郑本校云疑是“听”字之误,但“背听”意不可解,存疑待校。郑本所疑当是。“厅”“听”繁体此相近,“聼”借“廰”的省笔为字,意为信息不灵通,闭塞,被蒙蔽。今口语有耳背的说法。
第四双调套曲[驻马听]文“夫人每(们)依时按序,细搀(缠)戎(绒)全套绣衣服。包髻是璎珞大真(珍)珠”。“雁行般但举手都能舞[舞]”,宁本注云:原“舞”字后有重文符号,依王校删。原文有重文符号,且“舞”的前一字为动词,后字为动作名词,故不能删。[水仙子]“你不合先(掀)发头恕(怒)”。[殿前欢]“服(眼)黑处全无”,各本校是。宁本注释云“眼黑”,吴语。不当。释“指怒目相视,翻眼不识人”,义对,然不贴切。王本说明“形容夫妇不和时瞪眼珠的神态”,较贴切。实指翻白眼,《晋史·阮籍传》称阮籍好翻白眼,在文人圈广为流传。[得胜令]“交(叫)我死临侵身无措,错支剌心受苦”,“死临侵”义呆呆地,像木头一样;“错支剌”义纠结、揪扯、头绪凌乱,“支剌”辅助强调难受。[太平令]“子(只)合当婢为奴”“子(只)得和丈夫”。前述之外,本剧文字均从宁本校注。
由此本剧基本读通,为现代读者所理解①宁希元《元刊〈古今杂剧〉中形声字的“省借”和校读问题》云:从其所省的具体内容来看,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都是元人仅有的、独特的习惯用法,既与古无征,又不为现代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因此,除少数现今沿用者外,都应回改为本字。《金元小说戏曲考论》第48、49页,香港文星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本文从宁先生“与古有征”,“又为现代读者理解接受”的校注原则。本文作前,宁先生寄来本书及长信,颇受教益,谨兹致谢。。由是观之,有两点有必要说明,一是元杂剧至少早期剧作读音存在团、尖音不分现象,二是读音存在入声字,并非已“入派三声”。采用语音以山西中北部、内蒙南部、河北西部为主体,元蒙人于北京建大都后,未实行语音统一工作,文人虽云集居留于此,然写作并未全部采用大都语音。
二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读通,为解开元杂剧剧本和演出的疑案提供了依据。就元代杂剧的剧本基本只录曲文看,与元代文人将其视为作乐府直接关联,《中原音韵》虞集序称“北乐府”,讲“兴乐府以协律”,“文、律二者”“兼美”。周德清自序有“言语一科,欲作乐府”,“使成乐府”的说法。罗宗信序称“大元乐府”。锺嗣成《录鬼簿》有所谓“有乐府行于世者”。元人把写杂剧作为作乐府看待,首先是从文学上看待,所谓“成文章”。宁希元先生《元曲语词解诂的几个问题》注意到这个情况,不过认为乐府在元代专指当时的散曲而言。[1]92-93实际上散曲和用于戏曲的曲子在艺术本体上是同类,近代为了区分两者才有了“剧曲”的说法,故元代乐府的说法当也包括“剧曲”写作。
元代文人写杂剧视为文学创作,不过认为这种文学创作与以往不同,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说“必使耳中耸听,纸上可观为上,太非止以填字而已,此其所以难于宋词也”。周德清自序所谓“乐府之盛、之备、之难”,“彼之能遵音调,而有协音俊语可与前辈颉颃,所谓‘成文章曰乐府’也;不遵而增衬字名乐府者,自名之也”的不同之处。《录鬼簿》有“平日所学”与“歌曲词章”相区别的说法。“歌曲词章”按今天的话说属于音乐文学创作的范畴。然而杂剧不仅是音乐文学,而是叙事的音乐文学,所以《录鬼簿》有所谓“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说法,义指其为敷衍故事者。
其次基本只录曲文、简书人物行动标示语,如《诈妮子调风月》开篇书“老孤、正末一折”“正末、六儿一折”“夫人上,云住”“正末见夫人住”“夫人云了,下”“正末书院坐定”“正旦扮侍妾上”,表明演剧界当时有同剧目演出,至少有同内容的小说,因为如此写来读者都知道,都能读明白。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同剧目的演出可能性大。
当时演剧界的杂剧演出,其歌唱的比重有多大,因民间没有记录而无法比较。就目前所见文献看,即使有剧中歌唱,似以锣鼓来伴奏,类似今天发现的“锣鼓杂戏”或“干板秧歌”。其演唱歌词绝不会像作家所写的极具文采和叙事述情周至,否则作家就没必要写了,这是艺术实践的规律。退一步说,其歌唱的曲文也有文采和叙事述情细致,作家对此不满意而另作一套曲子,按当时文坛的习惯是会以小序的方式说明。今存山西明应王庙杂剧演出壁画演剧人物有操丝弦、管笛者,那是对“散乐”的描绘,“散乐”包括唱词曲者。由此,作家针对杂剧表演所写的曲文完全是新型的。
上述情况与杂剧演出史相关,所谓杂剧是杂戏,其义有二,一是多种表演杂陈,二是表演剧目题材类型多样化。其演化过程,《青楼集志》云“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原因是“‘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简言之,院本是闹剧,杂剧是正剧。演出题材类型有“驾头、闺怨、鸨儿、花旦、披秉、破衫儿、绿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长里短之类”,所以总称“杂剧”,主要演出于“京师”“郡邑”的“勾栏”。作为舞台的表演既有院本的节目,也有杂剧的节目,总称“散乐”。上述情况后来人们都不大清楚了,又因“杂剧”一词,把作家的剧本和演员的演艺对象混为一谈。
三
杂剧演出的剧目类型是根据题材而分,又和角色行当即演艺有关,与作家的剧本写作无直接关系,即作家并未按照演艺的剧目类型来写作。
杂剧所作剧本是否为演艺界演出,目前史上无征,据史料记载,杂剧作家与演员有交往,然《青楼集志》所有演员没有演出当时所写杂剧剧本的记述,目前所见记述当时城镇勾栏、农村寺庙、集会的文献,也未见有采用当时作家做写剧本的记载,[2]42-48包括所见各种舞台碑记与图谱。杂剧演员有演唱,也有唱当时作家所写,然演唱的只是杂剧作家所写的词曲,《青楼集志》有明确记载。杂剧剧本的文学创作,与当时的舞台剧演出处于双水分流状态。两者合一应在明初,至少在元末的《青楼集志》之后。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剧本汇刊本的判断是没错的,但书名不似元代当时的名称,倒颇似元代以后至少是明人的称呼,如臧晋叔之《元曲选》。杂剧剧本创作在元代地位很低,在文人圈也颇有争议,杨维桢《沈氏今乐府序》认为把关汉卿、庾吉甫的杂剧看做“治世之音,则辱国甚矣”[1]93,王国维说“元杂剧之为一代绝作,元人未知之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的评价符合史实。由此当时剧是演当时的剧,文人按照当时的演剧来专门谱写乐府,形成文学产品,故形成元刊本只录曲文的现象。
还可能是书坊激赏曲文,故只录曲文,为了卖与文人,除此而外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当时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了。但是,当时的人对简录宾白或不录宾白的曲文文本可以读懂,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元杂剧的剧本体制与艺人的演出形式,在元代初中期是两驾马车。至于元代的书会先生为演艺人所写的剧本,可能是演出本,类似后来演艺界所谓的“草梁子”,而不是文学本,演出本是纲要式的舞台的故事表演本,两者尚不是一回事,对此史上无征,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解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杂剧剧本与当时无论城镇勾栏,还是庙会和村庄的杂剧演出形态的记载存在诸多不一致。而且庙会和村庄的戏剧表演者重于祭祀活动,这个现象一直保留在建国初的“移风易俗”“反对迷信”前,这个历史是客观的。这类活动的戏剧表演的特点是戏杂,多是小戏,以说为主,山西潞城曹村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的表演,贵州的地戏、傩戏表演说明了这种情况。就戏曲文本的文学水准看,除了皇家以及明清达官贵人的家戏班外,不会有元杂剧那么高的文采和深厚的文学底蕴,包括城镇的勾栏。元杂剧的口语化是“嬉笑怒骂”金元散曲风格的放大,对此明代文人把它作为圭臬,因为要用于听,和情感表达直率,明人《元曲选》追捧的就是这个地方,反过来说明明代的戏曲尚与此有很大距离。
杂剧剧本的叙事与其他的“讲述”的叙事类型不同,是“显示”性的叙事[3]10。《诈妮子调风月》标示语的“上”“下”“闪下”,突出反映了显示性叙事的写作,作家叙事显示的界域定格在拟台口的四方框内,角色进入和退出为上场和下场,上场后下场为“一折”,角色在框内已无叙事任务则以“闪下”退出,尚有叙事任务的则为“住”停留在框内。当然这在今天的戏剧剧本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在元代以文学创作的延续和延伸,就成为及其新颖和突出的事,换言之,尚属于文学系统而非“剧学”系统。所谓“延伸”是有当时的戏剧表演可做模拟和比拟。杂剧作家依照舞台演出剧来做乐府,故《诈妮子调风月》剧本标示“老孤一折”、“正末一折”“夫人云了,下”,基本上不写宾白。
杂剧所编一本“传奇”采用四套曲子,为四段式曲式结构,承担故事的开端、发展、变化、结尾的歌唱式陈述。由于文学创作以一个角度写乐府词,故形成一人主唱的特点,这是文学创作的性质。所形成的旦本、末本类型,当与当时舞台演出剧的流行类型相关。对此后人混为一谈了。
[1]宁希元.金元小说戏曲考论[M].香港:文星图书有限公司,2008.
[2]李修生.元杂剧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3]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周德清.中原音韵[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夏庭芝.青楼集志[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6]钟嗣成.录鬼簿[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7]朱权.太和正音谱[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8]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