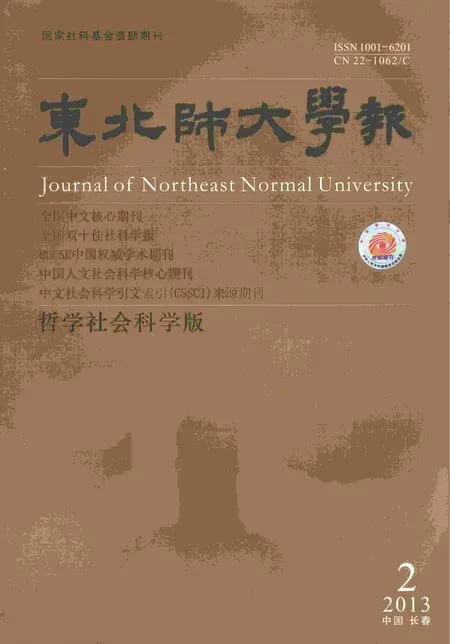郁达夫创作与翻译的美学一致性
张万敏,马建华
(长春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32)
郁达夫是“五四”文坛上与鲁迅并称“双峰”的优秀、多产的作家,他涉足文坛30余年,发表了近50部小说。他有留洋经历,精通英、德、法、日等多门外语,是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天才,然而他在翻译方面却并不多产。他单独发表的译作仅有28篇,其中包括3首诗歌、10篇小说、15篇杂文。在文学工作者地位卑微、多数作家难以靠创作活命、不得不靠兼做翻译聊以为生的旧中国,这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难以付诸实际的。这充分说明了郁达夫翻译选材之严格以及他对翻译所持的审慎态度。郁达夫的创作与翻译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二者有着极大的美学一致性。本文所探讨的郁达夫创作与翻译,主要是指他的小说类作品。
一、从作品看郁达夫创作与翻译的美学一致性
(一)作品中的“零余者”人物形象
郁达夫“最喜爱、最熟悉”[1]552的作家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子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1]552。郁达夫读了很多屠格涅夫的作品,写了《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等文章,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屠氏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给了他诸多启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十之八九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零余者》);他们虽有改变个人命运和报效祖国的强烈欲望,却苦于没有机遇、毅力或勇气去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们“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事物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青烟》)。理想的幻灭导致更大的精神空虚,他们变得更加孤僻、忧郁、敏感、脆弱,或是仰天悲叹“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一出毫无意义的悲剧”(《蜃楼》),或是沉湎于酒色以宣泄郁闷,如此又引发了更加深刻的“沉沦”,彻底沦落为“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茑萝行》)的“零余者”。这正是“零余者”的三部曲:从满怀理想、追求积极的人生到现实的残酷、理想的幻灭再到沉沦或自戕。譬如《杨梅烧酒》,主人公留学海外学习应用化学,满怀希望想学成回国后建一座工厂以报效祖国。然而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他的满腹经纶、满腔热血却是没有用武之地,理想最终破灭,这叫他怎能不沉沦?
郁达夫译作中的主人公也多是“零余者”。他们经济拮据、生活贫困,常常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被边缘化了;他们多愁善感、空虚压抑,情感也无所寄托,终日落落寡欢。《一个败残的废人》中的那个“出身高贵”却因“自己不习上”而导致中道败落的艺术家,他酷爱艺术,对艺术有着绝妙的构想,乃至于高呼“艺术万岁”;他嗜酒如命而又酒后无德,不断与人争吵以至于无人同他往来,“所受的教养痕迹一点儿也没有了”,形同“无聊的放荡败落的下流文乞”,最终被家人寄放在乡下。酒醉后,他颓废地高叫:“我是一只难破的船……一个败残的废人”[2]149-165。《浮浪者》则刻画了一个快乐、勇敢的浮浪者与八个受过良好教育却懦弱、疲惫的贫民形象,他们经济上无钱、政治上无权、精神上空虚(除了浮浪者本人之外)、情感上空白,又是一群“零余者”。
(二)作品的格调多呈现灰暗、感伤、颓废的色彩
“感伤主义”(也被郁达夫称作“殉情主义”)深受郁达夫的推崇:“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弃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莎士比亚的剧本,英国18世纪的小说,浪漫运动中的各诗人的作品,有哪一篇完全脱离感伤之域?”[3]243“感伤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缺少猛进的豪气与实行的毅力,只是陶醉于过去的回忆之中。而这一种感情上的沉溺,又并非是情深一往,如万马的奔驰,狂飙的突起,只是静止的、悠扬的、舒徐的。所以殉情主义的作品,总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1]128-129他认为这种文学思潮产生的语境是“国破家亡,陷于绝境的时候”,或是“生活不定的时候”[1]129。郁达夫的文学实践也颇受“感伤主义”的影响。无论是在创作中还是在翻译中,他都极其注重主观抒情,着意描写人生的悲苦和不幸,重点刻画人的精神痛苦和情感危机。“阅读郁达夫的小说,浓郁的感伤气息可谓扑面而来:感伤的个性与心理,感伤的情节与环境,感伤的情绪和氛围,感伤的抒情与叙事……这一切因素的融合,构成了郁达夫小说的感伤美学风格。”[4]49《南迁》中的伊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外语水平很高,还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同情大众。他胸怀三大抱负:金钱、爱情、名誉,有志为祖国奉献青春和智慧,却又为社会所不容,报国无门。最终他的理想破灭,纵情酗酒,自甘堕落,忧伤、凄凉无处不在。难怪人们常说,郁达夫的《沉沦》是悲鸣之作,《茑萝行》是悲哀的结晶,《寒灰集》是诉苦愁的哀曲,甚至连《春潮》中对儿童生活的描述也含着淡淡的哀伤和童心早熟的苦泪。
读郁达夫的译作,我们也几乎感受不到快乐和阳光,只有灰暗的色彩叠加着颓废、感伤、阴郁、悲苦等情绪,逐渐将读者的视线引向悲苦的人生,将读者的情绪引向忧郁、低沉。《幸福的摆》为我们弹奏了一支凄美的爱情悲曲:高中教员华伦爱上了百万富豪的女儿爱伦琪儿玛,却因为门第差异无缘牵手,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姑娘嫁入豪门;从此华伦开始浪迹天涯,直至弥留之际,他才听到他钟爱一生、等待一生的女人说:“我是爱你的,老早就爱你的,还没有把你忘记过。”[2]73这个故事还揭示了这样一个生活哲理:期待越高,失望越大;而当你无欲无求时,便再也没有失望和痛苦了。还有《马尔戴和她的钟》、《一女侍》等几部译作也都是关于普通人的悲剧,其中的主人公或因失去了他们的最爱而过着凄惨、孤独的生活,或因过度劳累、忧郁而失去健康乃至生命。故事的色彩都是灰色的,情调都是感伤、沉郁的。
(三)强调作品的主观性、抒情性,而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设计和人物形象的刻画
郁达夫的小说常被称作散文化现代抒情小说或“自叙传小说”,这是由他首创的一种新的小说体裁。这种小说一般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不注重精心刻画人物形象及性格,但是它注重主人公通过直抒胸臆的反复咏叹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展示自己的心理活动和内心独白,作品的语言多为娓娓道来的抒情散文式的,简单质朴、清新绮丽、韵味十足、流动性鲜明,彰显着散文诗的风格,作品中鲜有人物对话,并自由地插入诗歌等。这与传统的情节小说截然不同。譬如他的早期代表作《沉沦》就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对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等着墨也不多,但是对主人公主观情绪的宣泄、内心苦闷的传递却是浓墨重彩。他的后期代表作《迟桂花》同样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没有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作者以“迟桂花”这种自然景物为自己情感与理想的隐喻,是一个象征性的抒情形象,其他主要人物形象也多是象征性的抒情形象。
郁达夫的译作也多注重主人公的心理及情感的表达,而不注重曲折情节的构思和鲜活人物形象的刻画。《马尔戴和她的钟》中的孤女马尔戴自双亲去世后便失去了欢乐,离群索居,十年里与一个“她最能谈话的伴侣”[2]10和她“在一道的经过了许多甘苦”[2]14的旧钟相依为命的哀婉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只有“我”和马尔戴,所谓的情节也不过是以时间为线索,白描了马尔戴从天真的少女直至人近中年时暮气沉沉的生活,其中穿插了些许对往事的简单回忆。然而小说对马尔戴凄清、封闭、孤寂、苦闷等心理及情感的传递,却是非常成功。《一女侍》则以悲哀的语调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姑娘的凄惨遭遇。她漂泊到巴黎,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个咖啡馆里做女招待,她得了肺炎却无钱看病也不能休息。该作品同样没有用很多的笔墨刻画女招待的形象,也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描绘女招待的悲惨经历,只是通过“我”的旁观视角,夹杂着女招待轻描淡写的自我述说,以及咖啡馆里其他客人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最终绘成了一幅被命运“拨弄到极边的咖啡馆”[2]24的女招待悲惨一生的素描。郁达夫的译作中也鲜见浓墨重彩地描绘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多通过对人物心理、情感的描述,通过周围人的视角和语言,反映主人公的性格、境况及命运等。
(四)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偏爱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阅读了1 000多部外国文学作品,深受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郁达夫认为浪漫主义“把理智和意志完全拿来做感情的奴隶。情之所发,不怕山的高,海的深,就是拔山倒海,也有所不辞”[1]131;它是“情热的、空想的、传奇的、破坏的”[1]131。郁达夫非常崇拜卢梭(被其称为“卢骚”),认为“他的精神,到现在还没有死,他的影响,笼罩下了浪漫运动的全部”[1]375;世人对卢梭的不公正批评令郁达夫极为愤慨:“喜马拉雅山的高,用不着矮子来称赞,大树的老干,当然不怕蚍蜉来冲击,……小人国的矮批评家,你们即使把批评眼装置在头顶的发尖上面,也望不到卢骚的脚底,还是去息息力,多读几年卢骚的书再来批评他吧。”[1]359郁达夫还撰写了《卢骚传》和《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等文章,翻译了卢梭的著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极力向中国读者推荐卢梭。在卢梭的影响下,郁达夫格外强调文学的主观性,认为自我表现是文学的主要功能,文学中的情感表达远重于理性思考,文艺的重点应放在个人经验、个人想像及个人情感的传递上,文学家应更多依赖自我感觉。郁达夫的小说,如《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等多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所翻译的小说,如《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爱的开脱》、《理发匠》等也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郁达夫先天的感伤气质以及后天造就的忧郁气质使得他对充满凄凉、哀婉、痛苦、忧伤等格调的文学作品格外偏爱,所以他对唯美主义情有独钟。他曾撰写了《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介绍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还写了《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评价珰生诗歌的翻译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学思得”翻译观。他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就是取材于珰生的一段罗曼史。“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总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1]466这正是他感伤、苦闷、厌世、颓废等唯美情绪的一种近乎真实、自然的宣泄。他的译作《一个残败的废人》、《马尔戴和她的钟》、《幸福的摆》等也都具有鲜明的感伤、颓废、苦闷等唯美倾向。
二、郁达夫创作与翻译的美学一致性的其他佐证
对于翻译,郁达夫认为,“译文在可能的范围内,当使像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当然是要顾到的,可是译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样”[1]615。可见,他在尊重原作者的思想及原作意义的同时,强调要以创作的精神对待译文,并尽量使译文在文字、风格等方面与自己的创作风格保持一致。他同时代的作家、评论家也认为他的翻译与创作有着诸多的相似性。邹啸认为郁达夫“所译的《小家之伍》几乎是他的创作,因为那些外国人所要说的话正也是作者自己所要说的话。”[5]序1还有,《幸福的摆》发表后,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他本人的创作,沈从文就是其中一例,他以为这是郁达夫自己所做的小说,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外国人的假名而已”[1]628,因为它在表现手法和写作风格上与郁达夫所创作的小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后世的研究者也认为郁达夫的翻译与创作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谢天振、查明建说:“创造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郁达夫……的翻译活动与他的创作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翻译的选择和其创作中的借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他所译介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和德国作家林道,恰好都是对其创作影响极大的外国作家。”[6]76刘久明也持相似的观点:“郁达夫的小说不仅在表现内容和人物塑造上与施笃姆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艺术风格上,也明显地借鉴了施笃姆。”[7]162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郁达夫的创作与翻译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美学一致性。
三、郁达夫创作与翻译的美学一致性的影响及意义
郁达夫创作与翻译在美学上存在着鲜明的一致性这一特色,反映了创作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共同发展。首先创作影响翻译。承担翻译任务的译者,不可能不受到目标语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影响;译作的意义,也诞生于目标语的语言及文化语境之中,它必然要受到目标语语言、文学、美学及文化等观念的制约。有些情况下,译者在翻译选材时就刻意寻找与目标语中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作品的特色、风格相类似的原语作家之作品来翻译,或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采用相似性的翻译策略,刻意采用与目标语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篇章结构、写作风格等方面相类似的手法来翻译,使读者感觉似曾相识,在心理上产生亲近感,这有助于译作在目标中的接受和传播。反过来,翻译也影响创作。有些创作就是在翻译的影响和刺激下而诞生的,有些创作本身就是着意模仿翻译作品而为的,其中的语言、结构、主题及写作手法、美学特色等均与翻译作品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好的翻译可以使一些原本一般的原语文本得到较好的阐释与传播;也能使一些原本较差的原语作品获得新生,以崭新的面貌走入读者视野;还能使一些原本优秀的原语文本更加生机勃发,光彩照人。出身于文学家的郁达夫,他的翻译自然会受到他的创作经验及技巧的影响,同时他也会主动选择一些与自己的美学品味、写作风格比较相近的作家作品来翻译;身为翻译家的郁达夫,他的创作也自然会受到他的翻译经验的影响,把在翻译过程中学到的写作技巧、叙事手法等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创作中去。他于翻译中学习创作,于创作中领悟翻译,二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最终锤炼出了一代文学宗师和翻译大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个性鲜明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郁达夫非常偏爱散文化抒情小说。他所注重的不是如何对人生和社会现实加以客观的反映或揭示,而是如何对作品中人物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情感进行率真而深刻的表达。这种独具特色的写作手法,强烈地冲击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以载道”、“抒情言志”等传统文学观及美学观,为“五四”文学开创了新的文体形式,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丰富了文艺美学的内涵。
郁达夫文学实践中的这一特色还说明,对于一国之文学,翻译与创作同等重要。盲目地崇洋媚外,只把眼光放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而忽视本国的文学创作,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学的滞后、衰落,必然导致它在世界文坛的失语和边缘化;然而注重创作而忽视翻译、过分褒扬创作而贬低翻译或者把翻译视为创作的附庸,同样也是偏颇的,文学的近亲繁殖必然导致创作才思的枯竭、写作技术的陈腐,最终还是要招致本民族文学的枯萎和衰竭。一国欲图文学之发展,必须翻译与创作二者兼重,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都将误入歧途。这对于当下及今后的文学建设都具有警示性意义。
[1]郁达夫.郁达夫文论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2]郁达夫.郁达夫译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3]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上)[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4]刘久明.郁达夫与英国感伤主义文学[J].中国文学研究,2001(2).
[5]邹啸.郁达夫论[C].上海:北新书局,1933.
[6]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刘久明.郁达夫与外国文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