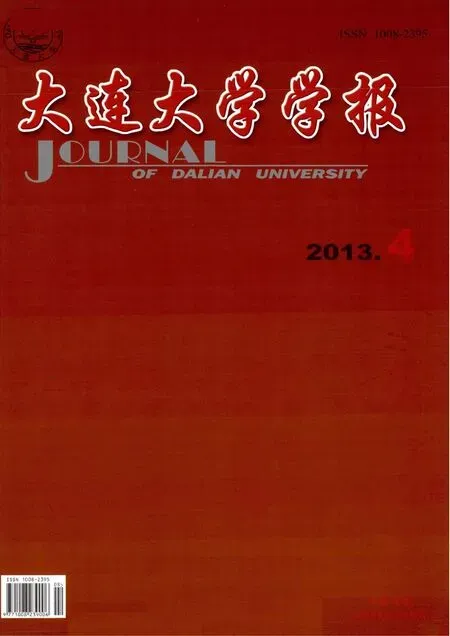试论宋代西南民族边区羁縻政策的特点
高小强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系,甘肃 合作 747000)
一
羁縻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政治统治政策。这种政策,采取笼络和松散管理方式,有利于处理中央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使其不产生异心,各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北宋建立后承前代之策,于西南民族边区设置了大量羁縻州县峒,以控御四夷、确保边地安宁。因此,羁縻政策是宋代一项非常重要的民族政策。马大正、杨建新、王钟翰等先生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的研究[1]。袁波澜、敏生兰、黄丽探讨了唐、宋时代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并从纵向和横向、宏观和微观比较两朝代羁縻政策之异同,总结两代民族政策的经验、作用和影响以及对于解决当今国内民族问题的现实意义[2]。郭声波认为,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总体上趋向灵活和宽松[3]。姚兆余指出,北宋统治者虽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制定和实施了招降纳顺、怀柔绥抚、羁縻远人、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但歧视和怀疑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思想影响和制约着北宋王朝的边政策略[4]。胡建华对北宋政府“以夷制夷”政策形成的原因和实施效果作了较详尽的论述[5]。戴建国指出,宋朝出于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给予种种优厚的待遇,一方面用各种优厚条件招徕归明人,对归明人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这一方面体现了宋政府开拓边疆、守固边防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朝对边地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思想[6]。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羁縻政策的特点作一重新探讨。
北宋初期,西南边疆民族政权林立。宋太祖赵匡胤经过多次征伐或招抚,先后吞并荆、湘,灭后蜀,至开宝八年(976年)十一月,宋军基本平定江南,“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诸州直隶京师”[7],南方实现了统一。统一南方后,宋在西南诸边族聚地设成都府路、夔州路、荆湖北路、南路,潼州府路和广南东西等路(即今天的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进行行政管理。在制度上,宋承唐制,设置羁縻州、县、峒,采取羁縻州统治形式进行统治,“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制为羁糜州”,“树其酋长,使自镇抚。”[8]
二
何谓羁縻?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尚书》云:“周礼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镇、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羁縻而已,不可同於华夏,故惟举六服。”《史记》亦云:“盖闻天子之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唐朝时期,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羁縻州县,主要分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4级,“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9]。这些羁縻州县,由中央任命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刺史或都督,并允许世袭其职,但受都护府、边州都督府或节镇的统辖。羁縻府州户籍一般不上报户部,也不承担赋税,但需承担向唐朝贡献。
根据龚荫先生的研究,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州共有263个,主要分布于黎州、雅州、茂州、威州和叙州等地,羁縻县22个、峒11个[10],笔者对此赞同,现根据《宋史·地理志》对宋设羁縻州县做如下统计:
黎州,设羁縻州54个[8]卷89,2213;雅州,设羁縻州44个[8]卷89,2212;茂州,设羁縻州10个[8]卷89,2214。
威州,设羁縻州2个[8]卷89,2214;叙州,设羁縻州30个[8]卷89,2218;泸 川,领 羁 縻 州18个[8]卷89,2219;绍庆府,领羁縻州49个[8]卷89,2226,2227。南宋时期,增至羁縻州56个;重庆府,领羁縻州1个:溱州,领荣懿、扶欢二县。以酋首领之,后隶南平军[8]卷89,2228;邕州,设羁縻州44个[8]卷89,2240,2241;融
州,设羁縻州1个:乐善州[8]卷89,2241;庆远府,领羁
縻州10个[8]卷89,2243。
宋代羁縻政策基本沿袭唐代,但在唐朝基础上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将唐代“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发展为“录用酋长,以统其民”的土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土官的封建隶属关系非常严密,由于土官为朝廷命官,直接对朝廷负责,所以它有严密的统治体系和衙门建制。这套土官制度,经元代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土司制度,成为元明清时期在西南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首先,北宋羁縻政策的重点是生蛮地区,主要是通过赏钱物的形式表示宋朝廷对少数民族的恩怀,促其自愿归顺宋廷,进而实现周边民族社会之安宁。因此,北宋立国后,在朝廷统治力量较强的西南地区,通过建立州县、配赋征役等实施直接统治;而在朝廷统治力量较弱的地区则选任少数民族地方土著首领实行委托统治(即间接统治),实施前代羁縻之策,选任有勇有智者镇守。史载,“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惯、习险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除辰州刺史,终太祖一世,无蛮陌之患,而边境妥安。”[11]这种被宋朝廷选任的当地土著官员非常多:如乾德元年(963年)七月,宋以彭允林为溪州刺史、洪赟为万州刺史[12]卷4,乾德元年癸亥,98,乾德五年(967年)六月,宋太祖授龙彦瑫为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蕃落使,武才为怀化将军,若启为归德司阶,若溢等8人“并为司戈”[12]卷8,乾德五年六月丁亥,195。
其次,羁縻州县官吏具有很大的自治权力。羁縻州县地大多数原为土官统治之制,“茂州旧领羁縻九州,皆蛮族也。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13]卷13,宋设羁縻州后,州刺史仍在管辖区内有任命下属土官、统治土民和世袭官职的自治权利。其州将“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所谓“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听自补置[8]卷493,蛮夷列传一·西南溪峒诸蛮上14178。”与“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相适应,各州刺史及属下峒主、头角官等均由原部落首领担任,其职名依籍而授。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宋神宗诏:“荆湖、广南、川峡、陕西、河东经略安抚钤辖司,具化外羁縻归明蛮、猺、夷、獠、熟户蕃部合补职名资级请授则例,及前后所补职名恩数异同以闻,按以置籍”[12]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未,7802,
且官职允其世袭、俸禄优厚,甚至给予“一州 租 赋[8]卷493,蛮夷列传一·西南溪峒诸蛮上14172”; 乾 德 元 年(963年),师裕长子彭允林袭任溪州刺史,治所迁至龙潭城(今麻岔乡弄塔),辖地无变动。
在各自管辖区内,州刺史甚至可拥有称为义军、土丁的土兵武装。羁縻州自己保留的部族军队,职责主要是守土守疆,是一种寓兵于农的组织,土兵平时为农,战时出征。土兵享有不纳赋税的待遇,所起作用很大,咸平年间“生蛮叛”,宋朝廷征调高州土兵讨伐,擒生蛮660余人,夺回汉人被俘者400余人。天圣年间(1023年—1031年),下溪州刺史叛,宋令高州刺史率土兵搜捕。类似这类对少数民族的征伐,不调朝廷一兵一卒。
第三,羁縻州县的疆域不大。根据“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的原则,宋代羁縻州县的疆域往往以某一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区域来确定,这一区域既可以划为一州,也可立为数州,故地域比当时的边郡要小得多,如宋仅在土家族地区就设置了八十七个羁縻州。就鄂西而言,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施州归宋,曾设清江郡军事,以后置羁縻州郡于清江南境。施州初属江南西道,后属夔州路,辖清江(恩施)、建始2县,在施州南部,还设有安定州、高州、顺州、富州等小羁縻州。
第四,惠而不苛。由于宋朝廷对西南边族以“务在羁縻”为要,因此,政府官榷和贸易方面的规定也有所放松或解禁,允许施州蛮以粟易盐:“咸平中,施州蛮入寇,诏以盐与之,且许其以粟易盐,蛮大悦。而后因饥,又以金银倍实直质于官易粟,官不能禁[8]卷496,蛮夷列传四·施州蛮,14242。”鉴于此,熙宁七年(1074年),北宋订立了《施州易粟法》规定:“施州蛮以金银质米者,估实直,如七年不赎,则变易之。著为令[8]卷496,蛮夷列传四·施州蛮,14242。”而且,北宋对各族首领的贡赋要求不苛,土地、户口均不入户部,但羁縻州县对中央王朝有上赋税、股徭役、入贡及供征调兵源的义务,作为朝廷命官的各州首领,则要定期向朝廷纳贡,入贡物品自然主要是各地土特产品。不过,朝贡贸易主要是宋朝通过丰厚赏赐羁縻笼络各族首领的重要政治手段。正如北宋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的吴淑论道:“蕃戎靡不贪慕财贿,国家诚不爱重币珍玩以啗之,爵赏荣耀以诱之。显示之以中国强盛,喻之以中国富厚,待之以至诚,临之以威重,夷落岂敢不从服哉。”[12]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已卯,1088蛮夷向北宋朝贡,北宋对朝贡首领加赐银两、给予重赏,如贡方物者每人赐彩帛3匹、盐20斤;无方物者每人也赐彩帛2匹、盐10斤。因此,朝贡显然成为政治上一种臣服的标志,“以辰州溪峒彭师宝知上溪州,仍令乾元节贡献如旧。师宝,仕羲之子也。盖自咸平已来,始听溪峒二十州贡献,岁有常赐,蛮人以为利,有罪即绝之。庆历四年,仕羲以罪绝贡献。其后数自诉求知上溪州,至是始许焉。”[12]卷170,皇祐三年正月戊寅,4078宋朝以此作为制约各羁縻州的手段,并对各羁縻州蛮夷的朝贡次数和人数也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四
为了减轻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朝贡负担,宋朝廷也因时因地对进贡物品、年限、人数等做了修改,以体现政府宽怀为民、羁縻远人的人道精神。天圣四年(1026年)八月,宋仁宗根据转运使北海王立请求,“诏施州溪洞安远、天赐、保顺州、南州、顺州等蛮入贡京师,道路辽远,自今听以所贡物留施州,其当施物,就给之。愿自入贡者,每十人许三两人至京师,其首领听三年一至。”[12]卷104,天圣四年八月已丑,2420明道元年(1032年)三月,因黎州卭部川山前后百蛮都王黎每三年一入贡的请求,宋仁宗“诏谕以道路遐远,令五年一入贡。”[12]卷111,明道元年三月丁酉,2579熙宁八年(1075年),广南西路经略司上疏:“西南蕃龙、罗、方、石、张、姓五族蕃部,或四年,或五年、七年一入贡,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张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龙、罗、方、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所贡惟毡、马、朱砂,往来馆券供给,并到阙见辞赐钱、绢、衫常,为钱二万四千余缗,而他费不在此。体访五蕃往来万里,颇惮艰苦,若令止邕、宜州赐钱物,可免公私劳扰,且便远人。”宋神宗“诏西南蕃五姓蛮听五年一入贡,不愿至京,听就邕、宜州输贡物,给恩赏馆券,回赐钱物等遣之[12]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卯,6451。”
总之,北宋对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的首要目标是边地安宁。在北宋君臣看来,控御四夷之术,唯羁縻而已,只有外夷怀服,中国才能安宁。针对西南旧边过去统治无力、社会弊端经常滋生的现象,“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旧无城,惟植鹿角。蛮人屡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辄取货于民家,遣州将往赎之,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茂州民甚苦之”[13]卷13,252-253,宋朝在西南边区选任土著首领统治当地、实行羁縻政策,置城邑、通道路、贸易,极力强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封建统治之下,使其“奉正朔,修职贡”,“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城邑以抚治之”[8]卷495,蛮夷列传三·抚水州蛮,14209;“咸平中,施蛮尝入寇,诏以盐与之,且许其以粟转易,蛮大悦,自是不为边患。”[8]卷496,蛮夷列传四·施州蛮,14242与此同时,北宋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一些重要城镇派军驻守进行武力控制,并对各种悖逆封建政府的行为予以严惩。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宋客省使翟守素调潭州兵镇压了苞汉阳、顿汉凌的叛乱。
宋代羁縻政策反映了中原汉族统治者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民族态度。鉴于西南诸族位居崇山峻岭之间,交通不便,所以朝廷认为,“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8]卷493,蛮夷列传一·抚水州蛮,14171”,这种民族态度的根源在于宋代统治者“华夷有别”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其实质仍然是中国古代王朝“以夷制夷”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夷荆、舒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于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14]。但是,宋代羁縻政策中体现了政府宽怀为民、羁縻远人的人道精神,客观上的确收到了一定效果,“再雄感恩,誓死报效。终太祖世,边境无患[8]卷493,蛮夷列传一·抚水州蛮,14172”,这是值得肯定的。
[1]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袁波澜,敏生兰,黄丽.唐、宋民族政策–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3]郭声波.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1).
[4]姚兆余.论北宋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J].甘肃社会科学,1993(3).
[5]胡建华.北宋前期“以夷制夷”政策初探[J].中州学刊,1988(1).
[6]戴建国.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归明人的政策[J].云南社会科学,2006(2).
[7][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1:51.
[8][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M].北京:中华书局,1975:903.
[10]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17.
[11][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3:1.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M].北京: 中华书局,1989.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考10[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