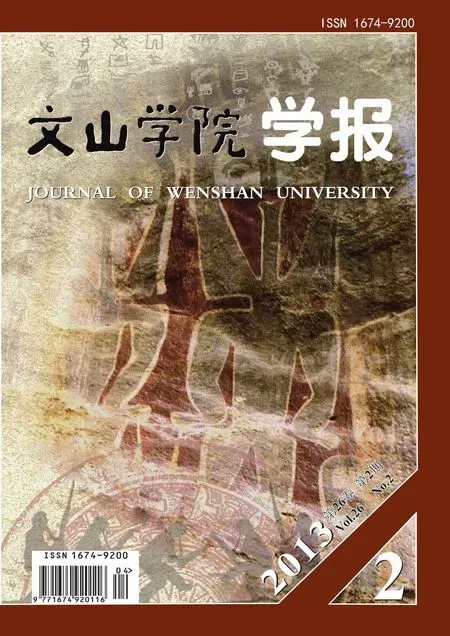不屈的灵魂
章艳萍
(文山学院 外语系,云南 文山 663000)
喜欢福克纳的作品,甚至是喜欢美国南方文学的读者,对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不会感到陌生。该小说以其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以及多线条穿梭式的叙事模式吸引了众多读者,也被评论家们称为“一部远未读懂的小说”[1](P31)。小说所体现出的人性思想及人性光辉,更好地凸显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成为了福克纳描绘美国旧南方生活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之一,极其广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小说里的人物莉娜和乔·克里斯默斯一直以来倍受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莉娜凭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被大多数评论家誉为“大地之母”,用其圣母般的光辉,点亮了整部小说黑暗的阴影,激励并启发了那些陷入黑暗而无法自拔的人;相反,克里斯默斯以残暴、罪恶、消极及悲剧式的形象呈现于读者和评论家的脑海里。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似乎没有丝毫的交叉点,但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巨大反差或相似性却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笔者尝试从另一个角度,以两个人物身上所共同体现出的对命运的不屈,来解析人物所映射出的文学及社会价值。
一、枷锁
人物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往往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及道德标准,决定着人们评判事物的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然而,是否所有的价值观及道德标准都合情合理,顺应民意?那些不合理,人们又无法改变的价值条例,往往被文学家们隐用在文学作品中进行批判。
作为小说背景的美国南方,当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方早已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制改变了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南方仍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南北战争虽废除了奴隶制但并没有使黑人的社会地位从性质上发生改变。北方工商业经济体制的入侵使得南方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开始崩裂,也严重冲击着南方人固有的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新的先进的经济社会价值体系与旧的落后的价值体系发生碰撞,使得当时的南方人处于水深火热中,他们既不甘心放弃旧南方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又不愿承认和接受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以一种抗拒或视而不见的态度,自欺欺人地生活在昔日的荣耀中。
除此之外,被南方人推崇至上的清教主义和种族主义如两道重重的枷锁捆绑着南方人。这两道枷锁既是他们借以体现旧南方荣耀和地位的圣物,又是使他们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束缚。清教信仰如“骑士精神一样已经深深嵌入南方的意识之中”[2](P78),长期以来钳制并规范着南方人的思想和行为,其道德规范中禁欲和女性的贞操在旧南方落后的社会体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毫无人性的道德规范下,很多人被逼上了绝望的边缘。黑人奴隶制在美国南方的存在历史悠久,人们长期以来坚信黑种人是上帝加在一个种族身上的诅咒,黑人注定是要为白种人充当奴隶的,这是他们赎罪的唯一方式。因此南北战争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黑人的地位在美国旧南方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许多作者笔下的黑人悲惨而绝望的处境正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残酷的清教主义教条和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使得人们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心灵遭到异化,很多人成为这种异化力量的牺牲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福克纳在描写旧南方的时候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既想通过作品真实地揭露旧南方的愚昧与落后,呼吁人们朝历史潮流看齐。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他与其他固守成规的南方人一样对南方拥有着深厚的情感,也不愿意看见南方的安宁与祥和在顷刻之间分崩离析。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充满着矛盾的影子。《八月之光》这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也毫不例外。从作者把小说的名字由最初的《黑暗的屋子》改成《八月之光》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南方的感情充满了纠结,但从整体上还是在朝前看。他虽然抨击旧南方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但对旧南方人们生活的宁静与祥和始终充满怀念与期待。
二、枷锁下被异化的灵魂
旧南方的大多数人持有一种“向后看”[3](P65)的生活态度,他们不愿也不敢接受新的先进的社会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竭力保留旧有的价值规范和道德观,于是出现了两类被异化的人:一类是沉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的人,另一类是不同于其他人而受到社会排挤的人。这两类人排斥社会或是被社会排斥,始终生活在孤独、迷惘与绝望中。
《八月之光》中的海托华、乔安娜、海因斯、麦克伊琴以及格雷姆都是沉迷于旧南方的荣耀或固守南方道德规范而接近疯狂的一类。这一类人代表了当时旧南方的社会历史大流,如同历史丰碑和被遗弃的锅炉一样,“以一头倔头倔脑、茫然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支撑着生锈的不再冒烟的烟囱”[4](P2)。
海托华沉醉于祖父在南北战争所创造的荣耀中。这个人物所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对过去的缅怀。于是自打从神学院毕业后就一心想留在杰弗生镇任职,在想象中重温祖父当年“在杰弗生横枪立马,冲锋陷阵的英雄形象”[5](P96)。他动用了多方面的关系最终来到杰弗生镇,但在任职过程中并没有履行神父的职责。他把教堂当成了宣扬祖父传奇故事的平台,每每在传教的过程中掺杂进祖父当年征战沙场的英勇。尽管对于他的祖父是英勇奋战而牺牲,还是偷鸡被人打死的事实人们持有怀疑,但他不顾不管始终沉浸在对祖父的崇拜中。他自欺欺人,既没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忽略了妻子的感受。最终他的妻子因跳楼自杀而被人发现与人私通,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他牧师的身份。而此时的他依旧站在神坛上眉飞色舞地炫耀祖父昔日的辉煌,直到忍无可忍的会众们将他赶出教堂,才结束了他有名无实的牧师生活。之后,他不顾长老们的劝告和人们的排挤,甚至三K党的威胁,坚持不搬离杰弗生镇。他用自己的积蓄在远离人们视线的角落建了一所房子,自此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的生命及时间早就在祖父落马身亡的那一刻终止,而他只不过是一个飘荡着的灵魂。
乔安娜是一个受到种族主义和清教主义思想双重折磨的人。虽然她的祖辈是来自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但她自小生活在杰弗生镇,和镇上的其他居民一样有着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并受到同样道德规范的束缚。同时她还得坚持父辈留下的事业,从事着黑人事务,帮助黑人争取更多的权益。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恪守成规,坚持祖辈遗愿的废奴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受到南方思想枷锁的严重异化。为了遵从南方人视为圣物的妇道,她强烈地压抑着自己的行为和情感,40多年来一个人住在远离他人的地方,整日穿着简单的印花便服,从事着男人应该从事的事务。虽然在遇到克里斯默斯以后,她的激情得到激发,但她终日惶恐不安,悔恨自己的生活陷入了腐败的深渊,“她想祈祷”[4](P175),祈求上帝对她行为的原谅。另一方面,尽管她是废奴主义者,从事着为黑人谋福利的事业,但她内心对黑人充满着厌恶。在得知自己的情人可能有黑人血液后,她从未拿他当平等人对待,为他提供黑人该住的小木屋,准备黑人才吃的食物,只有黑夜偷情的时候才让他进入她房子的主体,嘴里激动地叫着“黑人!黑人!黑人!”[4](P174)由此可见,在南方双重精神枷锁的禁锢下,乔安娜成为一个可悲的矛盾体,充满了情欲而不敢爆发,从事黑人事务而又鄙视有色人种。同时她作为一个杰弗生镇的外来者,还受到乡亲们的猜疑及排挤,生活单调孤寂。
海因斯和麦克伊琴在小说中作为克里斯默斯的亲人而有着不可名状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狂热极端的清教主义信奉者,冷酷无情,刻薄残忍。海因斯将自己推崇为执行上帝关于黑种人是劣种民族旨意的使者,一生最大的任务就是监视克里斯默斯的行动,并置其于死地。仅因听说克里斯默斯的父亲可能存在黑人血液,他便残忍地打死了克里斯默斯的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死于难产,并将刚刚出世就失去父母的克里斯默斯扔在孤儿院门口。从此他自诩为在上帝的安排下监视着克里斯默斯的一举一动,并教唆其他孩子叫克里斯默斯“黑鬼”。在克里斯默斯杀死乔安娜被捕后,海因斯更像一头发狂的狮子,气势汹汹,一面咒骂一面叫道“宰了这杂种!宰了他!杀死他!”[4](P232)对清教思想狂热的崇拜使得他忘却了自己是克里斯默斯外祖父的身份,让他坚信对上帝的顺从和崇拜没有亲情可言。而对于克里斯默斯来说,这个冷酷无情的人,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因为这个老头对黑人血液的臆断而开始了他一生对身份的苦苦追寻。
和海因斯对种族主义的狂热追求不同,麦克伊琴对清教主义思想的信奉体现在对生活的严格戒律上。他对待养子克里斯默斯严厉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从收养他的那一刻起就想用严苛的清教教义来规范和改造他的行为。麦克伊琴不仅改掉了“克里斯默斯”这个“带异教徒意味的名字”[4](P97),并妄想让克里斯默斯懂得“懒惰和胡思乱想是两大恶行,而干活和敬畏上帝则是两大美德”[4](P96)。他不顾克里斯默斯的反抗,强求他背诵清教教义,动不动就用鞭打和不给饭吃来惩罚他的懒惰与犯错。不仅如此,他还“祈求上帝饶恕孩子桀骜不驯的罪过”[4](P102),认为孩子的倔强与顽抗不驯是没有遵从上帝引导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自己的冷酷无情。在孩子眼里,他的养父如同一块坚硬的花岗石,妄图操纵和征服自己。孩子性格中的孤傲、倔强与冷漠无不与养父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视上帝高于一切的顺民没能把孩子调教成上帝的宠儿,反而让自己葬送在孩子多年积郁在心中的愤恨与不满之上。毫无疑问,麦克伊琴也成了清教思想枷锁下悲惨的灵魂。
海因斯和麦克伊琴都把自己当作是上帝旨意的执行者,他们的狂热与偏执不仅没能达到自己的愿望,反而把自己和亲人同时逼上了绝望的边缘。
小说中还有一个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明的种族主义者——珀西·格雷姆。由于太年轻,未能参加欧战,享受战争带来的荣耀,他为此愤恨不平,曾为了讨论战争而与老兵打架。后来他加入了民兵队,生命才得以充满激情。每逢有军事意义的重要节日,他总是穿戴齐整,以一个光荣武士的神态,在杰弗生镇行走,自行自愿地维护着杰弗生镇的治安。他对战争的沉迷让人觉得可笑,不管市民们怎么说,他依旧我行我素。他还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坚信白种人优于其他任何种族”[4](P303),当听说黑种人克里斯默斯逃跑后,他满腔的作战热情和对黑种人的愤恨得到了激发。他组织了一个排的人员,自己当了首领,并将他们分成了班组,装备齐整,作了战斗前的讲话。随后他将手下的人分别在监狱外、法院门口和广场附近设置了三条纠察线,配置了文书室和指挥部,俨然为此次战斗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到处巡逻,在发现克里斯默斯的踪迹后,立马追随,并将其处以残酷的私刑。他的做法和行为给读者带来的是强烈的血淋淋的视觉冲击,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是一头饥饿的狮子在荒原上穷追自己的猎物般的狂热与残酷的景象。这个被旧南方异化的人物让人感到恐惧。
小说中另一类被异化的人是由于自身与社会格格不入而受社会排挤的人,究其原因还是和旧南方的道德价值观有关。这类人在小说中的典型代表为克里斯默斯和莉娜。旧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造就了一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也造就了一批种族优越感极强且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因此,克里斯默斯身上可能存在的黑人血液注定会在这样的社会遭到排挤。在残忍的外祖父的一手安排下,他一出生就成了孤儿,随后被扔进孤儿院在别人的监视与排挤中度过童年。到了明白身上可能存在黑人血液的年龄,被人收养的他已经压抑不住内心由于此原因而带来的骚动,他孤癖倔强,最终因黑人血液而以德报怨地杀死了自己的养父,随后开始了一生对身份的追求,也造就了悲惨的人生。其悲惨的人生,与社会对黑种人的排挤与迫害密不可分。在这个白种人优越,黑种人总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中,黑人血液注定不会得到安宁。
莉娜在小说中虽然以一个光辉的角色出现,但笔者认为这是作者的故意安排。作为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大摇大摆地行进在一个充满着清教主义思想的社会中,是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排斥的。莉娜在小说中虽然得到善良乡亲们的帮助,但无可避免地遭受了很多非议。如阿姆斯特德的妻子和比尔德太太虽然都乐意帮她,但话语中不自然地流露出对她的冷淡与歧视。
小说中的大部分人无一例外地都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痛苦是由于‘传统世界’的消失,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他们痛苦的原因是由于‘传统世界’还继续存在着”[3](P65)。旧南方的荣耀已随着时间流逝了,但传统的价值观念却遗留给了后代,麻痹着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失去了方向感。
三、八月之光:黑暗中的灯塔
福克纳对南方的复杂情感在作品中的体现使得《八月之光》不仅成为“一部反思南方的种族仇恨和加尔文教徒的道德堕落”[7](P155)的小说,也蕴含了作者对南方的焦虑、批判与对人性的强烈呼吁。
作者把小说的名字由《黑暗的屋子》改成《八月之光》就印证了作者希望南方朝着光明的方向发展。其次,虽然整体上南方笼罩在病态、畸形的传统文化的阴影之下,但南方人的倔强、勤劳与勇敢是南方人恒久不变的美德,也是南方不可磨灭的光芒。小说中,虽然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南方人显得偏执而冥顽不化,对外来者及弱势群体充满了敌意,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南方人没有丢掉他们勤劳勇敢的品质(小说中的拜伦在没有他人的监督下依然奋力工作),也没有失去他们乐于助人的秉性(善良的乡亲们对未婚先孕女子莉娜的帮助)。
除此之外,作者对南方的批判造就了该小说萧条、凄凉与残酷的气氛,但对人性的关注以及用批判来震醒南方人的愿望在两个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是穿梭在南方黑暗中的光源,点亮了南方未来的希望。克里斯默斯在福克纳笔下是一个矛盾而饱满的人物形象,饱经风霜,一生都处于漂泊不定与对身份的苦苦追求之中。福克纳对他身份不确定的创造,使得南方人对种族主义的狂热与偏执有了得以蔓延的温床,也给了读者直面南方白人贵族阶级自高自大、冷漠荒诞的平台。克里斯默斯的悲剧是处在南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黑人的悲剧。对该人物的创造体现了作者对南方冥顽不化人们的批判,表达了作者对黑种人的同情,以及对黑种人作为平等民族的人性的关注。因此作者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笔墨来渲染克里斯默斯的悲剧,该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对社会、他人压迫与排挤的抗争,对自己人生的奋力追求,对所犯罪责的平静接受,都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作者想通过该人物展现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南方人所处的生活状态,呼吁这些人用自己心中的信念与希望来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沉迷于过往,坐以待毙。
莉娜在小说中的形象坚强、阳光而充满活力。一个未婚先孕的母亲,不顾乡亲们的异样眼光,怀着一家人团聚的愿望行走在杰弗生镇的路上。在人们对贞操如此在意的时代,她并没有为自己的未婚先孕感到耻辱,对待生活的态度仍然积极乐观。她笨重而优雅地行走,像贵妇一样进食,坦然接受乡亲们的帮助,当别人问及她的私事时,她也毫不忌讳,将自己的来龙去脉详尽地告诉他人,像是在说别人而不是自己的事。莉娜身上所散发出的热情与光明,感染了她身边所有的人。乡亲们暂时搁置了对贞操的留意,分别伸出了援助之手,那些处在自我沉迷中而无法自拔的人如海托华也最终在她的感染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开始融入社会,试图去帮助他人(克里斯默斯)。福克纳用莉娜风尘仆仆、不停行走的意象来表明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她所孕育的孩子是福克纳对南方充满光明的期待,希望这个充满热情与乐观精神的母亲,能够给南方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
许多评论家认为,福克纳对他笔下的重要人物都做了精心的刻画。这个出身于南方的贵族家庭,成长于南方败落之际的作家,和其他南方人一样体会着精神上无所依托的痛苦,但他以批评的目光,赋予人物的鲜活与饱满,代表着他对美国南方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也对人的生存状态及生存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探索,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福克纳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声明:“我相信人类不但会生存下去,而且还会发展兴盛。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是人在所有生物中拥有永不消失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忍耐的精神。”[8](P120)这种精神是沉闷八月之中不可磨灭的光芒,照亮人们通往前进的方向!
[1] 迈克尔·米尔格特. 是小说而非轶事[A]. 新论《八月之光》文选[C]. 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2] 陈永国. 美国南方文化[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3] 查日新. 解析美国南方的困境[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64-68.
[4] [美]威廉.福克纳. 八月之光[M]. 蓝仁哲.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 生安锋. 现代社会中人格的分裂与模糊—试析《八月之光》中的双重人格[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24S1):96-100.
[6] (美)柏里尼. 福克纳传[M]. 吴海云,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7] William Faulkner. “Nobel Prize Acceptance Speech”in Essays, Speeches & Public Letters[C].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