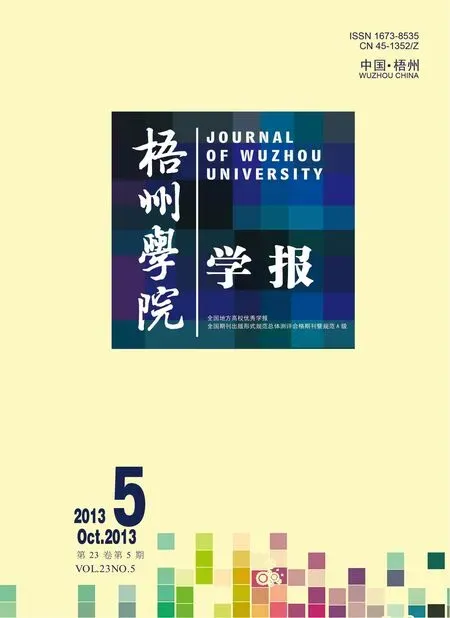诉前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检察监督机制探究
王世楠
(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检察院,广西梧州543002)
诉前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检察监督机制探究
王世楠
(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检察院,广西梧州543002)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创新规定,凸显其监督执行者、法律守护人和证据裁判官的诉讼地位。但是,由于新法对非法证据排除适用未作详尽措置,检察机关的证据监督操作依然陷入静态监督与动态监督、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配合协作与监督制约、证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四个方面的困境与迷思。鉴于此,结合我国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检察机关应从诉前环节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由单一制裁向合意、联动、参与监督转型的程序性建构,拓展预防和监控公安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的能动角色。
诉前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检察机关;监督机制
刑事司法权运行的核心是证据的采集与认证,监督制约刑事司法权,关键就是要建立刑事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证进入诉讼的证据“干净”,这是刑事司法权运行理性和公正的底限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实体适用法律的监督制约。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从法律文本层面构筑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取证合法性的前置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本质是证据监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确认,将会导致立案侦查、证据收集、证据供给等方面的变革、调整,必然引起检察监督模式增加新变量。中国诸多刑事错案的根本肇因源于侦查取证漏洞、违法,而仅仅依赖倡导性和象征性的程序宣示,难以根治非法取证行为由来已久的沉疴。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承载者,只有跳出司法控权传统范式的藩篱,在诉前环节规范侦讯主体的取证程序和取证方法,才能高效监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的不法行为,杜绝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张辉、张高平式的错案重演,提升检察监督公信力。
一、诉前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检察监督之赋新
刑事诉讼是侦查权和检察权碰撞较为激烈的场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解决刑事司法中程序违法或者不当的方案和“题眼”,意在规制公安机关对证据的随意取舍,约束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在诉前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它对检察机关的证据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一)突出检察机关“监督执行者”的角色定位
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下承担侦查、控诉和监督等多元职能,复合性特征显著,从履行监督职责和保证起诉质量的双重维度出发,具有监督证据提取、固定、纠错和采用的当然义务。这种审查判断证据、处分侦查结果的行为监督色彩浓厚,与西方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制度中仅由法院在审判阶段通过听审程序对非法证据作出裁量,检察机关充当被动应诉者的方式判然有别。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基础定位是取证合法性的监督者,被赋予抑制侦查违法、保障公民人权之使命。“传统侦查程序构造以有效控制犯罪为价值追求,以侦查权不受制约为基本特征。”[1]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是典型的侦查本位主义设置;基于侦查权权力垄断和扩张的本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必须强调侦查行为具备正当的法律程序,确保检察权对侦查权的适度约束和规训。这是科学配置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合理划定司法权力边界的规范表达,把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监督的抽象规定具体深化。因此,检察机关探索以规制公安机关侦查权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侦查程序构造,秉持宪政理念规范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取证方式,符合法律监督宪法定位的本质属性。
(二)恪守检察机关“法律守护人”的公正立场
追溯历史本源,创设检察机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设立受法律训练和约束的客观公正的法律官员,来控制警察的侦查活动,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2]。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也对检察官甄别、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作出设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法律保护人”的中立地位,要求其不能只以控罪和胜诉为目标,而应当履行客观公正义务,采取积极措施阻断公安机关滥用或者误用侦查权生成非法证据,保护犯罪嫌疑人让其免于侦查权的恣意擅断。1996年《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刑事监督权,但是并没有监督侦查人员合法取证的具体规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延展至侦查阶段,确立检察机关调查证据合法性的双重启动模式——职权启动和诉权启动。实践中,检察机关也不再局限于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实施事后监督,而是加强在侦查和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对公安机关取证行为进行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实行检察引导、调控公安侦查的侦诉模式,以否定违法侦查结果的方式来否定侦查行为的价值获益,对证据获取资格作出认同或者制裁的结果评价,保障检察机关在诉前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防止侦查权的不当倾轧。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用证据合法性标准监督侦查工作质量,为侦查行为合法取证建立合理预期,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流于形式而被虚置架空,出现“正当程序衰落导致实质真实误判”的“谬之千里”的不利后果。
(三)强化检察机关“证据裁判官”的功能属性
刑事诉讼的实质是司法权主导下的事实真相调查程序,而事实真相通过证据采集、认证所探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确保证据客观真实、促进证据可靠完整的系统诠释。“证明是诉讼的核心,证据是证明的依靠。”[3]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均围绕这一轴心运转。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旨在规范证据的收集、审查以及证明活动,要求证据不仅应当符合关联性和客观性,而且应当符合法律限定的资格条件。“在刑事诉讼中,错误成本的先期支付要优于后期支付。”[4]除了审查起诉阶段外,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监督适用还包括“向前延伸”(证据的侦查监督)和“向后延伸”(证据的审判监督)两种方式。其中,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与侦查阶段在时间和程序上更为接近,在诉前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比在审判环节更具备诉讼成本的优势。1996年《刑事诉讼法》及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规定检察机关负有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明责任,但是并没有明确检察机关采纳和采信证据的客观标准,导致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被视为天然合法,难以有效审查推断。新《刑事诉讼法》强化证据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的规范性,对证据合法性审查提出严格要求。检察机关应以“庭审前的预审裁判官”为己任,将证据采集的合法性标准纳入监督程序的法治轨道,于庭审前尽可能将非法证据阻隔到诉讼程序之外,防止非法证据流入庭审使法官形成“首因印象”进而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使侦查成果经得起法庭的严格考验,奠定刑事案件证明的基石。
二、诉前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检察监督之拷问
“法律实施遵循的思维方式不同,结果亦会存在差异。”[5]虽然立法机关力图通过构建精密化的刑事证据规则,以解决证据监督“衡证无方”的难题,但是囿于现实中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法证据排除应时立法的“美轮美奂”与实时操作的“捉襟见肘”形成鲜明落差,对检察机关提升证据监督效力、拓宽侦查监督空间造成极大羁绊。
(一)形式抑或实质——静态监督与动态监督的迂回博弈
侦查权的封闭性、保密性、隐蔽性是专制国家独有的表现,现代法治国家侦查权应具备公开、公正的形式特质。当前,检察机关证据监督仅对显性、积极性违法侵权行为奏效,而对隐性、消极性违法侵权行为的监督作用欠佳,实质上将监督方式桎梏在静态、单方和弹性层面,未向动态、多元和刚性监督转变。其一,案卷材料是连接侦查、起诉和审判等阶段的桥梁,检察机关判断证据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是查阅案卷,但是案卷材料极少反映出非法取证的情况,很难发现非法证据疑点。特别是新《刑事诉讼法》设置了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手段,使得认定非法证据愈加困难。其二,除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外,合法证据缺失的情况和原因也难以完全展示在案卷材料之中,甚至有些关键证据被公安机关以不重要或者与本案无关为由没有放进案卷,使得侦查人员对证据信息的采集处于“人不能知”的状态,监督阻却效果不彰。其三,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刑事政策观支配下,公安机关没有建立适时合理的开启证据机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了解侦查情况以及提起申诉、控告的渠道不畅,缺乏公开透明的沟通、质询与答辩的程序载体。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也没有与律师监督形成互动,辩护律师欲对非法证据进行鉴定和调查举步维艰。检察机关纵然有非法取证之虞,却难行审查监督之实。排除非法证据操作如果不能实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却希冀达到监督之时效,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例外抑或常态——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的证明壁垒
自建国以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证明机制没有根本改进,缺乏共同统一的证明标准业务操作平台。“司法证明活动规范化的内容之一是证明标准的规范化。”我国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证明案件事实的环节被淡化,诉前环节公、检机关的证明程序只处于初级形式,没有在建立案件证明标准和证明运作规则基础上的合作。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方式是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提交法律文书和随案移送案卷证据材料,却没有提供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提要,更没有开展案件事实的证明活动。这种自由证明模式下向检察机关证明案件事实的操作,“自向证明”特征明显,“他向证明”要素缺位,只是“查明”而非“证明”的诉讼思维。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证明活动上的脱节,检察机关需要对全案证据材料进行整理归集、分析论证才能确认或确信公安机关查明的案件事实,实现“侦查证明”向“公诉证明”的转换衔接。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中的“自向证明”方式不仅形成“重查明、轻证明”的侦查思维,而且形成侦查操作自我封闭常态化的证明环境,使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难以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纠正侦查疏忽违法行为和修正证明瑕疵的法律职责不容易落实。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取证出现证据遗漏和差误,也会造成审查起诉阶段证据补查修复、退回补充侦查的程序逆流,以及因证据来源合法性缺憾的否定性司法评判,导致检查监督与侦查取证无法实现同步。
(三)平衡抑或失衡——配合与监督的隔阂难以消弭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对非法证据处理的着眼点集中在侦检形成合力惩治犯罪的单一价值取向,检察监督权与公安侦查权的平衡机制无法充分体现。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传统侦检关系的发展理应呈现出新局面,有必要从部分突出公诉与侦查配合转置为全面强调监督侦查行为合法性,由公安机关在诉前环节对证据获取作出合法证明,否则将面临被排除的风险,从而“以压力回转的方式倒逼侦查人员规范取证行为”。但是,这种责任风险转移的模式能否真正实现,依然有待实践考证。现今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侦查取证手段成为惯常性工作,侦查权运行呈现“任意性”倾向。而法律仅规定检察机关以审查批准逮捕的方式实施监督,在侦查阶段并没有确立其他监督途径,侦检关系演变成重协作配合、轻监督制约的“流水作业”,难以发挥对侦查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公安机关凭借其固有的强势地位任意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成为导致浙江张辉、张高平叔侄等冤假错案迭现的关键因素,检察机关对此也只能徒唤奈何。“捶楚之下,何求不获”的错误思维一旦形成并内化于心,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和自由心证,无形中会削弱司法权威,加剧刑事司法权与公民权利的内生紧张性,大众舆论挞伐亦随之而来。可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监督失衡的情势下,会遭遇重重阻力而面临付诸阙如的危险。
(四)并重抑或偏重——证据证明力与证据能力的选择困惑
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前,证据的可采性(即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主要由法官在庭审中审查判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更偏重于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链的完整性,而对证据能力重视不足。实际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指的不是证据证明力,而是证据能力;限制的不是证据适用,而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证据能力作为证据的许容性条件,倘若不重视和关注,就意味着公安机关收集的所有证据均有可能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裁判依据。新法实施后,主动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成为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所在。但是,案件侦破的复杂性、侦查认识的逆向性及证据供给的有限性,造成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一样高度依赖证据信息,希望获取更多数量与内容的证据来弥补技术粗陋和证据羸弱的劣势,满足对证据需求的利益与动机。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庭审模式的渗透下,检察机关追求证明力及证明价值的欲望愈加强烈,很难产生排除非法证据的内在动力,为滋生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温床。以往检察实务中可资佐证的例子就是审查报告大多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分析与认定,很少有审查证据资格和关注证据能力的内容;瑕疵证据一般并不排除,而是将其直接补正或重作后转化为证明力予以适用。这种简单化的处理遮蔽了问题所可能潜伏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当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形成以证明力而非证据能力作为证据采集和采纳的导向时,证据审查证明性和可采性并重的原则变成为游移不定的难以抉择。
三、诉前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检察监督机制之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预期收益决定其未来走向。”尽管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耗费紧缺的诉讼资源,但是却能够产生明显的制度收益——遏制非法证据与未然状态,提高证据监督效率。检察机关应依托法律监督职责,在诉前环节建立合意性、联动性、参与性相结合的非法证据排除监督机制,完善证据合法性、正当性的监督程序操作。
(一)侦检关系的解构性重塑:非法证据排除合意性监督机制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职权主义诉讼还是当事人主义诉讼都需要诉前的侦检合作。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应探明与公安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逐步改良长期沿用的“分段包干,流水作业”模式,搭建合意性监督机制平台。合意性监督机制由确定证明对象、开列证据清单和规范证据监督三个步骤构成,检察机关应紧扣“指引而非指挥、到位而不越位”的思路,以逮捕标准和起诉标准指导、规范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工作,在深入研究分析案情的基础上由双方共同协商、讨论制定侦查计划方案,根据证明对象和证据清单收集证据和监督证据合法性,引导公安机关从“由供到证”的破案功能升级为“由证到供”的证明功能。
第一步,确定证明对象。证明对象是“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对象”,主要分为定罪证明对象、量刑证明对象两个类别。侦查活动看似为收集证据和实现犯罪嫌疑人到案,其实核心任务是刑事证明。证明活动围绕证明对象展开,证明对象作为证明的中心环节,决定证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证明对象又“诉因提示”确定,按照“诉因提示”转化为需要证明并予以认定的代证事实,使与待证事实无关的事项被排除在侦查活动之外。侦查人员需要围绕诉讼主张来证明有关要件事实,准确定性案件具体罪名,根据构成案件事实的情节、影响罪行轻重的量刑情节、犯罪嫌疑人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其他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事实等要素来推定考量定罪和量刑的证明对象。侦查人员要权衡协调各种证明对象的关系,注意证据的客观性、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和印证性,运用证明对象确定审查案件的方向、目标和重点。
第二步,开列证据清单。证据清单是侦查人员针对案情实施专门调查并形成案件事实有效证明的清单,是侦查目标和侦查结果的外在体现。证据清单要求侦查人员把案件证明对象的事实要素与证据联系起来,按照刑事证明逻辑关系对案件证据状态进行梳理、排序,实现侦查活动“证据总动员”的动态展示。证据清单主要包含定罪事实的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性说明和审查意见等内容。侦查人员根据证据清单要求收集、提取和固定证据,查明案件的事实情况,在侦查终结时提炼全部有用的证据信息。在案情扑朔迷离的侦查阶段,证据清单的形成具有变动性,需要根据案情发展和侦查进度及时调整。检察机关可以运用侦查意向书和补充侦查提纲告知公安机关调整侦查布局和指引取证方向,避免盲目侦查和无效侦查,保证取证行为更具目的性和服务性,实现侦查和公诉能力的接力传递。
第三步,规范证据监督。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应主动对每项证据材料附上合法性证明的必要信息,检察人员根据具体个案中的证明对象和证据清单查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判断侦查机关确定的证明对象是否科学,开列的清单是否齐全,便于评判、修正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这种强化同步指导与同步监督的方法,将侦查行为监督与侦查质量监督寓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协商合作之中,加强检察机关监督侦查取证行为的预防功能,及时纠正证据瑕疵、缺漏或者证据偏差,从源头上改善和提高证据质量。检察机关还要实行巡回与常驻结合的方式,在公安机关派驻人员定期收集分析公安机关普遍性、专门性的非法取证案件,及时制定非法取证风险评估预案,向公安机关发布预警,防范侦查取证行为游离于合法性程序之外走向错误的极端。
(二)捕速职能的聚归性整合:非法证据排除联动性监督机制
在我国现阶段侦检分离改革进路延宕的司法环境下,检察机关可以探索新型侦诉关系——捕诉一体化模式,实行“捕诉合一”联动机制,将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合并为刑事检察部门(以下简称刑检部门)集中行使捕诉职能,在刑检部门检察人员对案件实行“一体承办”的连同操作,根据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证据体系的不同特点,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对证据进行“二次过滤”,对非法证据进行筛选分流。
一是启动程序。刑检部门可依凭检察机关内部信息资源共享和对接机制,既要审阅案卷材料和接受当事人举报,又要接收控告申诉部门受理转介的申诉、控告,监督检察部门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羁押状况、审讯情况以及案管中心网络汇集的信息,侧重审查证据的形式合法性,对非法证据的线索和盖然性后果进行初步评估、预判,以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程序。结合公安机关非法取证较为隐蔽和犯罪嫌疑人提供线索较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对启动标准的设置不宜过高,只要综合案情认为不排除合理怀疑有可能侵犯当事人权益或者影响案件公正处理,即应启动排除程序。
二是调查程序。刑检部门可基于侦查阶段形成的合意性监督机制,在不同诉讼阶段选择适当的证据审查监督手段。
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对证据标准的要求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鉴于证据体系的非闭合性、实时性与可变性,公安机关在后续阶段仍可补齐更多证据,加之审查批准逮捕办案时限较短,因此,该阶段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要求应当略低于审查起诉阶段。刑检部门可以采用简化便捷的审查模式,从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取证是否符合法律要求以及是否有影响证据能力的违法情形等方面予以审查,快速确认证据是有效或有瑕疵。发现证据遗漏或者证据应当提取却没有提取附卷时,及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提取、提供证明,如有必要也可自行开展取证调查工作。刑检部门还要会同监所监察部门,结合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重大疑难案件备案审查以及执法信息和监控联网审查等机制,对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进行审查监督。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标准的要求是达到“确实、充分”,刑检部门应当对移送的全案书面、视听资料进行覆盖式审查,以询问知情人员、调取体检、就诊记录、鉴定伤痕伤情等工作为辅助,核查疑问关键点和矛盾指向点。一方面,对一般案件的非法证据,采取自主复核方式,根据侦查取证手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实质性侵害的程度确立不同强度的审查程序。对严重侵犯生命、健康、自由等人身权利获取的存疑证据(如刑讯逼供、强制羁押所获言词证据),发动强度较高的审查;对侵犯经济性、财产性权利获取的存疑证据(如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发动强度适中的审查;对轻微违法证据(如证据瑕疵),发动强度较低的审查。另一方面,当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对证据合法性有严重分歧要求质证或者排除存疑证据影响案件实质认定的,则采取听证方式。在听证过程中,公安机关负责提供存疑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并回应质疑方提出的意见事由,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针对公安机关证明进行质证辩论,刑检部门则根据双方意见以及掌握的证据材料判断存疑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三是处理决定程序。刑检部门经调查核实后,对可疑证据作出相应处理:属于不存在违法取得或者有瑕疵而经过合理解释、补正转化而实现复取的证据,决定不予排除;确系非法证据或无法排除其非法取证行为嫌疑,且排除该证据不影响案件定罪量刑,决定直接排除;对非法证据有严重分歧或者排除非法证据可能影响案件主要定性,经请示、讨论、审批后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被排除后,刑检部门应告知公安机关另行指派侦查员重新调查取证或者补充侦查。对非法证据材料,因丧失证明能力不能成为定案、逮捕和起诉的证据,将其从案卷中撤除并装入检察内卷封存备案。对非法证据所涉侦查人员,根据非法取证的严重程度提出纠正意见和追究相关责任。对因排除非法证据而未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或者建议撤案的案件,向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推行“公开答疑”、“不捕、不诉双向说理”等释法研判和息诉化解工作,营造透明公开的司法环境氛围。
(三)控辩交流的协同性导入:非法证据排除参与性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不仅要在外部确立侦检办案合意和在内部强化捕诉职能联动,还应当正视辩方参与监督的新命题,从适度开放控辩对抗程序和深化控辩意见交流等路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参与性机制,实现诉前环节控辩双层合力监控、排除非法证据的监督模式,弥合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审查证据合法性缺乏沟通衔接之弊端,开拓证据监督的“第三方”视野。
在侦查阶段,设置适度开放的控辩对抗性程序。在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尚未普及、律师在场见证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聚焦于将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与律师调查取证相结合,规范设计辩护律师自行收集调查证据、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查阅侦查内卷等程序,引导其通过证据信息参与监督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行为。根据该程序设定,辩护律师在法定情形下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代其提起非法证据之控告,向刑检部门提交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书面申请。刑检部门对书面申请进行细致分析,不准许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应当书面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同意调查取证的,应当在合理时间内通知公安机关执行调查取证工作。
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确立非法证据排除控辩意见交流机制。刑检部门在审查案卷和复核证据的基础上,实行检察机关阅卷与辩护律师阅卷双重监督模式,向辩护律师开示案卷中的程序性诉讼文书与技术性鉴定材料等证据,保障其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全面知悉证据合法性状况的应有权利。此外,刑检部门在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后,向辩护律师发出《提出非法证据意见通知书》,辩护律师认为证据合法性存在“合理怀疑”或者有瑕疵的,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法律意见,并提供证材料或者获取证明材料的线索途径。刑检部门认真审核书面法律意见,将辩护律师提交的线索、材料用来核实补充已有的证据,必要时要求侦查人员提供合法性说明。刑检部门于案件审结之日前对法律意见作出处理决定,并将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优化建构是中国刑事司法致力实现的目标,体现了立法者希冀诉讼理想与司法实现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景和关切,是“在正当程序与实质真实出现矛盾时,将正当程序置于实质真实之上的选择模式的产物。”新《刑事诉讼法》给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指向提供了鲜明的坐标和基准,掀开了以程序正当、理性为逻辑起点审酌证据排除、制裁取证违法的历史序幕。法谚有云:“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制度的权威在于执行。”检察机关应当在完善诉前环节证据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归束整合于检察权的框架之内,为监督侦查权的功能回归提供有效的洞察和创见。总之,追求司法公正的前进步履不会停息,考验也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实践正发生微妙转型,变革,正始于我们脚下。
[1]索占超.公正与效力视野下的刑事侦查与人权保障[J].湖北社会科学,2012(8):158.
[2]李宏辉.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5):69.
[3]汤唯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J].政法论坛, 2000(6):78.
[4]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88.
[5]徐静村.刑事诉讼前沿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160.
On the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M echanism of Elim inating Illegally-obtained Evidences in the Preaccusing Stage
W ang Shinan
(Peop le’s Procuratorate of W anxiu District of W uzhou City,W uzhou 543002,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n procuratorial authority’s eliminating illegally-obtained evidences in the latest Criminal Procedural Law,litigation status of supervisors of implementation,guardians of law and judges of evidence should strengthened. However,due to the lack of detailed rules in the latest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for eliminating illegally-obtained evidences,the supervision of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is faced with a problem in which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static supervision and dynamic supervision,self-guiding certification and non-self-guiding certification,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nd restrictive supervision,probative force of evidence and actual credibility of evidence.In view of thi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ature supervising power of procuratorial authority,it is proposed procuratorial authorities should perfect the procedural structure which is developed from a singlemechanism of eliminating illegally-obtained evidences illegally-obtained evidences by collective judgment,joint decis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supervision.Meanwhile,it is also proposed that procuratorial authoritie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initiative functions of preventing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from illegally obtaining evidence and controlling them in this regard.
pre-accusing stage;elimination of illegally-obtained evidence;procuratorial authority;supervisionmechanism
D926
A
1673-8535(2013)05-0044-08
王世楠(1963-),男,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检察院干警,研究方向:法律务实。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3-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