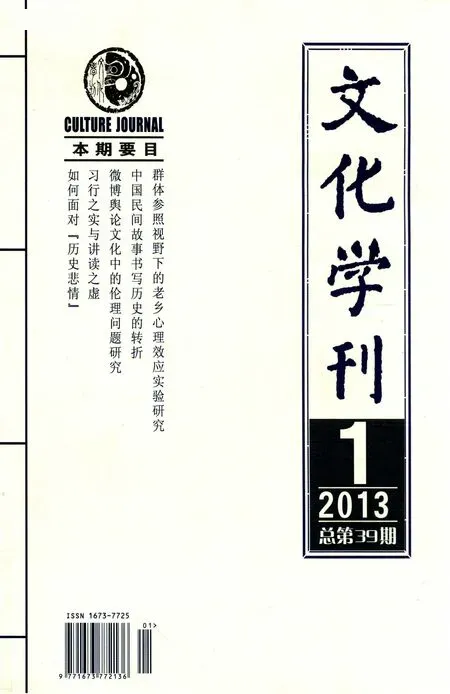博饼之路:从兵营游戏到民间风俗
冯少波 王毓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博饼最早见于康熙《台湾府志》,它是清代台湾“班兵”制度的产物。大量不带眷属、三年一换的将士轮流到台澎金厦地区戍守海疆。每逢中秋,这些主要来自北方和江南各地的将士们格外思乡。他们把平日打发无聊时光的赌博游戏与难得见到的家乡月饼嫁接到一起,又吸收了科举文化的因素,创造了最初的博饼。一些人偶然几次的游戏行为要变成大部分人自觉遵循的一种有一定规律的、相对稳定的习惯行为,乃至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风俗,需要很多条件和动因。在博饼行为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一些文化因素长期影响着博饼风俗的形成和演变发展,如涓涓细水,绵延不断,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与此同时,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也在这一风俗演变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
中秋节博状元饼的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当初它仅仅是兵营将士排遣思乡之情的一种节日游戏,其流行范围相当有限。在阅读清代历史典籍、方志资料时,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文献对博状元饼的记载都如出一辙:其经典的表述仍然是“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月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1]这里的月饼只有一个,而且一定是源自北方的大月饼。《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收录了清代台湾的10种方志资料,其中7种具有此类记载,另外20世纪50年代成书的《宜兰县志》和《基隆县志》也保留了这样记载。[2]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完全是对蒋毓英《台湾府志》的模仿或抄袭。一方面是地方史志中的记载大面积雷同,另一方面则是民间风俗研究著作中的记载空白。清光绪二十一年 (1901年),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人佐仓孙三被派往台湾在总督府民政局任职。公务之余,广泛收集当地民情、风俗、家庭、物产等信息,历时三年写成《台风杂记》一书。记载台湾风俗等114条,其中对除夕、端午节、盂兰会等节日都有记载,其中对盂兰盆会的记载尤为详尽:“台人劝业殖货之风,无贵贱、无老少皆然。是以一年三百六十余日,营营栖栖,未尝休业撤劳。唯中元盂兰会,户户争奇,家家斗奢,山珍、海味、酒池、肉林,或聘妓吹弹,或呼优演戏,悬彩灯、开华筵,歌唱管弦,亘一月之久;竟以荐祓幽魂之事,为耳目娱乐之具。大家则费数百金,小家则糜数十金,若计以全台,其所费实不赀也!”[3]唯独没有记载中秋博饼的情况,从文中措辞来看,恐怕并非疏忽遗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秋博状元饼的习俗,还没有成为不是当地居民普遍遵行的风俗,而只在外来的军队将士、地方官员和部分移民中间流行。
按照中秋博饼的游戏规则,博饼使用的是骰子,而骰子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赌博工具;博饼一定是在酒席饭桌上进行的,实际上是举家团圆、几代人在一起做游戏。在北方中原文化的传统中,赌博是属于市井俗文化范畴的东西,是粗俗、低级之事,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一般不会让未成年的子女沾染这种不良习气。中国传统的家教,大人对于小孩,从来都是教导“学好”,而制止“学坏”的。地位越低的人,还越是望子成龙;即便是乞丐、盗贼,也不教子女重蹈覆辙。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对当时社会上赌博盛行之风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且洋贩之利归于台湾,故尚奢侈、竞绮丽、重珍旨,彼此相效;即佣夫、贩竖不安其常,由来久矣。赌博,恶业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挟资登场,叫号争哄,始则出于典鬻,继则流于偷窃,实长奸之囮也。”[4]可见当时的正统观念对于赌博是非常鄙夷和排斥的。
还有,传统的北方人父子之间还有一种不能游戏的禁忌,即所谓的“父子不同席”。 “父子不同席”一语出自《礼记·曲礼》,意思是父亲与儿子在外作客,不能在同一酒桌上落座。大概古人认为酒桌是游戏的场合。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依然保留着:父子即使是同桌吃席,也绝对不能猜拳行令 (即俗称的“划拳”)。北方人有一种游戏的规则,叫做“爷爷孙子没大小。”人们在批评年轻人、晚辈或子女时,也经常说“你没大没小的。”这个“大小”的意思,就是要讲究班辈伦理。父子之间是不能随意乱开玩笑的,开口说话必有称呼,晚辈人与父辈人之间甚至都不能拍肩、握手。总之,一切有损长辈尊严的事情都不能做。《颜氏家训》说: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别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闽南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传统文化的积淀十分深厚。 《八闽通志》有载:“同安县,邑人知敬信朱子之学。元林泉生《大同书院记》:‘今去朱子二百年矣,所谓高士轩者,古老相传,敝则必葺。同安多古碑,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诵之,彼岂为虚敬哉?’”[5]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从博饼的赌博、游戏的性质来说,当地大多数民众的不大愿意接受的。
二
作为一种台澎金厦地区军营中将士们排遣思乡之情的节日游戏,中秋博饼怎样走进当地百姓的家庭?
从博饼自身的发展演变来说,原来的中秋饼中本来就包含着雅文化的因子——状元,玩中秋饼游戏最初的人群就是被称为“士子”的读书人,最初的状元大饼上本来就是“朱书一元”字,这个“元”字就是状元之“元”。在博饼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最初是骰子与月饼的结合,产生了博中秋饼的习俗。后来,中秋饼游戏又与状元筹结合,产生了博状元饼的游戏。这个中间,康熙时代台湾首开科举无疑是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汪士祯《池北偶谈》记载了台湾开科:“台湾新经归附,文教初开,应将台湾一府三县生员,照甘肃、宁夏之例,另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人一名。得旨允行。”[6]连横 《台湾通史》记载: “康熙二十五年,福建总督王新命、巡抚张仲举奏准,台湾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增广生如之。”[7]开科取士是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响应,其社会影响极其深远。史称“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试为一生大业,克苦励志,争先而恐后焉。”[8]正是因为原本低俗的掷骰游戏中吸收了高雅的科举文化因子,使得博饼由粗俗游戏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比较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活动。
博饼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睐,并得到空前的普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博饼的两条铁律:其一是绝不单独举办,有博饼必有宴席;其二是绝无空手而归,只要参与必定有奖。赴博饼宴的人,在座位安排上绝不讲究上席下席的“长幼有序”。传统的宴席以上席为首,第一个动手的人一定是上席就坐的尊者。但是在博饼的规则中,讲究机会的均等:第一轮掷骰,以点数大小决定胜负,优胜者为先。人人获奖的奥秘在于月饼数量的设计与参与者的人数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标准的宴席以10人为满,月饼的设置为63块为下限,平均每人有6.3块饼。有人计算过博饼的概率:参与博饼的人每投掷一次骰子,他的获奖几率是69.35%;中奖的点数概率越低,奖项越大,点数概率越高,奖品就越小。[9]我们作过计算:宴席上每掷骰一轮,大约需要3分钟,每人每次的中奖概率约为0.7,半个小时可掷骰10轮,能中奖7次。每场博饼一般需要掷骰20—30轮,耗时1个多小时。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15—20次的中奖机会,但实际上由于“奖品发完为止”的规则,奖品一完,中奖也就无效。不过只要一种奖品没完,掷骰就不得中止。实践中博饼者最高可获得两倍于“状元”价值的奖品,而最低也能得到与10个“一秀”等值的奖品。因为有美餐相随,每次都能满载而归,博饼能够最大限度地激起每一个人的兴趣,自然大受欢迎。
尤其是闽南柁工和台湾乡勇在博饼大众化、家庭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闽南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闽书·风俗志》: “枕山而负海……沿海之民,鱼虾蠃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地窄人稠,行贾寡出疆,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广东……而不知瘠土小民,非是无所得食。”[10]道光《厦门志》:“厦岛田不足于耕,近山者率种番薯,近海者耕而兼渔,统计渔倍于农。”[11]闽南本土民众以海为田,男子一般都能通识水性,懂得潮汐和风信规律,善长摇橹驾船,是天生的好船员。在近代西方文化扩张的过程之中,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西洋、南洋商船大量、频繁进入中国,引起了对船员需求的大量增加。大批的闽南渔家子弟为了谋生,而到洋船上做“柁工”。道光《厦门志》记载: “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12]这些人在与外国文化的直接接触中,学会了许多洋人的习惯。其中的一种就是赌博,没有任何禁忌的赌博。“赌博盛行;奸民开设赌场,诱人猜压,胜负以千百计。初由洋舶柁师,长年等沾染外夷恶习,返棹后群居无事或泊船候风,日酣于赌;富贵子弟相率效尤,逐成弊俗。耗财破家,害不胜举。……赌不一色,厦门三尺孩提既解赌;惟花会贻赌更深。人利其偿数十倍,虽深闺妇女,亦有圆梦、扶鸾、托人寄压者,灯光咒声,终夜喃喃。其流弊不可胜言。”[13]显然作者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批评厦门被“洋化”的现象的,这也正好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官方对赌博的否定态度,二是民间赌博已很盛行。
与此同时,在台澎金厦等新近收复的地区,清朝政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军力、兵响的不断增加,使清廷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频繁发生社会暴力事件,增兵需求与日俱增。在这种两难的情形之下,地方官提出了一种“减兵增勇”的方案,一则是朝廷减少对台澎金厦地区派兵数量,二则是准许当地军队或地方政府招募地方乡勇,以补充兵力减少带来的问题,保证社会的平安无事。连横《台湾通史》记载: (道光)二十八年,巡道徐宗幹上书朝廷,提出减兵增勇计划: “宗幹之议,一曰都守以上不用闽人,都守以下不用漳、泉人。二曰裁减精兵一半,以其经费,修理营房,分营居住。……八曰道、府、厅、县多养屯丁、乡勇,随时练习,以补兵力。书上,大府从之,而班兵稍受约束。”[14]道光年间,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在《台湾十七口设防图说状》中表陈: “地方不可轻动。其防夷海口,偎宜专用,水师及陆路本汛弁兵,第道里绵长,各路设防,最要、次要海口凡十七处,水师不敷分拨,自宜多雇乡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借此收养游手,消不靖之心。……通计四县、二厅,各庄内团练壮勇具册者,已一万三千余人,以备一旦有警,半以受庄,半出厅候调用。”[15]驻台军队招募地方乡勇补充军力不足,本来是一项军事措施,却对中秋博状元饼的习俗产生了影响:乡勇进入兵营的后果就是兵与民的直接接触,原本是军中节日游戏的博状元饼,通过乡勇,从兵营一点一滴地传播到了民间。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风俗,或者习惯的普遍齐一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个人面临同样的情境并作出同样的反应而存在的。但是风俗的持续存在,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各个个人在先前的风俗所规定下来的条件下形成了个人的习惯。”[16]如果不能勾起本地大多数民众的心理共鸣,博饼游戏是绝对无法成为一种地方普遍流行的风俗的。清朝的台湾正好具备这种接受博饼的社会条件,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地方。早在三国时期,大陆与台湾就有人员来往。南宋时期澎湖属福建泉州,移居台湾地区的汉族居民明显增加。“台湾”之名,就是一个来源于汉族人的称谓:“大员”。“‘大员’可能是闽南人民对根据土著番族的称谓译成的,所指的地区是台南市及其附近安平一带。这地方的海湾就称为‘大员湾’,简称‘大员’”。“来台湾的大陆人最初也多集中于此,其中以闽南人为最多,他们操的闽南话对‘台’ (dii)与大 (dei),‘员’(wan)与‘湾’(wan)音调极为相似。”[17]台湾人口,据台湾学者研究,“荷兰时代结束时 (1661),台湾的汉移民大约是两万五千人左右。郑氏延平王国覆亡前 (1683),大约是十二万人”,“直到康熙三十六年 (1697)先住民仍多于汉人”,“以今天的台南一带为例,整个荷兰统治期都属番人优势期,郑氏延平王国时代和康熙中期属于番汉均势期,康熙末年汉民大量涌入才进入汉人优势期。”[18]“及嘉庆十六年,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十七户,男女大小凡有二百万三千八百六十一口,而土番不计也。”[19]由此看来,最迟到乾隆嘉庆年间,汉族移民占台湾人口的绝大多数。“清代到台湾从事开发的移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来自闽、粤两省,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来自唐宋以来的世界名港——泉州,百分之三十五来自工艺发达的漳州,两地也都是农业发达、科名鼎盛、文化水平相当高的地区。”[20]为了控制移民数量,有效制止偷渡行为,清自收台之日就实行“凡渡台者禁带家眷”的政策,但在实行过程中又出现很多问题。乾隆二十五年,福建巡抚吴士功上奏朝廷《题准台民搬眷过台疏》,其中说: “凡向孑身漂流过台者,今已垦辟田园,足供俯仰;向之童稚无知者,今已少壮成立,置有产业。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又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系恋妻孥,冀图完娶之隐衷,实有不能自巳之苦情;以至急不择音,甘受奸梢愚弄,冒险偷渡,百弊丛生。”[21]在雍正乾隆长达七十年的时间里,围绕着解禁与开禁的问题,屡起争议,三开三禁,最后形成了有条件限制性开禁的政策。
从大陆沿海到台湾谋生的移民,同守台将士和官员一样,怀有深深的思乡之情。不过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文化,靠种地谋生的下层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文字,但是透过历史记载的故事,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们内心世界的秘密。为了家庭的团聚,他们不惜铤而走险,花钱雇船偷渡,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吴士功在奏折中坦陈:“在籍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 “故禁例虽严,而偷渡者接踵”。 “不肖客头奸梢将船驶入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荒岛人烟断绝,坐而饿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计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十月止,一载之中,共盘获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妇九百九十九名口。内溺毙者,男妇三十四名口;其余均经讯明,分别递回原籍。其已经发觉者如此,其私自过台在海洋遇害者,恐不知凡几。”[22]
来自闽粤浙沿海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男性,他们或孤身一人,或结伴而行,冒险渡海来到台湾,遵循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古训,以同乡同姓为纽带而结成互相帮助共同生活的社团,居住在一起。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我们有几万次实验使我们相信这个原则:相似的对象处于相似的环境下时,永远会产生相似的结果。”[23]他们跟守台将士具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境遇,也就有着同样的精神需求。在博饼风俗传来的时候,不仅不会排斥,反倒乐于接受,加入到博饼队伍的行列里来。不过,还有一点需要辨明:同样是从大陆来到台湾,面临着相同的处境,那为什么只有在军中才能创造出博饼的游戏,而民间却不能呢?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守台将士大部分来自于北方和江南各地,他们从小就养成了吃月饼的习惯,而台湾移民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闽南,在清朝前期闽南人还没有形成过中秋的习惯,如前文所述。事实上,闽南本土接受中秋月饼文化的时期,也正是台湾博饼风俗大力传播的时期。
三
然而,最初产生于台湾的博饼,为什么后来在台湾几近失传?却在一直默默无闻的厦门得以延续,并且获得了新的发展?
厦门的崛起得益于台湾的开发。自明代以来,厦门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一处军事上的要塞,明末清初又成为郑成功对抗清廷的根据地。清朝收复台湾后,厦门的地位更加重要:它成为福建通往台湾的海上交通要道,当时清代官员对此就有明确的认识,俞林家评价厦门说:“厦为全省出海门户,商贾所集富衍甲闽南。”[24]在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历史上,厦门是通往台湾的唯一港口,直到乾隆末年,才又开辟了鹿仔港、五虎门两个海港和两条新的航线。从大陆派往台湾的戍守官兵要从厦门运往台湾,三年后还要原路返回。每年支援福建的粮食,付给班兵家属的“眷米”,也是从厦门转运各地的。正因为如此,厦门又成为一处军事上的战略要地。驻守台湾的军队一旦有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撤回厦门。《林元戎亮传》记载:“澎台相距一水,居民汹汹,澎协将弁以孤岛难守,佥议撤归厦门,各出家属登舟,亮力排众议,按剑厉声曰:‘朝廷封疆寸土不可弃!……亮驰出江干申主将号令:驱官民家属各登岸,敢言退渡者,斩!’众心始固。”[25]直到清末,厦门一旦瘫痪,台湾就会陷入与世隔绝的状态。姚莹在《厦门有警台饷不敷状》中就说:“台郡自六月以后,厦船不到,粤中夷务无闻,省厦文报亦形隔绝。”[26]所以,清廷对厦门是以重兵把守,一旦失守,则会人心恐慌。“伏思厦门重兵所在,防守最严,传言恐尚未确,随令觅偏快船飞往侦探。台湾孤悬海外,全恃厦门为援。今有此警,未免人心惶遽,民情浮动之区,尤堪为虑。”[27]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的地位,成为厦门城市发展的主要的动因。城市发展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不但来自福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大量的移民开始在厦门居住。据统计,从1875年—1911年,仅经沿海口岸迁徙到厦门的人口就达到204686人。[28]厦门的发展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此定居。鼓浪屿就是一处外国人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康熙时代官方文献就记载:“鼓浪屿纵横七里,在厦门之西,圭屿之东南,东南望大担,北邻猴屿。上多居民,明初与大嶝小嶝俱徙,成化间复旧。约二千余家,率皆洋裔也。”[29]“1847年,居住在鼓浪屿的外国人有20多人,1890年有100多人,到1909年,增加到250人之多。”[30]随着洋人的增多,其与当地居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俞林家传》记叙了这样一则故事:“时诸海口皆通商,而厦门领事多恣睢不法,其译者辄鱼肉民,民怒执之,夷官率数十人持械至同知署,君出问故,夷气沮曰:从公往取人耳,君笑曰:吾民皆循良,守吾法度,焉用多人,命一隶往取之,须臾而至,夷大服。自是益敬畏君,每见必以免冠垂手为礼。”[31]一方面是受移居本地的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移居海外的华人的影响。“据统计早在1822年前后,每年有七万人左右经厦门移民海外,主要去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实际上是廉价劳动力,俗称 ‘卖猪仔’。”[32]从 1875—1911年,厦门总共出国1998620人,每年平均54016.76人;总共回国1032727人,每年平均27911.54人。[33]由于大量的华人移居海外,要寄信或汇款给国内的亲友,所以私人经营的具有邮政功能的“侨批局”应运而生。 “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侨批信局在厦门有七十六家之多。”[34]在与外国人的日常交往中,受到外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是非等级观念不可能不受到冲击。
正当厦门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台湾却遭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甲午海战,清军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驻守台湾的军队和行政官员全部撤回内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烟台换约,诏饬守土官撤回。”福建水师提都杨歧珍“率所部归厦门”。台湾巡抚唐景崧“携巡抚印……乘德商轮船逃……至厦门。”台南守将刘永福战败乘“爹多利士船主”民船出逃,“日舰八军山追之,至厦门,搜其船,不得。”[35]台湾割让后,大量台湾人口返回厦门定居。“据户籍统计,台湾籍在厦门居住的,民国6年有2883人,民国11年有5226人,民国15年有6332人,加上未登记的偷渡者,台湾籍在厦门的有 8000—10000人。”[36]这也就正好回答了为什么起源于台湾的博饼,反倒在厦门得以流行的疑问:戍守台湾将士和那些怀念故土的台湾居民大量返回大陆,对于台湾正在发展之中的博饼风俗而言,不吝是釜底抽薪,而对于厦门博饼的发展来说则是风助火势。厦门的中秋博饼就是在这个时候与台湾拉开了距离,本来是凤尾的厦门一跃而成为了鸡头。
新来的移民在这里演绎着新的文化。中国人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观念。那些告别了故土,定居在厦门的外来人,每到中秋佳节同样格外思念亲人。本来象征大家庭举家团圆的月饼,在家庭得不到团圆的情况下,扮演着团圆情感的精神寄托物的角色,而博饼游戏中的欢声笑语则填补了背井离乡之人的内心空虚。博饼在内心深处引起了外来移民的思想共鸣,使得它能够为绝大多数新来的岛民所乐于接受。
现代厦门博饼的最后形成时间应该在清末,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厦门文史专家也认为,“玩状元筹博中秋会饼游戏”在厦门始于清末“光绪宣统年间。”[37]清末厦门本地诗人留下许多描写博饼的诗作。清末厦门举人黄翰《禾山诗钞·赌月饼》中有“六子齐投任变翻,街头巷尾笑言喧。科名久已遭人唾,犹集群儿抢状元”[38]之说。光绪厦门举人王步蟾(1853—1904)《鹭门杂咏》一诗更有“冰轮三五又中秋,闺阁听香吉语求。月饼团圆新买得,拈骰夺取状元筹”的描述。其自注曰: “妇人拈香墙壁间,窃听人语以占休咎,亦古镜听遗意,亲友相馈以月饼,间有赌状元筹者。”[39]这充分说明民间已有博饼习俗,只是当时的博饼与现在还有所不同:在没有“博饼”之名的情况下,只好借用“赌状元筹”之名,博饼也还没有普及,在掷骰点数与月饼奖品之间还有筹条作为识别和联系的媒介。①有人以“当时的厦门人在中秋博状元筹,不博饼,月饼是用来馈赠亲友的”为由,认为王步蟾《鹭门杂咏》中的秋诗不能证明博饼的存在(详见2004年09月25日《厦门晚报》第三版:《我市发现博状元最早文献》)。我们不以为然。其一,诗中明确提到“中秋”和“听香”,文中又有“听香”解释,而听香自古就是闽南中秋节民俗,表明这些行为一定发生在中秋节;其二,从诗文的前后语境来看,作者两次提到月饼和状元筹,均为一句话的前后两个部分,如果毫无关联,那是不可思议的,说明这两者之间必定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其三,古代的状元筹是一种赌博工具,除在算命时单纯使用外,主要是用来决胜负定输赢,博取金钱和财物的。在中秋节这个特定的时间,不是博取月饼还能是什么?其四,全诗描绘的是厦门人过中秋的情形,节俗内容的多重性决定了诗中所写的三项活动,并不存在互相排斥或否定的情况。据此我们推断:在博饼行为产生之后,博饼名称尚未确定之前,完全有可能仍然沿用“赌状元筹”的名字,而且在人们掌握博饼方法和熟悉各种名目之前,状元筹中的筹条正好起到了一种媒介和标识作用:借着筹条上的刻辞,认识骰子数字,知道所获之奖。只有在熟练到相当的程度之后,才会在骰子数目与月饼等级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最终将筹条彻底淘汰。至于中秋亲友馈赠月饼,与博饼之间并无矛盾,赠完月饼之后再来博饼,就如同听香之后再去馈赠月饼一样。
总之,博饼行为之所以能冲出兵营走进民间,得益于博饼中包含的科举名称,以及博饼必有宴席和参与必定有奖规则,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闽南柁工和台湾乡勇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至如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大量的守台将士、官员和民众撤回大陆,则是导致台湾博饼几近失传、博饼风俗盛行于厦门的直接原因。
[1]重修福建台湾府志[M].清乾隆七年刻本.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1383.
[2]其中包括《台湾府志》、《重修福建台湾府志》、《重修台湾府志》、《宜兰县志》、《台湾县志》、《基隆县志》、《章化县志》、《诸罗县志》、《凤山县志》等9种。参见丁世良.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1380.1383.1386.1459.1562.1593.1654.1769.1876.
[3][日]佐仓孙三.台风杂记[A].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177)台游日记 台湾游记 台湾游行记台风杂记(合订本)[C].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390-391.
[4][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38-39.
[5][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44.
[6][清]汪士祯.池北偶谈[M].上海:中华书局,1982.84-85.
[7][8][14][19][35]连横.台湾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9.189.215.117.25-31.
[9]张扬文.博饼规则的概率趣谈[J].统计教育,2006,(1):20 -21.
[10][明]何乔远.闽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942.
[11][12][13][清]周凯.厦门志[A].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39、40)厦门志[C].1984.644.644-645.653.
[15][26][27][清]姚莹.中复堂选录[A].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42)东槎纪略东溟奏稿 中复堂选录[C].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404-405.427.427.
[16][美]杜威.人性与行为[A].<哲学研究 >编辑部.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八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14.
[17]陈木杉.海峡两岸编写“台湾史”的反思与整合[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97.51-56.
[18][20]尹章义.台湾开发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26.581.10.7.
[21][22][清]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Z].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726.726-727.“自巳”,原文如此,疑为“自已”之误。
[23][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5.
[24][25][31]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清代碑传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034.570.1034.
[28][33][36]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223.218-22.213.
[29][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影印本).1055.
[30]张镇世.“公共租界”鼓浪屿[A].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Z].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5.
[32][34]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哲夫,等.厦门旧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64.61.
[37]龚洁.厦门中秋博饼的起源与辩误[A].政协厦门市思明区委员会.思明文史资料(第三辑)[Z].2006年10内部发行本.22.
[38]黄翰.禾山诗钞·赌月饼[A].转引自刘海峰.科举民俗与科举学[A].上海嘉定博物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C].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36.
[39][清]王步蟾.小兰雪堂吟稿(卷二)[Z].清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13 b.原书作者亦署“王金波”,书名亦标为《小兰雪堂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