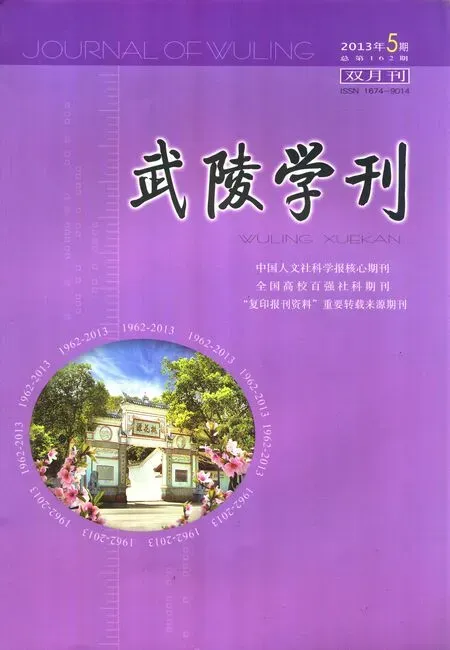商誉及其法律保护的新思考
杨源哲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 商誉保护模式的理论分析
(一)设权模式、反不正当竞争模式及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法律保护的对象包括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此处的“权利”指一种立法上明文类型化的绝对权,如物权、著作权、专利权等,而非宽泛意义上的行为资格或行为自由。所谓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是指法律上主体所享有的、立法没有做类型化处理的、只能受到消极保护的利益。与权利相比,此种法益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权利客体和公示的权利内容,其受到的保护力度也较弱。比如在知识产权法中,尚未被制定法明文类型化的、知识产权以外应受保护的利益①包括商业秘密、未注册商标、作品标题等。
权利与法益的区分并非仅是理论上的偏好,它有其实际意义。在制度设计上,立法者设计出设权模式和反不正当竞争模式来分别保护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二种保护模式的区别大致如下:第一,设权模式属于支配性财产权体系,反不正当竞争模式属于侵权法体系[1]。前者从正面规定主体享有的权利,权利的客体、内容、边界、要件、救济方法及免责条款等都是公示的,他人因此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后者则是从反面禁止某些行为,权利内容无从得知,难以苛求他人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也有学者据此将知识产权法分为权利赋予法和行为规制法[2]。第二,保护强度不同。在设权模式中,法律提供的是事前的、积极的保护,权利人享有的是有明确范围和对世效力的绝对权以及由绝对权派生的一系列请求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模式中,法律提供的是事后的、个案的、消极的保护,权利人只享有“有限的、相对的、几乎没有什么非排他性质的利益”[3],以及只能对抗特定恶意竞争者的请求权。
就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而言,它是指知识产权必须由制定法加以明确类型化,没有被类型化的因知识的创造所带来的利益不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任何机构不得在制定法之外为知识的创造者创设某种知识产权[4]。根据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域名、商业秘密、商誉等对象都未被知识产权成文法明确类型化,因此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或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防止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过度扩张、警示立法者慎重创设知识产权、防止司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或随意创设知识产权。应当说,区分设权模式和反不正当竞争模式的观点与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二)商誉在现行法中没有“权利”的名分
本文认为,从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或者说从区分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的角度来说,某一保护对象只有受到了设权模式的保护才能被称为“权利”或者说享有“权利”的名分。因此,“商誉权”的提法不严谨,其他诸如“商业秘密权”②、“域名权”③的说法也不准确。第一,这些所谓的“权利”在现行立法上都没有被明确规定并类型化,其主体充其量只是享有某种无明确范围的、排他性极弱的、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以及在个案中的、有限的、对抗特定人的请求权。简而言之,这些利益并没受到设权模式的保护,其受保护的依据仍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侵权法的一般原理。在使用“商誉权”这一称谓时,学者们忽视了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的区别。正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曾指出:“权利在私法中所占的主导性地位,长期以来遮住了传统学说考察其他思路的视线,人们将那些仅仅通过个别的命令或禁令得到保护的法律状态也视作了权利。”[5]第二,不能以法律中有个别保护商誉的条款就认为存在“商誉权”。因为即使将某种法益放入某部法律中保护,也不能当然推导出该法益本质上就属于某种权利,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物权法中规定了对占有的保护,就认为我国承认占有是一种权利。
从以上分析可知“商誉权”这一概念在现行法中不存在。当然,如果仅仅是纠缠在某个概念的称谓、叫法的问题上,难免有玩文字游戏之嫌,我们尚须讨论商誉有无必要以及有无可能上升为权利,或者说商誉是否应该以及是否能够以设权模式来保护。下文将分析是否有必要和可能给商誉一个“权利”的名分。
(三)赋予商誉“权利”名分的不必要性
首先,通过对商誉载体的保护即可实现对商誉的保护,专门设立“商誉权”只会浪费立法资源。第一,商誉的价值蕴藏于企业的各构成要素中或附着于商标、商号等载体中,并凭此反映出自身的价值所在。在企业资产评估中,若将商誉和商标、商号等无形资产分开估价,实际上会导致资产的重复计算。第二,实践中,通过对商号及注册商标的设权保护已足以解决多数商誉保护的问题。至于其他类型的侵犯商誉行为,如诋毁商誉和侵犯未注册商标的行为等,交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即可。这样一来,设权模式与反不正当竞争模式互为补充,已足以实现对商誉的充分保护,无必要再设定专门的商誉权或者说以设权模式来保护商誉。从比较法或实证的角度看,极少有国家正面规定了商誉权,多数国家还是通过对商业标志的设权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侵权法的一般条款来实现对商誉的保护,此种模式在实践中也无太大问题。
其次,“商誉权”的创设将使原本停留在法益状态的某些利益不合理地上升为权利,打破因区分设权模式与反不正当竞争模式而带来的利益平衡,削弱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意义。实践中,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同为商誉利益的载体,前者受到保护力度更强的设权模式的保护,后者则受保护力度较弱的反不正当竞争模式的保护④。法律厚此薄彼的原因在于,注册商标符合了法律的公示要求,可以满足行为人的某种合理期待,因而可以享受更强更明确的保护,侵权人使用注册商标将被推定为有恶意。而未注册商标没有公示,难以让他人知道权利的边界和内容,自然不能享受注册商标的法律待遇,权利人需要在个案中证明对方的恶意。这种法律设计合理地平衡了商标权人和行为人(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既保护了商标所有者的私权,也满足了行为人(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这与专利法中区分保护发明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一旦创设了“商誉权”,未注册商标将可以通过“商誉权”与注册商标平起平坐,进而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
(四)赋予商誉“权利”名分在立法技术上的不可行性
从立法技术上说也不可能规定“商誉权”。首先,商誉的保护范围无法确定。商誉是指公众从商主体的经济能力或经济活动的角度对其偿债能力、经营能力、商品质量、服务水平、商业道德等方面的情况所作出的综合性评价。可见商誉的范围其实非常宽泛。即便是主张专门设立商誉权的学者也承认商誉权是一种没有恒定保护范围的无形财产权,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不同,其保护范围无法基于客体的表现形式(作品)、技术特征(专利)或标记构成(商标)来加以确定[6]。
其次,商誉的内容难以进行类型化处理。立法者之所以通过设定权利来保护某些类型的法益,就在于这些法益具体明确且具有相同的特征,能被类型化并共同适用一套规范。比如说字母、数字、颜色、图案都属于可视性标志,被类型化处理后便成为了现行法上的商标。有的人还将声音、气味也包括进来,认为商标只要是可感知的标志或符号即可,不要求有可视性。然而,商誉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缺乏相同的特征,难以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实际上,能被类型化的只是商誉的载体,商誉本身是很难甚至不可能被类型化的,商誉载体的类型化不等于商誉本身的类型化。
再次,即便强行规定了“商誉权”,也难以归纳出其权利内容。商誉自身范围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立法上很难给“商誉权”归纳出具体明确的权利内容。既然客体都不确定,权利的边界自然也难以确定。有学者尝试归纳“商誉权”的权利内容,认为商誉权包括了商誉保有权、商誉维护权、利益支配权、利用权等[7]。但本文认为,这些权利内容都太过宽泛,难以起到公示效果,他人无法从中准确得知该权利的范围和边界,也难以明确预知自己的某一行为是否会侵犯该权利。
最后,强行规定“商誉权”会影响原有法律体系的和谐。第一,“商誉权”难以和商标权、未注册商标相协调。虽然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同为商誉的载体,但立法者基于平衡各方利益的考虑对二者采用了不同强度的保护模式。强行引入“商誉权”很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如何在不破坏原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协调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的关系进而将二者一同纳入“商誉权”中尚须仔细考量。第二,“商誉权”难以和名誉权协调。商誉与名誉是何关系?商誉是否属于名誉?若认为商誉属于名誉,则“商誉权”将与名誉权有所重复,浪费立法资源。
(五)从名誉权中推出“商誉权”的不可行性
有人认为“商誉权”类似名誉权或者说名誉包括了商誉,既然我国立法上规定了名誉权,自然可以仿照名誉权推出或分解出“商誉权”。比如有学者指出,可在未来民法典中从原来的法人名誉权分解出独立的商誉权[8]。本文不赞同此观点。
首先,商誉与名誉不同。理由如下:第一,二者内容不同。名誉主要是主体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评价,而商誉主要是对主体的经济能力或经济活动方面的评价。第二,二者两者体现的利益不同。名誉属于人格尊严,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商誉体现的是主体的财产利益,商誉本身可以被估价甚至转让。第三,从商誉的发展史也可以看出,它和名誉不是同根生的兄弟或姐妹。在英美法中,商誉是与诋毁之诉不同的仿冒之诉的保护对象,名誉与商誉分属不同的令状形式下⑤。
其次,即便退一步,认为名誉包括了商誉,也难以从名誉权推出“商誉权”。第一,名誉权的概念本身也有争议,名誉有无“权利”的名分尚须讨论。在英美法中,名誉主要通过有关禁止诽谤的“诋毁之诉”来保护。在大陆法系,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也仅有涉及名誉保护的规定而没有名誉权这一概念。我国虽然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名誉权,但并未从正面归纳出具体的权利内容⑥,也没有明确名誉权客体的范围,这种规定只是一种宣示性的或列举性的规定。有学者甚至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作宣示性的列举性规定也是不必要的,独立成编更是多余的,只需要在自然人部分明确规定人的自由和尊严受法律保护并在侵权行为部分从保护的角度对具体侵害类型做出规定即可[9]。关于应否从正面规定和确认人格权及其客体以及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的问题涉及民法理论的重大争议,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但本文认为,名誉权至少在现行法上仍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表面上看,立法者给了名誉一个“权利”的名分,但实际上并未让名誉享受到权利的待遇,名誉权的权利客体、成立要件、权利内容、边界范围、侵权行为的要件、救济形式、免责条款都未明确。因此,不能认为名誉已经受到了设权模式的保护,既然没有受到设权模式的保护,那么也不宜采用权利⑦的称谓。如果名誉权的概念尚存争议或名誉本来就没有“权利”的名分,那么从名誉权中推出或分解出“商誉权”的观点则更难以让人信服。第二,难以从法人名誉权推导出商誉权。关于法人有无人格权的问题,民法理论仍有较大争议。有学者指出法人基于民事主体资格而产生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本质上只能是财产权[10]。人格权设立系基于伦理人格而非法律人格,法人无人格权,法人享有的所谓人格权实质上只是财产权[11]。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法人无人格权(法人名誉权)的观点成立,那么从法人名誉权推导出商誉权的逻辑前提就存在疑问。
最后,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从名誉权分解出商誉权进而将商誉归入人格权范畴的做法不利于对商誉主体的保护。首先,现实中名誉权纠纷案件的赔偿数额往往较少,而商誉主要体现的是一种财产利益,若将商誉侵权案件按名誉权纠纷案件处理,其赔偿数额相对于商誉受损带来的经济损失只是杯水车薪,这将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再者,若将商誉视作一种人格利益,则现实中让商誉随其载体转让的做法将同人格权的专属性特征相矛盾,理论与实践将难以衔接。
二 商誉保护模式的实证考察
(一)英美法系对商誉的保护
普通法系不存在体系化的民法典,其侵权行为法自成一体。法院一般通过判例法制度将商誉的保护纳入到侵权行为法尤其是仿冒之诉的适用范围。商誉的概念由诋毁之诉中的名誉演变而成。由于一开始的“低毁之诉”仅仅适用于自然人名誉受侵害的案件,而自然人的名誉是涉及个人情感、人格尊严、社会声望等伦理道德方面的社会评价,法人非伦理意义上的主体,似乎不应享有这样的评价,作为法律拟制主体的法人在受到商业诽谤后将不能提起诋毁之诉。法人并无精神利益或人格利益,它提起诋毁之诉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尊严或情感上的伤害受到救济,而在于获得一种金钱上的赔偿以弥补其财产因商誉降低而遭受的损失,这种损害用“名誉”已无法涵盖其意义,于是,“商誉”的概念以及仿冒之诉由此产生。商誉成为财产法规范的对象,并始终被作为财产类型之一种[12]。在美国,《兰哈姆》第43条第1款规定了禁止商业诋毁的行为:若在商业性广告或促销中,就他人的商品、服务或商业性活动的性质、特征、质量或地理来源进行虚假陈述,那么该商品的经营者就可提起诉讼,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商业损害的责任。
(二)大陆法系对商誉的保护
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并未设立商誉权或信用权,而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侵权法中的一般条款来保护商誉。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以竞争为目的,对他人的营利事业、企业或企业领导人,对他人的商品或者服务,声称或传播足以损害企业经营或业主信用的事实者,只要无法证实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则应向受害人赔偿发生的损害。受害人也可以请求停止传播这些事实。日本在1975年修订后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通过陈述虚假事实或散布这种虚假事实进行的妨害有竞争关系的他人在营业上的信用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此外,还有的国家采取侵权法的一般条款保护信用(如法国)或通过扩张名誉权来保护信用⑧。受大陆法系影响较多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在第195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信用权,有人认为,该规定使得商誉可以通过信用权来保护。
(三)国际条约框架下对商誉的保护
WIPO(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第3条(1)款规定:在工业或商业活动中,对他人企业或者其活动,特别是对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诋毁或者可能诋毁的任何虚假或不合理陈述,构成不正当竞争。可见,示范法反应了两大法系在商誉保护模式方面的某种共性。
(四)我国对商誉的保护
在我国,保护商誉的规定散见在《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侵权责任法》之中。《民法通则》第5章规定了法人名誉权、荣誉权。《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刑法》第221条规定了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此外,《侵权责任法》作为一部以救济为主要功能的法律,其保护的权益范围非常广泛。该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据此,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13]。如此,商誉作为未上升为权利的利益也可通过以上概括式或兜底式的条款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由此可见,我国在实践中也是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模式来对商誉进行保护。
结 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实中确实有加强商誉保护的需要。但是,“商誉权”这一概念是否合理,或者说是否有必要采用设权模式来保护商誉,则需要谨慎分析。首先,从区分设权模式和反不正当竞争模式的角度,“商誉权”在现行法中不存在,“商誉权”的提法不严谨。商誉只是一种法益,不能直接以设权模式来保护,无必要也不可能上升为类型化的权利,更不能从名誉权分解出“商誉权”。其次,从比较法或实证角度,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都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侵权法中的一般条款来保护商誉,实践中此种模式并无多大问题,从正面明确规定“商誉权”及其内容或者说直接以设权模式来保护商誉的非常少见。当然,各国商标法通过对注册商标的设权保护间接使一部分商誉享受到了“权利”或设权模式的待遇,但此时被立法明文类型化的是商誉的载体,而非商誉本身。综上可见,将商誉定位为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并以反不正当竞争模式来保护不仅能满足理论的逻辑要求,同时也符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我们没必要耗费立法资源或另辟蹊径去创设新的“商誉权”。
注 释:
①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③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页。
④当然,未注册驰名商标及在先使用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未注册商标,在我国《商标法》中还是做了规定,但这两类商标均有其独特性。
⑤参见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9页。
⑥学界对是否有必要从正面规定和确认人格权尚存争议。参见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1-91页;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429页。
⑦再次强调此处的“权利”仅指一种立法上明文类型化的权利,如物权、著作权、专利权等。
⑧参见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张新宝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1]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4.
[2]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
[3]韦之.论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25-32.
[4]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J].中国发展,2006(3):49-54.
[5][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3.
[6]吴汉东.论商誉权[J].中国法学,2001(3):91-98.
[7]郑新建.商誉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53-54.
[8]江帆.商誉与商誉侵权的竞争法规制 [J].比较法研究,2005(5):40-51.
[9]李永军.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56.
[10]尹田.论法人人格权[J].法学研究,2004(4):51-57.
[11]郑永宽.法人人格权否定论[J].现代法学,2005(3):89-93.
[12]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8-79.
[13]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