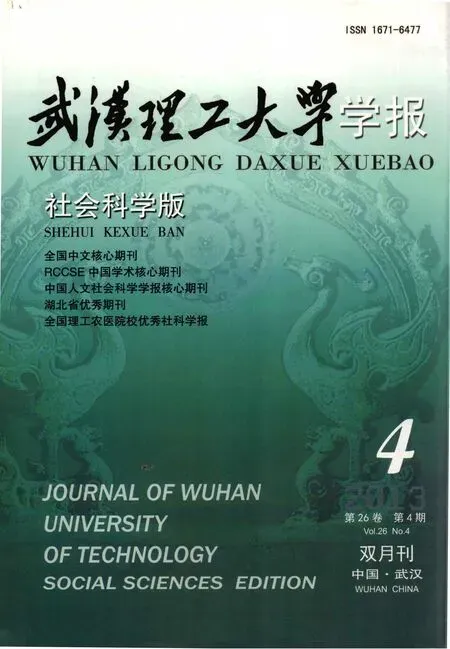华兹华斯的自然情缘及其文化意义*
杨惠芳
(江汉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华兹华斯(1770—1850)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自然风景诗人和自然思想家之一。他几乎终其一生与自然为伴,不仅创立并发展了西方自然诗派,而且诠释和确定了自然的深刻意蕴。像华兹华斯这样对自然表现出特别情怀的大家古今中外并不多见,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华兹华斯与自然的情缘不单单反映出他个人深爱自然这一现实,且更具有超越其上的人类背景和意义。
一、华兹华斯自然情缘的特别之处
自然风景和物质社会是伴随人类的两大存在,古今中外,与自然结下情缘的诗人、画家、哲学家灿若繁星。但考之中西思想文化史,华兹华斯的自然情缘却具有很多特别之处。
其一,华兹华斯在并不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几乎是横空而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欧洲“走向自然”的文化土壤不仅不深厚,而且没有一以贯之。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山水自然意识起源早,动因多,积淀深,影响广,“走向自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终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可以让人走向自然;“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玄对山水”的玄学思想、“归心山水”的佛家思想也可以让人走向自然;“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的隐逸思想可以让人走向自然;“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漫游思想也可以让人走向自然。基于此,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初步的山水情怀,汉代出现了铺陈山水的大赋,三国以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走向自然的魏晋风度,东晋时期诞生了中国的山水诗派和田园诗派,成长出谢灵运和陶渊明等著名诗人,而唐代盛行漫游风尚以至于少有诗人和散文家不纵情山水,不描写自然。自唐而后,自然诗派以一种惯性向前发展,讴歌自然的大家不断,佳作迭起,使山水自然意识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主流。而反观欧洲,则不尽然。虽然不能说欧洲没有滋生和积淀自然意识,但其自然意识时断时续,不深不厚,难入主流却是不争的事实①。如果说在中国产生山水文学大家是顺理成章之事的话,那么成长于欧洲的华兹华斯就称得上是横空出世了。
其二,华兹华斯之深爱自然在西方尚无可以比拟者。如果把为人、为诗及思想结合起来看,在英国乃至西方能持之以恒地走向自然,描写自然,阐述自然者,当首推华兹华斯。华兹华斯童年时代就与自然为伴,1789年定居湖区后直至终老,即使外出,也多是徜徉山水。华兹华斯并不深居简出,而是以步行为目的,以步行为享受,不管阴天和晴天,都在湖区内散步。不仅仅是徜徉自然,华兹华斯更以创作篇幅多、质量高的自然诗歌而著名。同为“湖畔派”诗人的柯尔律治主要在伦敦等城市生活,而且自然诗歌较少。骚塞虽然在湖区住了40年,但并没有多少自然佳作传世。稍晚于华兹华斯的拜伦、雪莱、济慈等诗人,虽有自然之作,但并不以此而名于世,而且也没有长时间寄居山水的经历。放眼欧洲大陆,同样找不到与华兹华斯相匹者。至于后继者,虽然英国的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德、托马斯等诗人,欧洲大陆的艾兴多尔夫(德国)、海涅(德国)、雨果(法国)、莱蒙托夫(俄国)、卡尔杜齐(意大利)、瓦雷里(法国)等诗人,美国的布莱恩特、朗费罗、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弗洛斯特、庞德等诗人作家都曾钟情于自然,并创作了自然诗歌,提出了自然哲学,但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却明显逊色于华兹华斯。即便梭罗在生态伦理思想上可与华兹华斯相提并论,但在有关自然的人文综合领域上的成就不及华兹华斯;即便庞德创作了很多自然诗,但他过分强调意象而忽略了具体山水,且没有多少关于自然哲学方面的论述。
其三,华兹华斯的自然情缘在多方面超越中国诗人。毫无疑问,中国赞美自然的诗人和诗篇之多远非西方所能比,而且山水田园诗的整体成就也远高于西方自然诗,但就单个作家而言,则另当别论。首先,中国以自然诗而占据文学史重要地位的作家并不多。虽然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王世贞、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写有大量山水诗,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袁宏道、袁枚等写有大量山水散文,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更高。与华兹华斯相类似的只有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徐弘祖等少数作家。其次,这些作家所揭示的自然意蕴不如华兹华斯全面。陶渊明、孟浩然之诗多围绕隐逸和乡村生活展开,透露出一种与世无争的闲适情调。谢灵运是“壮士郁不用,泄为山水诗”,寄寓其孤傲性格、失意悲愤和厌世情绪。王维之诗虽有“长河落日圆”等气象,但更多的则是通过自然参佛养性。徐弘祖游历名山大川,著有《徐霞客游记》,文学和旅游审美价值很高,但并未深入阐述自然观。华兹华斯则通过走向自然,描写自然,系统地阐发了自然的文学题材价值、审美愉悦价值、宗教启示价值、旅游休闲价值、民族认同价值、诗意栖居价值、女性比附价值等②。再次,华兹华斯通过自然对社会的反思更为深刻。中国诗人在无奈面对社会时往往选择一种“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把山水田园作为栖息身心的最后领地,更关心的是如何标榜自我的独立人格,如何保持自我的高洁情怀,而不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自然来深刻反思社会。华兹华斯在走向自然后,反思并否定了不理想的社会生存状态,探索了理想中的人类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西方自然诗晚于中国,自然意识弱于中国,但华兹华斯们对自然的思考深度却非陶渊明们所能比。
二、华兹华斯走向自然的深层原因
华兹华斯走向自然,并与自然结下特殊情缘,不能仅仅从“性本爱丘山”这一层面来思考,而应从人类之存在和发展这一角度进行多维透视。
(一)华兹华斯走向自然,是个人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双向作用的产物
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往往是个人文化心理结构基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能动地创造的结果。华兹华斯走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华兹华斯的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包含着强烈的自然意识。童年时代,华兹华斯便在幼小心灵里积淀了深厚的自然元素。得益于家居的地理因素,他能更容易地接触身边的自然山水;归因于家庭背景,他能相对自由地在自然中释放童年无拘无束的天性③。虽然童年时代的华兹华斯走向自然带有很大程度的非自觉性,但这种非自觉行为对华兹华斯文化心理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华兹华斯成年后经常回忆起与花草为伴,在冰湖嬉戏的童年时代,并强调“孩子到四岁后,有了鲜花、草地、牛群、羊群,就根本不需要其他的玩伴了”[1]。华兹华斯还认为,自然的属性与童年的天性在“自由”这一点上异质同构,成年人不能再返回童年,要保持这份自由,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向自然。基于此,华兹华斯在长大成人后进一步发展了包含强烈自然意识在内的文化心理结构,最终与自然结下特殊情缘。其次,欧洲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滋生着自然意识的因子。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自然意识就在慢慢积淀,萨福、维吉尔、贺拉斯等都描写过自然山水,赞美过田园风光。16世纪以后,自然意识已逐步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就哲学思想而言,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人性,走向自然成为当时新的思潮和行为,法国哲学家卢梭还提出了“返归自然”的新理念。就文学艺术而言,欧洲描摹自然的画派崛起,并以意大利为代表,英国也有吉尔平、威尔逊等画家;赞美自然的诗句频现,英国的斯宾塞、马娄、莎士比亚、纳什、格雷等极力讴歌自然风景。就社会风尚而言,18世纪以来,寻找“如画风景”的热潮在英国迅速兴起,很多人出于爱国主义情怀而走向自然,努力探寻欧洲大陆风景的英国版本[2]58,华兹华斯本人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总之,个人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契合促使华兹华斯走向了自然,而华兹华斯通过走向自然又使欧洲的自然观念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发生了裂变。
(二)华兹华斯走向自然,是基于特定现实对人类生存方式进行思考的需要
华兹华斯所面临的特定现实,既有社会制度变革意义上的法国大革命,又有生产方式变革意义上的英国工业革命。在华兹华斯看来,尽管这些革命都在推动人类进步,但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英国工业革命,即使取得再大成功,也不能对人类生存方式给出满意的回答。华兹华斯曾经欢呼的法国大革命最后变成了暴力,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心灵解放的问题;英国工业革命在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在华兹华斯眼中,城市不仅人口膨胀,公害蔓延,社会混乱,环境污染,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城市的所谓文明法则和科技理性也极大地压抑着人性,让人感到窒息。他在《伦敦,1802年》中认为伦敦毫无生机可言,进而非难工业文明造成的恶果,“我们的和平,我们敬畏的天真,我们视为法律的纯洁宗教都无踪无影”,并无奈长叹,“我不知道在哪儿寻求安慰,因为我感到透不过气来”[3]1115。既然城市不再是人类理想的栖居场所,所谓社会文明也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方式,华兹华斯只能把目光投向自然。“我深为欣慰,能从自然中找到我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认出我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4]129。从这种意义上说,华兹华斯走向自然,是为了反思进而否定不理想的社会生存状态,并借自然的本真状态来启迪人们寻找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他对北英格兰和苏格兰高地朴实无华的乡村生活的赞美,也是这一思想的有力佐证。
(三)华兹华斯走向自然,是其构建的“五位一体”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华兹华斯在面对世界时,以“自然二”④为宗,涵盖上帝、儿童、青春女性、平民生活、自然等要素,构建了“五位一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精神世界都应该以其本来的方式存在,而不应矫揉造作地加以改变。上帝是整个世界的原动力,所以华兹华斯在描写伦敦祥和的一面后向上帝禀告:“千门万户都沉睡未醒,这整个宏大心脏仍然在歇息”[5];儿童是天真无邪的存在,所以华兹华斯说“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4]257;青春女性秉天地灵气而生,所以华兹华斯按照“自然二”法则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美女露西形象;“自然是上帝在世间留下的神圣碎片”[6]78,所以华兹华斯描写了大量处于本真状态的山水、花鸟、天象等自然风景;平民生活远离所谓的文明法则和科技理性,所以华兹华斯写下了《孤独的割麦女》等许多反映乡村乡民生活的名篇。在华兹华斯看来,未遭人类破坏的自然,未被世俗侵袭的儿童,未走极端模式的宗教,未受文明熏陶的乡村,未为男人染指的少女“五位一体”,乃世界之理想状态,他希冀出现这种理想状态。基于这种世界观,华兹华斯走向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自然在“五位一体”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更具有现实可能性,因为儿童、少女终归要长大成人,乡村开始遭到文明的入侵,宗教也已被时人操纵,最能寄予希望的就是尚能保存完好的自然了。在华兹华斯看来,未被破坏的风景宁静祥和,自由自在,乃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也是他心灵的归依之所。他心甘情愿地与自然两相契合,视自然为疗治心灵之伤的驿站,并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三、华兹华斯自然情缘的文化意义
基于与自然结下的特殊情缘与走向自然的特殊背景,华兹华斯的出现对于英国乃至全人类都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体现在旅游审美、民族认同、文学发展、生态伦理、生存方式等各个方面。
(一)华兹华斯走向自然山水,开启了英国自然风景之旅
华兹华斯之前,也有人流连于山水,但总体上看,英国的自然对于人们来说仍是一个陌生而可怕的存在。1786年,英国风景画家吉尔平仍然认为“湖区山峦呈现了古怪的、奇异的形状,是令人不愉快的”[7]。华兹华斯以其诗歌创作展现自然之美,“摇曳着花冠,轻盈飘舞”的水仙花[4]100,让人们看到了动人的景象,“纵身下去,从茅檐屋下,传来阵阵歌声”的红雀[3]1293-1295,让人们听到了美妙的旋律。可以说,华兹华斯的诗歌开启了人们欣赏大自然的眼睛,引导人们走向了自然风景之旅。不仅如此,华兹华斯还身体力行,率先尝试度假旅游方式。不同于中外游历诗人在旅途中的观光揽胜,华兹华斯长期居于人们称之为“鸽舍”的小农舍,并在湖区散步作诗;这不仅本身成为现代度假旅游的雏形,而且对湖区成为英国乃至世界旅游度假胜地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二)华兹华斯赞美具体风景,增强了英国人的民族认同感
华兹华斯自然诗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将英国风景特定化,描写了瓦伊河谷、湖区、斯诺登山、雅罗河等一个个具象风景,这与其前人是根本不同的。长期以来,英国人心中的自然风景停留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贺拉斯诗歌所描写及意大利风景画家所描绘的自然风景上,“甚至到了18世纪末期,游客还是以意大利情结来欣赏湖区的”,并在其中寻找阿尔卑斯山的影子[2]58。华兹华斯穷其一生,踏遍英伦,寻找英国如画风景,用“纯净、鲜明、流畅、有力”[4]207的诗句将其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因此而“不稀罕阿尔卑斯山雷鸣的湍濑”[4]207。正是因为华兹华斯等人的努力,才真正创造了自然风景的英国版本,确立了英国风景在欧洲的地位,并让英国风景成为英国民族综合体的一部分。在英语中,湖区特指英格兰湖区,高地特指苏格兰高地,足以说明英国人对风景的民族认同感;这虽非华兹华斯一人之功,但华兹华斯起到的推广作用不容忽视。
(三)华兹华斯描写自然风景,填补了欧洲文学史的空白
中国自然文学(山水田园文学)源远流长,严格意义的田园诗派和山水诗派也已在4世纪末5世纪初形成。但英国乃至欧洲的自然山水文学却发育迟缓,不能不说是欧洲文学史的一大缺憾。华兹华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诗人,虽然“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宣告了欧洲自然文学的诞生,从而填补了欧洲文学史的一大空白。没有华兹华斯,欧洲文学史也许将会失色不少。诚然,华兹华斯之前的很多作家都赞美过自然风景,但华兹华斯毕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以风景为主要题材的诗人,也是自然诗派(湖畔派)的主要创立者,更以其高质量的自然诗作奠定了自然文学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当时的人们公认“华兹华斯所创之诗篇风格新颖,独具一格”[8],《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和拜伦等诗人责难华兹华斯的诗歌背离主流传统,却也充分说明了华兹华斯在自然文学上的开创之功。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评价华兹华斯“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然’这个名词,描绘了一幅幅英国北部的山川湖泊和乡村居民的图画”[9]。
(四)华兹华斯呵护自然风景,启迪了现代生态伦理思想
华兹华斯走向自然后,并不是独自陶醉其中物我两忘,而是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使命。看到廷腾寺下游的瓦伊河谷风景受到铁厂破坏,他非常痛心,并在比较中更加向往上游生态环境的恬静和优美[10]。面对格拉斯米尔湖即将被入侵,他曾气愤地写信给《晨报》道:“如果曾静立此处体味风景的诗人格雷还活着的话,面对铁路的入侵及其对土地的碾压和分割,面对因火车而产生的机器轰鸣声和浓烟,面对乘坐火车蜂拥而至的追逐风景的有钱人,他又该是何等的哀伤呢?”[11]更难能可贵的是,华兹华斯从全英国乃至全人类发展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提出将风景上升为“国家财产”[2]158的高度,而且在他看来,“自觉保护荒野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是保护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圈这一永久栖息地,也是维护人类的精神家园”[6]89。华兹华斯近200年前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自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华兹华斯描绘“同在”意境,指明了人类理想的生存方式
人类如何在自然中生存和发展,既是一个自然命题,也是一个社会命题。华兹华斯在诗歌中展示了一种“与自然同在”的生存境界,那就是以保护资源之心,友爱环境之情与自然相处,与我国提出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思想差可相似。关于保护资源,上面关于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的阐述已经非常明了。关于友爱环境,华兹华斯一直在追求一种与自然和谐对话的境界:有水仙花这样愉快的伴侣,“我的心灵便欢情洋溢,和水仙一样舞踊不息”[4]100;看到蝴蝶飞舞,他希望“咱俩在一起,话儿说不尽”[4]187。他的《访雅罗河》更是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环境友好”的美丽画卷:“你永远年轻的水流持续着,活泼欢愉的旅程,我口中能按着你的节奏,发出快乐的歌声……雅罗河!你真实的身形,将跟我同在,使我欢悦”[3]1397。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广为流传的儿歌《小燕子穿花衣》所崇尚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华兹华斯显然指明了一种更为理想的人类生存方式。
注释:
① 法国汉学家侯思孟在《山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中曾说:“中国人走向大自然的倾向和欧洲人背离大自然的倾向成为他们各自都延续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生活方式。欧洲人直到19世纪随着浪漫派的出现才真已醒悟过来去领略大自然的美景。”见《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第262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6月版。
② 作者在《华兹华斯与英国风景价值的多维呈现》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见《理论月刊》2012年第7期。
③ 华兹华斯童年居住和上学的地方都靠近湖区,为其接触自然提供了便利;由于父母早逝,华兹华斯由其舅父照管,所受的约束相对较小。如果不是这些因素,华兹华斯的人生也许将是另外一种轨迹。
④ 为便于叙述,将表示“本真状态”的“自然”标记为“自然二”,以区别于表示“大自然”的“自然”。
[1]John Purkis.A Preface to Wordsworth[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76.
[2]达比.风景与认同[M].张箭飞,赵红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帕尔格雷夫.英诗金库[M].罗义蕴,曹明伦,陈朴,编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杨德豫.华兹华斯诗歌精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
[5]杨德豫.华兹华斯诗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71.
[6]鲁春芳.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7]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
[8]梁实秋.名人伟人传纪全集之81:华兹华斯[M].台北:名人出版社,1983:124.
[9]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M].徐式谷,江 枫,张自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
[10]Bate John.The Song of the Earth[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145-146.
[11]Malcolm Andrews.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89: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