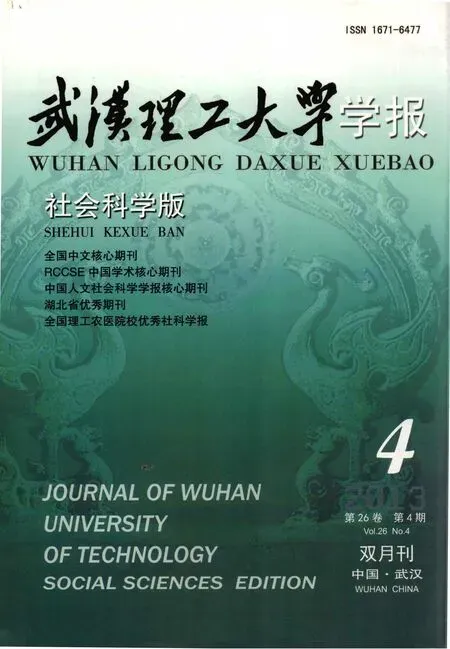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研究*——基于UPOVC视角
刘介明,谭 清
(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为了促进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推动世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协调发展,1968年8月10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UPOVC)应运而生,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UPOV)也即成立。UPOVC的主要目的在于确认和保护植物新品种育种者的权利,并由公约缔约国组成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联盟,从而形成当代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体系的基础,为国际间开展优良品种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合作交流及新产品贸易提供法律框架[1]。1999年4月23日我国成为UPOV第39个成员国,同日开始受理国内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这使得我国的育种技术创新和种子产业开始真正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之中,此举通过国际公约的手段加强了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对推动我国种业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强力推动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该协定对成员国知识产权保护设立了最低保护标准,如果达不到该标准,将受到贸易制裁。协议第27第3项(b)规定:WTO成员应以专利或有效的专门制度或两种制度结合,给植物新品种提供有效保护,并在建立世界贸易协定生效的4年之后进行检查。该协议把加入WTO与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挂起钩来,意味着凡是WTO的成员国都必须对植物新品种提供知识产权法律上的保护,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2]。
一、现状与问题:UPOVC框架下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位阶低
根据UPOVC和TRIPS协议的规定,各成员国可以采用专利方式或某种特别制度,或者两者的结合来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因此,可以将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模式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单一型”的模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如法国、德国等,以前以专利法的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自签订欧洲专利公约之后,这些国家及该公约的所有缔约国都将植物新品种排除在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外,而以特别法形式给予保护。我国也是采用“单一型”模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我国专利法明确将动植物品种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外,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来实现。但是该条例法律位阶太低,非常不利于对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我国亟需制定专门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唯此,我国才能从保护形式上与其他UPOV成员国对等,也便于与他国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此外,从当前国内广大农作物育种者和种业经营企业的现实情况来看,要求制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二)保护范围小
UPOV 1991年文本将授权保护范围扩展到所有植物的属或种,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解除了限制。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按照UPOV 1978年文本精神,只保护国家新品种保护名录中的植物品种,而不是全面放开对所有新品种的保护。2013年修正本也只对罚则中的第39条和40条进行了修改,对保护范围没有进行修改。截至2010年1月18日,农业部先后发布了8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现在纳入保护范围的共有80个属种,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当前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农业,不利于我国对育种人权利的保护,不利于我国新品种的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更不利于我国农业特别是育种技术的发展。
此外,UPOV 1991年文本还增加了对派生品种的保护,规定派生品种的商业性应用需经过原始授权品种权人的许可。所谓派生品种是指在原始品种基础上嵌入一个或两个基因使其在表达上产生新的区别于原始品种的特异性而形成的新品种,派生品种同样需要满足授权条件。与原始授权品种相比,派生品种的培育技术是建立在原始品种权人的培育技术之上的,要便捷和容易许多。增加对派生品种的保护,能够协调育种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他们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利用遗传工程进行育种的技术尚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原始品种容易被发达国家稍加修改而形成许多新的派生品种,因此,为了有效防止我国农业植物品种资源的流失,通过立法增加对派生品种的保护就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三)保护期限短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期限的长短,直接关系到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的强弱,同时还关系到品种权权利人的合法垄断与农业发展、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依据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期限为自授权之日起,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为20年,其他植物为15年。建议适当延长保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延长为25年,其他植物延长为20年。这一修改不仅适应了UPOV 1991年文本的修订,即将木本植物的保护期限延长为25年,一般植物的保护期限延长为20年,也体现了对植物育种者创造的进一步鼓励,也反映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与国际发明专利制度的保护期限的协调[3]。
(四)投入与转化不足
从我国目前育种科研经费的投入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经费由国家承担,作为市场主体的农业企业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从经费流向来看,大部分农业科研经费也都投向了国有科研院所和教学单位,真正投入到农业企业的科研经费非常少。这种科研体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容易导致科研成果与科研成果转化的脱钩,这也是我国农业科研创新效率不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的原因所在。为此,需要从激励农业科技创新的角度,进一步推动农业科研体系的创新,鼓励农业企业加大投资育种科研经费的投入,鼓励农业企业与国有科研院所和教学单位联合创新,从而丰富农业科研创新资源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二、趋势与反思:UPOV1991年文本及其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影响
(一)UPOV1991年文本与UPOV1978年文本的对比分析
在一些欧洲国家长期的推动下,1961年,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在巴黎签署了UPOVC,标志着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制度的形成。UPOVC现有三个文本,即1961年文本(1972年修订)、1978年文本和1991年文本。相较UPOV1978年文本而言,UPOV1991文本给育种者带来了更强大的法律保护,UPOV1991文本生效后,UPOV1978文本成为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员国现行法律的最低标准[4]。见表1。

表1 UPOV 1991文本与UPOV 1978文本的比较分析
表1重点对UPOV 1991年文本与UPOV 1978年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显然,UPOV 1991年文本比1978年文本更严格地保护了育种者的权利。如1978年的文本允许农民保留种子再次播种,自繁自种和自由交换(虽没有明确写明),1991年的文本却严格地限制农民这种特权,育种者的权利延伸至收获的材料。UPOV公约的1991年文本还将育种者的权利扩大到禁止侵权品种进口。在强调保护育种者权利的同时,UPOVC对育种者的权利也有所限制,如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或者为了推广新品种,可以不经过育种者同意而使用、繁殖其新品种。1991年文本对育种者权利的限制则更为具体,规定育种者的权利不适用于:私人的非商业活动;试验性活动;培育其他新品种活动。但培育派生品种以及需要反复利用受保护品种进行繁育品种的除外。
(二)UPOV 1991年文本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在此情况下,更应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与UPOV1991文本规定的耦合程度,特别是深入分析我国育种能力与育种免责问题、农业发展与农民免责问题,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制度抉择,而非忽略客观实际,一味跟风式地加入。
第一,育种免责与育种能力问题。所谓育种免责,简言之就是指任何人都可以把别人所拥有品种权的品种拿去进一步改良,从而培育成另一个新品种[5]。然而,植物育种的基础工作就是拿既有的品种来改良,UPOV 1991年文本作了更为严格的育种者豁免限制,顺应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育种能力强的发达国家的需求。而纵观我国育种能力,我国的种子企业整体在近几年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表现为“散、乱、小”的整体格局,各企业研发能力也尚在提升中,并未做好推行此类强保护模式的准备。
第二,农民免责与农业发展问题。“农民免责”也称“农民特权”,是指农民利用受保护品种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种植为目的生产种子的行为不受品种权的约束[6]。具体而言,是指农民在合法获得授权品种进行种植后,在其收获的作物中,留出供下一个种植季节所需的种子,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还可交换、销售所留的种子,植物品种权人均无权干涉,也无权要求支付费用。我国人口众多,农业是国家兴旺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石,因此涉及“三农”问题的制度必须经过慎重考虑和实际调研。目前,我国对于农民特权的规定与UPOV 1978年文本的原则性规定一致,而UPOV 1991年文本将农民特权列为非强制性例外,我国对是否加入1991年文本的分歧之一就在于农民特权的规定上。UPOV 1978年和1991年文本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于构建规则保护育种者的权利而非农民的权利[7]。由于UPOV 1991年文本体现的是发达国家对于育种者的强保护,这种强保护反映在对品种权限制的削弱上,也就要求削弱甚至除去农民特权这一规定。与发达国家大规模、标准化的农场经营不同,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由小农经济发展而来的小规模、家庭式耕种模式仍占主流,发达国家在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的同时正是在削弱农民特权,因此,鉴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农业种植的实际情况,过早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显然并不合适[8]。
三、应对与策略:我国加入 UPOV 1991年文本前的必要准备
2012年底及2013年初,关于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多项政策文件及规章制度出台,例如,2012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2013年1月,科技部、农业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2013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开始施行。多项政策文件及法律法规的出台,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推向了新高潮,彰显了我国正在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得力的措施,应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
前文对比看出UPOV1991年文本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保护领域、保护期限及保护手段等多方面比1978年文本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以新品种保护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发展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新品种保护制度是经济与科技强国为主导制定的制度,它既是发达国家强力推行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得不适应的游戏规则。UPOVC是由工业为经济支柱而非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推行的,与我们不同,在这些国家,农业经济由富裕、拥有大生产规模的2%至7%的人口承担,而我们由大量的零散而处于底层的农民承担[9]。
发达国家主导的UPOV1991年文本显然对新品种权拥有量多的国家有利,对新品种保护制度刚建立不久及品种权拥有量少,特别是种子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差的国家明显不利。立足UPOV 1991年文本的要求,结合新颁布的多项政策文件及法律法规,我们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做好加入UPOV 1991年文本的必要准备。
第一,全面提升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意识、研发水平和保护能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制度实施却起步较晚,科研人员、企业、农民等对植物新品种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仍然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宣传、教育、动员,全面地提高品种权人的维权意识,激励和引导科技人员创造更多的智力劳动成果,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是当前保护植物新品种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入UPOV 1991年文本,跻身国际竞争潮流的基础准备。
我国在强化品种权保护意识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增强育种领域的研发技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种子企业、研究机构的竞争实力都无法与国际大种子公司相抗衡,因此,增强育种领域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能力,增强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已成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实践中,种子企业应充分发挥在商业化育种、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整合农作物种业资源,争取“产学研”合作、赢得政府支持和社会资金投入,推进种子企业做大做强。
政府应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农作物种业发展环境,重点支持育种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经营规模较大的种子企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吸引社会资本和优秀人才流入企业。政府相关部门还应积极采取必要措施,提升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能力,例如,针对新品种权申请与授权效率低,影响植物新品种市场价值的问题,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及DUS测试机构(DUS测试是指对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的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所进行的测试)应进一步强化服务本位,积极、主动、及时地与育种者进行沟通,除了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所必需的时间周期外,应尽量简化程序,提高申请和授权效率。此外,政府还应大力推进农作物植物新品种权交易服务,建立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交易平台,加速授权品种供需对接和转化应用,实现植物新品种的经济效益[10]。
第二,平衡法益,完善制度。在我国内部制度构建之中,应当加大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研究,从立法技术、执法水平的提高上来确保我国适应1991年文本的要求,不断地总结经验,积极策略地运用UPOVC的原则和规定[11]。
育种者与农民、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与基础农业的发展是同一天平的两端,在侧重对一方利益的保护时,必定增加对另一方利益的限制,这也正是立法选择时的一对矛盾。一方面,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较弱可能会降低本国育种者的研发热情,影响对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的吸收和接轨;另一方面,我国育种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对较弱,不适时的植物新品种强保护模式也可能导致植物新品种权被外国寡头所控制,增加我国农民的负担,影响我国农业的正常发展。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应当遵循“法益优先保护”的原则,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应当首先考虑对农民权益的充分保护,这也是我国在加入UPOV1991年文本前应考虑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当前的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选择应立足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同时也应当与国际接轨,做好加入UPOV1991年文本的准备。
第三,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争取立法修法话语权。置身于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在加入UOPV1991年文本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以赢得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规则制定和修订过程中的话语权。一方面,应当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上先进的政策法规,加大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修订以及发展趋势的研究预测;另一方面还应密切关注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规则的变革,充分利用WTO等谈判平台和组织机构,主张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以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国际平衡。
[1]段立红.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M]∥知识产权审判指导与参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08.
[2]吴向东,龙 凤,丁 怡.TRIPS和植物新品种保护[J].当代法学,2003(7):128-131.
[3]王志本.从UPOV1991文本与1987文本比较看国际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发展趋向[J].中国种业,2003(2):1-4.
[4]Noel Byrne,Plant Breeding and the UPOV[J].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1993(2):136-140.
[5]程 勇.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植物专利保护制度思考[J].世界农业,2012(8):36-40.
[6]李 剑.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限制[J].电子知识产权,2008(6):41-44.
[7]Helfer L 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Plant Varieties:An Overview with Options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Z].Rome: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2002.
[8]黄丽娜.论植物新品种权限制中的农民特权[J].中国种业,2011(9):16-18.
[9]Suman Sahai.Protecting Plant Varieties:UPOV Should Not Be Our Model[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96,31:2788-2789.
[10]祝宏辉,郭 川.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状况及问题分析[J].中国种业,2012(7):1-4.
[11]王志本.积极策略地运用UPOV公约的原则和规定[J].中国种业,2003(3):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