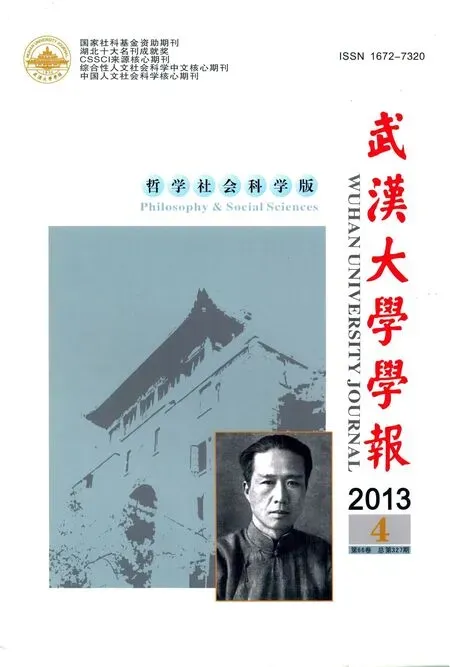世界宗教文化建构的妇女形象
罗 萍
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何光沪,1991:1)。在过去的世纪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宗教活动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宗教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过:“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何光沪,1991:1)”。那么,人是怎样建立这个神圣世界的,在这个神圣世界里,宗教是如何规范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如何塑造女人形象?西蒙·波伏娃(1986:23、518)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不是自然的产物,……是文明塑造出来的”。女人是被文化塑造出来的,什么文化?男权文化。宗教文化是最典型的最本质的男权文化。本文从总体上分析世界宗教文化建构的妇女形象,以及女性形象发展史。这就是由肯定的正面形象向否定的负面形象转化;我们期盼着否定之否定,即女性正面形象的更高层次上的转化与回归。
一、肯定的妇女形象
(一)头顶王冠
许多文化起源之初,妇女是人性的平等所有者,神性兼有男女两性的特征。在文化上,妇女哺育和照看子女,使她们在许多部落中都成为医药和诗歌民谣的保存者。从宗教上说,这些活动都是神圣的,因为它们全都与生命的秘密和力量相关连。在当时文化下,成为一个女人就是成为一个人的极好方式。古代神学一般兼有男女两性的特征。在世界宗教的起源阶段,神性的神秘总是一种“女性—男性”的整体。因此,曾有过一个“上帝是一个女人,女人头顶着王冠”的时代,那就是人类的母权制时代,可见,那时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两性平等的人性在各种文化中都有表现:佛陀(佛教)和耶稣(基督教)两人都与妇女关系密切;穆罕默德(伊斯兰教)通过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改革了他那时的文化;希纳莱人的《圣经》教导说,人生来即有男性和女性;日本的原夫妇双方,对于日本民族的开始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吠陀》的证据显示出,古代印度妇女从事研究和担任献祭;古代中国把阴阳作为宇宙的二个同等因素,让一对为王的夫妇作为宇宙的统治者。
在早期的母权制社会中,古代宗教并没有性别歧视的色彩,神是男女兼体的,甚至主要是女性或母性的。在那个时代,妇女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与男人平等的形象,两性平等仅此而已。这是人类一段美好的时代,真正男女携手的时代。不过,它如人类的婴儿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妇女在宗教发展史上曾经是头顶王冠的权威形象。
(二)富有创造性
古代人都尊崇妇女的一切母性,女性神受到崇拜,特别是单一的、半统一的大女神宗教。“生殖”完全是女性的创造,妇女享有神圣的生殖力,即某种伟大的宇宙母性。不少国家都有创世的女神,她们创造了字母、语言和书写系统。其他文化也有将农业及医药追索至某些善良女神的传统。古代妇女对其部落的语言、耕作、医疗活动曾作过巨大贡献,同时妇女是神的主要传达人。
那时,女性的出生常常是喜庆的事。妇女在宗教仪式中受到尊崇,妇女可以是史官、医生或顾问。部落的历史将许多文化贡献归功于女性的发现。由此,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妇女可以参加社会的决策活动。大女神文化是和平的而不是好斗的,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女神文化并不像后来的父系文化那样要证明每一个孩子的父亲身分,它不会将某些孩子斥为是不合法的。大女神文化是一种性别平等的文化。
当时的女性角色和女性形象是以其母性生殖力为中心。非洲的俾格米人以喜悦的心态看待月经初潮,它是个人和部落的喜庆日子。经血是一种礼物,是感恩的场合,是召唤人们占领生命。因此,姑娘们都盼望月经来潮。美洲土著人中,月经期的妇女被认为是特别强大的,因为这时她的神圣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妇女在婚娶事务上拥有发言权。各地有一种妇女社团:珊德,它在婚娶中成为新郎新娘双方的男女亲族进行磋商的机构。珊德分会允许妇女自己作出决定,居住地由自己选择。那时,妇女是受人尊敬的,富有创造性的(卡莫迪,1991:175)。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美好时代,但它后来被父权制社会代替了。
二、否定的妇女形象
(一)否定性评价
当父权的先知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中东的女神习俗相遇便发生了冲突,前者获胜,其经典和文化便成为“正统”,而注重女性生殖力的宗教便成了肮脏的邪教,由此导致妇女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及其性活动的被限制。社会开始了对月经期妇女的禁忌,男人回避月经期的女人。
对月经危险、污秽的否定性评价是后起的、歪曲了的解释。这种文化说月经期妇女会释放出某种危险的“女性力量”,由此对月经期妇女禁忌,并延伸到对一般妇女的禁忌,妇女不能与武士相遇。因为女性生殖力的本质与猎人杀生力量是相反的一极,若丧失平衡会引起瘟疫、火灾、洪水、作物歉收或狩猎落空,因此要用禁忌将这种力量守护起来。
这些人为的禁忌使妇女不能参加社会事务和宗教生活,将妇女封闭起来,使其失去了社会舞台。更重要的是,父权文化使妇女成为一种危险的、可憎的力量,必须禁忌它。一个活力旺盛的性别,一群鲜活的女人、母亲就这样被父权文化窒息了,并被放进父权社会从属于男人的一列,从此女人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奴隶般生活的时代。由此可见,对“月经”的推崇与禁忌使妇女生活在两重天。
(二)从属的妇女形象(卡莫迪,1991:177)
在后来的父权制社会文化传统中,女人落到了低男人一等的从属地位,男女权利不平等情况便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中。在东西方文化中,一个妇女通常得依附于某个男人,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地位和名分。几乎在任何文化中,结婚和离婚这种人生大事,都无须妇女本人知道或同意。
东方和西方各宗教传统事实上都同意:妇女绝不是独立的,而始终都是隶属者。例如,印度教不给女人系表示新生象征的圣线;佛教的尼姑要侍候最年轻的和尚;基督教教导主妇在教会内缄默,要顺从其丈夫,丈夫是她的头;伊斯兰教妇女隔幔的深闺制度要求穆斯林妇女用帷幔把自己遮盖起来,只有其丈夫才可以看见她,而妇女获救的标准,不是服从真主安拉,而是其丈夫。这无意于说,每个女人都要服从相应的某个男人;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或几个女人服从他。
贬低妇女的宗教地位就是为了使妇女心悦诚服地从属于男人。宗教文化沿着“月经”禁忌进而限制妇女参与宗教活动,有效地将女人排斥在宗教之外;同时,妇女的宗教地位又是其现实生活的反映,由对妇女“月经”的禁忌到宗教地位的贬低,直通妇女从属男人之路。
(三)堕落的妇女形象(卡莫迪,1991:177)
男人认为女人与他们的差别要比与其的共性更重要,宗教也相信了这种性别差异的说法。女基督徒被要求在教会中默不作声,女犹太教徒不被邀请去诵读《托拉》,女穆斯林在清真寺中不受欢迎,女印度教徒只有重新投胎成为男人之时才能得到解脱,女佛教徒不能成佛,中国妇女之于男人如同平民百姓之于帝王。整个世界妇女都只受到极少的正规教育,女人被当成男人宗教进步的工具,被认为是比较软弱的一类,都被更多地与自然而不是与文化相联系。大多数重要的宗教都把女性和现实中黑暗的、虚假的、非理性的、不洁净的一面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圣人贤哲全都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淫荡,以此为阴蒂切割、缠足和深闺制寻找合理根据。
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宗教将女人同男人一样平等看待。在宗教文化中,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女人则只是两个极端:女人要么被拨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她一直未能平等地分有同样的人性。
关于妇女的宗教象征也偏重于恶的一端。在古代传说中伽厉就是印度教中那佩戴着骷髅项链的嗜血和毁灭的女性;佛教中也有魔罗(撒旦)的女儿们企图引诱觉醒者佛陀,使其不能实现和宣讲神圣的中道的故事;伊斯兰教让妇女住在火狱中,因为她们天生就是忘恩负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给信徒散布以小孩为食的利勒特(女魔)和使人类遭受灾祸的夏娃的故事。
为了保证妇女的愚昧,东西方在规定妇女教育这一点上,都竭力阻止妇女的智力成长,规定妇女只应研习做妻子的技巧,对妇女行愚民政策,这是保证妇女安于卑下地位的最好办法。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这样。
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1996,30、78)中指出:“教穷人读书写字就是你让他们脱离上天所给他们安排的地位”。“有权势的人无论何时都在寻求盲目服从,所以暴君和肉欲主义者竭力把妇女保持在无知的状态中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
纳粹德国提出“母驴理论”,不仅将大部分妇女赶回家,而且将妇女赶出专门职业,令其进入低收入的行业,其收入全部交给男人。妇女被分配的角色严格地限于全力以赴当好母亲,服务家庭,母亲应能全心全意地为她的孩子和家庭服务,妻子应能全心全意为丈夫服务。妇女为国家、为男性的伟大事业充当附庸的职务。纳粹德国认为女人的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家人、孩子和她的家庭,外部世界与她隔缘。妇女企图跻入男人的世界是不合适的,男人支撑国家事务,女人支撑家庭,女人和男人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种类。纳粹的政策就是要将妇女排除在公共生活和公职以外。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及所有宣言和文告中,都贯穿“母驴理论”,即“女性教育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令其成为未来的母亲”(米利特,1999:252)。妇女卓越的、最崇高的事业永远是妻子和母亲的事业。宗教把妇女说成是堕落的,因而阴蒂切割、缠足和深闺制是合理地选择。将妇女排斥在社会领域之外、局限在家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综上所述,世界宗教文化建构的妇女形象从头顶王冠,富有创造性,到否定的、从属的、堕落的形象。妇女形象变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三、宗教妇女观的否定之否定
在世界宗教文化纵向发展历程中,妇女最先呈现出的是头顶王冠,富有创造性的肯定性形象;其后变为否定性,呈现出从属的、堕落的形象。从宗教文化发展史上妇女形象变迁可以看出宗教发展与女性发展的关系。
(一)宗教歧视妇女的起源
早期宗教原本不歧视妇女。宗教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在远古时代,相对于男人狩猎经济收入的不稳定性,从事采集收入的稳定性,使女人在生产生活中居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女人生育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代起着重要作用,女人凭借自己的力量与对部族的贡献,在部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创造了那时宗教文化中的两性平等,那时的社会是两性和谐相处的社会。
当私有制产生后,宗教便与男权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创造了男人至上的父权文化,男人本位的文化。就在这时,文化上出现了两性不平等,女人成了次等的第二性的人。为了使这种不平等永远延续下去,男性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了崇拜男神(人)的宗教,宗教中的男神崇拜反映着并直接转化为现实社会生活中两个性别的不平等关系。性别利益不仅加深着这种不平等,同时又使历史的长河延续这种不平等。
男人中心论需要创造歧视女人的宗教。歧视女性是随着父权制产生发展的以男性为中心为本位的父权文化的本质。头顶王冠、富有创造性的女性形象妨碍男性中心男性本位的确立,以男人为中心,女人就必须是从属的,要让女人从属首先要将女人变成堕落的。女人从属形象与堕落形象并非与身俱来,是父权文化人为塑造的结果。从男神崇拜到男性崇拜,到男性中心,男性本位,到父权文化,这一切都从宗教制造的男神崇拜开始。为了巩固男权文化,就需要贬低女人,贬低女人就要制造出一些“理由”。宗教文化便开始了对生育过程中“经血”的否定评价。早期宗教将月经视为喜庆,视为礼物,视为生命。男神宗教时期则将月经视为危险,视为污秽,必须禁忌。经血是女人为人类生产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与产物,具有性别性。宗教视它为危险、污秽,而加以禁忌,从而贬低女性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贬低女性旨在抬高男性。“经血”是女人独有的,“血”是两性都有的,只贬低“经血”,并不贬低“血”,就是为了只贬低女人,贬低“血”并不是因为“血”本身危险、污秽,而是因为是女人独有的“血”——“经血”。男人的血是圣洁的、英雄的、伟大的;交战中战士的血就意味着英雄的创举。所以,制造“经血”危险、污秽、禁忌理论并不在血本身,而只是女人的“血”,旨在贬低女人。
有了“经血”危险、污秽、禁忌的理论,因此,祠嗣活动禁忌女人,宗教活动禁忌女人,政治活动禁忌女人,男人不能进产房,生育女人住侧屋,男人不入,就是丈夫也在门外而不入。就由于女人生育中的“经血”是卑污的、下贱的,女人被打入另册。每一个女人都会有“经血”期,所以每一个女人都是卑污的、下贱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深闺制、面纱、足、男女各自职分等都是将有“经血”的女人与外界隔绝,将女人局囿于家庭。由于“经血”卑污、危险,所以阴蒂切割、寡妇禁嫁与殉葬就是情理中的事,或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论对女人如何伤害就都没有障碍了。由此,由男神崇拜,到“经血”贬低妇女,密织着父权文化大网,男人不断塑造着女人。女人卑贱地位不是天生成的,而是被男人塑造的。(波伏娃,1986:23)只要父权文化仍然是社会主流文化,女人就是从属的与堕落的,妇女卑污、危险、下贱、禁忌形象就不可能改变。
(二)宗教传播根源
性别利益是歧视妇女的宗教文化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阴蒂切割、缠足、束胸和深闺制等“习俗”都是从男人利益出发残害女人的文化规范。男人想独霸世界,他们就创立了深闺制、缠足、蒙面纱,提出男女各自职分理论(米利特,1999:117),规定妇女为妻子和母亲角色,将妇女局囿于家庭私领域,使妇女与外部世界隔绝。男人想按自身意愿纵情淫欲,他们就规定男人可以多妻,但又阻止寡妇再婚。他们还残忍地对女人施阴蒂切割术,旨在扼杀女人对性的要求,从而对女人实行性的统治,做性霸主。
男人为了能有效统治女人,中国的孔圣人提出“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四书五经,1993:32)。男人按自身需要创造的宗教不让女人染指,捏造女人不洁净。特别是月经期的妇女,生育中的妇女,以此限制妇女参加宗教活动,使女人长期愚昧地相信男人排斥女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理由与禁忌,并将男人的宗教视为神灵的启示。印度教创造的“业轮回解脱”和种姓制度,成为压迫妇女的强大理论根据。
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宗教将女人同男人一样平等看待,性别利益仍然高于和压制公平公正和平等,说明父权文化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的任务就是筛选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救出婴儿,泼掉脏水,取出麦粒,扬弃麸皮。清理宗教文化中歧视妇女的糟粕和泼向妇女的污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趋势,是妇女解放的迫切任务,是维护妇女人权的基本要求,是开发妇女人力资源的时代呼唤。
(三)两性和谐宗教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两性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其文化是决定宗教形象的最终根源。远古时代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由此形成了两性平等文化,并决定了两性和谐宗教。进入农耕时代封建社会后,女性被赶回家庭从事辅助性生活事务劳动,掌握话语权的父权文化又将家务劳动视为无社会价值,使妇女经济地位下降,直接导致其社会地位的下移,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女性被排除在宗教生活之外,而那时的宗教生活被看成是生活的精华,生活的顶端,是最高等的生活,妇女就这样被逐出这生活的顶端。反过来说,宗教生活就成了显示人们社会地位和握有特权的象征。
从反映两性和谐相处的宗教进入到男性宗教的“否定”之后,再要回复到两性和谐的宗教,即“否定之否定”,必要前提是两性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平等。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是经济社会的客观的直接的反映。
由此可见,两性平等宗教的到来必须是现实生活中两性平等的完全实现。而我们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男女平等实现还有许多障碍,因而今天任何形式的宗教都只能是父权宗教,即压抑女性保护父系利益的宗教,各宗教崇拜的神无一例外都是男神。要实现两性在宗教生活中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妇女自身的觉醒
要实现两性在宗教生活中的“否定之否定”的确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压迫制度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上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剥削制度的颠覆尚且如此艰难,那么若要结束宗教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那意味着改变半数人压迫半数人的生活方式,要比起颠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剥削制度困难更大,任务更重,过程更长。改变剥削制度需要受压迫者的觉醒,需要受压迫者对这种制度的真切了解与认识,只有认识了剥削制度的本质才会有动力与其斗争并争取胜利。因此,受压迫的妇女需要接受教育,迫切需要提高认识;在宗教盛行的社会中,妇女需要打破宗教对女人的禁忌,不能失去宗教这个社会舞台,以便认识宗教的本质。然而,宗教制度剥夺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堵决了妇女涉入宗教的可能。
剥削者压迫者不情愿让受压迫者接受教育,懂得道理,因为压迫者就害怕被压迫者懂得道理后认识到自己受压迫的处境与找到出路,所以,压迫者要保持被压迫者的愚昧。同理,宗教性别压迫需要保持妇女的愚昧。要使人心甘情愿受奴役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其愚昧无知状态。所以,压迫阶级总是希望被压迫阶级愚昧,宗教文化必然希望女性愚昧。一旦被压迫阶级、被压迫的女子有了知识,提高了觉悟,他(她)们就会起来反抗。所以,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行愚民政策,男性对女性行愚民政策,剥夺他(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让他(她)心甘情愿地处于受压迫地位。李达先生在《平等女学》中尖锐地揭露了这种愚民政策的实质,他指出“有钱有势的人不愿意无钱无势的人有智识;男子不愿意女子有智识,因为无钱无势的人若有了智识就觉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而发生反抗运动,要脱离有钱有势的人的掠夺和压迫。女子若有了智识就觉悟到自身所受的苦痛,生出反抗行为,不甘做男子的奴隶和牛马。所以,有钱有势的对于无钱无势的行愚民政策,男子对于女子行愚民政策”(李达,1980:28)。没有文化的妇女,很难认清宗教的本质。
在宗教文化盛行的时代,宗教生活被看成是生活的精华,生活的顶端,是最高等的生活,参与宗教活动还同时是显示人们社会地位和握有特权的一种标志。为了把妇女排除在宗教生活之外,宗教文化对妇女有很多限制,特别是“月经”的限制,宗教文化沿着“月经”禁忌进而限制妇女参与宗教活动,有效地将女人排斥在宗教生活之外。对“经血”的厌恶与禁忌,使女人远离宗教生活。宗教由对经期妇女的禁忌,延伸到对一般妇女的禁忌,妇女不能与武士相遇,妇女简直就是倒霉、不幸、灾难的代名词,当然就不能参加神圣的宗教活动了。这些人为的禁忌使妇女不能参加社会事务和宗教事务,将妇女封闭起来,使其失去了宗教时代的社会舞台。即使让女人参加某些宗教活动,也有严格要求,女基督徒在教会中要保持默不作声,女犹太教徒不能诵读《托拉》,清贞寺不欢迎女穆斯林,只有重新投胎成为男人之时女印度教徒才能得到解脱,女佛教徒不可能成佛,中国妇女要遵循“夫为妻纲”。妇女就这样被拒绝被限制参加宗教活动。男人按自身性别需要创造的宗教不让女人染指,统治压迫女人。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保证了宗教的男权文化本质。为了保证妇女不参加宗教活动,也不要求参加宗教活动,就必须保持妇女的愚昧,竭力阻止妇女的智力生长,不让妇女参加宗教活动也是保证妇女于愚昧状态的最好途径,因为她们对宗教没有任何知识,就只能听任宗教对女人的任何裁判。
宗教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颠倒事实的文化,是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种族、性别服务的文化与制度。宗教将生活中的男权文化点点滴滴密织成神圣的经典。宗教文化排斥妇女,制造两性不平等关系。凡有宗教的地方,妇女就生活在男权制的深渊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宗教都具有父权性质,所以,凡是宗教文化统治的地方,就有男女不平等,就有性别统治,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提倡性别平等的。在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中,女人是最大的受压迫者。出路是什么呢?如果人类社会还需要宗教文化的话,那么就是彻底改变宗教的男权性质,创立新宗教,即创立一种建立两性和谐的宗教文化,那就是我们要建设的公平公正和谐社会。
[1]D·L·卡莫迪.1991.妇女与世界宗教.徐钧尧、宋立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西蒙·波伏娃.1986.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996.女权辩护.王蓁,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凯特·米利特.1999.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5]吴根友点注.1993.四书五经.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
[6]李达.1980.李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