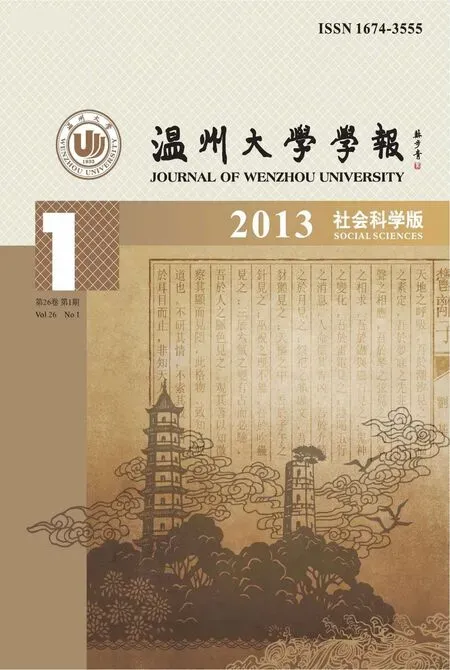汉语并列四字格的文化意义研究
李少虹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文法系,河北邯郸 056001)
四字格是现代汉语中客观存在的一种重要表达手段,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现象。在四字格的各种形式中,并列四字格是数量比较多的一类。吕叔湘先生就曾指出汉语四音词语2+2并列式占优势,而这恰恰是汉语的特点所在[1]。很多语言中都有并列句法结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并列四字格。
并列四字格的独特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并列四字格结构的认识最早可能始于陆志韦先生。1956年,陆先生在《语言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汉语的并立四字格》,陆先生当时用的是“并立”而非“并列”。他认为,四个字(音节)在语法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四字格,其中两两并立的叫做“并立四字格”,而并列四字格的来源可以上溯至《诗经》、《屈赋》、《易经》、《论语》等古文献作品[2]。在陆先生随后的著作《汉语的构词法》中,转而使用了“并列格”这一名称,并专辟一章论述[3]。
吕叔湘先生先从音节结构的角度列举了七种类型的四字格,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并列四字格。他认为四字格结构的形成和音节有密切关系[1]。在以后的研究中,吕叔湘先生给这类词语定性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短语,它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一,分前后两段,两段的结构相同;二,前后两段的意思或者平行或者对称;三,一般不能单用的语素在四字格里当单词用[4]。尤其是第二点是并列四字格的典型特征。
蒋文钦、陈爱文则从调序和音节奇偶角度考察了并列结构词语的内部次序[5]。他们的考察不限于四字格,也有三字或五字以上的,但以四字格为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语音(声调次序和音节奇偶)对并列结构的内部次序是起作用的,但是不排除意义决定次序这种情况。时秀娟分析了并列四字格结构的构词理据,指出并列四字格的构成是由于构词的规律、音节的需要,认知的便捷和文化的传承等因素决定的[6]。
从前人和时贤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给并列四字格定性,或者侧重于并列四字格的内部次序和构词理据,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研究并列四字格的尚属少见。
汉语的并列四字格中包含了广泛的汉族社会文化涵义,反映出汉民族的认知特点、对事物的概括和归类方式等,是民族心理在语言上的映射,是反映汉语文化因素最主要的语言形式。
为研究方便,我们从形式上把并列四字格分成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ABCD型,即四个语素都不相同的。在这一类型下再细分为(1)AB+CD型,如:称兄道弟、镜花水月、苛捐杂税、移山倒海等;(2)A+B+C+D型,如: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经史子集、生老病死等;(3)ACBD型即第一和第三个语素能组合成词,第二和第四个语素也能组合成词,如:精打细算、奇形怪状、甜言蜜语等。第二种是ABAC型,即第一和第三个语素是相同的。如:碍手碍脚、大红大绿、古色古香等;第三种是ABCB型,第二和第四个语素是相同的,如:好说歹说、千难万难、有意无意等;第四种是AABB型,如:吃吃喝喝、风风火火、婆婆妈妈等;第五种是固定格式词(也有人称这种为带嵌格式)。第五种其实和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有些是重合的,比如“七…八…(七手八脚、七拼八凑)”同时也是ABCD型;“半…半…、没…没…”也是ABAC型;“大…特…”也是ABCB型,只不过由于经常使用,凝缩成一个固定格式,我们可以把相应的语素放进去。如“千…万…”式就可以类推出:千山万水、千军万马、千秋万岁、千头万绪、千丝万缕、千言万语等词语。
下文将从几方面论述并列四字格的文化意义。
一、不同语言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不同
洪堡特曾说过“词不是客观事物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的反映。任何客观的知觉都不可避免地混杂有主观成分……而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部分人类的整个概念和想象方式的体系”[7]72-73。确实,每一种语言表述客观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正如利奇所说:“人们用语言来划分事物类别的方式,有时显然是以人为中心的。”[8]后来的新洪堡特学派根据洪堡特的论断明确提出了“语言中间世界”理论,创造性地论述了语言是一种精神塑造的力量,认为语言是处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人与外界之间的一个特殊世界,一个中间环节,是客观实际和人的内部世界之间的一种媒介。人类是透过语言的意义构造眺望外在世界的。“在语言中反映的与其说是客观现实,不如说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态度,即一种语言世界图。”[9]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可以认为词义或概念并不表示外界的客观世界,而代表人类认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心理状况。因此,它们不是人类肌体之外的物质的性质和关系的符号,而是人类感知和认识外界现象的内部机制的符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外部世界对一切语言来说,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共有的宝库,而各个民族又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中间世界”去感知客观世界,各取所需,对事物现象进行各不相同的归类。由于客观实际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大体上是接近的,不同社会的基本文化需要也是相似的,因此,人类对外界事物的归类也是大体相当的,例如,在各种不同的语言里,猫与老鼠、猪与狗、人与猴、风与雨等归类从来是不会混淆的[10]。但对有些事实,不同语言的归类方法就有可能是不同的。基于各自的主客观文化背景,不同语言集体对关注对象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粤语中不区分“雪和冰”,“雪”和“冰”都混叫“雪”,蒙古人把稻子、大米都称为TʊTʊrg-a,因此,“观察、归类角度不同,赋予词在分类系统中的价值也就不同”[11]。
二、从汉语并列四字格透视汉族人的分类观
(一)分类的主观性
汉语的并列四字格实际上是一个对现实世界分类和归类的过程,体现了汉族人的一种分类观。这种归类有很强的主观性,文化起着决定作用。洪堡特举过一个美洲土著语言的例子,美洲土著居民把星辰、动物归为一个语法类别,这就意味着,他们显然是把星辰看作自行运动的、具有个性的物体,认为他们可能在天上操纵着尘世的命运。汉语说“飞禽走兽、珍禽异兽”,这说明在畜牧狩猎经济影响下,汉族人把禽、兽归并在一起。禽、兽均处于人类的养殖环境中,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地位接近,都是人类生活的依靠,所以人类倾向于把兽、禽归并在一起。“枪林弹雨”一词中,我们把“枪”和“弹”归在一类,在“明枪暗箭”一词中,又把“枪”和“箭”归在一类。在“枪林弹雨”中把“枪弹”归类,是因为它们同属于武器和武器发射出来的东西。在“明枪暗箭”中“枪、箭”都同属于武器。
(二)归类的相似性
在进行分类和归类的时候,人们总是趋向于选择相近或相类的事物。比如:“伶牙俐齿”中“牙”、“齿”是相近的事物。“唇枪舌剑”中“唇”、“舌”也是相近的事物。“狼心狗肺”中“心”和“肺”的归类。“牵肠挂肚”中“肠”、“肚”的归类。“有血有肉”中“血”和“肉”的归类等。很少有不同事物归在一起的例子。除了“脑满肠肥”,在人们的意识中,很少把“脑”和“肠”归在一类。
再以数字词为例:相当一部分并列四字格是由数字组成的,构成形式要么是第一和第三个语素为数字,要么第二和第四个语素为数字。当然在这类数字式并列四字格中,数字的意义往往虚化,反映出汉民族独特的数字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比如汉语“三”与“两”组成的词语多表示少数。如三三两两、三言两语。“三”与“五”组成的词语则表示多数:三令五申、三番五次、三年五载、三茶六饭、三姑六婆。“三”与“四”组成的词语则多含贬义,如:不三不四、低三下四、朝三暮四、颠三倒四、丢三落四、说三道四。“七”和“八”组合,多表示杂乱如:七零八落、七上八下、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七拼八凑。关于这点,学界论述得很多,兹不赘述。
(三)归类的民族性
不同民族在对事物进行归类的时候,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性。以数字词为例,汉语并列四字格中出现数字的地方,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要么是数字不对应,要么根本就不出现数字。比如汉语的“五湖四海”,在傈僳语中就是“ʃÎ31mu31ku55lo33”[12],字面意思就是“七地九谷”,而英语则是 all corners of the land,根本就不涉及到数字。汉语的“千山万水”,苗语叫“ʨua31toŋ43ʨua31xaŋ55”[13]40字面意思是“九山九谷”。英语是 countless mountains and valleys,同样也是不出现数字。汉语说“三心二意”,英语是be of two minds,be half-hearted。汉语的“四面八方”,英语是all directions,all round。汉语的“四分五裂”,英语是fall apart,split up。汉语的“七上八下”,英语是on tenterhooks,或者是on pins and needles,数字的意义完全消失了。
再比如,汉语说“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在英语中叫neither fish nor fowl,在藏语中叫“ʑa mən lukə mən”[14],意思是山羊不是,绵羊不是。汉语说“伦类”“驴马”这是一类,“伦”的本义就是“辈”、“类”的意思。《说文》说“伦,辈也”。而在英语里,说成neither fish nor fowl,翻译过来是非鱼非鸟,把鱼和鸟认为是两类不同的种类,而在藏语里就成了“山羊不是绵羊不是”,这说明藏族认为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种类的两种动物,可是对汉族人来说,除非特殊场合,否则这两种动物没有区别的必要。上文中我们举过一个例子,汉语中的“明枪暗箭”,但在藏语里却说“明矛暗箭”,把“矛”和“箭”归并在一类。这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归类方式是不同的,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此外,还有自然界现象(天与地、山与水、冰与雪、风与月等)的对举等等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比如在汉语里用“天地”对举格式表示的,如:惊天动地、战天斗地等,在其他民族语言里是用“地人”来表示程度的。比如湘西苗语里表示大声地喊,喊天叫地时说“nhɛ53tɯ35nhɛ53ne31”[13]33,意思是喊地喊人。说吵闹不已时说“nɔ35tɯ35nɔ35ne31”[15],意思是“闹地闹人”,“天昏地暗,天气很阴”说成“te33tɯ35te33ne31”[15]意思是阴地阴人等等。
三、从并列四字格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
思维和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思维离不开语言,思维的发展推动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也推动着思维的发展。思维和语言的这种一致性也正体现出思维和语言具有同构性的特点。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16]王国维的话已经把语言与思维及文化结构的关系都说到了。
(一)思维的民族性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7]21“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7]52-54。这些论述强调了语言是一种民族现象,各民族的语言在结构形式、意义内涵上有所不同,一定的民族语言与一定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相维系,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17]我国学者陈保亚也认为“语言浇铸思维模式,语言构建文化精神”,他还从语音、语法、词汇三个层面来论证“语言差异带来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科学语言给科学思维带来的差异。”[18]并且,他还论证了语言的变化会引起思维模式的变化。
(二)汉族人的二元思维观
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着诸多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世界。比如汉民族喜欢把事物分为阴阳两性。天为阳,地为阴;太阳为阳,月亮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等等,这是汉族人的文化世界。但俄罗斯民族和德意志民族常把事物分为阴性、阳性和中性,而且某一事物属某一性也有差异。比如俄语中的“冬天”是阴性,在德语中却是阳性。
并列四字格的语义场一种是对外部世界客观的反映,如“红男绿女”,现实世界就是“男女”两分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语义场对事物的划分,是从人的认识,交际的便利与习惯来考虑的。汉语也像其他语言一样,为了交际的便利,有时宁可区分得简略些。这样就出现了二值倾向(two-valued orientation),把一些多元的甚至是无限的事物,都用二元语义场反映出来。如“偷鸡摸狗、说东道西”,其实偷窃不仅仅指偷鸡和摸狗,说东道西显然也不仅仅是说东西,而表示尽情谈论各种事物。
并列四字格词语中出现的词的对举用法,比如“手”和“脚”、“头”和“脑”、“眉”和“眼”等等反映了汉族人的逻辑心理。也就是说在汉族人的逻辑-心理结构,即认知模式里,是突出了两极对立,模糊了灰色过渡地带即中间地带(尽管这个地带存在着)[19]。比如汉语中说的“善恶是非”,意思是善恶黑白。而西方人的逻辑心理结构,是容忍了中间地带的,即承认了灰色的过渡地带,所以比较多地选择了三分结构。汉族人的这种二元思维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我们说一个东西介于“长”和“短”之间时,不会再另造一个新词,而说“不长不短”。同理,我们也说“没大没小”、“没轻没重”。
四、结 语
总之,语言表达除了要符合句法和语法要求以外,还要有感情表达的成分在内。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仅仅把语言看成是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纯粹的符号系统①参见: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明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而对于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估量和重视,忽略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这必然不能对语言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外在形式看,语言确实似乎是一种符号或符号系统,但从本质上看,它还有社会性和人文性,各民族的语言在结构形式、意义内涵上有所不同,一定的民族语言与一定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相维系。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掌握使用它的同时,也接受了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意义,在语言的身上,记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历程,浸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成为反映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 中国语文, 1963, (1): 10-22.
[2] 陆志韦. 汉语的并立四字格[J]. 语言研究, 1956, (1): 45-82.
[3] 陆志韦. 汉语的构词法[M]. 修订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105-112.
[4]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2
[5] 蒋文钦, 陈爱文. 关于并列结构固定词语的内部次序[J]. 中国语文, 1982, (4): 289-301.
[6] 时秀娟. 浅析汉语并列式四字格结构及其理据性[J]. 莱阳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13(3): 44-47.
[7]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8] 杰弗里•N•利奇. 语义学[M]. 李瑞华,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37.
[9] 申小龙. 古典洪堡特主义与当代新洪堡特主义[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1): 64-69.
[10] 张公瑾, 丁石庆. 文化语言学教程[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16-117.
[11] 马清华. 文化语义学[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30.
[12] 徐琳, 木玉璋. 傈僳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33.
[13] 王辅世. 苗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4] 胡书津. 藏语并列四字格结构初探[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9, (4): 58-69.
[15] 向日征. 湘西苗语的四字格并列结构[J]. 民族语文, 1983, (3): 26-32.
[16]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C] // 姚淦铭, 王燕. 王国维文集: 第3册.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111-112.
[17] 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M] 李荣, 王菊泉, 周焕常,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39.
[18] 陈保亚. 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J]. 哲学研究, 1996, (2): 28-34.
[19] 钱冠连. 哲学轨道上的语言研究[J].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6, (6): 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