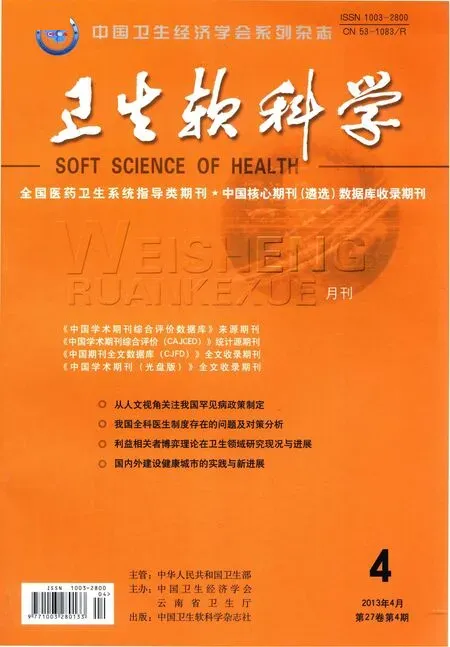疟疾患者求医行为的影响因素概述
李思颖,李晓梅
(昆明医科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1 前言
疟疾发生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是以周期性寒战、高热、大汗等临床症状为表现形式的一种虫媒传染病,反复发作可导致贫血等疾病,重症病人可出现昏迷、谵语等,甚至危及生命。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全球急需治疗、控制和重点防控的3种传染病之一[1]。全球大约40%的人口受到疟疾的威胁,每年有3.5~5亿人感染疟疾,110万人因疟疾死亡。每天有3000人死于疟疾,其中绝大多数为5岁以下的儿童[2~3]。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以及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全球范围内疟疾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4]。然而,在热带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疟疾仍然是威胁人们健康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在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多数疟疾高发区已经基本消除了恶性疟,但近年来由于部分地区防治工作力度有所削弱,经费投入不足,人口流动频繁,周边一些国家输入性疫情对我国边境地区的影响日益严重,使得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回升,个别地区时有局部暴发[5~7]。因此,疟疾防控形势依然很严峻。
在预防和控制疟疾疫情时,通过患者的求医情况进行分析,可以获得疟疾病情的种类、分布乃至疫情程度,从而做出相应的防制对策。尽管求医只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但它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和社会行为,受到多种因素比如个人信仰、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病人对疾病的认知能力、经济以及当地的医疗基础设施等的影响[8~9]。尤其是当患者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地理位置偏远时,患者的求医将变得极其困难。本文以求医行为理论模式为基础,对疟疾患者求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做了详细的论述,为今后的疟疾防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2 理论模式
求医行为模式是1968年由Andersen博士[10]首先提出的,曾广泛应用于居民的求医行为和医疗保健服务,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后来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修改。根据Abraham和Sheeran[11]的分析,个人的求医行为受人的意识形态和内部动机的影响,认为人的意识形态可以影响到人的求医行为,于是将人的信念引入到求医行为当中而提出一种全新的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该模型认为健康促进的目标不是改变行为的过程,而是人们为自己设定需要达到的健康状态,但仅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强调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此外,Andersen也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倾向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s),能力因素(Enabling factors) 和需求因素(Need factors)模式[12]。倾向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结构和健康信念等,而能力因素则是指个人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能力,比如个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等,需求因素是个人感到身体不适或者出现疾病症状时所产生的一种求医需求,它包含自觉健康与疾病状况两个层面的影响。由此可见,这3类因素的关系依次是倾向因素影响能力因素,再影响需求因素,最后影响医疗保健服务的应用。众所周知,疟疾是一种易反复发作的疾病,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高原地带和医疗居住条件差的地方,疟疾发生的频率比较高,而这些地区的居民一旦感染疟疾,受社会因素、经济条件、对疾病的认知能力、地理位置等的影响,患者的求医将变得非常困难,因此,Andersen的这一模型能够很好的适用于疟疾患者的求医行为。
3 求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根据Andersen模型中的3要素,影响疟疾患者的求医行为因素可以包括以下5类:
3.1 人口学因素
疟疾患者在求医治疗中很大程度上受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Andersen模型当中,这属于倾向因素范畴。通过大量的文献报道发现[13,14],在疟疾的感染人群中,尽管是以儿童受感染的人群居多,但在求医的患者中,中年人占据了较大比重,且男性多于女性。由于儿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女性需要更多的时间忙于工作和家务,自我防范意识较弱,因此,求诊的几率较低。在Mohapatra和Das[15]的研究中发现,在主动求医的患者中,18~20岁的患者占9.6%,21~30岁的患者占20.7%,31~40岁的患者占24.9%,41~50岁的患者占17.8%,51~60岁的患者占14.7%,61~70岁的患者仅占8.9%。而Awwal等人[16]在研究孟加拉国就诊的疟疾患者时,发现男性占 78.3%,而女性患者仅为21.7%。同样,Sangeeta等人[17]研究印度国家医院的113例疟疾病患,结果发现男性比例为73%, 女性仅占 27%。大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在疟疾患者的求医行为中,男性高于女性,中年人群要高于其它年龄段人群。
3.2 认知能力因素
在任何文化背景下,对症状及疾病严重性的认识程度都对求医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对疾病的认知受个体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知识、社会化程度和以往经验的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就越强,也越容易理解。在Andersen模型当中,认识能力同样属于倾向因素范畴。在疟疾感染初期,患者没有明显症状或只有轻微的不适,如果认知能力不够,很有可能会忽略自身感染疟疾的状况,求医行为也就不会发生。对疟疾知识的知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求医行为。蒋静等人[18]调查疟疾治疗率时发现对疟疾及疟疾传播途径等知识的知晓率随文化程度的升高而升高。而Lingsay等人[19]研究尼日利亚东南部埃努古市的466名患者的求医行为发现接受中等教育以上的患者占据了 46.1%。Niklaus等人[19]研究和比较了喀麦隆疟疾患者的教育程度,接受中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占了 51%。大量实例说明疟疾患者的求医行为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患者的就诊机会也越大。
3.3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在Andersen模型中属于能力因素。在疟疾的防治过程中,通常有3个部分的费用支出,即疟疾的预防性支出、疟疾治疗时的直接支出和间接支出[20]。对于贫困家庭,一般不会有预防性支出,而一旦感染疾病,他们的求医行为更会受到经济的制约,这也是为什么疟疾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的缘故。发达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较高,能够承受预防性支出,治疗费用也不成问题,因此发病率和死亡率普遍偏低[21]。赵文晓[22]在社区居民就医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13.2%的居民选择去社区卫生服务,而56.1%的居民选择去药店买药,9.2%的居民选择不治疗。其中除了经济因素外,就近原则亦是居民选择医疗服务机构的因素之一。Ahmed等人[23]研究了孟加拉国疟疾患者的求医行为,结果发现当居民感染疟疾之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38.7%的患者不做任何处理,10.8%的患者进行自我治疗,32.3%的患者去药店购买药物治疗,只有 13.0%的患者寻求专业治疗。因此,当家庭经济状况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疟疾患者的就诊的可能性就越大。
3.4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则属于Andersen模型中的需求因素。地理位置和气候在疟疾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作用[24~27]。疟疾发病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的高山或丛林地带,远离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卫生服务薄弱,一旦被感染,很有可能会推迟诊断甚至是放弃治疗。Labhardt等人[28]在喀麦隆进行传统治疗和西医治疗疟疾患者的比较时发现,患者所处的位置距离最近的卫生所、医院和专业治疗机构的距离分别为7.7公里,13公里和78.5公里,患者所居住的地方离专业治疗机构的距离较远,限制了疟疾患者获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3.5 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
医疗保障系统是否齐全、医疗专业水平的高低乃至医疗服务的优劣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就医行为。城镇的医疗保障系统和设施要优于乡村,在发展中国家及乡村地区,医疗卫生系统较落后,医疗保障系统较差,使得这些地区的疟疾疾病循环现象比较严重,有着恶化的趋势。
影响疟疾患者求医行为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儿童、老人、女性群体的体质要弱于男性,从而易受病菌的感染,而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使其忽略自己受到疟疾感染的事实,即便是得知被疟疾感染,也很有可能会放弃治疗。在偏远的乡村,一方面,居民生活水平底下,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医疗保障制度落后,设施不齐全,即便是得知已被疟疾感染,都有可能仅仅只是进行简单的治疗甚至是放弃治疗,从而形成越是落后的地区,流行越是猖獗,难以制止的恶性循环。
4 展望
Andersen模型中所提出的倾向因素,能力因素和需求因素能够很好地应用于患者的求医行为。患者的求医行为,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它还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针对影响因素,在疟疾的治疗和预防过程中,不仅需要不断完善医疗措施,研发新药物以降低疟疾治疗成本,同时需要提高医疗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在疟疾高发区及传染期要充分开展疟疾的知识普及宣传,培训讲座和咨询指导,提高人们对疟疾危害性的了解与认识,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主动防治和就诊,从而降低疟疾的发病率。随着社会发展和就医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健康的就医行为将逐步形成。
[1] VITORIA M,GRABICH R,GILKS C F,et al.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HIV/AIDS,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Pathology,2009, 131(6):844-848.
[2] ALEMU A,TSEGAYE W,GOLASSA L,et al.Urban malaria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in Jimma town,south-west Ethiopia[J]. Malar J,2011,173(10):1-10.
[3] TOMASS Z, DEJENE T, KIDANE D.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KAP) about Insecticide Treated Net (ITN) usage against Malaria in Kolla Tembien district,Tigray,Ethiopia[J]. Momona Ethippia Journal of Science,2011,3(2):64-77.
[4]车河龙,林 栋.疟疾的防控现状及进[J].热带医学,2010,10(2):218-220.
[5] 周 升,杨中华,杨 锐,等.云南省边境疟疾流行区居民疟疾防治 IEC策略制定的需求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5):2873-2876.
[6] 杨绍杰.云南省昌宁县2003-2008年疟疾疫情分析[J].中国病原生物学,2010,5(2):1-2.
[7] 陈国伟,王 军,黄兴周,等.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19个口岸入境者疟疾血清学检测[J].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2010,28(1):54-57.
[8] UZOCHUKWU B S,ONWUJEKWE O E.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alaria:a case study of four local government areas operating the bamako initiative program in south-east Niger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2004,3(1):1-10.
[9] RAHMAN M,ISLAM M M,ISLAM M R,et al.Disease Pattern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in Rural Bangladesh[J].FARIDPUR.Medical College Journal,2011,5(1):32-37.
[10] ANDERSEN R, ADAY L A. Access to Medical care in the US:Realized and Potential[J].Medical Care,1978,16(7):533-546.
[11] HORSMAN J M, SHEERAN P.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HIV/AIDS: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Social Sicence& Medicine,1995,41(11):1535-1567.
[12] 王小万,刘丽杭.医疗保健服务利用行为模式[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182(8):500-502.
[13] HLONGWANA K W, MABASO M L H, KUNENE S,et al.Community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KAP) on malaria in Swaziland A country earmarked for malaria elimination[J].Malaria Journal,2009,8(2): 1-12.
[14] DMAZIQO H,OBASY E,MAUKA W,et al.Knowledge, attitudes,and practices about malaria and its control in rural northwest Tanzania[J].Malaria Research and Treatment,2010,1-9.
[15] MOHAPATRA M, DAS S. The Malaria Severity Score: a Method for Severity Assessment and Risk Prediction of Hospital Mortality for Falciparum Malaria in Adults[J].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of India, 2009,57(6):119-126.
[16] AWWAL, AMIN M R, HAFIZ S,et al.Immunochromatographic Test over Microscopy in Diagnosis of Severe Malaria in Bangladesh[J].Journal of Armed Forces Medical College,Bangladesh,2011,7(1):4-7.[17] GUPTA S,GUNTER J T,NOVAK R J,et al.Patterns of Plasmodium vivax and Plasmodium falciparum malaria underscore importance of data collection from privat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 India[J].Malar J,2009,227(8):1-8.
[18] 蒋 静,程 波,杨小兵,等.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县人群疟疾知识知晓情况调查[J].中国病原生物学,2011,6(4):294-296.
[19] MANGHAM L J,CUNDILL B,EZEOKE O,et al.Treatment of uncomplicated malaria at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and medicine retailers in south-eastern Nigeria[J].Malar J,2011,155(10):1-13.
[20] SOMI M F, BUTLER J R G, VAHID F,et al.Economic burden of malaria in rural tanzania: Variations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ason[J].Trop Med Int Health,2007,12(10):1139-1147.
[21] 杜建伟,吴开琛,节译.全球疟疾的控制和消除:技术性评议的报告(Ⅱ)[J].中国热带医学,2010,10(8):965-969.
[22] 赵文晓,陈莉军,刘艳丽. 居民求医行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利用情况的调查[J].护理研究,2009,23(8):258-259.
[23] AHMED S M,HAQUE R,HAQUE U,et al.Knowledge on the transmiss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laria among two endemic poplations of Bangladesh and their health-seaking behaviour[J].Malar J,2009,8(7): 1-11.
[24] 郭传坤,李锦辉,覃业新.广西疟疾媒介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和传疟作用研究[J].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2007,18(2): 112-115.
[25] 周 升,张再兴,李 丽,等.云南盘江垦区疟疾患者门诊使用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动物防制,2004,20(3):165-168.
[26] 何昌华,李凯杰,王光泽,等.海南省南桥地区上山夜宿人群疟疾防治KAP 调查[J].中国热带医学,2010,10(6):670-672.
[27] 周正斌,朱淮民.疟疾监测方法研究进展[J].国际医学寄生虫病,2011,38(5):286-290.
[28] LABHARD N D,ABOA S M, MANGA E,et al.Bridging the gap:how traditional healers interact with their patients.A comparative study in Cameroon[J].Trop Med Int Health,2010,15(9):1099-1108.
——“零疟疾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