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爆发时,舆论褒贬不一
大革命爆发时,舆论褒贬不一
◎德国于2012年发行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诞辰300周年的纪念银币
大革命引起了整个欧洲的瞩目,催生了一个模糊的信号——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欧洲各国也模糊地感觉到了必然会有改变和改革,但没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模糊的预感使民众的思想骚动起来,但各国的君主和重臣们却没有感觉到这种骚动,他们认为,革命是每个国家制度都有的慢性病,这场革命只是其中一场发作,结果只有一个,不过是踩着邻居的尸骨在政治上向上爬。
各国的君主和重臣们不知道大革命的真谛,却在无意中说了出来。1791年,德意志的主要诸王齐聚皮尔尼茨城堡(Pilnitz),宣称欧洲各国都处于威胁法皇的危险之下,他们说的是真的,但实际上他们心里却绝不是这么想的。当时的秘密文件证明,这个说法只是个巧妙的借口,用来掩盖他们真正的意图,在大众面前伪装起来。他们完全明白(或自认为完全明白)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场地方性的偶发事件,渔人得利即可。以这种观点为前提,他们精心布局,充分准备,秘密缔结联盟,在战利品出现之前就吵得不可开交了。总之,他们连横合纵,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只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事实。
英国人有自己的历史经历,所以明智,已经长期享受政治自由的乐趣,所以透过重重迷雾看到了一场大革命的稳步迫近。但他们没看清它的形式,也没看清它注定会对世界、对英国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在大革命爆发前,亚瑟·杨格正在游历法国,已经感到有场大革命迫在眉睫,但对它的实际结果却判断得非常错误,他害怕大革命会进一步增加特权阶级的权力。“对于贵族和教会,”他说,“如果这场革命提高了他们的优势地位,恐怕会弊大于利。”
自大革命爆发第一天起,埃德蒙·伯克满脑子就被恨意点燃,但也曾一时有过怀疑。他首先得出推论:即使大革命没有把法国夷为平地,至少也会削弱法国。“当下的法国,”他说,“从政治角度看,即将被排除在欧洲大国体系之外,很难判断她重新跻身领袖大国的可能性。但现在我认为,政治意义上的法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非常确定的是,要重新恢复以前的积极状态需要很长时间。这一代法国人将来评价起自己的国家来,会说:‘我们听说高卢人也曾经非常骁勇善战。’仿佛骁勇善战的法国已经成了古老遥远的历史。”
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人们,判断也很失准。大革命爆发前夕,还没有哪个法国人知道革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当时的所有陈情书中,我只找到两份似乎略带着对人民的畏惧情绪。所有人害怕的都是皇族或者王庭(那时候还这么称呼来着)继续保持过分的特权。人们说三级会议太软弱,为期太短。人们害怕自己会遭受暴力,贵族对此尤为不安,几份陈情书坚决要求“瑞士卫队必须宣誓绝不攻击平民,即使在暴动和暴乱中”。他们相信,只要三级会议能自由召开,就会纠正一切弊端。尽管必要的改革很多,但并不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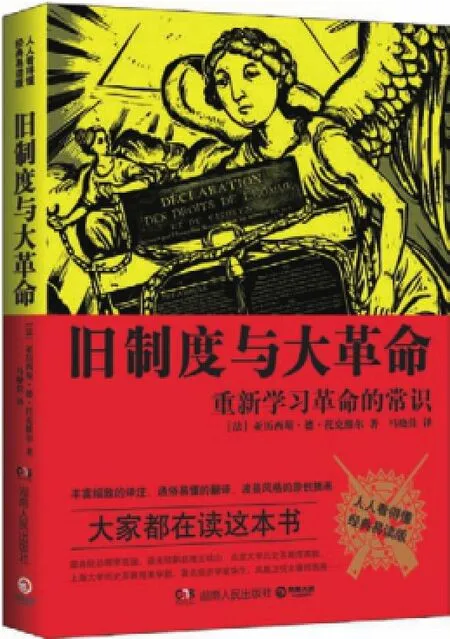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亚历西斯•德•托克湖南人民出版社博集天卷32.00 ISBN:9787543893924
为什么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减轻负担,却激怒人民?为什么威胁整个欧洲所有国家的大革命会在法国爆发,而不是其他国家……这部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既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经典注释,又依据海量史实资料,精心补充了大量译者注。波普风格波普风格的原创插画,提高了大众化的、通俗的趣味。
同时,大革命在按自己的步伐向前迈进,就如同魔鬼奇异恐怖的头部显现出来。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政治制度后,又开始着手摧毁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法律体系,甚至要改变人们的说话方式。大革命在粉碎了政府机器后,开始摇晃法国的社会根基,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攻击上帝本身;它很快就越过了国界,开始用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手段、战术和谋杀性的口号(皮特称之为“舆论武装”),打倒各个帝国的一个个地标,打碎一个个皇冠,压迫所有的人民(说起来奇怪,民众被革命争取过来支持革命)……直到发生这一切,人们的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君主和政治家们开始明白,大革命起初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历史事故,但却发展成了一场非常新奇的事件,和以往的所有经验都对不上号;它波及的范围如此广泛,带来的变化如此恐怖,如此难以理解,甚至完全超出了当时人类心智的理解能力,怎么都解释不明白。当时,一些人认为,一定存在某种未知的力量,它强大无比,没有别的什么力量可以增加其分毫,也没有别的什么力量可以使其减损毫厘。就连它自己也无法遏制自己,而且,这股力量会把人类社会引向最后的彻底分解。梅斯特尔在1797年评论道:“法
国大革命有种魔鬼撒旦的特性。”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则在大革命中看出了上帝之手,并得出结论说:这是全知之主的恩泽计划,要革新法兰西民族甚至人类种族。当时的几位作家被某种信仰恐慌所攫住,就像萨尔维初见野蛮人时感到的信仰恐慌一样。伯克继续自己的思想,他宣称:“法兰西被剥夺了政府,还完全丧失了社会秩序,法兰西人民从帝国子民一下子堕落成了一堆旁观者。在周边的邻邦强国看来,法国不再是一个威慑群雄的国家,而是成了一个值得被同情和侮辱的对象。君主制被谋杀,而从君主制的坟墓里,升起来一个巨大无比、力大无穷而且面目狰狞的幽灵,一个超出人类所有想象力、打破人类一切心理防线的可怕怪物。它直奔目的地,不惧危险,毫无忌惮,它无视一切常识和原则,蔑视一切常规手段。人们接受这个邪恶幽灵的存在,倒不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而是习惯了就好了。人们说服自己接受它,不是因为它的存在符合个人的幸福原则和日常行为模式,而是,谁不相信它可以存在,便被它摧毁。”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它确实像当时的人们感到的那么不同寻常吗?确实像他们想的那样旷古绝今、摧毁一切吗?那场奇异而恐怖的革命的真正特点和真实意义是什么?它到底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呢?
这些问题可以支撑一个庞大的主题。大革命已经过去,那些令革命家们目眩情迷的激情早已远逝,但大革命离我们又不太远,我们可以欣赏激活大革命的精神。再过些时间,讨论这一主题就会很难了。因为革命一旦成功,革命的初衷就会消失,从而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理解,这是个自动的过程。看来,现在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期正好可以让我们准确地研究和评判那个伟大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