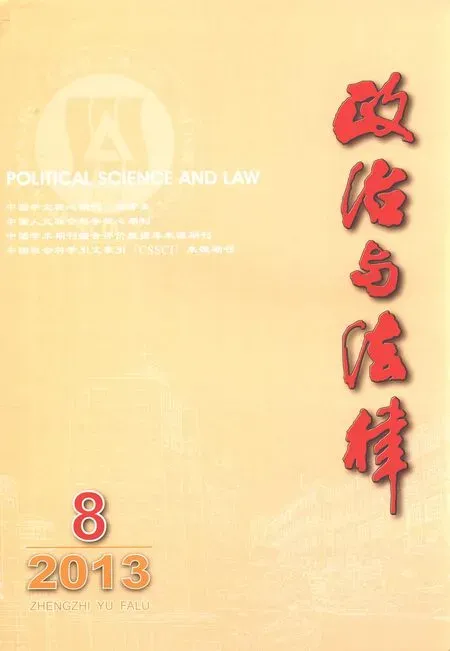论销售假药罪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消解*
孔祥参 刘 芳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沈阳110004)
论销售假药罪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消解*
孔祥参 刘 芳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沈阳110004)
《刑法修正案(八)》对销售假药罪的修正必然引起司法运行的变化,这一修正是否适当应以司法运行的实际情况予以说明。通过对有关司法判决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销售假药行为被定罪科刑。这是由立法修正和司法适用中的重刑化倾向共同造成的,在立法修正上,因假药的认定采用的是行政法的形式标准,销售假药的行为是否蕴含了实害发生的高度盖然性值得反思;而在立法已经修正的情况下,应通过能动司法消解立法带来的问题。
销售假药罪;抽象危险犯;重刑化;司法解释
一、抽象危险犯——销售假药罪之性质界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销售假药罪作了修正,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取消了基本犯单处罚金的规定,并删除了罚金刑中有关数额的具体规定等,从而降低了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解决了司法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难题,体现出从刑事政策上从严惩治销售假药犯罪,构筑严密刑事法网的立法倾向和努力。但是对于修正后的销售假药罪的性质如何,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删除“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只要存在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是将这一犯罪由危险犯修改成行为犯;1另一种观点认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是一种具体危险犯的规定,删除这一要件,意味着将销售假药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2亦有观点认为修正后的销售假药罪既是抽象危险犯也是行为犯。3然而,因学者对销售假药罪性质展开专门研究的成果较少,一般均没有论述理由。
笔者认为,修正后的销售假药罪应当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学界对于行为犯这一概念存在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4这是从犯罪停止形态上做的界定;有学者认为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单纯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就足以构成犯罪,而无须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5这是从犯罪成立角度做的界定。无论学者对于行为犯的界定如何,均不否认行
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行为犯的成立都不依赖特定结果的发生。而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危险犯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实害犯是以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依据危险状态的不同,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指将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规定在刑法条款中,法官必须就具体案情逐一审酌判断,而认定构成要件所保护之法益果真存在具体危险时,始能成立犯罪之危险犯;抽象危险犯是指符合构成要件中所预定之抽象危险即成立犯罪之危险犯。6因此,具体危险犯需要司法对于危险是否存在做出具体判断,而抽象危险犯一般只要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存在抽象的危险而认定构成犯罪,不需要司法做出具体判断,但是仍应具有发生实害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关系问题,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行为犯包括了危险犯,7有学者认为二者截然不同,8而仅就犯罪分类的标准不同而言,二者应有重合。9基于犯罪的实质为法益侵害的立场,犯罪是对法所保护的利益或价值造成侵害或引起危险(威胁),10就修正后的销售假药罪而言,笔者认为将其性质界定为抽象危险犯较为合适。修正前销售假药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是具体危险犯的规定,危险是否存在需司法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这一要件的删除,意味着司法可基于销售假药行为本身的存在即认定其具有对法益侵害的危险,进而认定犯罪成立,此时销售假药罪转变为抽象危险犯。同时,基于犯罪应至少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行为犯也是如此。如果仅有销售假药的行为,没有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就不应认定为犯罪,因而从这一角度而言,行为犯应是抽象危险犯。根据抽象危险犯的基本理论,一般而言,只要实施了销售假药的行为就认定产生了抽象的危险,进而构成犯罪。而认为销售假药罪是行为犯的观点,在论述时也多认为之所以实施了销售假药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是因为销售行为本身就蕴含了刑法所不允许的法益侵害危险。
二、重刑化倾向——销售假药罪实证分析
对销售假药罪的司法运行情况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确定研究样本和研究要素。对于研究样本的选取而言,司法者实施法律的最终成果是案例,案例是研究法律运行最重要的载体。因此,各级法院关于销售假药罪的司法判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一罪名的实际运行效果,笔者选取某副省级城市三个基层法院关于销售假药罪的全部生效司法判决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范围为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1月6日(以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生效之日止)。其中,A法院,生效判决为91份,适用修正前刑法的为31份,适用修正后刑法的为60份;B法院,生效判决96份,适用修正前刑法的为23份,适用修正后刑法的为73份;C法院,生效判决64份,适用修正前刑法的为15份,适用修正后的刑法的为49份;另在其他三个基层法院随机抽取样本共计15份,适用修正前刑法的共计3份,适用修正后刑法的共计12份,以上司法判决共计266份,其中适用修正前刑法共计72份,适用修正后刑法共计194份。
在研究要素的确定上,基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销售假药罪的修正,结合司法实践情况,选取犯罪行为、刑罚裁量以及犯罪行为与刑罚裁量的对应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要素,对销售假药罪的司法运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要素一是犯罪行为。销售假药罪规制的是销售假药的行为,这类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销售假药的种类、数量、次数,生产、销售假药的销售金额、未销售的数量以及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等,同时对销售假药这一类型犯罪行为进行研究也应关注犯罪行为发生地的问题。
适用修正后刑法的司法判决共计194份,其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适用修正前刑法的司法判决共计72份,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况详见表2。

表1

表2
从以上两个图表可以看出,自2011年5月1日修正后的销售假药罪实施以来,无论是依据修正前刑法还是修正后刑法,司法实践中,假性药占了假药的94%以上,同时就适用修正前刑法的司法判决而言,因销售“VIAGRA”(万艾可)被认定为销售假药的占了相当大比例。因部分司法判决中并没有论述药品被认定为假药的具体依据,无法对药品被认定为假药的原因做详尽分析,但在有论述的司法判决中因“未在我国被批准进口上市销售”而被认定为假药的占了40%以上,因“没有或伪造许可证或者批准文号,且属于处方药”而被认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占了适用修正前刑法的司法判决中的60%以上。就被认定为犯罪的销售行为而言,适用修正后刑法的判决中,销售金额在人民币100元以下的占了60%以上,适用修正前刑法的判决中,销售金额在人民币100元以下的占了
30%以上,而无论适用修正前或修正后刑法,销售次数为1次的均占75%以上,犯罪行为发生在性保健品店和药店的均占70%以上。就司法判决的具体情况而言,大量情节显著轻微的销售假药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如:被告人陈某某在某地早市地摊上以每盒人民币10元的价格向高某某出售状元郎牌、参茸肾宝牌疑似假药各一盒,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认定上述药品为假药,构成该罪。
要素二是刑罚的裁量。本部分对销售假药罪修正前后的刑罚具体裁量进行分析,包括拘役、罚金、有期徒刑、缓刑等刑罚的适用情况。适用修正后刑法的销售假药罪的刑罚裁量实际情况,共计司法判决194份,犯罪人共计218人,详见表3。适用修正前刑法的销售假药罪的刑罚裁量实际情况,共计司法判决72份,犯罪人共计79人,详见表4。

表3

表4
从以上两个图表中可以看出,就销售假药罪的刑罚裁量而言,无论是适用修正前的刑法还是修正后的刑法,适用拘役的均占到司法判决的94%以上,这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销售假药罪的基本犯。就适用修正后刑法的销售假药罪的刑罚裁量而言,结合本文图2可以发现,并处适用的罚金刑的罚金数额较高,数额在1万以上的占到80%以上,数额在3万以上的占到近50%,而数额在5000元以下的没有,5000元似乎成了销售假药罪罚金刑的起点。就适用修正前刑法的销售假药罪适用罚金刑的情况而言,因修正前刑法“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立法设定,罚金的数额一般较少,但仍有个别案例突破了这一立法设定,判处的罚金数额远远高于销售金额的二倍。在缓刑的适用上,无论适用修正前刑法还是修正后刑法,缓刑的适用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5年至2007年全国法院适用缓刑占判罚率的比例分别是21.88%、23.23%、24.43%,13且是在本文所涉及销售假药罪90%以上属于基本犯的情况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销售假药罪较强的打击力度。
要素三是犯罪行为与刑罚裁量的对应关系。对何种犯罪行为进行何种刑罚的裁量是
整个刑法运行的核心过程,对有关销售假药罪之犯罪行为与具体刑罚裁量之间的具体分析,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这种刑法运行的详尽过程,进而对其适用问题进行价值衡量和判断。我们首先从上述194份和72份司法判决中分别随机选取若干案例,分析销售假药罪的犯罪行为与刑罚裁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就销售金额和罚金刑数额之间做详细分析。
适用修正后刑法的典型案例有五件。案例一,曹某某在某地以30元的价格将标识“Vigour”(“万艾可”)的药片一片销售给高某某,经鉴定上述药品为假药,曹某某认罪态度较好,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案例二,王某某在某地以90元价格将“德国黑金刚”两盒、“黑金”一盒销售给赵某某,上述药品经鉴定为假药,王某某认罪态度较好,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案例三,李某某在某地以30元价格将“银伟哥”一片销售给杜某某,上述药品经鉴定为假药,李某某认罪态度较好,积极缴纳罚金,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案例四,孙某与焦某经预谋后在药房内以30元、20元的价格向白某销售美国“伟哥王”及“鹿鞭藏虫草”各一盒,上述药品经鉴定为假药,孙某认罪态度好,焦某所起作用较轻,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和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案例五,侦查机关于王某经营的保健品店查获“夜超人”四盒,经鉴定上述药品为假药,王某积极缴纳罚金,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从适用修正后刑法的五个代表性案例中,可以看出,销售假药罪的刑罚裁量明显呈现出重刑化倾向,就销售假药的行为而言,五个案例中最轻的为以30元的价格销售一粒“银伟哥”,较重的是以90元的价格销售“德国黑金刚”两盒、“黑金”一盒,但是无论是最重的还是最轻的销售行为,在笔者看来均应属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就刑罚裁量而言,五个案例中,被告人均被判处拘役,只有一人适用缓刑,就并科适用的罚金刑而言,在有销售金额的四个案例中,最低的罚金数额为人民币五千元,是销售金额的600倍,最高的罚金刑为人民币五万元,约是销售金额的555倍,而倍数最高的达到了约666倍;在没有销售金额,被查获“夜超人”四盒的案例中,罚金刑的数额也达到了人民币两万元。
以上五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修正后销售假药罪定罪和科刑中的重刑化倾向,这一倾向在销售金额与罚金刑数额的对比中更能得到体现(详见图1、图2)。
适用修正前刑法的代表性案例有两件。案例一:李某以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出售标识为“Viagra”药品十片,并在其经营的保健品店内收缴上述药品32片,经鉴定为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李某部分犯罪未遂,认罪态度较好,能主动缴纳罚金,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元。案例二,张某在其经营的性趣加盟店以200元的价格将标识为美国生产的“Viagra”出售给刘某,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安机关同时在店内搜缴“Viagra”1瓶2盒,经鉴定为假药,如购买者服用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张某部分犯罪未遂,认罪态度较好,积极缴纳罚金,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一百五十元。修正前整体的销售金额和罚金数额可详见图3和图4。

图2 罚金
从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案例与适用修正后刑法的案例对比来看,其销售行为上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销售行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标准大多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即“没有或者伪造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批准文号,且属于处方药的”,而刑罚适用上区别较大的是罚金刑的数额,前者罚金数额较小也是基于立法的限制,但是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案例中仍有极少数突破了立法限制。
三、能动司法——销售假药罪立法修正问题的消解

图3 销售金额

图4 罚金
销售假药罪的立法修正和司法扩张与风险社会不无关系,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安全事件使得民众对风险的恐惧不断加深,人们对于安全保障有了更高的诉求,“结果本位主义的刑法在危险预防与法益保护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作为结果的危害渐渐不再是刑法关注的重心,尤其在法定犯中,惩罚的根据越来越不依赖于现实的侵害结果,而是取决于具有风险的行为本身”。14刑法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在实害发生之前进行规制,导致刑法的扩张趋势明显。就假药犯罪而言,出现了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制售假药案,安徽华源公司的假欣弗案,2007年全国多地出现的假冒“人用狂犬疫苗”案等一系列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重大刑事案件,加剧了
人们对药品安全的担心,在功利导向的风险规制语境中,刑法采取了应急式的政策性对策,对销售假药罪作了立法修正。
就立法的修正而言,至少有两点需要给予理性考量。一是《刑法修正案(八)》将销售假药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正为抽象危险犯,这一修正将犯罪关口前移,降低入罪标准,未必是合适的。抽象危险犯是法律依据人们的一般经验而判定某类行为本身蕴含了对法益侵害的高度危险而设定的一类犯罪,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移,这种前移必须具有充分的根据,只有对依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的判定离实害发生距离很近并且发生的概率较高的危险行为才能实行犯罪化。15诚然药品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销售假药的行为蕴含了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实际损害的高度盖然性。这种损害一方面指使用假药后对使用者人身健康的损害,另一方面指因假药的使用而耽误治疗的时机所造成的损害。但是并不是所有销售假药的行为都蕴含了实害发生的高度盖然性。这与我国刑法上设定的其他抽象危险犯不同,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这一罪名中,食品指的是“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这种食品的销售必然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对作为犯罪对象的食品采用的是刑法上的实质判断标准即有毒、有害,而在假药的认定标准上,我国采用的是行政法的形式认定标准,即按《药品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照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在依据该规定被认定为假药的案件中,假药本身未必是有毒、有害的,未必蕴含着实害发生的高度盖然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假药是不可能造成实际损害发生的,从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的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司法运行的实际情况中,可以看到在被认定为犯罪的案件中,假性药占90%以上,而性药被认定为假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因为这种药品未在我国批准上市销售,也就是这类案件被认定为犯罪不是因为假药本身蕴含着对健康的危害,而是出于药品秩序的考量,16同时,假性药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并不具备导致实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二是取消单处罚金和“销售金额”与罚金比例的规定,固然意味着从刑事政策上从严惩治销售假药行为,也增加了罚金刑适用的灵活性,但是这种规定也同时意味着销售假药罪刑罚适应性的减少和司法机关罚金刑自由裁量的增加。立法将实践中千差万别的销售假药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将其设定为犯罪,需要对这类行为的危害性的最大和最小的可能性给予关注。就这类行为而言,固然有如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制售假药案一样造成十几人死亡具有极其严重危害性的情况,但是也应注意到这类行为本身可能仅造成极其轻微的危害后果,如销售极少量假药的行为等,依据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单处罚金的取消,也就意味着对于这类行为不再具有作为犯罪处理并科处刑罚的实质依据。同时取消“销售金额”与罚金比例的规定后,在适用修正后刑法的194份司法判决中,罚金刑的最低数额为人民币5000元,数额在1万以上的占到近90%,数额在3万以上的占到了近50%,如此高数额的并科罚金刑不仅不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而且结合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分析,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同时无限额的罚金刑本身是否合理就是一个问题。17在194份司法判决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犯罪人无固定职业,被科以较重的罚金明显会进一步加重其经济负担,降低其回归社会的可能性。这样,不得不说适用高额罚金刑的社会效果堪虞。
销售假药罪运行中的重刑化倾向除与立法修正欠缺理性考量有关之外,还与对有关理论的认知偏差和司法实践中对刑法文本的过度依赖不无关系。在立法已作修正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限制因立法修正欠缺理性考量带来的弊病。
一是厘清抽象危险犯的有关理论,为销售假药罪提供出罪的可能。关于抽象危险犯是否只要行为存在即可证明危险存在,进而认定犯罪成立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是法律依据人们的一般经验而拟制的风险,具有发生危害的潜在性,因此无须对其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发生严重危害的可能性或者现实性做出判断,仅根据其行为的形式即可肯定其抽象危险的存在。这种观点本身就自相矛盾,在具体的案件中,行为是否具有抽象的危险并非完全不需要作判断,而只是不需要作具体的判断,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只是认定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时,对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进行的抽象程度高,若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能够判定不存在危险时,即应排除抽象危险犯的成立。18也就是说,在司法中不能仅仅因为销售假药的行为存在而认定犯罪成立,仍需要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做出判断。司法实践中,应该允许反证的存在,即“允许被告人证明在当时具体情况下,自己的行为确实不同于普通情况下的类似行为,确实能够证明该行为不产生侵害客体的危险性”,从而证明自己无罪。19
二是以刑法总则“但书”的规定作为对销售假药罪的成罪限制。关于犯罪的成立问题,我国刑法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量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刑法总则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以及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情节恶劣”、“损失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表明行为危险性程度的规定,在分则具体罪名没有明确量的要求时,总则量的要求当然适用,这种量的要求同样应作为对抽象危险犯的适用性限制。20受到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限制,并非只要有行为即可认定存在抽象的危险,进而认定销售假药罪的成立,否则会模糊刑法与行政法的界限,颠覆部门法的划分。应坚持基本的犯罪判断标准,对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销售数量、数额极少的假药的情节显著轻微的违法行为,应当排除在犯罪之外。
三是处理好刑法与行政法的关系,适用行政法的各有关规定处理情节轻微的销售假药行为。我国行政法对销售假药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规制,即《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在销售假药罪修正后被虚置,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与其修正前的适用情况大相径庭。有关资料反应,近年来每年药监部门查处并给与行政处罚的生产、销售假、劣药和假、劣医疗器械等违法行为的有20多万件,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数量较少,2005年至200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只有300余件,21而刑法修正案实施之后,仅某副省级城市三个基层法院不到两年时间内审理的销售假药罪这一单个罪名的案件就超过了200件。22具体分析有关司法判决可以看出,销售假药罪几乎成为打击假性药犯罪的专项规定,这反映出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和社会控制系统中定位的错误。
四是通过刑事强制措施和刑罚的适用实现销售假药罪的罪刑均衡。笔者注意到在销售假药犯罪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上,取保候审的使用率极低。在本文所涉及的全部266份司法判决中,即使在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案件中,有70%左右被审判机关决定逮捕;而在刑罚的适用上,销售假药罪呈现出缓刑使用率低和并科的罚金刑数额极高的特点,这反映出司法中存在明显的重刑化倾向。为了限制因立法修正欠缺理性考量所带来的问题,可以在刑事强制措施上适用取保候审和在刑罚的裁量上适用缓刑,同时降低并科适用罚金刑的数额,以达到罪刑均衡的法律运行效果。
注:
1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高铭暄、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储槐植、李莎莎:《生产、销售假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为视角》,《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刘晓莉:《降低入罪门槛的当代价值探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修正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
2参见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3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周光权主编:《刑法历次修正案权威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4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5、7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第272页。
6林山田:《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106页。
8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鲜铁可:《论危险犯的分类》,《法学家》1997年第5期。
9关于危险犯与行为犯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涉及犯罪的实质是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等刑法基本理论。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赞成犯罪的实质是侵害法益。
10张明楷:《新刑法与法益侵害说》,《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11一般而言,性药泛指用于增强性功能提高性快感的药物或处方,本文所论及性药指市场上所销售的一切以能增强性欲、提高性功能为主要功能的药物。
12本文所涉及数额问题,以下均不包含本数,以上包含本数。
13郝川、王利荣:《再谈社区矫正制度方案的调整——以〈刑法修正案〉(八)的公布实施为视角》,http://www. 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pkID=32340,2013年2月16日访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调研课题组:《关于我省法院缓刑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http://www.gdcourts.gov. cn/gdcourt/front/front!content.action?lmdm=LM52&gjid=21519,2013年2月12日访问。
14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15、18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
16这里涉及销售假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问题,由于这一罪名放在刑法第三章第一节中,其保护的法益是我国的药品管理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看似其保护的主要法益在于前者,但是,生命健康的法益应重于秩序的法益,同时秩序的背后应有个人法益的支撑,刑法排除单纯违反秩序的行为,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7关于罚金刑的详尽论述,参见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4页。
19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0谢杰:《“但书”是对抽象危险犯进行适用性限制的唯一根据》,《法学》2011年第7期。
21参见祝二军、刘涛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做的解读,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009)》,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22刑法修正案实施后,因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适用原则,适用修正前刑法的案件在三个基层法院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也有70多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法修正之前销售假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少的情况,恐怕不是刑法本身造成的,而是刑法的实施执行中的问题所造成的。
(责任编辑:杜小丽)
D F623
A
1005-9512(2013)08-0021-09
孔祥参,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沈阳行政学院讲师;刘芳,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2012-2013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课题(省部级)(课题编号:13H ZK T369)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