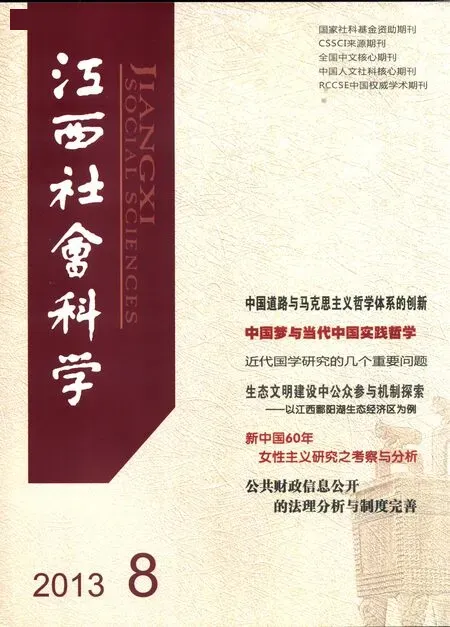江西傩戏汉族族群文化的表征
■曾 澜
在国内傩文化研究领域,但凡涉及傩文化的族群性研究,被观察的对象往往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少数族群之上,如土家族的傩堂戏、彝族的“变人戏”等。而事实上占据中国傩戏遗存多数比例的汉族傩,其汉族族群文化的承载则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江西傩戏的研究之中:汉族族群文化特征在江西傩戏的研究中鲜少涉及。虽然江西境内汉族人口99.66%的占比①造成江西人族群身份意识的潜隐,傩戏的汉族族群文化特性亦被忽略,但也正是汉族人口的极大占比,造就了江西傩戏汉族族群文化特性的凸显。江西傩戏就其本质而言是汉族族群记忆的一种具体化形态,呈现了自古傩祭仪式传承至今的汉族族群文化基因。秦汉时期的吴芮在江西南丰开始传播傩仪时,就曾明确地表明要“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1],而恪守“祖周公之制”得以传承的江西傩戏,无论是仪式的功能结构还是傩神信仰蕴含的观念内涵,都体现了自周公之始历代文字记载中傩仪的汉族族群文化特征。
一、傩戏功能结构的族群性传承
从傩祭仪式的功能结构来看,江西傩戏,尤其是南丰县、万载县的傩祭仪式,传承了自周傩以来汉族宫廷傩仪以驱鬼逐疫为核心的文化功能,及与此相关联的包括面具服饰之逐除装扮、执戈扬盾之逐除动作、唱和呼应之参与方式、索室逐疫之逐除方式以及集体逐除在内的五大基本情境性要素。这五大情境性要素既在行为框架上保证了驱鬼逐疫核心功能的实现,又是这一功能的具体呈现方式。
有文字记载的周代傩仪便具备了驱鬼逐疫的核心功能及五大情境性要素。这集中表现在傩仪“狂”这一总体情境性氛围及构成“狂”的五大基本情境性要素。“狂”,“盖饰鬼者以为人之鬼之灵魂凭依于身,故其动作为狂怪”。[2]在傩祭仪式中,“狂”显然并不止于动作的“狂怪”,还在于其他几个要素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周代“方相氏,狂夫四人”[3](P946),“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4](P971)。“丑陋”的面具装扮、执戈扬盾的狂怪动作,再加上强烈的驱逐鬼疫目的都促使方相氏进入到一种类似于萨满跳神的“迷狂”状态。而且,无论是方相氏的“狂夫四人”还是“帅百隶”,数字的约略描述均表明了傩祭仪式参与者的众多和逐除行为的集体性质。这种“狂怪”的逐除状态及由此而呈现出来的巫术氛围,亦会因为傩祭仪式参与者人数的众多及集体奔突的气势而更为凸显。
从文字记载来看,虽然自周以后汉族宫廷傩仪经历过不同时代的演变,各情境性要素的构成因子亦附加上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但傩仪之驱鬼逐疫的核心目的,逐除行为所呈现出来的以“狂怪”为特征的总体情境性氛围,以及其中所涵括的五大情境性基本要素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重要的是,汉族傩仪的功能结构仍然体现于江西大多数的现存乡村傩仪,其中以被誉为“中国傩舞之乡”及周傩“活化石”之南丰县石邮村为甚。石邮村传傩时期便体现了这一传承。吴氏族谱中《乡傩记》载:“春王元旦起傩,乐奏金鼓,以除阴气。玄衣朱裳,执戈戟斧钺驱邪具物,蹈舞于庭,虽近于嬉戏欢娱,乡人至愚,犹不敢亵越视之,此孔子朝服阼阶之意也。乡人名曰‘演傩’。及至元宵后一夜,灯烛辉煌,金鼓齐喧,诗歌自唱,手执铁链,铮铮然有声,房室堂庭遍处驱逐,以除不祥,神威达旦。是夜寂然,鸡犬无声,乡人又名曰‘搜傩’。”[5](P84)即便是现在,石邮傩仪亦呈现了较为完整的古傩仪结构。石邮村的沿门逐疫仪式(俗称“搜傩”)是在正月十六晚举行,挨家挨户进行逐除。笔者在2010年正月十六晚参与了石邮村的搜傩仪式:傩神庙搜完傩之后,傩班弟子在十多挂一万响的鞭炮声、十多支炮铳的放炮声和一路上的尖锐呼哨声中奔向各家各户搜傩。与此同时,在傩班弟子还未到达时,各家各户男主人就必须准备好爆竹,带领全家大小手拿点好的线香在门口恭迎傩神的到来。此外,还有两三个炮手拿着炮铳立于门外,傩神一到,随着傩神唱颂歌而相互应和,同时点燃爆竹,放炮铳,搜傩的“钟馗”、“开山”和“大神”依次起跳小跑进入厅堂,手持神链(即铁链)上下挥舞,由东往西击打四方,“搜傩”以驱鬼逐疫。另有参与帮忙的村民或者举着火把,或者挑着桶(盛放傩神的供奉品),或者运送炮铳,有二十余名村民随行奔突,鼓炮震天,气氛显得威严而又神秘。
虽然石邮傩仪中作为逐除核心人物的方相氏变成成由傩班弟子扮演的“钟馗”、“开山”和“大神”,但是逐除的面具装扮这一要素并未改变,而且逐除动作、逐除方式、唱和呼应、集体参与、逐除的核心功能及由此基本要素形诸而成的神秘狂怪之情境性氛围很显然与历史中的傩祭仪式一脉相承。不仅石邮村如此,江西其他乡村的傩祭仪式亦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傩仪式的基本功能结构,体现了汉族族群文化的传承:如赣北都昌县,“上元夜分,合族丁壮鸣锣击鼓放爆,挨家循行,谓之逐疫;亦古傩遗意”[6](P136);赣西北靖安县正月十六,“各燔薪于厅,事拔除不祥……落灯风过,傩神出市,黄金四目,犹然周礼之遗”[7](P187-188);赣西萍乡“立春先日,乡人舁傩集于城,俟官迎春后即驱疫于衙署中及各民户”[8](P2563),乐安流坑村《董印明房傩神会略》也有“元宵装扮神像,扫荡街巷”[9](P58)的记载,等等。
除了江西本土居民在春秋战国时期融合于中原华夏族民成为华夏汉民族的一部分,江西傩文化便自然而然传承了汉族傩文化的特征外,江西历来保守的文化氛围亦使得大多数乡村的傩仪保留了原初汉族傩祭仪式之驱鬼逐疫的核心功能。而且,由于江西大多数傩祭仪式都依附于当地的宗姓大族,具有宗族传承的性质,因此傩仪的进行总是村落集体性的,并遵循着固定的仪式程序,逐除的行为方式和仪式的结构模式在较大程度上沿袭了历代汉族傩仪遵循特定时间、特定路线沿门逐疫的逐除模式。这与一些以“还愿”为核心的汉族傩仪和少数族群的傩堂戏、傩愿戏、师公戏等相区别:这些仪式以祈愿还愿为核心目的,仪式的参与和操办亦从集体型转变成个体家户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古傩仪众人呼和,齐心逐除“狂”之情境氛围。古傩仪所需要的一些情境性基本要素也因为仪式核心功能的改变而发生变异:某些要素缺失或者直接转变成为地域性或其他族群性的文化标志性符号,从而使其转化为各种类傩仪形态。比如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三川地区虽有被当地人称为“纳顿”的面具舞蹈,但是其目的并非是驱鬼逐疫,而是在丰年时期以面具舞蹈感谢地方神灵的护佑,是当地土族一种典型的民族性酬神活动。同为汉族的贵州安顺地戏,亦是古傩仪转化之后的一种类傩仪形态。
当然,江西傩仪除了驱鬼逐疫的核心功能之外,也与当地民众的生活相结合,衍生出各种祈愿还愿的仪式,如南丰县石浒村的“跳八仙”,乐安县流坑村的“玩喜”等。即便是被称为古傩祭仪式“活化石”的石邮村,其傩仪也具有为村民求子祈愿、还愿的功能。尽管如此,驱鬼逐疫的逐除环节(俗称“搜傩”、“解傩”等)仍然是整个傩仪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也是仪式中最为隆重的部分,以驱鬼逐疫为核心功能的仪式结构和行为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汉族傩祭古礼,呈现出较为原生态的汉族傩仪文化。譬如南丰甘坊村的“解傩”仪式,其原意便如东汉王充《论衡·解除》所言:“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纳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10](P386)
二、信仰观念的文化同一性表达
江西傩戏不仅在仪式的行为方式和功能结构方面保存了汉族古傩祭仪式的面貌,而且其背后所蕴含的鬼神信仰及由此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更体现出傩史一脉相承之汉民族独有的族群宇宙观和价值观。
江西傩戏所蕴含的汉族族群价值观首先体现为傩仪的时空观及其投射出的宇宙秩序观。时间的标刻以及空间的布局往往是被历史地、文化地以及范畴地限定着,其投射的是一个特定族群的宇宙秩序观。而宇宙的时间过程和空间格局又是支配神鬼系统的依据和建构的背景[11](P359),仪式便成为神鬼系统与人的关系相互映射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于华夏族构成成分之一的周人而言,这种宇宙秩序集中体现在被称作周礼的仪式规制之中。周代具备了一套完整的时空观和鬼神观,借此而展开的傩祭仪式,其逐除鬼疫的行为便具有严格的时空约定。
从时间的约定上看,《礼记·月令》记载:
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仲秋之月,天子乃难,御佐疾,以达秋气。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12](P1374)
从上述记载来看,周代的傩祭仪式分别在季春、仲秋和季冬三个不同的时节举行。“‘季春之月,命国难’。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故难之”;“云‘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者,按彼郑注,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故难之,以通达秋气,此月难阳气,故惟天子得难”;“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按彼郑注,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故难之”。[3](P1043-1044)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时难”的傩祭仪式情境之中,时间的约定是仪式举行的前提性条件,这与中国古人的阴阳观具有极大的关联。《周礼·疾医》载:“四时皆有疠疾”,郑注:“疠疾,气不和之疾”。[4](P131)也就是说,疫病的发生产生于四时之恶气,在“季春”、“仲秋”、“季冬”三个特殊的时节,会产生阴气、阳气和寒气,并由此而引出不同的疫鬼,出而害人,因此,需要在这三个时节分别举行傩祭仪式,驱除疫鬼。不同的疫鬼是应时节的不同而各自“出行”,因此“时难”的时间不同,其傩祭行为目的也就是傩仪驱除的疫鬼对象也不同。
从空间的约定上看: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壙,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魍魉)[4](P971-972)
《礼记·月令》中有记载云:“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注云,“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天子乃傩,以达秋气”:王居明堂礼曰:“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注云:“旁磔于四方之门”。[4](P571、P615、P653)《淮南子·时则训》注:“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攘四方之疫疾也。”这里的“四隅”“九门”皆体现了古代汉族的空间观。方位的出现说明了在“时傩”这一严格的时间约定中,空间观依然在发生作用:四时皆有恶气,由不同时间季候所生发的疫疾厉鬼,并不是到处都有而是从宫室或居室的四方逸出害人,因此时傩的时候,还必须在四方安置磔牲,以延伸四方神来镇压、逐除四方鬼。
由此,周代傩仪中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是融合在一起的,体现了早期汉族文化时空一体,相生互证的宇宙秩序观念。事实上,依据考古学界的发现,中国人在相当早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四方有神祇作为象征的空间观念[11](P16-19)。后在四方的观念上产生了“中”的观念,且其神圣性逐渐超过了“四方”。从发生认识论的原理来看,当“主体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处于一种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宇宙之中的所有客体中的一个,他在什么程度上学会了怎样有效地作用于这个宇宙,他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这个宇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3](P24)。“中”的观念便体现了古代汉族观察、体验宇宙方式的改变,即人开始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进入宇宙的整体体验和认知结构之中,并逐渐建构和掌控了天、地、人之和谐一体的象征秩序:中央不仅在空间秩序上统辖四方,而且在价值等级上也优于四方。“中国”、“中原”的称谓便表明了“中”之于“四方”的掌控,傩仪中“方相氏”居于中央戈击四隅便是鬼神观念中“中央”之于“四方”的掌控。随着“中”之观念的出现,“五行”、“五方”“五岳”等也逐渐成为人们宇宙认知的重要观念,“由于日月运行、五星盈缩产生出来的‘五行学说’,就是中国人社会思想的本质,也就是宗教信仰的中心”[14](P585)。与空间观念发展的同时,时间观念也不断生发,并与空间观念相融合:四方各有星象,四方又与四季相连,四季又各有物候,四方与四季相关联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意思[15](P42);因为四方与四时的关系是对应的,所以四方帝亦发展为四时帝,四方、四时鬼疫的鬼神观念便依时空观念而得到了配置。
古人正是依据对宇宙天地的观察、体验和文化想象,把时间和空间进行了秩序化的配置,并依此配置的宇宙自然秩序同构了人间的社会秩序。原初傩祭仪式中所承载的阴阳五行及鬼神信仰的核心观念渗透进仪式的时空安置之中,并一直传承至今。虽然对于历史上便一直远离皇城、政不下县,而今仍处于现代化进程边缘的乡村社会而言,反映了族群宇宙观的时空观念并不总是会以一套类似于周礼一般的礼仪制度强调并凸显出来,而是碎片化地分散在乡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潜意识中的一种生活知识或思维惯习,俗称“规矩”而难以察觉,然而仪式是“宇宙观固定性的领域”,是“宇宙观知识的理想载体”,“在这些仪式中,宇宙观与平常百姓的种种体验相结合,因此,人们对宇宙观的理解以及与宇宙观打交道的方式是仪式的关键”[16](P209、P211)。
这样,我们亦就可以从现存江西的傩祭仪式中看到一直潜隐于其中蕴含有汉族族群宇宙观的时空观念。如笔者前面所论述的,与以“还愿”为核心功能的类傩祭仪式不同的是,江西的大多数傩仪仍然是以驱鬼逐疫为核心功能,因此病疫鬼神的出没及其被神灵的镇压、逐除仍然是以时空观念的框架来想象并表达的,由此而来的傩祭仪式其空间和时间的安排,也就自然相对严格地沿袭了历史上汉族傩祭仪式的基本时空约定。在时间安排上,现存江西傩祭仪式大多是在正月举行,时间约定虽然并未能确切如周礼“大傩”一般限定在季冬之月,但是其时间的安排除了是与生活相适应而做出的改变外,本质上也是应新年和春天的到来驱除阴气所滋生的鬼疫以达阳气、祈盼来年平安和谐的目的。较之以个体家户还愿傩仪的时间更为灵活来说,江西傩祭仪式的时间安排大多遵从祖制,更为严格也更为固定。如在萍乡:“先春之日,乡人乃傩”,“驱疫疠以达阳气”,仪式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春天到来之际,驱逐寒气以导阳气。南丰县石邮村吴氏族谱中的《乡傩记》载:“春王元旦起傩,乐奏金鼓,以除阴气”,“及至元宵后一夜……乡人又名曰‘搜傩’。如古者磔攘旁磔之法,以疫为阴之气所感,不可不有以除之也”。在这里,江西傩戏虽然安置在元旦至元宵期间,与周礼略有不同,但是傩仪中鬼疫滋生的原理及其逐除的目的仍然显示出,江西傩仪这一时间安排及其背后的观念本质上与周礼傩祭中季节变换,阴阳更替,进而鬼疫出没,需神灵逐除的观念相一致。
除了时间的约定之外,江西傩戏也有着非常显著的空间规约。这尤其体现在傩仪的逐除动作和诵神咒语之中。如万载县潭埠乡池溪村沙桥傩班(即丁姓傩班)在扫屋仪式中,“雷公”作为逐除的主神,念咒站在房中央,面向门外,“钟馗”立“雷公”前,面向“雷公”。“头将”站在东方,“二将”站西方,“三将”站北方,“四将”站南方,“四大天将”均面向“雷公”。“雷公”进入“总房”后,即拜东南西北四方,拎起一只雄鸡,先给鸡灌酒,又在五方的瓷碗中斟酒,口中边念五方咒:“一祭东方甲乙木神煞,二祭南方丙丁火神煞,三祭西方庚辛金神煞,四祭北方壬葵水神煞,五祭中央戊己土神煞。”宁都中村的傩戏“判官点书”节目中,“判官”要用唱的方式点东、南、西、北、中对应的五方神来收伏五方小鬼,继续用唱的方式来表达写文画符以驱鬼的内容,最后以“五方小鬼都化尽,判官无事归天宫”的道白来重复强调鬼疫被逐除的主题。乐安县东湖村傩舞节目中的《鸡嘴》、《猪嘴》在进屋搜傩逐疫之前,傩班领头人就要率众弟子揖拜四方神,念诵“伏兮伏兮,十方四界,值日星宿,功曹使者”,以祈求四方神灵附体显威,逐除鬼疫。在这些逐除仪式之中,作为逐除的主神总是站立于中央,号令或者指挥四方神来镇压逐除四方鬼,这不仅体现了历史上汉族观念中“中央”之于“四方”的主导地位,而且通过人敬奉牺牲供品延请五方神灵、佩戴面具装扮成神获得神功,并挥舞法器逐除四方鬼疫的空间方式体现了傩祭仪式之人、鬼、神各自回归其本位,即神护佑人、鬼疫被逐除、人重新获得平安之天、地、人和谐一体的宇宙秩序观。
此外,江西傩戏表演内容中所宣扬的价值观亦为自汉以来汉民族一直崇尚的儒家价值观。自董仲舒“独尊儒术”的论断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学便成为根深蒂固的“汉家制度”;西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儒学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都没有受到过根本性的冲击,一直牢牢地处在社会核心价值的位置上而主宰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大的风气与人心向背。[17](P28)江西历史上便推崇儒学,崇古尚礼,境内各州县都将儒学奉为圭臬,如境内袁州府(即今宜春市),其俗以“艺文儒术为盛”,“儒风之盛,甲于江右”[18](P84),南丰则“承先士文献之后,故士多俊才,礼教信义不减东鲁,兼有上世遗风”[19](P313),因而“儒家思想意识是江西继原始鬼神观念之后的又一文化主体意识,是江西人文进化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构成因素”[20](P5-10),至今江西傩戏仍然保存了诸多宣扬儒家价值观念的表演内容。
江西傩戏除了因宗族文化依附及其中所呈现出来的寄寓于宗族祖先崇拜之“孝”、“贤”、“忠”、“义”等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之外,就傩戏的江西地域文化特征而言,最突出的一点则是江西大多乡村傩仪中对魁星的崇拜。“魁星”俗称文曲星,是传说中主管文化和科举的神灵。“魁星”崇拜显然与江西重视文化教育与进仕科第的人生观密切相关。历史地观之,江西的经济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江西的文化教育以官学和书院两种形式出现在江西各地,十分普遍。名满天下的“四大书院”之首便是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同时,江西也是宋代理学渊薮之一,理学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之一。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说阳明之道赖江右而得以不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21](P331),即是指江西理学的兴盛及其精神的传承。而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在江西任职讲学期间,各地学生纷至沓来,江西学风大盛。他与陆九渊在江西讲学时的“鹅湖之辩”,更成为学术思想开放的标志。书院教育加上理学思想的兴盛促使了江西进仕科第人生观的形成,也使得江西成为当时全国最有成绩的科举大省之一。据初步统计,自隋唐科举考试开展以后,江西的进士就有11 100多人,是全国的12%点多。宋元明三代科名都在各省前五名之内。江西这些地方文化精英“做官大都从事儒家文化的传播,通过教化的努力把统一的精英价值贯彻到地方的行政中去,贯彻到当地的民众生活中去”[22](P14)。
江西教育及科举进仕的文化传统成为江西的一大地方特色文化,这一地方性文化特征投射到民俗中,则使得魁星也很自然地成为江西傩神信仰中的一个神灵。傩舞跳魁星尤以抚州地区为甚。抚州地区素有“才子之乡”“文献之邦”的美誉:“旧志云,地无乡城,家无贫富,其子弟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23](P814),其人“好古务学,崇礼尚贤,科名辈出,蜚声仕籍”[24](P310)。晏殊、晏几道、曾巩、王安石、陆象山、李觏、汤显祖等历史上的文人政客均为抚州人。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抚州傩仪成为一个崇尚儒道、礼于诗书、遵循周礼旧制之汉族族群文化历史记忆的载体,魁星面具亦成为傩神的象征接受人们的供奉,跳魁星几乎成了抚州南丰县、乐安县、崇仁县等各乡村傩舞表演的一个固定节目。在傩舞表演中,魁星会不时向观众点笔,据说被他点中的定会金榜题名,成就仕途。“魁星”面具和跳魁星不仅体现了江西傩仪的地方文化特色,更是历代汉族崇尚礼制,读书博取功名,积极进仕科第之汉族文化人生观的投射。
与表征着汉族族群文化属性的魁星崇拜相同的,则是江西傩仪中普遍存在的“和合”神崇拜与“跳和合”傩舞节目。据《建昌府志》载,“小儿辈戴面具戏舞于市,似古傩礼”,指的便是“和合”。“和合”神在民间有着诸多的传说,然而其观念意识却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和”“合”二字首先被发现于甲骨金文之中,先秦时期,“和”被赋予了“合”的含义,从而出现了完整的“和合”概念。“‘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联合、融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24](P1)以后,和合观念被春秋各派思想家征用,并在历经各代思想家的阐释之后衍变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江西傩仪中的和合舞则是这种大传统思想融入江西地方文化并从当地傩俗中投射出来的。江西有着各具不同象征意义的和合舞节目:有象征夫妻和谐恩爱的三坑、神岗《和合》舞,文武双全的罗家堡《和合》舞,祈神赐福禄财喜的上甘、水北、广昌《和合》舞等。江西傩戏的和合舞大多表达了江西乡民和谐喜庆的朴素生活观,恰如水北村和合舞所祝福的,“读书者,聪明智慧;求功名者,早登金榜;做生意者,一钱为本,万串为利”。这和江西以外其他地方汉族民间年画《和气致祥
一品当朝》、《和合二仙 状元及第》、《赐福财神》、《端阳庆喜》中的生活寓意并无二致,正所谓“愿世间和万象之新,合一元之气,并和气而保福禄财喜,合理而升公侯伯子男”[25](P788),反映了汉族文化的传统生活理想。
由此,无论是从功能结构还是从傩神信仰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观念形态来看,江西傩戏本质上是汉族族群文化的具体化形态,是汉族族群记忆的具体承载方式。显然,江西傩戏所表征出来的汉族族群文化是汉民族主流文化向江西民间社会的投射和延伸,亦是江西文化调适于自身的一种民间表达,体现了汉族族群文化在江西民间文化上的传承和融合。江西傩戏汉族族群文化特性的研究无疑能够丰富我们对汉族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注释:
①该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江西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dfrkpcgb/。
[1]南丰县金沙余氏族谱[Z].清同治版.
[2]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J].燕京学报,1936,(20).
[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周礼注疏 [A].十三经注疏[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吴其馨.吴氏重修族谱·乡傩记[Z].清光绪十八年版.
[6](清)狄学耕等修,黄昌蕃等纂.都昌县志[Z].清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7](清)徐家瀛,舒孔恂.靖安县志[Z].清同治九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8]刘洪辟修,李有鋆等纂.昭萍志略[Z].民国二十四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9]陈志华.流坑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10](汉)王充.论衡(卷二十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礼记正义(卷十六)[A].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瑞)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4]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5]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6]Michael Herzfeld.Anthropology: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1.
[17]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8](明)严嵩原修,季德甫增修.袁州府志(风俗卷一)[Z].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19](清)孟炤等修,黄祐等纂.建昌府志(风俗考卷八)[Z].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20]余悦.江西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2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22]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赣文化研究[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3](清)童范俨等修,陈庆龄等纂.临川县志(风俗卷十二)[M].清同治九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24]杨建华.中华早期和合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5]戏剧四种[A].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