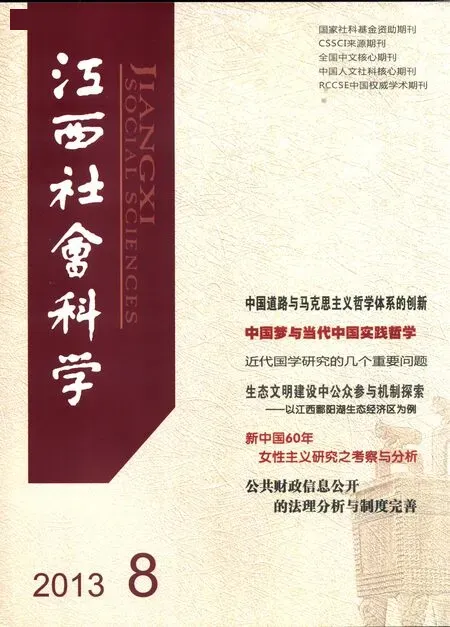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及其当代启示
■邓美英
友爱问题在古今中外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友爱问题经历了从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蜕变为一个边缘性概念、再重新兴起的历程。[1]亚里士多德在幸福的框架内探讨友爱,从友爱的角度去寻求幸福的答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思路:在共同生活中,朋友如何能够成为“另一自我”;友爱就是自爱,从自爱到友爱,友爱从自身的德性达到了对他人的德性;“与他人同生者”,友爱使幸福更完满。
一
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幸福。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2](P1)称之为善的幸福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作为一种合乎德性的行为选择,幸福当然是在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看起来幸福也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正如我们所说,赤手空拳就不可能或者难于做好事情。有许多事情都需要使用手段,通过朋友、财富以及政治权势才做得成功。”[2](P15)
把友爱列为获得或想要获得善的人必备的东西之一,是亚里士多德最具智慧的地方。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德性的事情;或者说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谁也不会愿意去过那种应有尽有而独缺朋友的生活”[2](P163)。幸福高尚的生活不能没有朋友,在各种类型的人之间都存在:“那些富有的人和大权在握的人最需要对朋友的惠赠,保全其财产。人在穷困和其他的灾难之中只能指望朋友的帮助。对青年人可以帮助他少犯错误,对老年人则可以加以照顾,帮助他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对壮年人则帮助他们行为高尚。”[2](165)友爱在人们的生活中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富人、穷人,或者老年人、青年人都离不开朋友,他们因为有友爱而过上幸福的生活。与作为德性与幸福的联系的其他外在的善不同,友爱自身就是德性,或者包含着德性,这显然使友爱成为联系德性与幸福的更本质的环节。
《尼各马可伦理学》全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论证,即在探讨幸福、德性、公正之后,用两卷篇幅来详细谈论友爱,最后又转向对幸福的探讨。看来,如果缺少了友爱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是不完整的。如果将伦理学只局限在个人的德性范围之内,也不可能构成一种完整的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把友爱看成是连接幸福、德性与公正的桥梁,正如学者厄姆森(J.O.Urmson)所说:“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关于友爱的两卷在理论上似乎是单独考察人的幸福的伦理学与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考察人的幸福之间的桥梁,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其他部分忽略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对于人的幸福的重要性,关于友爱的两卷似乎是在对这一疏漏作必要的补救。”[3](P261)其实,亚里士多德不仅仅是补救,而是非常关注友爱,对它的讨论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友爱的讨论,标志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旨趣真正转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
二
古希腊的“友爱”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友爱”的意义有着很大的区别。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友爱”一词,它包含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学者指出:“苗力田说他在译亚里士多德这本名著时也为如何译这个词费了许多心力。他是由希腊文译的。英语中friendship和德语里die Freundschaft在希腊文是Philia,中文通常都译作‘友谊’。但是在希腊文里,它原是从动词Phileo(爱)变化来的,所以本来有着‘爱’的意思。因‘爱’,人们才成为‘朋友’,于是philos(由动词变来的形容词或动名词)既是‘爱’也是‘成为朋友’的意思。因此苗先生认为,对于我们通常译为‘友谊’的Phili(friendship,die Freundschaft),还是译成‘友爱’要更合适一些,可以把其中的‘爱’的意思表达出来”[4]。这种包含了丰富“爱”的情感和“爱的”行为的友爱思想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正如不同的活动追求不同的善,不同的友爱必然也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友爱分为三类,其数目与可爱的事物相等。每个人在相互之间都有毫不掩饰的友爱,相互爱着的人们都希望对方过的好,他们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朋友。有些朋友是为了有用,而不是为了自身而相爱,对他们相互之间都产生好处,同样有些是为了快乐而相友爱,人们愿与聪明的人相交往,并不是为了他们自身,而是为了使他们愉快。”[2](P166)这三种类型的友爱分别是德性的(善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为了快乐和有用的友爱都是利己的友爱,例如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友爱。青年人因为快乐需要友爱,老年人因为利用需要友爱,这两种都是较低层次的友爱。德性的友爱是最高级别的友爱,因为“善良者的友爱是完美的,而且在德性方面相类似。他们互相希望在善上相类似”[2](P167)。只有真正的“德性的友爱”是利他性的,体现了在交往中能够秉持相互尊重和协商合作的精神。对友爱三种类型的划分,为进一步探讨友爱实践提供了一种范式。友爱在不同关系、不同政体、不同群体等方面的运用也就有所不同。
三
从德性的友爱来看,友爱就是自爱,它与只追求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我们所说,道德的爱却保持其自身,始终如一。”[2](P187)如果我们以幸福高尚(高贵)的生活为标准来判断各种友爱价值,那么结论就应当是:在德性上相近(同类)的好人之间的友爱最能帮助我们实现这种生活。“人们说,一个人应该爱他最好的朋友。而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个希望对方就其自身而善的朋友,即或并没有他人知道。这种情况,在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时候最经常出现,用来规定朋友的全部其他属性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一切与友谊相关的事物,都是从自身而推广到他人。……因此,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最好的朋友,人所最爱的还是他自己。”[2](P199)自爱在人之生活的省察中表现为人性之爱。自我在社会中不断与他人接触,与他人共同生活中得到强化。“爱将交往双方统一起来。自我通过他者获得自身的实存。因而将自我与自身的内在关系经由他者的中介达成一种同一。”[5]
作为德性的友爱,基本的问题是实践:某人通过与另一人做朋友而成为朋友,正如通过做勇敢的事而成为勇敢的人。友爱更多地是在爱之中,而不是在被爱之中。“一种强烈的友情就是如同对待自己一样的关怀。”[2](P193-194)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完整的友爱即德性的友爱需要祝福、行善于朋友,并且只是为着朋友之故。所以,他说:“事实上善良的人,总是为了朋友,为了母邦而尽心尽力,必要时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他鄙弃金钱、荣誉,总之那些人们竞相争夺的东西,为自己他只求得高尚。”[2](P201)他只需要和朋友在一起,通过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善而获得幸福。看来,我们选择朋友,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完善我们自己。“因为朋友们都是同类相聚,近朱者赤。”“对邻人的友谊,以及对友谊的规定,似乎都是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自身。”[2](P192)从他者的角度,我们认识了自己,也照亮了自己的德性或善。真正的自爱,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与他人相互关系的观念,也提供了尊重正义的基础。
在德性的友爱中,朋友成为“另一自我”。当我们开始思索“朋友”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构成单纯的人与他人关系的割断。但正是这种割断能更深刻地揭示在自我与他人结成关系层面上的“他者的存在”。良善的朋友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也以善良人自身的这个样子选择这种朋友。“自我”是无法获得确证的,必须通过他人,正如黑格尔用“他者的他者”这种形式规定自我:“自我是自我本身与另一个对方相对立,并且统摄这对方,这对方在自我看来同样是只是它自身。”[6](P115-116)但自我意识“被表明为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和它的对象的对立被扬弃了,而它和它自身的等同性或统一性建立起来了”[6](P117)。“自我”和朋友之间已经没有了障碍,“由于善良人对自身都是这个样子,他对待朋友也正如对待自身(因为朋友就是另一个自身),而在朋友那方面也是如此,这一切也就是作为朋友所应真实具有的。”[2](P193)我们从朋友中各取所需,朋友从我们中也各取所需,从而满足了各自追求幸福的需要。
德性的友爱,将对待朋友的善与对待自己的善统一起来。从朋友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在共同生活中友爱成为高尚的选择。“善良者的友爱是完美的,而且在德性方面相类似。他们互相希望在善上相类似。作为善的人他们都是就其自身而善的。那些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为善才最是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只要善不变其为善,这种友谊就永远维持。”[2](P167)朋友的作用在于朋友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说:“不论在思考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两个人都比一个人更有力量。”[2](P163)这种由己及人、推己及人的友爱,非常强调相互关系对人自身发展和城邦共同体幸福的重要性。
因而,友爱在这两种情况下如何存在:“在幸运中,还是在不幸中更需要朋友呢?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寻求朋友。遭不幸的人期求援助,在幸运中的人需要陪伴,他们想做好事要求有接受好处的人。所以,在不幸中,有用的朋友更为必要,在幸运中高尚的朋友更为必要,因为在不幸中更为急迫,在幸运中更为高尚。”[2](P206)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生经历的不都是幸福之事,那么在不幸之时,也许我们更需要朋友的援助和支持。早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给了我们处理各种生活的答案。人们学会了如何才能不作为私人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公民来行动。
对于幸福之人来说,朋友当然是必要的。“把至高幸福,至福当作是孤独的,似乎荒唐,谁也不会选择单独一个人去拥有一切善。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这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他具有那些自然而善的东西,但还有和朋友在一起,和高尚的人在一起,这显然比和陌生人和偶遇的人在一起好。所以,幸福应该有朋友。”[2](P202)真正的友爱显得极为有意义:“一个极大快乐的短时胜过多日,一年的高尚生活胜于多年的平庸时光,一次高尚伟大的行为胜于多次琐碎活动。这样一些人经常地舍弃他们的生命,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光荣。他们肯于舍弃金钱,只要朋友们获利更多。因为,朋友所得到的是金钱,他们自己所得到的则是高尚,这样,就把最大的善分给自己了。”[2](P201)
由此看来,友爱从自身惠及朋友,又从朋友之处回归自身,由此完成了通向幸福之路的一个历程。
四
“朋友是另一个自我”用“自我与他人为同等主体的关系方式”置于城邦生活的最基础部位,体现了“与他人同生者”[7]的最基本的伦理品德。共同生活是人类的特点。“因为友谊就是共同性,怎样对待自己,也怎样对待朋友,对自己感到存在令人欣慰,对朋友感到存在同样令人欣慰,而这种感觉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现实活动,所以人们自然要追求共同生活。这种生活,或者与每个人的存在相关,或者与生活的选择相关,人们都愿意与朋友共同度过。”[2](P208)在共同生活中产生友爱,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对待朋友的善与自身的善在共同生活的统一体中展示出来。友谊“由于接触而增长。他们在现实活动中,在相互促进中变得越来越好”[2](P209)。因而友爱和友爱的事物总是属于实践者的。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雅典民主制开始衰落,城邦内部出现各种危机。为了挽救雅典城邦统治,他提出了理想的城邦概念。他认为,城邦有好有坏,好的城邦不止是存在,而且是为其公民的好生活而存在。城邦是由好公民之间的友爱维系的。所以,造就好城邦的第一位问题是造就好公民。一个好城邦的直接表现就是:人们懂得友爱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在政治群体中直接表现为好公民与好公民之间的关系。
由于公民在社会实现活动的过程中,不可能单独承载自己的社会活动,必然由友爱承载自己的事情。况且,从人的自然本性来看,在人的天性中似乎也存在着与自己的类共同生活的习惯。共同生活使人们养成相互的熟知性和情感的亲密性。“在所有的公共团体内,我们都可发现友谊与公正。在一条船上的旅人、在同一队伍中的士兵都成为朋友。”[2](P176)爱也许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友爱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它在全部群体中存在。“任何共同体都需要它的φιλια(友爱)作为维系的纽带,正如古老的氏族部落成员关系是那种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一样,公民的φιλια(友爱)也是新的城邦共同体的联系纽带。”[8]
友爱成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代名词。“友爱把城邦联系起来,与公正相比,立法者更重视友爱。”[2](P164)在城邦最初的建立时期,完全依赖友爱的力量。因为友爱比公正更具有团结的效果。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就把友爱与政治的关系联系起来,在希腊城邦社会中凸显政治友爱的作用: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是同一的,因而公民需要作为个人较多参与城邦公共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公民之间会相互结伴,而结伴就意味着两个人之间在家庭之外的更多的交往,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友爱——“与他人同生者”的伦理品德。而“自我”进一步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
友爱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基石,对城邦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一种巨大的促进。政治群体为了全部共同福利而开始,并由此得以维持,它不同于只是以部分利益为目标的其他群体。“水手们就是为了赚钱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进行航海活动。军队就在于去进行战斗、劫掠、取胜和破坏活动,那些氏族成员和居民也是这样。”[2](P177)作为城邦社会的凝聚剂,友爱的两种作用非常明显:一是使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团结,二是使公民之间的仇恨得以消除。尤其是友爱能超越差别、消解矛盾,避免各种猜疑和纷争,使公民之间关系的极端化走向公民之间关系的调和与折中,引导和规范城邦社会人际关系向理性方向发展,为城邦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城邦只有在公民与公民之间产生团结的力量时才能生存,而要能团结得紧密仅仅靠公正是不行的。“对公正的人却须增加一些友爱。所以在最大的公正中似乎存在着友爱的东西。”[2](P164)因为公正不能完全解决城邦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的纷争,利益纷争产生的内讧有可能毁掉城邦。只有在城邦中所有公民之间的友爱、所有人之间的友爱,才是真正的团结和真正的公正,才能给城邦秩序以牢固的生存基础和力量。随着城邦社会的巩固,友爱与公正开始并驾齐驱。“随着友情的增加,对公正的要求也同时增加。”[2](P177)
在共同生活中,“自我”与“他人”作为公民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展示出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之友爱伦理。但从更广泛的领域来看,人更是文化动物。对贤哲的尊敬、对父亲的崇敬、对长辈的敬重、对伙伴和兄弟的坦诚相待,祸福与共,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是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讨论,已经实现了从自我的伦理学到人际关系的伦理学,从个体德性的伦理学到人际伦理的伦理学转变。“看起来在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伙伴和同学之间这都是不相同的。”[2](P182)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该首先自己主动地实现自己或出于意愿 (善意)或出于习惯的爱的行动,它并非出于偶性的实践,而是持存在两人相似的共同生活境遇之中”[9]。因而我们理解至福之人,“与他人同生者”,只有在现实共同生活中,在社会关系和交往当中,才能真正过拥有善、拥有完满幸福的生活。
五
建立在道德一致性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已经无法解决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友爱问题。麦金太尔曾指出:“亚里士多德自足的理想人格严重损害和扭曲了他对友谊的阐述。”[10](P120)正是希腊贵族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对朋友类型的看法。“适合于一定的社会生活这一背景画面中的一定的角色或功能,这种善的观点总不得不以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为前提。”[10](P203)所以,像奴隶、“野蛮人”、妇女、小孩子和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都属低贱之物,这样的友爱是不能支持一个好城邦发展的。因此,作为“另一类友爱”,如父子、夫妻、长幼、君臣之间的友爱,是“包含着不平等”关系的友爱。这些关系彼此各不相同: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不同,夫妻关系与父子关系也不同。这类爱的特点是,其中每一种和每一方的德性和作用都不同,并且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相爱。“尽管朋友对方有着很不平等之处,但可以使之平等,成为朋友。其中,平等和相同性至关重要,它们自身的坚定性就保证互相间友谊的持久。”[2](P175)虽然对于各种不对等的友爱,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是各取所值,并不是不公,也不是不等,但对这种友爱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却缺乏深入讨论。为什么这种从属关系的友爱会是持久和良好的?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似乎对此不屑一顾。
友爱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行为,而“对于亚里士多德,一个人与他人有关系的活动,最终不过是达到这种沉思活动的一种辅助性活动。人也许是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但他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不是最主要的活动”[10](P124)。虽然亚里士多德也在某些方面(如政治领域)比较强调友爱践行,但是作为极少数有闲人的代表,他的理论变成了在为一种非常狭小的群体做辩护。亚里士多德将友爱看成“在创造和维持城市生活的共同计划中的共同分享一切,一种在个人特殊友谊的直接性中的共同合作”[11](P196)。但是,因人类共同体的范围无限广大,利益关系纷繁复杂,友爱怎么可能会在不同民族、种族、社会、文化、性别等方面共同分享一切呢?在今天,没有限定性的人类共同体友爱也只能剩下一具空壳。友爱在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也明显不同于希腊城邦时代。况且,将友爱永远停留在道德上的相互尊敬,表现出来的也只是亚里士多德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这个具有伟大心灵的人的理想社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呢?”[10](P120)因此,建立在希腊城邦制基础之上的友爱历史局限也就在所难免。
黑格尔曾言:“我必须以理智来爱他;非理智的爱也许比恨对他更为有害。但理智的、本质的善行,在它最丰富和最重要的形式下,乃是国家的有理智的普遍善行;与国家的这种普遍行动比较起来,一个个别的人的个别行动根本就显得缈乎其小,微不足道。”[6](P282)所以,“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也仅仅就是一条著名的戒律。没有强制限制的友爱,与法的普遍性相比,它适用的范围当然也就仅仅是作为一种狭小地域范围内的道德戒律。
亚里士多德建立在希腊城邦统治上的友爱论,似乎难以全部用于今日社会生活中,但是,他对友爱的理想描绘却为追求人与人之间良善的思索和实践留下了空间。在现代生活节奏紧张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似乎难以体味友爱的温情。重温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无论是在体味自身、朋友、家庭、国家之间的温情,还是为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国与国之间的仇恨,都提供了友爱德性之美——通向幸福之路的无限魅力。
[1]陈治国,赵以云.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研究的觉醒与演进[J].哲学动态,2012,(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杨适.“友谊”(friendship)观念的中西差异[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5]陈良斌.启蒙现代性叙事与黑格尔的承认哲学[J].江西社会科学,2012,(7)
[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日)熊野纯彦.自我与他者[J].龚颖,译.哲学译丛,1998,(4).
[8]廖申白.友爱在希腊生活中的意义[J].河北学刊,2000年,(2).
[9]王青元.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人际和谐思想[J].道德与文明,2008,(3).
[10](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