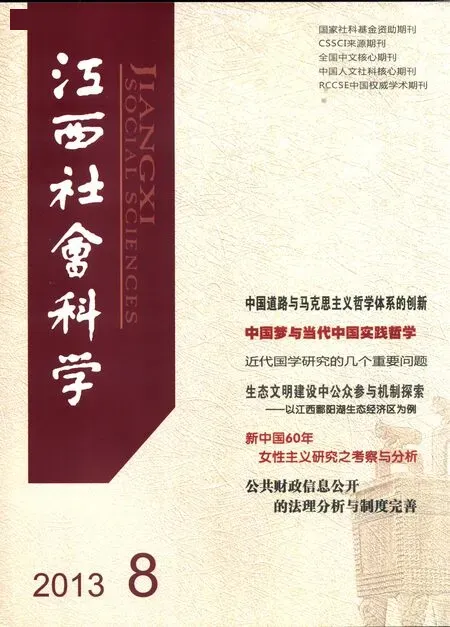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流行音乐的价值叙事——以阿多诺的音乐美学为参照
■贺晓蓉 陈德志
20世纪70年代末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大陆,它所带来的除了新鲜感觉外,还有巨大的冲击力。反对者说它是资本主义的毒品,支持者则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良药,对立双方分歧严重,火药味十足。但不管怎样,流行音乐在大陆逐渐生根、发芽。人们对它的态度也慢慢发生转变,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把流行音乐视作社会改革的力量,也不会有人对流行音乐感到恐惧。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态度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如何看待新时期以来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流行音乐在这急剧变化的三十几年里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本文尝试结合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与流行音乐三十年的价值叙事诉求,来透视这些问题。
一、阿多诺:以社会现实为参照评判音乐的价值
阿多诺在他的《新音乐哲学》中比较了两个音乐家,即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是德国表现主义音乐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充满痛苦、扭曲的情绪和不协调的声音。听这种音乐,并不能获得愉悦的感官享受,相反,会给听者以强烈的刺激,迫使听者去思考造成音乐中痛苦的原因,进而得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斯特拉文斯基是新古典主义乐派的代表。他的作品倾向于采用神话传说等古典题材,远离现实生活的情境。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试图传递给听众的是一种“同一化”的思想,它以集体、种族的名义来牺牲个体的自由。在阿多诺看来,勋伯格的音乐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否定性”反映,让音乐干预社会历史,具有“进步的”价值,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却脱离了现实,让人沉溺于虚幻的同一性假象中,是“倒退”的。
阿多诺对音乐的“否定性”要求,显示了他与康德美学的对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美的“四个契机”,对艺术做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其中之一是:美是不涉利害关系的愉悦性。[1]康德认为艺术属于独立于理性知识和道德实践之外的感性领域。这是一个自律的王国,不能用理性的概念或道德的准则来干预艺术。人们在艺术王国中感受到的是审美的愉悦。阿多诺完全不赞成康德的“艺术自律说”和“审美愉悦说”。针对艺术自律论,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自律原则本身也是一种慰藉,因为在声称能够假定其自身具有一种非常完整的总体性的同时,艺术自律原则不管愿意与否,均会造成一种假象,使人以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2](P3)针对审美愉悦论,阿多诺认为这是一种审美享乐主义,是一种伪装出来的假象,“在康德那里,我们看到艺术欣赏往往披着无利害关系的伪装,这种伪装使欣赏变得难以辨认”[2](P22)。阿多诺对艺术欣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艺术欣赏不是沉迷于一种虚幻飘渺的快感之中,而是要从艺术中获得对现实的一种认识、判断。审美愉悦论是对现实的逃避,违背了艺术的否定本质。在真正的艺术欣赏中,“艺术作品真正要求我们的是认识,或者说得好听一些,是公正判断的认知能力;作品要求我们意识到其中的真伪”[2](P27)。
作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始终把艺术与社会存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把艺术作为自律的王国,独立于社会历史环境是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幻想,艺术总是与社会历史发生关系。对音乐等艺术现象价值的判定需要以社会历史为参照系。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思考也是如此。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总结批判了流行音乐四个特点:标准化、伪个性化、导致听者听力涣散以及充当社会粘合剂。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流行音乐提供有益的参考,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在两个方面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非常相似,一是大规模的工业化,二是流行音乐作为一个重要的新事物出现。阿多诺坚持从音乐与社会的张力关系出发来评价流行音乐,这也是我们看待新时期中国流行音乐恰当的视角。
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流行音乐的价值叙事与身份变化
(一)抒情叙事——意外的“先锋”
20世纪70年代末,港台流行歌曲开始进入大陆,以邓丽君、侯德建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或其作品以迅猛的势头席卷大陆。在它的影响下,诞生了李谷一、程琳等一批内地流行音乐歌手。就歌曲的内容来说,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大陆本地音乐人创作的,绝大多数都是抒情歌曲,其中又以爱情歌曲为主。如邓丽君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些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我只在乎你》以及翻唱三四十年代的歌曲《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几乎全是轻柔甜腻的“恋人絮语”。对于听惯了革命歌曲的大陆听众来说,这种轻松舒适的抒情叙事带来巨大的感官享受,使得抒情叙事成为那一时期流行音乐绝对的主题。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最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几十万群众来信参与评选,结果选出《金梭和银梭》、《月亮走我也走》、《难忘今宵》等十五首歌曲,这十五首歌曲无一例外地都是抒情歌曲。
对于这种急剧的变化,一些人开始接受不了,对流行音乐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批判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流行音乐表演方式的“看不惯”。流行音乐在演唱方法上与美声和民族唱法有很大差异,它大量使用气声,显得有气无力,舞台表演夸张、激烈,这些与刻板的革命歌曲形成强烈的反差。习惯了革命歌曲的人难以接受流行音乐的表演方式,有人蔑称之为:“每歌必嗲,每唱必啃,每演必扭。”二是对流行音乐的定性批判。把流行音乐归为旧中国“靡靡之音”的死灰复燃,或归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腐朽音乐。“港台‘时代曲’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三十年代靡靡之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二者是一脉相承。”[3]流行音乐“是音乐生活中的一种污染,是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化、商业化、庸俗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它和我们的文艺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陶冶高尚的情操等方面的原则背道而驰”[3]。三是痛斥流行音乐带来的不良影响,认为流行音乐的低俗、空虚会腐蚀人们的心灵。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周扬说:“港澳的流行歌曲,很多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我们的作曲家和歌唱家当然不应当受它们的影响。”[4]周扬的话代表当时官方对待流行音乐的基本态度。
流行音乐在进入大陆初期之所以所遭受如此猛烈的批判,是因为它太具有破坏性,从表演方式到思想观念都构成对当时主流音乐文化乃至主流社会文化的“否定”。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流行音乐具有了阿多诺所说的“严肃”音乐的品质,充当了一种否定社会现实的工具。当邓丽君的“轻、柔、低、绵”取代了红色革命歌曲的“高、强、响、硬”,当“爱情柔情”取代了“革命激情”之时,流行音乐无意中充当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先锋。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抒情叙事本身并不具有“否定性”的内涵,大陆流行音乐与其他地方的流行音乐并无本质的不同。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否定性”只是一种被动的“否定”,其先锋者形象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错位造成的。流行音乐抒情叙事的破坏者角色也必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回归原位。
(二)非理性叙事——负面情绪的“宣泄者”
80年代中后期,流行音乐开始自觉地对社会、历史和文化展开反思,其中的代表性音乐现象是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尤静波在《中国流行音乐通论》中说:“随着摇滚乐的兴起,内地流行音乐开始体现出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它的触角开始触及到了对社会、对文化的思考。”[5](P202)1986年在第一届“百名歌手演唱会”上,崔健演唱了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歌词的叙事具有强烈象征意味。在“一无所有”的声嘶力竭的吼叫中,有对嘲笑者的反抗,对前途的迷茫,对孤独的感伤,对理想的困惑。这是一种反抗,却是非理性的反抗,没有旗帜,没有方向,没有计划。它表达了一种否定的情绪,这种情绪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能让观众的疯狂。这首歌后来被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收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七卷)》,作为一种经典艺术形象被肯定。1989年崔健出版了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专辑的第一首歌《新长征路上》也充满了非理性的否定色彩:
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这首歌虽然以“长征”这一革命主题为叙事对象,但它所叙述的长征既没有《十送红军》里的“军民鱼水情”,也没有《长征组歌》里的“雄心壮志”,有的只是一种迷惘、困惑、前途未卜的心绪的表达。歌曲叙述的重点不再是决心和胜利,而是如何找到自己,从宏大的理性叙事,掉入到琐碎的非理性的自我叙事中。从1987年到1989年,中国先后成立了“黑豹”、“ADO”、“唐朝”、“状态”、“1989”等多支有影响的摇滚乐队,至于不知名的摇滚乐队则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在那个时期集中爆发,声嘶力竭的呐喊扯下了流行音乐一直以来温情缠绵的面纱,把人们心底和社会阴暗处一些真相揭露出来。但与此同时,摇滚乐也遭受到最猛烈的批判。
陈志昂的《流行音乐在批判》首先对摇滚定性:“从80年代中叶开始,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流行音乐的倡导者们转而求助于西方的摇滚乐,来表现一种狂躁的情绪、歇斯底里的心态、玩世不恭的‘痞子精神’。”[6](P35)之后又进一步指出这种非理性的音乐具有极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最危险的是摇滚乐以其非理性的狂乱节奏与粗野音调,使听众丧失理性,陷入盲目的冲动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导致暴力和恐怖主义”[6](P36)。
给摇滚乐冠以“非理性”的帽子,加上“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罪名,是一部分人对摇滚乐的破坏性害怕的表现。但事实上,尽管摇滚乐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但并没有达到毒化人心、煽动暴力的程度。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因为听摇滚乐而发生的恐怖事件。相反,在90年代,摇滚乐的风潮就逐渐平息下去了。
从阿多诺的理论来看,这是必然的。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无法承担严肃音乐的“否定性”重任,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流行音乐以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也只是一种“伪个性化”的表象。它通过释放人们似乎很独特的要求来消除隐患。此时流行音乐真正发挥的是弥补社会裂痕、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阿多诺称之为社会“粘合剂”。阿多诺将之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节奏型”,一种是“情感型”。在节奏型中,人们的个性特点因为标准化的节奏而被统一化,对节奏的认可逐渐地使人认同被标准化,从而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反抗的动力。在情感型中,流行音乐通过宣泄人们的情感来弱化人们的斗争意识。“流行音乐是大众的宣泄工具,不过宣泄却使得人们整齐划一。流泪的人不会比行进中的人更能坚持反抗。流行音乐正是通过让听众承认他们的不幸的‘宣泄’方式,来调和他们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7](P462)流行音乐的非理性就属于情感型一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在80年代后期日益尖锐,社会上普遍存在一些不满情绪,摇滚乐恰好在这个时候兴起,它以非理性的叙事话语,公开地扮演了人们心中的反抗者角色,并以疯狂的演唱为人们负面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摇滚乐表面上看是在否定和批判,而实际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三)民族叙事——民族精神的“宣传者”
流行音乐的抒情叙事和非理性叙事自觉或非自觉地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因此受到激烈的批判,被扣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批判的顶点是1989年8月开展的全国范围内图书、音像市场整顿,控制流行音乐的出版发行。从流行音乐进入大陆之时起,就有人思考如何驯服这个外来的异端。主流的意见是控制加引导,使流行音乐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在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上的讲话是这种声音的代表,“我们应该重视流行音乐作品的思想性,善于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手法,表现我们所要提倡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操,‘寓教于乐’,使作品具有催人奋发向上的力量”[8]。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学院派人士的赞同。蔡仲德说:“今天的中国流行音乐品位较低,从创作、表演到欣赏都是如此,与世界优秀流行音乐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因此我们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而应进行引导,加以提高。”[9]1988年《音乐研究》编辑部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共同召开关于流行音乐的座谈会,对于流行音乐,与会的大多数专家的态度是:流行音乐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要对它加以引导,使流行音乐高雅化。[10]
对流行音乐改造的重要途径是民族化,将流行音乐价值叙事的中心从“低俗”的情感与“非理性”的疯狂,转化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上来。在民族化的引导下,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大陆出现了一大批以民族叙事为核心的优秀流行歌曲。第一波民族化的浪潮是1987-1988年流行的“西北风”歌曲,出现了像《信天游》《黄土高坡》、《少年壮志不言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以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民歌为创作素材,曲风粗犷、浓烈,歌词以刻画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形象为重点,如“黄土地”、“月亮”、“故乡”、“酒”、“粗糙奔放的乡土爱情”等。他们比“D味歌曲”(邓丽君风格歌曲)强烈刚劲,又比摇滚歌曲积极理性,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
90年代以后,民族化的创作一直持续不衰,出现了一大批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为叙事主题的歌曲。如《东方之珠》(1991)、《满江红》(1993)、《涛声依旧》(1993)、《纤夫的爱》(1994)、《大中国》(1995)、《中国人》(1997)、《中国功夫》(1997)、《精忠报国》(1999)。这些歌曲或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如“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或是表达对种族身份的认同,如“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或是表达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敬仰,如《满江红》直接以爱国英雄岳飞的词入曲,《涛声依旧》则化用了古诗《枫桥夜泊》的意境;或是表达民间生活的甜美幸福,如“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这些歌曲所传达的价值诉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听者往往为之激动神往。
对于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精英人士引导的结果,它同时也是流行音乐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向。从阿多诺的理论来看,流行音乐的首要特征是标准化,流行音乐并不能承载挑战社会既有秩序的重任。“流行音乐整个结构就是标准化。即使那些预防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是标准化的。标准化存在于流行音乐最一般的特征中,也存在于其最特殊性的方面。”[7](P439)流行音乐的标准化本性要求流行音乐必须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要求,找到满足各方诉求的共同点,并通过强化这些共识来巩固扩大自身的影响。所以在流行音乐进入大陆后,音乐人就一直在探索能够为绝大部分国人接受的流行音乐标准,民族化是这种探索自然的结果。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叙事,调和了流行音乐与官方弘扬主旋律的要求以及精英阶层高雅品味之间的对立,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到了合法性的基础。至此,流行音乐已经摆脱了异端身份,成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渠道,成为消弭社会裂痕、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工具。
(四)国家叙事——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民族叙事使流行音乐获得了稳固的社会地位,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进一步发展。如周杰伦的“中国风”系列歌曲:《爷爷泡的茶》(2002)、《东风破》(2003)、《发如雪》(2005)、《菊花台》(2006)、《青花瓷》(2007)、《兰亭序》(2008)。这些歌曲在两个方面具有极强的民族色彩。一方面,它的意象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形象,如“茶”、“菊花”、“青花瓷”、“兰亭序”。这些形象很容易使人产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联想。另一方面,它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文言化语言,有些歌词甚至直接摘录古诗词入曲,强化了作品的民族色彩。不过,这些歌曲又与90年代有明显不同,它们在曲风上有着显著的西方色彩。周杰伦的中国风乐曲,大量采用R&B节奏、现代唱法等西方流行音乐技巧,使这些歌曲听上去具有很强的西方流行音乐印迹。这种中西结合的做法让歌曲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既古典又前卫,既像中国的又像西方的。这些矛盾性因素的糅合,体现了创作者也是社会对流行音乐的一种诉求:即以世界为参照,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周杰伦的中国风歌曲有一个隐含的叙事对象——西方,在中西方元素强烈反差的糅合中,显示出中华文明虽然古老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其他一些歌曲中,国家叙事倾向更加明显。有两首歌可为代表,一是由郑楠作曲,施人城、郑楠作词,S.H.E.演唱的《中国话》,另一首是小柯作曲,林夕作词,百名群星演唱的《北京欢迎你》。这两首歌曲中,叙事的听者已经不再隐约存在,而是被别明确指出来——“你”,即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国话》叙述的是中华文化的走出去,《北京欢迎你》叙述的是欢迎外国人走进来。这一“出”一“进”,显示出的是一个自信、包容、强大的中国形象。新世纪以来,中国入世,申奥成功,经济奇迹持续,文化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中国人的自信心增至历史最高点,这些都使得人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放眼世界。90年代流行音乐民族叙事主要还是面向国内和华人群体,凝聚他们的爱心、热心,共同为民族复兴奋斗,而到了新世纪,民族化叙事的重点由内转向了外,担负起国家叙事的重任,成了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三、结语
阿多诺对音乐理解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阿多诺的出发点是社会历史语境,人类所有的事业——就此而言,尤其是艺术,更具体地说是音乐——都要在这一语境中被审视。”[11]阿多诺一直强调把音乐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才能认清音乐的本质,才能客观地评价一种音乐现象或一个音乐作品。对于新时期以来流行音乐在大陆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三十多年来,大陆流行音乐价值叙事诉求不断发生变化,从情感的抒发,到非理性情绪的宣泄,到民族精神的表达再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它所扮演的角色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外来的“异端”,到非理性的“宣泄者”,到表达民族精神的“宣传者”,再到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流行音乐价值叙事的阶段性变化,既是流行音乐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才导致了流行音乐价值叙事的变化。流行音乐在每一阶段的主导叙事诉求都与相应的社会语境相一致。流行音乐的身份几经变化,但它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必须要服从于社会现实和主流的社会文化,这也是中国流行音乐未来发展所必然要遵循的规律。
[1]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瞿维.关于“流行音乐”的对话[J].人民音乐,1981,(8).
[4]周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J].人民音乐,1980,(6).
[5]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通论[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6]陈志昂.流行音乐再批判[J].人民音乐,1990,(5).
[7]Adorno, Theodor W.“On Popular Music”Essays on Music.Susan H.Gillespie,Tra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8]朱小丹.在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上的讲话[J].人民音乐,1994,(7).
[9]蔡仲德.我看流行音乐[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3).
[10]赵沨,祖振声,等.谈流行音乐[J].音乐研究,1988,(2).
[11]Mitchell, Anne G.and Wesley V.Blomster.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New York,London:Continuum,2002.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