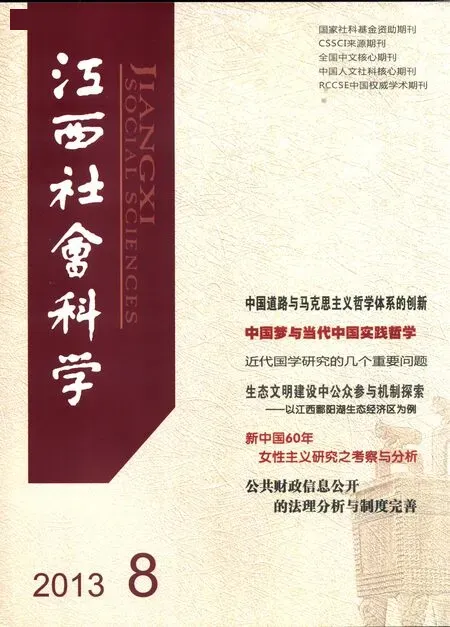元代色目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失语现象
■秦 琰
“色目”是元代极具特色的社群。它泛指除蒙古、汉族之外的西北、西域乃至欧洲各族人士。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目民族包括汪古、乃蛮、唐兀、回回、康里、阿速、哈剌鲁、畏兀、吐蕃、钦察等。[1](P6141)色目文学的创作主体就来自于这个民族归属、文明形态、地域范围、宗教信仰都十分复杂的群体。
从总体来看,以异族人为汉文汉诗是色目文学最显见的特征,“大量母语并非汉语的各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仅见的情况”[2](P4)。这意味着色目作家是双重文化的承担者,他们既携带有民族文化的传承印记,又吸纳接受地文化(汉文化)的基本因子,由他们创作的色目文学则是异质文化共生文学,它应当兼具色目自我文化与汉文化的品性。但是,当我们把色目文学置于元代总体文学观照时会发现,色目文学实际上所具有的文化品质与汉人文学别无二致。也就是说,异质文化共生文学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未清晰地呈现于色目文学中,色目文化传统在文学文本世界中是几近失语的。
那么,色目传统的失语有怎样的表现?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失语?色目文化与汉文化又形成了怎样独特的交往模式?本文将考察色目文学的民族文化失语现象及其形成原因,并由此解读汉民族与异民族的文化交通特性。
一、民族传统文化在色目文学中的失语
文学是文化承继的重要载体,而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色目文学来说,色目人原有的文化内核几乎没有明确的显现。
(一)文学品质的汉化
色目文人对文学的认知和利用与汉族文人并无差异,文学亦是他们借以言志、抒怀、讽谏、析理、互动的工具,并且他们遵循了与汉人相同的创作法则,这使得他们的文学无论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布局、意象的撷取、音韵的安排,还是整体的品质,都呈现出绝对汉式的风格。这一点在第二、三代以后的色目作家身上尤为明显。如贯云石,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心绪、情怀、感悟、思索等与汉族文人是一致的,比如他的组诗《咏梅》中的“谁人共听黄昏角,说与栏西未落花”、“砧韵敲寒惊楚曲,有人漂泊在江南”、“而今清瘦无消息,人与梅花总在南”[3]。“梅花”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学意象,诗人借“梅花”展现了自己内心的寂寥之情、漂泊之感,这与谢枋得、刘因等人将失国之痛、无根之忧倾注于“寒梅”意象的审美表达如出一辙。元代文学没有分明的夷夏之差。
(二)民族个性的趋同
色目文人无意于在文学中实现民族文化寻根,我们无法透过文本世界了解作者所从出的民族属性、民族生活、民族风情、民族文化重心等。虽然有一些色目文人在创作中也表达了对家园故土的怀想,如马祖常的《灵州》《庆阳》《河湟书事二首》等边塞诗,饱含着诗人对西域故园的深挚情感,被认为是最“没有边塞情结的边塞诗”[4](P335)。贯云石也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了怀恋故土的心绪,一首《秋江感》承载了诗人浓郁的乡愁。但这种家园意识始终附着于作家的思乡之情,并常常与作者所处的生活境遇纠缠在一起,它无法表征色目作家有了自觉的民族身份意识。实际的情况是,色目作家归属不同的民族,但他们的创作却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质——用汉人的方式言说汉人的思想,民族的个体性被挤压掉了。色目文学没有突出的民族之别。
(三)宗教意识的弱化
宗教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是构成一个具体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有信仰的民族来说,宗教往往是其民族特性的主要标志。但是,活动于中原的色目文人却淡化了自我信仰,甚至在文本中表示了对其他宗教形态的认同,元代的也里可温作家就是很好的例子。也里可温作家所信奉的景教是基督教的异端分支,但他们却没有坚守基督教的独一神信仰原则。他们在生活中与佛道人士往来密切,在作品中大谈佛道教理教义。如与马祖常同时的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就是马氏的好友,《石田文集》存有二人相酬答的诗歌共7首。在《石田文集》中,与佛教相关的诗文有5篇,与道教、道士相关的诗文共46篇,后者占全集的十四分之一。在金元素的《南游寓兴诗集》中,谈及佛教的诗歌有18首,涉及道教的有15首,其中一首《代答》:“镜体本自莹,浮云岂难除。譬以水濯衣,垢去衣复初”,已直接深入佛教思想内层了。现在所能看到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元代文学作品只有三种:一是元曲《东堂老》(这是张乘健先生的观点,是否成立值得商榷。);一是金元素的《寄大兴明寺元明列班》[5];一是围绕马黎诺里所献“天马”的诗文辞赋。其中,与基督教有直接关联的是金元素的《寄》。这首诗歌尽管描写了景教教堂的荒凉境况,但作者借以抒发的却是中国士大夫常有的怀古幽思之情。在也里可温作家的诗文作品中,读不到有关基督教信仰层面的信息。色目文学没有宗教意识的冲突。
(四)自我反思的缺失
色目文人普遍没有身份的焦虑感。对于身份焦虑,赛义德这样形容道:“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者’,是一个对立面,是迁徙与定居的几何图形上的瘕疵,是一个流放者。沉默和谨慎掩盖着伤痕,身体缓慢地摸索前行,慰藉着失落感和叮痛。”[6](P48)在色目文人留下的诗文中,我们看不到类似情绪的表达,也看不到色目人对自我身份的追问。如同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他们的情感波动只与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相关。他们会因民生凋敝而痛心,“兵甲何时息,予心日夜忧”[5];会因仕途不顺遂而失意,“明放着伏事君王不到头,休休,难措手”[7](P76);也会寄情山水间,以适意逍遥的姿态缓解内心的苦闷,“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7](P75)。但他们的内心全然没有身份危机意识,没有因处于异质文化中间地带生活而引发的挣扎、矛盾与彷徨。色目文学没有身份意识的困惑。
二、色目文化与汉文化的对话模式
卡冈认为,文艺(包括文学)是“形象——综合地表现文化的完整性,即文化的各个方面、因素、成分以及相互关系都能在文艺中体现出来”,“文艺能成为每种具体文化在同其他文化交往中的‘密码’,文艺对其他文化能起到‘解码’的作用”。[8](P341)因此,从整体文化结构入手,能效地推进有关文学本身的研究。我们认为,色目文学中的民族失语现象与元代异质文化交往模式相关。在元代,色目民族以让渡自我传统的方式全面接受了汉文化的熏染。
(一)对汉文化的绝对认同
绝对认同并自觉地依附,是色目族群接受汉文化的基本态度。对绝大多数色目民族来说,不断抛弃原有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汉化、伊斯兰化或蒙古化倾向,是他们共同的际遇,如廉氏、偰氏、马氏家族是以汉化为主的色目人家族,钦察土土哈家族则更多呈现出蒙古化的倾向,而生活于中亚地区的色目人已经完全伊斯兰化了。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汉化”问题。
元代色目族群对汉文化的认同表现出既自觉又主动的态度。蒙古人在中国本土发起的一系列战争使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儒士们流离失所,大量死亡,少数存留下的儒士或被驱为奴,或改务农、匠、商,所谓“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9]描述的即是战后汉地文化衰败的景象。同时,早期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也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汉文化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色目人出于对汉文化的仰慕,肩负起了推行和保护汉文化的职责。唐兀人高智耀是最先为儒者出力的色目人。他向蒙哥汗进说“儒以纲常治天下”的道理,指出:“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10]因此,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1](P6154)康里人不忽木上疏世祖,请求广兴庠序,弘阐国学,培育人才,并从立国之本的高度阐述了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这篇被陈垣称之为《兴学疏》的文章是西域人华化的重要文献之一。元初色目人在保护儒士、举荐硕儒、为儒士争取权益,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变了中原治理的策略,推行汉法,实行以汉治汉,完成了由游牧部落向封建王朝的历史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得以复苏,并获稳步发展。此后,色目人逐步成为传承汉文化的中坚力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考订华化士人共127位,其汉文化造诣丝毫不逊于汉族士人。其中,康里不忽木、汪古马氏、高昌偰氏、畏吾儿阿里海涯等都是汉化很深的色目家族,家族成员对汉文化的认同,已由儒学扩展至包含儒释道在内的全部汉文化,并由经术的学习转入了文学、艺术的领域。元代中后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色目儒士,而且色目人已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创作群体。如诗人萨都剌、马祖常、丁鹤年、余阙,曲家贯云石、薛昂夫,画家高克恭,书法家夔夔等,都是名留史册的大家。以色目人而能为汉诗、汉文,以异族而长于中国绘画、书法者,在历史上确为少见。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如此庞大的色目士人文人群体,这绝非靠汉文化单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能实现,其间必然包含着色目人对汉文化的主动投取。汪古人马祖常就是典型的例子。苏天爵《滋溪文稿》中说,马祖常“自少至老好学弥笃,虽在扈从,手亦未尝释卷”[11]。马祖常以浸润汉学之深而感到骄傲,在《马公神道碑》中说:“我曾祖尚书世非出于中国,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俾其子孙百年之间,革其旧俗”[12](卷十三),并以“出入邹鲁俗”、“家学赡诗书”、“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等自诩。[12](卷一)再如齩思永虽为色目人,却“日种学绩文,非儒生不交,纨绮气习,濯刮殆尽”[13],以儒士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以儒家思想为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杆,以革除旧俗、超越汉儒为人生追求的核心目标,这都代表了色目人对汉文化的极大认同。
(二)疏离自我文化传统
徙居中原腹地的色目人大多无法坚守游牧文化传统,表现出对传统不同程度的背离。
色目族群的先辈多以军事联盟者的身份随蒙古人进入中原,他们大多在马背上建立功勋。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廉氏第一代布鲁海涯等都是以军功进入统治阶层的。而色目族群的第三、四代以后的子孙则已从元朝军事领域中逐渐退缩了,他们更多担任一些文化类职务,从事文化类工作。这一特点从高昌偰氏家族成员入仕途径的转变上也能得到很好的说明。根据萧启庆统计,偰氏前三代族人主要经承袭、宿卫、军功而入仕;第四代以下,则更多经由科举与学校争取登仕的机会。[14](P718-731)元代科举仍以汉文、汉学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延佑二年恢复科举以后,“每试,色目进士少者十余人,多者数十人”[15]。元代共举行十六次科举考试,被录者达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色目人约占四分之一。“弃弓马而就诗书”[14](P507),不以战功而以科举入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色目人对传统游牧生活习俗的背离。
这种疏离在色目人的语言、思维、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如传统色目人有氏族之别,但无姓,更无字号,姓与字号的采用是色目人汉化的指标之一。根据张沛之的统计,廉氏成员的30人中,拥有汉式名、字、号的有22人,保留畏吾儿人名的只有9人。在汪古马氏家族中,有姓名可考的共计74人,有汉名的45人,这45人中,进入中原腹兴的第六到九代成员就占了44人。[16]
(三)双重身份的单维化
色目族群是双重文化身份者,他们一方面有游牧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汉文化浸染。但两种文化在他们身上并未形成平等的对话模式。在色目文化与汉文化的交往过程中,汉文化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影响也是单向的。萧启庆总结了色目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甚小的几种表现:1.色目人所拥有的地理知识并未改变中国人的华夏中心世界观;2.外来的科技影响零碎而肤浅;3.外来宗教始终外在于中国宗教领域,并未吸引大量的汉族信徒;4.中原学术、文学、艺术未受外来影响。[14](P52-54)正如牟复礼所说:“这个时代的汉人菁英不能说是已真正国际化。也就是说他们还未能对外来民族、思想、事物的本身发生兴趣。那个时期的作品没有多少探讨外来事物的内容,知道外来的事情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与此相反,许多著述不经意地将远方地名相互混淆。并且分不清摩尼教、景教与佛教,或者引用了某些当时流行的外来语汇,却说无法知道它的真正含意。……总之,我们看不到元代外族文化对当时或者以后的汉人生活带来的影响。”[17](P54)
可以说,在色目族群身上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并非交互式的,而是替代式的,即汉文化基本置换了传统的游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双重身份就趋向了单维。
那么,汉民族与色目族群如何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文化交通样态呢?
三、建构特殊对话模式的原因
(一)生活状态的改变
文化是环境所形成的东西,“各种文化之所以不同,往往就是由于环境的差异”[17](P213)。色目族群以少数者的身份徙居中原后,生活状态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游牧民变为农业定居民。因此,接受适应农业生活的汉文化成为必然。
并且,在与汉人杂居的过程中,大多数色目民族并不执著于保护传统特性,与汉人通婚、与汉人密切交往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如汪古马氏家族第四代到第十代成员中,以汉人为通婚对象的占其联姻比例的75%,与汉人通婚的结果是,不仅大量汉文化被引入色目家庭,而且色目人的血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色目人的社会交往中,汉人也占有很大的份额。色目人“透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品题而参与汉族士人文化活动的主流”[14](P507),他们与汉人共同形成了元代多族士人圈。如与马祖常关系密切的袁桷、胡助、虞集、王士熙、张之翰、吴澄、柳贯、贡奎、曹元用等,均为汉人,与他们的酬答唱和是其《石田文集》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这样,汉人的影响已不可避免地深入至色目族群的生活内层。
(二)文化形态上的差异
色目民族虽然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他们的文化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大多数的色目部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摄,甚至缺乏统一的民族特性。色目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最主要体现在军事而不是文化上。我们在追溯西域部族的历史时,会陷入困境,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所谓的部族仅仅是短暂的军事联盟,缺乏相对凝定的文化整一性。
就已形成的色目民族文化来看,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一般生活习惯上,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民族性表达得不够充分。如元代文献大量记载了汪古部人的宗教行为(祈祷、唱诗、洗礼等),而很少涉及汪古人对其信仰本身的认知与阐释。这说明色目民族文化结构还不完备,成分的独特性不够鲜明,整体上还处于准文化形态。
准文化形态使得色目民族在面对成熟的文化时易于被大范围地改造。“灵活性”是色目民族文化在与异族文化交往时的主要特征之一。色目民族习惯于征服和被征服,并且能迅速地融入当地的强势文化。“灵活性”确实体现了色目民族强大的生存能力,也有助于他们提升自身文化水平,但“灵活性”的另一面则可能导致原有文化被“拔根”,被吞噬。
(三)边缘身份的困境
色目族群始终处于身份微妙的边缘境地或者说中间态,一边是人数不多但握有政治统治权的蒙古民族,另一边是虽被统治但文化强势的汉民族。作为统治者的一分子,色目人享受着比汉人优越的诸多特权,但他们又不是“大根脚”,无法真正进入统治核心。面对汉人,由于缺乏蒙古人有意为之的对汉文化的防备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他们易成为文化的被征服者。色目传统所具有的依附性又强化了他们的边缘身份。边缘即意味着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边缘者更易于被他者影响。
(四)多元共融的身份让渡
从族群的内部构成来看,除色目外,元代其他三大族群基本上是由单一民族形成,而色目族群则复杂得多。
应当说,色目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现状,但当“色目”作为一个群体符号被对待时,事实上,各民族就被迫让渡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或者说,个体民族身份被一般化了。我们知道,符号在文化系统中一经确立,其能指与所指便会产生交互影响作用。色目族群成员在接受“色目”这一符码的身份定位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出让自己的个性,而更多地“屈从”于共性。亦即,政治符号对民族符号的取代削弱了被统摄者的民族个性。
色目人对汉文化独有的接受策略加速了元代文化的同质化进程。特别是四、五代以后的色目人,由于出生并完全生活于中原,他们甚至失却了对西域故土的怀想。如高昌偰氏,从偰文质以下,该家族成员均以溧阳人自居了。元明易代之际,一部分色目人随蒙古人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留下的色目人也完全汉化了,如哈剌鲁人乃贤之子马鼎,留居于庆元,但入明后,在涉及庆元的文献中,已不见有关哈剌鲁人的记载。在元代后期,色目传统的失语已经不限于文学领域了。
色目文化传统的失语,一方面当然导缘于西域各民族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汉文化的宽容态度相关。正是汉文化在面对异己时的宽容才消除了文化壁垒,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文化争论所带来的能量耗损,使社会以更加符合人类总体利益的方向前行。对我们来说,这种对话态度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1](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A].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3](元)贯云石.咏梅 [A].(明)解缙.永乐大典(卷二八一三)[M].
[4]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5](元)金元素.南游寓兴[M].尚未出版,诗集由杨镰先生提供.
[6]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元)不忽木.仙吕·点绛唇·辞朝 [A].隋树森,编.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
[8]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元)元好问.紫微观记[A].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五)[M].
[10]高智耀传 [A].(元)宋濂.元史 (卷一二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元)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A].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M].
[12](元)马祖常.石田文集[M].
[13](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六十五)[M].
[14]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官与汉化,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6]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17]陈序经.文化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